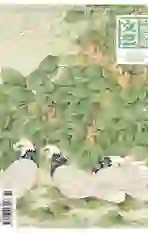一座村庄的突围
2020-08-14吕峰
吕峰
1
车载马驮,舟楫飞机,公路铁路,都可以出行,都可以走四方,也都是人的智慧。
船是河流的使者,撐着它,可顺流而下,也可逆流而上,抵达水源起头的地方。每次坐船,我觉得我与大运河有了最亲密的接触,或者说是肌肤之亲,惊讶、兴奋、激动,甚至想放肆大叫。此时此刻,我所有的感官都被眼前的河水慑服,我的血脉不由自主地随着那河水声跳动!
祖父讲他年轻时,村里人的生计,一半靠在地里谋生,一半靠在水里谋生,由此产生了跑船帮。说是船帮,无非就是把村子里的船组织在一起运输货物,或北上,或南下。祖父最远去过杭州,说杭州的红烧肉和小笼包好吃。跑船不易,在面对惊涛骇浪的同时,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祸,五叔公就是在跑船的途中去世的。祖父说,看着一奶同胞的兄弟,死在眼前,自己却无能为力,难受极了,不过跑船人死在江河,如同将士战死在疆场,也值了。
祖父说这话时,被岁月的风雨镂刻得沟壑纵横的黑红脸庞,散溢着柔和的光彩,他微仰着头,任河上的风轻抚着白发。江上无风也生浪!在水上谋生哪是这么容易的事?跑船的人对生死也看得淡,有酒就喝酒,有肉就吃肉,讲究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讲究的是快意恩仇。有时祖父乘着酒兴,干脆扯开了嗓门,一声粗犷的“依哟——嗬嘿——”的号子骤然而起,让我出现一种间歇性的恍惚,觉得船帮依旧存在,只不过不在运河里,而是在九天之上的银河里。
最早的船是一根木头。人们骑着漂浮在水中的木头躲避洪水袭击,从而想到了造船。造船离不开木匠,木匠王是沿河一带很有名声的造船工匠。“做屋打船,昼夜不眠。”打造一条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手多,时间长,工序复杂,千头万绪。木匠王壮年时,身材魁梧,腿脚利索,一身气力,碗口粗的木料,他挥动那把大砍斧,三下五去二就能砍成半成品的毛坯。他造的船,船舷开阔,过溜平稳,经得起风浪。
木匠王最开始造船,后来不用船了,他就改造木桶、木盆、木柜、木椅子、木凳子、木条几。木桶和船一样,可漂于河上,渡河而去。木箱子是姑娘出嫁一定要有的,有了它,姑娘在夫家的日子便有了依靠,便能幸福美满。木匠王会享受,每天中午都要躺在自制的躺椅上打瞌睡,或眯着惺忪的眼睛望着天。阳光照在身上,像盖上了一层被子。
木匠王的院子里,堆放着一根又一根木料,梧桐木、槐木、松木、檀木、梨木……用途不同,用的木料也不同。此外,就是各式各样的工具,锯、刨子、镗刀、墨斗、钢尺、砂纸、铁圆规、老虎钳……对我来说,每一个工具都是陌生的,都是神奇有趣的。喜欢看他刨板子,一来一回,刨花如雪花、浪花般飘落,站在刨花堆中,好像站在童话的城堡中。
村子对岸是另一个村子,两个村子隔河相望,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隔着银河相望的牛郎和织女。两个村子有数不清的婚配姻缘,随随便便提及河对面的一户人家,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像河中的水草,枝枝蔓蔓,牵扯不断。有嫁进来的,也有嫁过去的,还有招女婿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村里人的骨子里还坚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
村东头的泉润爷是闻名十里八乡的艄公,他大半辈子时光都是在船上度过的,无数风浪在他的篙下化险为夷。他喜欢蹲在岸边,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呆地看着河水,神情专注,不知是在想念一起跑船的兄弟,还是想念萍水相逢的女人,我不得而知。有时兴致来了,他还会扯着嗓子,吼几句颤悠悠的拉魂腔,粗犷,苍茫,在河面上如波浪般荡向远方,听得人心里潮潮的、润润的。
摆船需要谙熟水性,需要有胆有识,需要从容不迫。从根本上来说,摆船只属于真正的男人,属于那些在面对严峻生活、面对生死时依旧坚强的人。艄公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写照,饱含着艰辛,也显示着坚韧。村子里最后一位艄公是泉润爷的女儿,不过渡船变成了电动船。虽说是女子,可她精气神十足,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声音也响亮,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她开船的技术好,人也豁达、风趣。平时,过河的人不多,她一边开着船桨,一边哼着歌,在哒哒的马达声中,和过河的人摆着“龙门阵”。
雨季来临,河水暴涨,船要拖上岸,以免被打翻淹没。天大的事,也要等水定了才可以起船。有一次,风雨来了,鱼老大还在河里。远望去,人与船渺小成一个黑点,像一只在风浪里挣扎的蚂蚁,一个浪就能将他吞噬。近看,鱼老大站在船上,随波涛的起伏而颠簸着,像是在踏浪前行,让人提心吊胆。看他的样子,四平八稳,有惊无险,颇有“我自端坐,任他风浪”的味道。
我喜欢坐在船上看风景,船摇晃,人的心也跟着摇晃。阴雨天,常见鱼儿在船外翻腾跳跃,忽地一下跃出水面,来个漂亮的翻转,然后啪一声落入水中,引得在岸边溜达的狗儿汪汪大叫。春日,河岸的桃树竞相绽放,一大片一大片粉色,像泛滥的少年梦,撩拨着一颗颗年轻的心。
少年时,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拥有一艘船,一艘属于我一个人的船。我开着它,在风中顺流而下,像鱼儿从陆地进入水里,像鸟儿在空中展翅,一直开到很远的地方,可以是海鸥飞翔的大海,可以是开满鲜花的峡谷,可以是避世的世外桃源。累了,困了,直接躺在船上,在水声中入睡,然后在鸟鸣中醒来。
“千载江流,百年一瞬。”日子亦真亦幻,虚虚实实,不知不觉间,河滩边常有倒扣过来的斑驳旧船。曾经渡人、载物的船,突然成了时间的弃儿,被长久地弃置在那里,像极了一位自我放逐的老人,静待着泥土的覆盖。风吹,日晒,雨淋,时间久了,曾经搏风击雨的坚硬的船木,开始腐朽、腐烂,最后归于尘土。
在离开家的许许多多个夜晚,我反反复复梦见一条河,梦见河上的星月,梦见河滩上的树,梦里河里翻腾的鱼,梦见河上的船,梦见船开到了河的尽头,开到了海的开端。
2
有河就有桥,河多桥也多!村子内外有各种各样的桥,木桥、石桥、水泥桥、钢铁桥,有过人用的,有过汽车用的,有过火车用的。黎明,太阳从桥的这边升起,傍晚,在桥的那边坠落。一升一落间,横着隔代的光阴和蹉跎的岁月。
木桥窄而短,多就地取材而建。粗壮的树干做桥墩和桥梁,桥面由宽窄不一的木板拼接铺成,桥两侧也没有护栏。走在桥上,从木板的缝隙可看见桥下的河水。稍稍用力踩就嘎吱嘎吱作响,人多的时候,甚至会摇晃。秋天,一场霜打在草上,也打在桥上。上学经过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书本上的“人迹板桥霜”。冬天,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两岸树木萧瑟,桥面滑溜溜的,走在桥上,稍不留意,就刺溜一下溜到了桥下。
村子里的渡船是哪年消失的?是有了水泥桥之后。水泥桥造型简陋,甚至是丑陋,可它更宽阔,更结实,再大的风浪也不怕,哪怕是狂风裹挟着暴雨,掀起阵阵惊涛骇浪,水泥桥也稳如泰山。桥下常有妇女们在洗衣服,边洗边聊家常,有说有笑,桥上过往的人行色匆匆。
水泥桥横卧在河面上,让两个村子有了更密切的往来。最热闹的是婚嫁,抬嫁妆的汉子,吹唢呐的师傅,送嫁的姑娘,男的女的,老者少者,涨潮般涌上桥,队伍排得好长好长。人们吹着号,打着锣,放着响亮的鞭炮。新娘子,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被喜气的红色裹着,始终羞涩地低着头,眼睛紧紧盯着这条娘家路,不知是憧憬着未来,还是难舍离家。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有娶媳妇的笑声,也有不舍女儿、不舍父母的哭声,《百鸟朝凤》的唢呐声也在河面上飘荡。这个时候,新娘子可以放声大哭。等过了桥就不能哭了,要高高兴兴的,要把喜气带入婆家。
桥头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果实可洗衣服,用来洗头可防止脱发。我捡拾过皂荚树的果实,紫褐色,有点透明。夏天的夜晚,人们趿拉着拖鞋到树下乘风纳凉。偶尔,二伯也拿着二胡,在树下说上一段。说侠义,《七侠五义》《五鼠闹东京》;说忠良,《杨家将》《岳飞传》。二伯说到畅快处,听书人陶醉,说书人自己也陶醉,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恍若置身其境。说书,听书,不知不觉中普及了历史知识,也在孩子心目中种下传递真善美的种子,听书的效果,不亚于铅印的文字。
水泥桥另一头的河滩上生长着一片竹林,也不知是何人栽下的。举目望去,成方成阵的竹林,如整装待发的军队,似乎一声令下,即可奔赴战场。竹子是用根来繁衍的植物,只要根不死,它就会在春天给你一个惊奇。一场春雨过后,新芽破土而出,直指云天,正所谓“清明一尺,谷雨一丈。”那时,我们常去河那边挖竹笋,可能是气候的原因,挖出的笋又瘦又小,并不能食用,可依旧乐此不疲。
桥上的栏杆比较矮。夏天,常见半大的孩子站在桥上,一个纵身,落入水中,技术高的,像跳水队员般,很少有水花。然后,像鱼儿一样,在水里畅游,来来回回。水里的孩子在阳光里做着梦。桥下是纳凉消暑的绝佳去处,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喜欢。在桥下,抽一袋烟,洗一把脸,吹一会牛皮,整个人都舒坦了。歇够了,暑气消了,拍拍身上的土,起身,开始未完的行程。
桥下有个剃头摊子,摊主之前在镇上开过一间理发店,后来年纪大了,落叶归根,又回到村子里。为了打发时间,他就在水泥桥下,置了个剃头担子,一把凳子,一个小煤球炉,一个搪瓷盆,一把剃刀。剃头也没讲究,年轻人多是寸头,年龄大的多是光头。剃刀沾了水,在砂布条上来回荡两下,剃出的头又光又亮,最后抹点头油,滋润头皮。
给大人剃完头,他会拿出一把折刀,给客人刮鬓角、光脸,小孩子则不需要。有时,母亲告诫我,剃头,千万不要光脸,容易长络腮胡子,难看,不好娶媳妇。我一直谨记着,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长大后,竟有一脸络腮胡子。每天早上,刮胡子都要消磨好长一段时间,一天不刮,就像河滩上的野草疯长。剃头匠见多识广,一把剃刀就是镇子的半部镇史。桥上桥下都有故事,在桥上看河水,在桥下渡船,和走过的人聊聊天,一天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那时,村里的男人像河里的鱼和河滩上的树,喜欢享受月光下的露天浴,穿一条大裤衩,光着背,拿条毛巾和肥皂到河里洗澡。打好肥皂,将毛巾拉直,在背上来回搓动,然后往水里一跳,水花四溅。有时互相搓澡,搓着搓着,就闹了起来,那些刚结婚的壮小伙,开起玩笑来,荤素不忌,闹成一片。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别人说这话,可能是夸夸其谈,祖父说这话,我是信服的,他曾跟着船帮走南闯北,从他的嘴里时不时蹦出村子以外的物与事,哪怕他说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样的话,我也丝毫不惊奇。祖父问我:“你知道孔老夫子这句话是在哪说的吗?就在南边的吕梁洪。”说完,祖父又说,“你知道秦始皇泗水捞鼎在哪吗?就在北边的秦梁洪。”可惜吕梁洪不在了,泗水也成了大運河的一段水域。祖父的话,让我对吕梁洪、秦梁洪有了期待。
有一天,我循着祖父的话,去寻找秦梁洪。我从家出发,沿途经过了一座又一座桥。前面的桥诱惑着我,这种诱惑是潜伏在心底的向往远方的情结的延续,或者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渴望。太阳在头顶照着,河水在身旁流着,我不急不慢地向下一座桥走去。终于,我来到了秦洪桥。
桥很高,高到我需抬头仰望。桥上桥下不止我一人,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也有像我一样似乎是专门来看河、看桥、看船的人。河边有戴着头盔的工人在打桩或捆扎钢筋,河上有无数的船,是真正的大船。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直到太阳染红西边的云彩,慢慢坠入黄昏,我突然莫名的后怕,似乎不远处有一条蛇在盯着我。于是,我的额头、肩上、背上瞬间冒出了冷汗。我蹲下身来,闭上眼睛,双手抱住腰,这样做的明显效果是头脑开始清醒。我抚平自己的情绪,开始往回走。那一刻,我想到的只有两个字——回家。直到太阳彻底坠入黑暗,我才回到家。为此,我还受到了母亲一番训斥。
河上还有一种船,是挖淤泥的。源源不断的淤泥来自哪里?来自空气中的灰尘,来自水体中的泥沙,来自植物腐烂的根系,来自鱼类排泄物的沉淀。淤泥品质的好坏,一眼能看出来,黄色最差,灰色次之,黑褐色最肥沃。淤泥很金贵,与杂草、秸秆一起发酵,可做田里的基肥。不过,那时没有人叫淤泥,都叫河泥。每年冬天,水位下降,河面也热闹起来,一艘艘挖泥的船行驶在河面上,打破了冬的寂静。
人这一辈子,要走过多少座桥,才能到达彼岸,谁也不知道。其实,无论是哪一座桥,只要走在上面,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故乡。
3
船航行在水上,飞机飞行在天上,周围都是空空荡荡的,无边无际,触不到实体。火车行驶在大地上,安全稳定。大地厚重的怀抱托着它、牵着它,无论是穿山越岭,还是横跨平川,都有坚实的依靠。火车奔跑在大地上,将无数的人送往目的地,人们乘着它去认识外面的世界。
对村里人来说,火车一度是神奇的或者说是神秘的,让村里人没想到的是,火车竟然要从村子里驶过,确切地说是从村外的河上飞驰而过。消息来自无数的生面孔,他们如陌生的使者,在村子外聚集,水泥、沙子、钢筋被运至河滩边,麦场成了他们临时的家。村里人无比惊奇,原来要修铁路。人们奔走相告,像过年的鞭炮在村子里噼里啪啦地炸响。寂静的河滩开始变得喧闹,变得热火朝天。
千盼万盼,过河的高架桥建好了,枕木运来了,轨道架设好了,火车也终于喷吐着长烟呼啸而来。火车过桥时,桥在微微颤抖,真担心它会承受不住那长龙般的碾压。每天放学,沿着铁路走回来,经常看到一条绿色的巨龙飞驰而来,它载着形形色色的人南来北往、各赴前程。火车来的时候,远远地就会鸣笛,然后沿着铁轨奔来,又带着咣当咣当的声响远去。起初,我很好奇,经常驻足看火车里的人,听车厢里熙熙攘攘的声音,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火车给孩子带来了新的乐趣。当时,有几个胆子特别大的,喜欢挑战时间的极限,干些危险事情。当有火车经过时,他们在铁路上蹿来蹿去,比谁的胆子大,一边蹿,一边吆喝着“还敢再来一次吗?”直到远处传来火车来势汹汹的声音,才知道害怕,一溜烟从铁路上跑下来,那速度比兔子还快,引起在旁边观望的孩子的笑声。
有一次,我犯了大错,被父亲责打了一顿。父亲那垒砖砌石的大手打在身上,疼得很。即便如此,我也没敢躲闪,因为我知道躲闪会带来更严厉的责罚。半大的孩子,正是傲娇的年纪,我气冲冲地跑出家门。等来到铁道旁时,泪水早干了,眼睛里只有两道冰冷的铁轨并列着通向远方,消失在天的尽头。对我来说,那个远方是未知的,也是遥不可及的,当时的念头是离开家,再也不回来。
那念头一经萌发,像田里的禾苗,迫不及待地疯长起来。我沿着轨道向远方跑去,偶尔在枕木上来回跳跃。跑累了,跳累了,停下来,坐在铁轨上,摆弄铁轨边的小石头。当时好奇,铁轨边为啥有这么多的小石头?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直到今天,依然不清楚那些小石头的作用。跑着跑着,人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气也消了,开始沿着轨道往回走,所谓的离家出走也宣告终结。
那时,铁路和公路基本都是平交,在火车道的两旁有长长的护栏,路口有岗亭,有专人进行看护。当听到鸣笛声,两边的护栏被缓缓放下,将行人挡在两边。即将有火车经过时,往往在绿灯闪烁的最后几秒,经常有人疯狂地蹬着自行车,希望赶着时间的尾巴冲过去。赶不上的,只能在铁路旁驻足,默数着一节节车厢从眼前轰隆隆驶过,直到眼前豁然开朗,护栏抬起,放行。
第一次乘坐火车是去南京,我像一头兴奋的小兽,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生怕错过沿途的风景。火车驶出站台,经过一座又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或炊烟袅袅的村庄,经过一个又一个灯火不熄的车站闪烁着无穷的信号灯、电线杆、标志牌。在我的注视下,树林来过,河流来过,村庄来过,更多的是站在田野观望的人,像儿时的我。火车在他们的眼皮下,咣当咣当急行而去,留下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记忆。
火车一路走一路停,上车,下车,来往各地的人,流浪的异乡人,闯荡世界的人……车厢里总是拥挤嘈杂,充满了烟火味。沿途停靠的时候,可下去走走,反正停留的时间很长,8分钟、10分钟,或者更长。站台上有推着小车吆喝土特产的小贩,热闹得像菜市场,不过东西确实物有所值。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我没敢下去,只是在车厢里待着,看着身边的人上上下下,看着他们购买、享用。
在火车里坐久了,对它的神秘感消失殆尽,人也疲倦起来。快到长江时,身边的人说前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了。虽然无数次在人民币和宣传画上看到过它的样子,可我依然很兴奋,立马有了精神,睁大眼睛,只见一个雄伟的大桥迎面而来。火车经过大桥时,持续了十几分钟,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终于到达南京火车站了,人流如海。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惊慌失措,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像一滴水注入大海,溅不起丁点浪花。其实,在天地万物面前,人不过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火车是流动的,人也是流动的,被火车载着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形形色色的人,在火车里观望沿途的风景,同时又在火车里见识形形色色的人,与一座座陌生的城市打交道。有的城市只是飞鸟般经过,或者说只是匆匆一瞥,却永远地记住了,这种铭记是一辈子的,以至于到了晚年也不会忘记,会像孩子般炫耀起来。
其实,火车单调的节奏,像一个人,重复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等一年年过去了,人生就到站了。坐在车厢里,眼前是一群未知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夹带着不同的过往;对别人来说,我也是陌生的,未知的。你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也可以感应到彼此的心情,甚至还会觉得熟悉,却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到了站,陌生的人群,甚至来不及告别,便匆匆离去。火车稍稍停留,又开始咣当咣当晃动起来,站台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寂寞,只有暖人的灯光,依旧安详美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乘坐的火车是绿皮车。绿皮车从来都是拥挤的,人在火车里移动只能看着脚,或者说看着各式各样的鞋子。车厢内的灯永远明亮,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没有安谧的夜晚,没有敞开的幻想。人好像飘浮在尘埃中,模糊而具体。夜间一觉醒来,看着旁边东倒西歪熟睡的面孔,闻着浑浊不堪的空气,一种对人生未知的惶恐浮现在心头。等到天亮了,车厢里又沸腾起来,凌晨时分的惶恐、无助便无处可寻。
春节回家,往往是一票難求。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人,管理人员的小喇叭循环播放着:“不要急,慢慢来,看好自己的物品,防止小偷。”即便如此,偶尔还能听到被盗的哭声与叫骂声,也看到过小偷被抓与逃跑的场面。为了躲避小偷的冲击,人群自动分开,像船划过河面,很快又合拢,聚集,像一条河水缓慢流动,周而复始。
上了车,人极多,除了行李就是人,南来的,北往的,各地方言,全在车厢里聚集。而且车窗里还不停地爬进男人、女人、孩子。就连洗手间、车厢的连接处,都是一双双脚,有的脚上还粘着泥雪,气温一高,洇出一片水渍。那味道自然不会好到哪儿去,烟草味、饭菜味、脚臭味、汗臭味混在一起,无从分辨,让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盼望着快点抵达终点。最挤的时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干脆铺上报纸,钻到椅子下面睡觉,倒也自得其乐。
火车似一尾巨大的鱼,机械、无情、冷漠,人在它的肚子里游向陌生的地方。人乘着火车出站、到站、进站,又出站,好像鱼把人载到目的地,丢鱼卵似的被丢下,然后自顾自游走,人便在这地方生长、觅食、过活、老去。过了一段日子,若是发现与这个地方不融合,就再次钻进鱼肚子,开始新的漂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