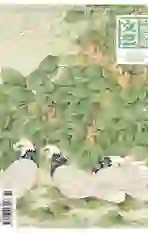雪白的冬天(外一篇)
2020-08-14凌珊
凌珊
秀儿觉得饿极了,前胸贴着后背,肚子仿佛是一个防空洞,里面有人轰隆隆地跑,每一步都像是在扯着她的心。八岁孩子的心经不起太多撕扯,她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姐姐用小瓢在面缸里用心地挖着,她不过比秀儿大两岁,瘦细的胳臂像瓢上飘忽的秧。瓢磕着缸底刮刮地响,和着外面树上嘶嘶叫着的蝉——它是不是也饿得想哭?
秀儿实在是哭不出来,自从姆妈死后,眼泪仿佛都哭干了,也不能喊饿;过分的早熟让她懂得还要哄着小妹小弟,让他们不觉得饿。
她带他们玩,说要给他们做好吃的。
她把石子堆成一排,递一块给妹妹,再递一块给弟弟,说:“这是面鱼儿,吃吧吃吧。”灰色的小石子斜长平滑,倒真有点像油面做出来的面鱼儿。姆妈搓面鱼儿最拿手,一溜儿扁平,下到汤里好吃极了。
五岁的小妹对着石子面鱼儿哧溜哧溜假装吃得喷香,两岁的小弟有样学样,拿起来就往嘴里送,秀儿连忙把那小石子抢过来,再擦去沾在小弟脸上的星星泥土。
这要真是面鱼儿就好了,油润饱满,爹爹吃了一定会好起来的,爹爹卧床不起滴水不沾有一阵了。
老城躺在床上却一点也不觉得饿。他只觉得身子轻;脚下的棉絮像云朵,他则轻飘飘地在天上飞,像天使一样。他想着要追赶淑娥,也许很快就能赶上了。
那天,他也想快来着,但还是不够快。飞机的轰鸣声在头顶上嗡嗡响起,轰隆一声巨响,人群骚动——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老城放下行李房里正在磅秤的行李物件,跟着人群往外跑。他往家的方向跑。
老城像出膛的子弹,沿着铁路的轨迹往回奔。这是1947年10月初的河北张家口。阳光白亮,铁轨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两条伸展蜿蜒的长蛇。
那颗炸弹就扔在家的附近,淑娥那时正抱着小的,护着大的,惊惧万分。轰天震地的一声巨响,院子里的水缸哗啦啦地碎成了瓦块,水流遍地,墙角的梨树枝被削成了碎片。
淑娥觉得身体内的一个部位也跟着巨响崩裂了;有一种液体往外流,像菜汁一样又苦又绿的液体。苦绿的液体从深秋流到初冬,不到两个月的光景,淑娥死了,留下老城和四个弱小的孩子。
老城想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蒙眬间又好像看到淑娥正朝着他笑呢,脸颊上一边一个酒窝,依旧那么年轻。她才三十出头啊,他们一起生活了只不过十余个年头,不是说好要走完一生的吗。他们很穷但很快乐,一家人其乐融融。如今她却撇下他跟孩子先走了,要他怎么活下去?死生契阔——他也要跟了她去。
老城想着,身子也跟羽毛似地飘了起来;他影子一樣摇摇晃晃地进了里屋。
屋角椅子上搭着一条淑娥的长围巾,老城用鼻子嗅着似乎还能闻得到她的颈香。他要把围巾绕到梁上,一秒钟就可以见到淑娥了。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是一只布松鼠,那是淑娥用碎布料给拴儿缝的玩具,松鼠绿茸茸的长尾巴调皮地弯到背上,两只黑豆做的眼睛圆鼓鼓地瞪着他。老城脑子里闪过儿子的笑脸,抓着围巾的手没了力气。
夏天好热,风都是热乎乎的;拴儿张着两只小手啊啊地叫着。他刚过了两岁生日,会冲着老城叫爸爸了。老城三个闺女下来才得了这么个儿子,又是中年得子,一家人对拴儿都特别宝贝。
拴儿实在是个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两只眼睛滴溜溜的,像墙角葡萄藤上的山葡萄,黑黝黝,亮晶晶,光滑剔透。他似乎就是这些黑葡萄的孩子——沉静,哑然。拴儿很少哭,喜欢笑,笑起来跟淑娥一样一边一个酒窝。
屋子里空空荡荡,米面疯长,没钱买米粮。拴儿像一只饥肠辘辘的小老虎,瞪着两只黑漆漆的眼睛。
桥头有人卖包子,刚出笼屉的肉包子,雪白透明,热腾腾地香气扑鼻。大姐像发现了宝贝似的让秀儿赶紧去买;拴儿有了包子就不愁只喝棒子面粥没菜下饭了。
秀儿小心翼翼地攥着借来的钱,来往穿梭在家和包子铺的路上。
这些日子,路上的小石子似乎都认识她了,道旁泥土地里的苦菜花金灿灿地开着,也像是在跟她打招呼。薄薄的包装纸透出包子特有的肉香,秀儿身体内的防空洞越来越深;“不能吃,这是给弟弟留的。”她小声地嘀咕着,悄悄话像是说给路边的野花听。她不懂别的,只知道小弟有包子吃就好。
夏天要过去了,拴儿突然变得沉默了。他趴在床上一声不吭,小肚子鼓得像一支皮球。大姐急得要哭,他是生病了吧?千万不要生病啊!三个小女孩围着家里一大一小奄奄一息的两个男人,束手无策。窗外的夜虫嘶嘶地鸣着,像男人们病中无力的呻吟。
拴儿嘴角一线白,是从口里慢慢涌出的虫!
大姐还像往常一样帮着拴儿穿衣服,怎么也穿不上。来帮忙的邻居大婶道:“这孩子腿都硬了!”
秋天来了,老城像是冬眠的蛇终于苏醒过来。他想吃东西——西瓜,对,就是西瓜。他觉得喉咙冒烟,胸膛着火,只有西瓜才能救火灭烟。
行李房的同事找来满城里夏天最后一个西瓜,对大姐说:“要死的人了,尽量满足他吧。”
西瓜汁像甘露,浇灌着老城干枯的躯体;老城像枯草一样复苏了;他第一次清醒地观望着四周。
三个女孩在身边转:“拴儿呢?怎么不见拴儿?”
大姐说:“拴儿死了。”
老城眼神渺茫得像是在梦里,道:“好!死了好!”
过年了,老城挣扎着起来,他要给孩子们做年饭。每年这时候都有淑娥一起张罗年饭,今年他要独自带着孩子们过年了。窗外冷气逼人,大门被寒风吹得忽闪忽闪地扇动着。他用力把门关上,一阵风过,门嘎吱一声又开了。
“淑娥,是你吧,我知道是你。”老城对着风口轻声说,“你回来了,是来看孩子们的吧?拴儿跟着你好吧?”
桌子上的油灯一忽一闪,像是倾听着老城的叙说。他把一盘蒸好的雪白馒头放到供桌上:“淑娥,这是给你和拴儿的,咱们家一起过个年吧。”
窗外下起了雪。雪花静静地飘着,院子里残留的梨树枝上盖上了一片积雪,像是开满了满树的雪白梨花。
雪 国
窗外的风呼啸,树枝被刮得摇摇晃晃,像在天空练字。练出的字,落在我手上变成大大的两个黑色的“雪国”。传奇,怀旧,适合回忆。
许多年前,我看过这本书,而且跟隔壁的芦叶有关。
“芦叶啊,跟人跑了。”电话里我妈说,“好像还是个什么大款,总之是跟人走了,家也不要了。”
“那工作也不要了?”
“她本來也不工作,先前顶替老芦胖子工作,行李房搬东西,不知道怎么把脚砸了,从此就办了工伤,不工作了。”我妈答道。
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圆圆脸的女孩儿。圆圆的眼睛,黑而密的睫毛向上弯曲,厚厚的嘴唇,头发上毛茸茸的卷儿,像蜻蜓的薄翼在飞。
“出来跳皮筋吧。”芦叶在门口叫。
皮筋儿一头挂树上,一头搭在门边的大石头上。我跟她一前一后,跳:一五六,一五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芦叶的两根长辫子,在后背上甩来甩去,尾稍卷曲,像两条弯弯的小溪。紫色的条绒衣服上有暗色的小格子。当年的条绒衣服就像是如今的公主服。她的是黄格,我的是红格。我们还特意穿着这衣服去“常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瞧你头抬那么高,眼皮都不看人。”她说,“那么傲气。”
跳完了皮筋儿,抓骨头,弹杏仁。骨头很大,名曰嘎拉哈,是把猪蹄啃干净后攒下来的。杏仁呢,也是自家树上吃剩的。芦叶家的杏树搭着我家院门,杏子小得像精豆。树干癞癞巴巴有棕色的树脂麻麻癞癞地淌下来,像芦胖子擦胡琴用的松树香。
芦胖子爱拉胡琴,听说松香擦过的琴弦拉起来好听。“胡琴头包着的是蛇皮啊。”他煞有介事道,示意小孩儿别动。把胡琴弄得很神秘。咿咿呀呀,芦胖子一手擎弓,一手拨弦。
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小孩儿们嬉笑着。芦胖子半闭了眼睛,当他们不存在。他哼着西皮二黄调,脚打着拍子,“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浪。”
芦胖子其实并不胖,只是长了一张大饼子脸,短脖子,眯缝眼,再加上笑起来只见鼻子嘴巴不见眼,一天到晚总像弥勒佛一样笑眯眯的,就得了个芦胖子的外号。这基因大概占了主导位置,大女儿芦慧跟儿子芦伟都像他。除了小女儿芦叶。芦胖子是老来又得女,芦叶跟哥哥姐姐差了快二十岁。
“人家都说你是捡的呢。”邻居们故意逗芦叶,“还有那一头卷发,看你家谁是毛毛卷?”那些人极力怂恿着。
芦叶的厚嘴唇加上一头自来卷,让她看起来有点儿洋气。芦奶奶就嫌麻烦,因为每天给芦叶梳头的是她。卷发容易打结,给芦叶梳头的功夫能热好一瓶牛奶。牛奶是给芦胖子喝的。芦胖子喝牛奶吃小灶。
“你媳妇身上的肉都长你身上了。”邻居男人玩笑加嫉妒。芦胖子就伸出手臂给那人瞧,意即:看到了吗,这是福气,口福。
芦胖子手背上长了一撮长长的黑毛,刷子一样立起来。邻居男人就加了一许服气,默默地点头,走开。
芦叶不喝牛奶,长得却特别结实。
大桥对过三组有一个老太婆尤其喜欢芦叶。老太婆脸上永远架副老花镜,见了面就拉着芦叶的手说:“去我家吧,给我做干女儿。”
大人们就更要打趣了:“瞧,你从前的家人来找你了。”
有一回,家里摆了新鲜面包,香气萦绕。芦叶伸手去拿,正想往嘴里送,芦伟逗她说是眼镜老太婆送的。她立刻扔回去,大叫:“谁要吃她的东西。”过后芦伟再怎么哄她开心也不管用。
芦奶奶倒是对她挺严厉,好像总是在呵斥她,“玩过的东西要收好了”“不许出去太长时间了”,等等。不过,芦奶奶本来就很少见笑脸,整天哮喘上不来气儿,手边总带个喷雾器样的东西。喘不过来气了,就赶紧对着嘴巴“噗噗”喷两下。
那天,芦叶来我家,表情神秘。“陪我出去一下。”她说。
出了门,才注意到她怀里鼓鼓囊囊地窝着个什么东西。
“小猫。”她按了一下怀里的东西,“同学家里的猫刚生了一窝小猫,给我拿来一只。我妈不让养,叫我扔了。”
“往哪儿扔?”
“不知道。刚才给我扔到大街拐角了,可它又自己找回来了。”
我跟着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绕过右边的一趟房,又绕过一趟房。这次要走远点。她托了一下怀里的猫:“我把它眼睛蒙上了。看不到,就找不回来了。”说着,她掀起衣襟的一角给我看。
我看到一团黑黑的小东西,支棱的耳朵下面露出浅浅的灰色茸毛。
不知道走了多远,芦叶终于把怀里的小猫放了下来。
也许真是走得够远,或者给蒙得晕头转向,以后真就再没有看到那只小猫。
上中学了,我去了铁中,芦叶比我低一年级。等到他们那届,却没有按居住区分到铁中,而是去了十八中。
十八中挺大,就是位置奇怪,地势低洼,像升降机突然掉到一个盆地里。四层楼高的两幢教学楼也不过跟外面的马路平起。这外面的马路因为地势高,形成滑梯一样的大斜坡。坡底下是一条小水沟。冬天雪地里结冰,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弧度坡势的溜冰场,所以总有人骑车冲下来掉到这水沟里。后来水沟上面加了一层水泥预制板,还架了一个小桥。许多年后,我在梦里还总是出现水沟跨不过去,要掉到里面的惊慌。
十八中的大门朝着小水沟,住在坡上的学生图方便快捷,就取道从墙上爬下去。墙上被人蹬出了一溜儿凹进去的小坑,阶梯一样挂在上面。走过那里,如果正好碰到上课铃声大作,就会看到墙角上有人像蜘蛛侠一样在往下爬。
我也试过爬那墙,有点儿惊险稀奇的兴奋。
进了中学的芦叶似乎很喜欢看小说,或者说喜欢拿小说来给我看。“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好看呢。”她说,“你看吧,看完了,我再给你借。”
倒像是她家开图书馆,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我看过的几乎所有琼瑶的书都是从她那儿拿来的。
又一天,她来找我,不是送书,而是要起名字。
“我嫂子要生小孩儿了。”她说,“猜猜我哥要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芦花。”她自问自答着,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不是正好。芦慧,芦苇,芦叶,再加上一个芦花,整一个芦苇荡了。”我笑着说。
她也笑了,站在那里磨磨蹭蹭地说:“不行,芦花太土了。芦慧就够了,若不是叫芦慧可能还不会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呢。”
芦慧跟老芦胖子一样的性情模样。上山下乡,嫁给了当地农民,生了个儿子,邻居的小孩儿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土包子”。他一来,小孩儿们就奔走相告:土包子来了,土包子来了。
芦慧呢,就站在一旁笑,眯缝了眼,嘻嘻的,脸上的腮红像秋天红透的山楂一样。
芦伟也下了乡,却赶上返城,没多久就回来了。回城后进了一家手表公司。起个什么名好呢?我想起来哪里读的一首诗,就说:“芦笛怎样?芦笛声声,保准进不了青纱帐。”
“嗯,好听。”芦叶也很满意。
“芦笛现在都上大学了。”我妈电话里说。我想起那个大眼睛,歪着小辫子,啃着冰棍的小女孩儿。
芦叶是不想上大学的。那一次她拿着川端康成的《雪国》来给我,就表明了意思。“很好看的。”她说着把书递给我。
“你整天看这些书,还要不要考大学了?”我忍不住问。
“我不要考大学。”芦叶一脸不屑,“老师说了,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考大学都一样。琼瑶也没上过大学呢,还不是照样有名。”
我愣着,不知道怎样回答,脑子里浮现出十八中大操场墙壁上那些凹凸小洞上的“蜘蛛人”。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琼瑶当年是多么渴望上大学。她的那些书,或许就是那些渴望的延伸。
终究也没弄明白《雪国》里的故事,除了那最初的描述。女人的脸,映在车窗上,合着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男人盯着车窗上女人的倒影,车轮轰隆轰隆地往前开。
这最初的描述带着芦叶拿着书时的神采。藏青的绿色书皮握在她的手里,敦厚柔软,像一块光滑细软的缎子。
芦叶爱打扮了,十七年华,时尚而且时髦。长辫子早剪成了短发,迷你裙,高跟鞋,身材婀娜有致,脸上的胭脂白里透红。
“去军分区看电影吧。”她说,“我有票。”
军分区的电影票她也能弄到,看来很有本事。那是我大一的暑假,正天天待在家里闲散。
电影叫《一个和八个》。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芦叶搔首弄姿的情景。
“是对着那几个男孩子吗?”我诧异地望着门口的几个男孩儿,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几个男孩儿,大背头,还叼着烟卷,这样的人也配跟她调情?她却把头扭转着,嬉笑着,言不由衷地左顾右盼,眼角像挂了指南针直指门口,屁股像长了钉子坐不下来。
再下一个暑假我回来,芦叶已经结婚。嫁了一个分局的公务员。“小蒲也是大学生呢。”邻居们说,“还是倒插门。芦胖子在房子旁边另接出来一间小厦子给他们住。”
芦叶站在门口呕呕地干吐着。她弯了身子大幅度地呕吐,像戏台上无声电影里的角色。芦奶奶还是老样子,在锅台灶下忙碌着,话语好像更少,人更瘦,眉眼也更低。芦叶大声地训斥她,像训斥小孩儿。从前连小猫都不能养的人,如今要养小孩儿了。
芦奶奶跟那眼镜老太婆成了冤家。原因是芦奶奶因为听了眼镜老太婆的劝说,才鼓励芦慧嫁在农村。
扎根农村,反正是要一辈子的。眼镜老太婆鼓动道:“你看我家老大就在本地找了一个。不受欺负啊,还能得些照顾,工分都能多拿不少。”
眼镜老太婆的大女儿身体力行,芦奶奶信了。可是等到蘆慧嫁给农民没多久,却开始了返城运动。芦奶奶为此恨死了眼镜老太婆。芦慧后来也有了一个进工厂的机会,却被丈夫游说到让给了他自己。
“芦奶奶死了,某一天哮喘一口气没上来。芦胖子也死了。”
“芦胖子怎么也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
“饿死的。”
相信吗?我想起懒人吃饼的故事。古代一懒人,老婆出门,给他脖子上挂了一张饼。老婆交代他饿的时候就咬一口。可是懒人还是在老婆回来之前饿死了。懒得动口,脖子后面的饼没吃到。
芦胖子就这样给饿死了。没人做饭,自己不会做也不想动。最后就饿死了。
“芦叶呢?也不管他吗?”
“她连自己都管不了,还能管他?”电话里我妈的声音平淡得稀奇,“生的儿子,留给了小蒲。小蒲后来又结婚另娶,这孩子就没人管。后来芦叶又给那个什么大款甩了,整天游神一样,从此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所以她那儿子就总去找芦笛。芦笛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芦叶的儿子也去了深圳。
我想这个孩子应该叫蒲棒草,芦叶结出的果实不就是蒲棒草么。
芦笛声声。我又想起那个夏天,那个晴朗有着轻风的夏天。芦叶站在屋中间,跟我比画着起名字。还有《雪国》里那最初的描述。女人的脸,映在车窗上,合着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男人盯着车窗上女人的倒影,车轮轰隆轰隆地往前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