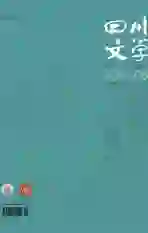窥伺青春
2020-08-10吕虎平
吕虎平
窗外是潮湿的路,漫漶的雨水向着秋日的方向步步紧逼。一道闪电,划过黑夜的锋利触角,我感到了少有的虚弱和恐慌。少年时,我对双手充满了好奇。我曾经无数次举起它们,或握紧拳头,仔细地观察这双在我看来,全身上下最为神秘的肢体器官。有时,它们呈现出软弱和忍让,有时,又呈现出力量和刚强。由此令我想起许多侠义之事,比如,一身中山装的林觉民手执步枪,怀揣炸弹闯入广州总督衙门的时候,让我想到快意恩仇的江湖大侠。还有那个元初的侠士王著,杀死宰相阿合马,同伴劝他快逃,他却镇定地对禁军士兵说,吾为天下人除害,死而无憾。还有一个侠士更为惨烈,那就是侠客聂政,他以孝亲侠义闻名。为感大臣严仲子以百金为母祝寿之恩,只身仗剑刺杀侠累,然后挖眼、毁面,剖腹自杀,以免连累姐姐。
年纪稍长,内心的英雄崇拜犹如火苗,节节攀高。不仅仅是我,与我同龄的孩子,都有过如此这般的一段英雄记忆。正在街上走着,忽从街巷深处冲出一队人马,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手里操着棍棒,嘴里喊着冲啊、冲啊!有的喊着电影里的台词,只不过他们都记错了,搞得张冠李戴而已。
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叫混搭:“喂,喂,长江、长江,我是王成,我是王成。”“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垒起七星灶,全凭嘴一张。”这些自然是孩子们的游戏,也掺杂了小小的博弈。然而,大人的游戏当真成了血淋淋的搏杀。有一年,父亲要进城,有消息灵通者劝告父亲:“你不要命了,两派斗起来了,城门楼都架起了枪!”
那年月,即使一家人当中,也有猜忌和斗争。也不知为何,我很迷恋火,这一种奇怪的嗜好,类似返祖式的固执与魔怔。生活让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我甚至对猫呀狗呀老鼠呀,也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有人说,抵御内心的恐惧,需要自身的强悍。我开始练习拳脚,首先是腿功。买不起沙袋,将一条屁股磨破了洞的裤子剪下双腿,灌满沙子,用线缝起来,就是沙袋。只有在上学路上,我把沙袋缠在小腿肚。就这样,蒙混了半年,也没被母亲发现。一天,母亲找那条裤子,我说破了。母亲说拿来她要缝补。我说在柜子里。母亲翻箱倒柜,愣是找不出那件被我做了沙袋的裤子。很长时间,我为此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春节,母亲为我们做新衣服时,又提起那条裤子,我心里不由一紧,好在她老人家没再过多往下说,我算是躲过了一劫。
其次就是练手劲。我家前后院子的树,几乎都被我掌劈过。当然,我的功力远不及武侠小说写的那样,掌如风、疾如雨,或腰斩了树身,或劈开了树皮,粗糙的树桩反而硌破了我的手掌。好多次,我都是满手血污,或者带着紫斑,被父母揪着耳朵训斥。母亲最是严厉,生活中,总爱发脾气,很难露出笑意。我喜欢绘画,她二话不说,把我画的画一把撕碎了。她从来不喜欢给窗子贴窗花,给墙上贴年画。现在想想,那时的母亲,不知承受了多大压力,心里不知装了多少苦水和恐慌。母亲好像对什么都没兴趣,她的兴趣只停留在农活和家务上。她一刻也不闲下来。放学了,我也得随她投入到烦琐的劳动中,锄草、间苗、拢沟、灌溉。
接下来是铁砂掌。一部《少林寺》,铁砂掌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青春少年的武术时尚。一个脸盆,撮一盆沙子,成为练铁砂掌的器械。你很难想象,我对铁砂掌着迷到什么程度。那时,我看到什么都想插,在地里拔猪草对着土插;在河里游泳,对着水插。现在想来,真是荒唐。不过,在练习铁砂掌的问题上,我看出了自己的毅力。一天,因过于沉迷练铁砂掌,而疏忽了太阳已奔往西天。
这可怎么办?肯定要遭母亲训斥了。我急忙弯下腰,拼命割草,而荆条筐却像一个大肚罗汉,总是吃不饱。如血的残阳,在西天犹豫不决。一只乌鸦在头顶盘旋,我怕它发出凄厉的叫声,但它还是叫了,叫得狂妄而恣肆。不祥的叫声,让我恐惧。当我跨进门的时候,我发现全家人都很忙乱,原来祖母病危了。我跑到院子中间,对着盘旋的乌鸦大声喝骂。可恶的乌鸦,让人诅咒的乌鸦!我喊了好久,嗓子喊哑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祖母奇迹般好了起来,她用柔弱的手,抚摸着我的头,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十三岁那年,我考入细柳中学。父亲成为西安一家私营木器厂的学徒。解放初期,纺织厂在乡村招工,母亲也进了城。我的父母亲都是普通工人,他们虽跳出了“龙门”,微薄的工资却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1962年,他们相继返乡回到了农村,一来是响应职工大返乡政策,二来,毕竟在农村还能分得一亩三分地的口粮。
说来也怪,母亲名字里有个“绵”字,她做了一名纺织工人;父亲名字里有个“林”字,便做了木匠。我不知道这是否冥冥中的定数。祖母对我的教育,多有迷信。院中柿子树挂果的时候,祖母不让用手指。前不久,跟几个同学去终南山玩耍,在一个山民家,看到院子里有几棵柿子树,聊天中,说到这样的话,同学称他们家大人也不让用手指指着,这虽然没有任何依据,但我至今还是不会伸手去指树上的柿果。就像不能说出父母的名讳一样。
说起来也算是凑巧,前段时间,忽然遇到邻村乡党李明启,他在北京做设计,自称读了我不少文章,勾起了他对家乡的回忆。他问起我一个名叫阿强的发小,居然是他初中的班主任。那时,我和阿强天天一起玩,但不知什么原因,玩着玩着就恼了,就吵了。他比我个子高,身强体壮,骑在我身上,像骑马一样。他挥起双拳,一拳一拳打在我身上,像落下的重锤。我一边挣扎一边抡起双拳,到底有几拳打上了他,我也不記得。其实,孩童之间的打斗,本来也没什么,但他母亲找到我家,声色俱厉地说,我儿子今天中午吃的是肉饺子,你知道吗?你担得起吗?他母亲兴师问罪的时候,我和阿强就躲在我家后院的柴房里,大气都不敢出。
我母亲正慌神呢,阿强却拉着我去掏鸟雀了。
北方冬日,夜幕降临得早一些,我和小伙伴们在月光下,玩打仗。嘿嘿哈哈地喊,像少林寺的武僧。我们的声音清脆爽朗,整个村子都能听到。母亲叹气说,这孩子往后怎么办?
关于这个,曾经有一个算卦的婆子给我和我哥指出了人生未来的方向。她说我哥将来做教书先生,说我将来吃公家饭。虽然我哥后来因工资待遇问题,辞职回家,毕竟也做了几年民办老师。
就在上个周末,我回家看母亲,嫂子一脸兴奋,她告诉我,因我哥做了4年多的乡村教师,镇政府正在给他办理养老待遇。我哥三岁时,身体不好,落下后遗症,但他心高气傲。辞职后,先是养鸡养兔,因为瘟疫,兔子和鸡死了一大片;又养鸽子,不知被谁放了毒药。后来,他还干脆摆摊修鞋,修鞋的活儿脏是脏,毕竟是正经营生。其间,他还写了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遗憾的是没有出版;他又开始练书法,前后练了三十多年,但也仅限于做个乡村书法家。谁家有红白喜事,必请他做账房先生,书写礼单。过春节的时候,家家门楣上的对联,也是他的大手笔。我春节回家,我哥要是写不过来,有人也让我写。我推辞不过,就划拉几笔,但与我哥的字比起来,就是小巫见了大巫。不过,村人不是很计较,总是高高兴兴拿着回家了。
最让我动容的还是侠客,比如荆轲刺秦王,他们的侠义肝胆不知是为谁?他们愿意赴汤蹈火,愿以死换生,将死置之度外,不由令人慨叹唏嘘。我崇拜嵇康,曾写过一篇名叫《广陵绝响》的文章,就是关于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我真想不明白,一个即将被砍头的人,竟能如此冷静沉稳,把一曲凄美的音乐,弹出了旷世绝响。
有关侠客的记忆,先是电影里的英雄形象,后来有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习惯模仿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嘿嘿哈哈地喊一气、闹一气。模仿是孩子的本能,尤其是模仿侠客。那时,看到电影里的侠客扎着头巾,我悄悄把父亲早年在西安工作时的一条围巾缠裹在自己头上,这样的装扮,也许与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父亲却拒绝把那条围巾送给我或者我哥。有一次,母亲提出了这个要求,父亲却瞪着眼睛,只吐出两个字:休想!这条围巾,一定藏着父亲的一段什么故事吧?我还将父亲的长衫当袍子,把桌布当披风,将草帽剪掉宽边,再将顶部捏出棱角来,当作侠客的礼帽。
母亲发现我剪坏了草帽,气得肺都要炸了,操起笤帚追打我。
侠客仗义,出言必信。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侠客大多独来独往,如世外高人。
往往,模仿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故意呼朋唤友,显摆。我们当着众人的面说谁谁像谁,谁谁又像谁。装扮不像的,就回家重新找行头,有的家里找不出像样的道具,只好看着别人的一身装扮流口水。我们几个聚会,也有接头暗号。无论多晚,只要一声“水鸟”叫,不大工夫,一大群伙伴就会聚拢起来。然后用《沙家浜》里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对答,如此准备完毕之后,带了弹弓、红缨枪,或者木棍,去和外村的小伙子们打架。我们村子大,人多势众。只要我们一出现,其他村里那些所谓的侠客,个个都成了“王连举”“蒲志高”。
我们也优待俘虏,给他们分发“武器”,比如,分配剩下的弹弓,自制的火枪,还有削尖头的木棍等等。对于投降的人,我有点瞧不起他们,总是认为,叛徒早晚会出卖自己的弟兄。但是,下店村的王观,让我佩服。他从不低眉顺眼向谁讨好,有谁做了叛徒,他就悻悻地回家了。我们这边有人发狠,大声骂和威胁他,他权当耳旁风。我佩服他,正是因为他有骨气,像电影里的共产党员,有气节。
事有凑巧的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俩分在一个班,我们之间便保持着亲近的关系。
王观脸上的青春痘大规模爆发,是从他父亲的一耳光开始的。王观偷摘了邻家的一颗青苹果,被他父亲狠狠地扇了一耳光,脸上的五个红指印,胎痣一般,七八天没褪去,痘痘也成批、成批爬满他那张红润的脸庞。
王观是宋绮云(即宋元培,中共党员。1929年由组织派到杨虎城军部工作,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后对杨虎城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9年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警卫室)的护卫官王迁升的外孙,他大智又大愚,大拙又大巧。
所谓的护卫官,就是贴身保镖。王迁升曾经被父母送去少林寺学艺,功夫了得,赤手空拳七八个壮汉近不了他身。他有一个结拜兄弟叫刘勇。他们俩一个是我们村西头王家的二小子,一个是南门刘家的大小子。王迁升拳脚了得,被宋绮云相中,做了贴身保镖,而刘勇却走了黑道,专做偷鸡摸狗的事。不过他也有过一次义举,因叛徒告密,宋绮云在我们蒲庄村里被抓,特务把他五花大绑押往西安城的时候,刘勇和王迁升一路悄悄跟踪,希望能在半途劫掉囚车,但因人少势弱,加之特务的枪硬,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绮云被特务送走了。
村人说,要是那次成功了,解放初,刘勇就不会做土匪被镇压了。当然,村人有村人的认知,合不合乎规矩,倒是其次。王观随舅爷学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他坚决不做“王连举”“蒲志高”,事实上,谁也没见王观露過两手,大多只是听说。我让王观摔打摔打几下,他只是笑笑,催急了,最多拉个大顶,蹲个马步,真的没什么稀奇。
我对戏曲也有点天赋。蒲庄西头有一座古戏楼,那年月只唱样板戏。几年下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些戏词没有一出是我拿不下来的。先不说大戏,就是那时的三句半、快板书,至今还能对出不少。再说戏联吧,就是戏楼两边木柱上刻的对联。那副戏联是行草阳刻,字体遒劲,粗拙有力。破“四旧”时,被人用刀刮过,但苍劲的字迹还清晰可见。上联是:台上作戏台下看戏尽是逢场作戏;下联是:台上装人台下整人皆为双面之人。当我能完全参透那二十八个字的时候,心底不由一惊,感觉世事虽纷繁,但我和你、你和他、他和更多的人,我们这一辈子啊,全被这副对联道出了本真。
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时的我,轻狂得可以,哪里会对着一副戏联一想再想?时光的确飞快,一瞬间便像满脸皱褶的老妇。那年,我已升入高中,记忆至此告了一个段落。如果你把记忆当回事,它就像漫漶的洪水,肆无忌惮,横行肆虐。比如说大表哥,很多年没见他,他的从前几乎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表哥学过两年功夫,但他做不了侠客。他常惹事,惹出事就跑,就躲,由姑父姑妈给他擦屁股。表哥脾气暴躁,哪里只要有他在,总是会弄出大的响动来,惹得姑妈时常抹眼泪,说表哥不会装(逢场作戏)。一次,表哥带我去邻村看电影。那年月,我以为我们国家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一个是朝鲜。那天,我们看的电影,就是朝鲜的《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没开始,露天场地黑洞洞的,只听到人声,只能看到晃动的人影。于是,我和表哥坐在一堆麦草垛上等开场,身旁有几个女生在聊天。借着月光,我看到旁边的那几个女生,一个长得水灵、耐看。我知道表哥的脾性,就捅了捅他的胳膊。很快,表哥就跟那个女孩子搭上了话。他竟然把我抛在一边,跟那女孩子站在一起聊电影。表哥口才好,由他添油加醋,把一部根本没看过的电影,讲得天花乱坠,几个女孩子听得眉飞色舞。忽然,从暗地里冲出几个男孩子,对着表哥挥拳便打。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表哥身上就挨了几拳。表哥被打蒙了,其中一个男的骂表哥勾引他的女朋友。
表哥这才回过神来,突然跳出圈外,蹲成马步,在他的周身就有大半圆的气场。他变花样似的从身上摸出一把螺丝刀,大喊一声,谁敢过来,老子放谁的血!把几个男孩子唬住了。表哥趁他们愣神的空当,撒腿就跑,却把我丢下了。几个男生凶巴巴问我,是不是那流氓的同伙。我怯怯地说不认识他。他们围着我转了几圈,又问,是不是?我当然不敢承认。他们正狐疑呢,电影开始了。
我吓得够呛,想回家,一个人不敢走夜路。继续待着,又没了看电影的心情。满是恐惧、无助、焦灼、无奈。这个经历令我不寒而栗,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都是表哥被围追堵截的情景,它像个电影镜头永远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了。我想把它擦去,但没有抹去它的东西;我想忘却,记忆的图像却总是更加清晰。
还有一次,表哥在我们村的篮球场打篮球。表哥的动作很潇洒,当时在方圆几里算是有名的灌篮高手。我们村子的村主任也喜欢打篮球。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就打在了一起。表哥拿篮球砸村主任的头,还揪着村主任的衣领骂。那时,我家正在挨批,表哥这一闹,等于又捅了马蜂窝。当晚,村主任就带着人又来抄我们家。事后,夜深之际,表哥一个人翻墙进入村主任家,用被子捂住村主任的头,狠劲在被子上踢、踹,用冷拳砸,吓得村主任筛糠似的哭爹喊娘。表哥给我讲这些的时候,很是自豪。他一边讲,还一边学着他是怎么动手,村主任是怎么求饶的。
第二日,村主任乖乖把抄没的东西还回来了。
不过,表哥夜闹村主任家,让人解气,我对他开始敬畏了。那年月,我又何尝不想给村主任扔黑砖、捅冷刀子呢?但因我的软弱和胆怯,只能眼看着家人被欺负。我大姐身上穿的一条花裙子,被村主任的老婆强行脱下来,把她女儿的破衣服扔给大姐。大姐那天哭得水洗一般,母亲只能忍气吞声。我看着大姐哭泣,心里就发狠,一定要把那狗日的弄死。
很长一段时间,我整日处于幻想中,想象我如何整村主任,让他老婆跪地求饶。以前我表哥有点痞和赖,那次事件之后,我对他开始另眼相看了。
1979年,父亲在日化厂做临时工。暑假时,我随父亲到西安。父亲住的地方很大,是木工房兼做卧房。白天,父亲给车间维修桌椅板凳门窗,晚上,一个人睡觉。父亲没其他爱好,喜欢听收音机。我在西安的那段时间,父亲专门支了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供我睡觉学习。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完了《野火春風斗古城》《万山红遍》《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还听了袁阔成的评书《三国》,可惜,只有半截。不知为什么,只讲到“华容道”就收手了。
我有两个同学,一个是刘武,一个是江明,他俩的父亲也都在日化厂工作。
江明是个二愣子,大街上走路也要骂骂咧咧,骂那些呼啸而过开车的司机,骂那些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社会青年。工作后,他的脾气也不改,一次与同事发生口角,竟操起板凳要砸人,要不是其他同事及时摁住他,祸就闯大了。后来,这个愣头青给他家里出了个难题。一次,他周末无事,被人拉去打麻将,一晚上输了好几千。那年月,这可是两三年的收入。他父亲当即给了一巴掌,骂他吃屎了,脑袋让驴踢了。他母亲哭哭啼啼说,人家出老千坑你难道不晓得?江明嘟着嘴说,血战到底嘛,出不了老千的。我们这样的人,不博一把,永远不能出人头地,下次还能博回来。他母亲一听,气得瘫坐在沙发上,半天缓不过劲来。
刘武与我要好。也许跟他的名字有关,打小他就喜欢“嘿嘿、哈哈”吼上几嗓子。只要他站在你面前,从来不会闲着,一会儿扭扭手腕,一会儿踢踢腿、弯弯腰,更像有多动症。虽然这样在我面前张牙舞爪,我却不厌烦。他家属于“一头沉”,母亲在农村,住在村子东头,紧挨村堡的围墙。围墙是夯土的,墙宽三丈多,顶上并排可跑两辆大马车。没多久,村人盖房取土,慢慢地将围墙掏空了。我随父亲在日化厂期间,常常找刘武玩。刘武父亲住在过渡房,在日化厂福利区南头,紧挨着露天电影院。刘武的舅舅是放映员,每次有好电影,他就带我去。别人需要买票,我们去了,他舅舅站在老远招招手,检票员就放行了。
我们找到合适的位置坐下来,忽然来了一个穿着酸朴的怪人:旧布衣、黑皮包和一副老式近视镜。他坐在我身边,气氛显得不大对劲。人往往是敏感的,也许有一种说不清的气场,在暗示、指引。他主动和我搭腔,说自己会武功,一人能敌多少条好汉。经过一番对话,我才知道他是精神病患者。见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就站起来,拽着我要比试。跟一个正常人比试倒不怯场,毕竟,我和刘武都算是练过几手拳脚的人。关键是,他是一个精神病人。正不知如何应付呢,刘武拽着我离开了,后边传来他骂骂咧咧的吆喝:“总有一天让你娃明白,我究竟是不是会拳脚。什么陈氏太极,什么张三丰、黄飞鸿,你们会后悔的……”
上初二那年,刘武的父亲将家属户口全部转入西安,他们家“农转非”了。刚开始,刘武还回村子看看我们,时间长了,也就疏远了,以至于后来失去了音讯。前不久,听朋友说他在鱼化街道开了一家轧钢销售部,生意不好不坏,但吃穿不愁。我按照朋友的指引,找到了刘武。和当年那个高大的帅男孩相比,他有些发福、谢顶,眼睛显出了浑浊,没有了当年的英气、帅气。那天,我们在附近一家酒馆吃饭、喝酒。没想到几杯酒下肚,他竟然有些微醉。回到他的店铺,他坐在沙发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诅咒:“这是什么玩意啊,他妈的,今天这个找你麻烦,明天那个找你麻烦,挣来的钱,不够支应各路神啊!”我笑着说,你不是会几手功夫吗?他们来了,打出去。刘武突然破涕为笑,他说,我那叫功夫?哈哈,那还叫功夫!
我们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城市返回蒲庄,而我在80年代末,从蒲庄走进了城市。也就是说,一个农民的孩子,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成了一个城里人。虽然我不比城市的土著居民更熟悉这座城市,但我更爱它繁华的商场,爱它宽阔的大街,爱它交通的喧哗和便捷,爱它风光片一般美丽的公园。在西安,有一段时间,我总会在夜里醒转,好像专意为梦寻一个着落。那种黄粱梦,气派、势大。醒来,却还是一场空。于是,我便找拗口的书读,这种书让人悲催,权当催眠术,弄得我似梦非梦、似醒非醒。早晨起来,甚至一整天,都似在混沌的梦中,脑海里还续接着那一场好梦。我盘算着自己的生计,谋划着自己的资金。我甚至想象着,不给会计打招呼,来个突然袭击,翻开账册,指出账目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我是会计专业毕业,但不告诉会计他。我会让他瞪大了眼睛,以为我是神人。人性之中也许天生就存在着某种幻想。侠客的幻想,也在其中。幻想游离于世俗的天空,一不留神,就以血淋淋的面目呈现在眼前。
我们时常站在镇街上看美女,双手抱在胸前,吊儿郎当的样子,坏坏地看和笑,坏坏地吹着口哨。有泼辣的女子,目光直逼过来。对那样的目光,我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我的肌肉、皮肤、血液,突然像过电一样,嗖嗖地颤。她大胆,目光如炬,走过去了,还会回过头来,盯着我们。
过于喧哗浮躁的时候,人便需要一种别于寻常的安静。一度,我离开玩伴,独自一个人去镇街上玩。一个人逛书店,一个人看录像,一个人从东街走到西街。有时,坐在清晨,回想那些逝去的青春,梳理那些值得我幻想的细节,便有些许失落。但我们已经过了少年强说愁的年代,沧桑,或者说,平静,已经无端地爬满我的头发。少年的梦想同样不再,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梦里的一切,让我只是成为其中的窥伺者。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