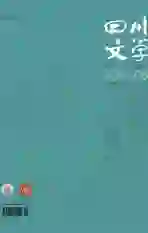磨刀
2020-08-10阎海东
阎海东
镇子上几乎所有人都见过家昆的那把刀子。
家昆的刀子,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看见的。为了让人们都看见那把刀,家昆有一个相当奇怪的习惯:在街上到处磨刀。别人一有空,就坐下来喝水休息,家昆坐下来,则一手拿出有一半砖块大的磨刀石,另一只手拿出刀子,坐下来磨刀,沙沙作响。别人有空就聚在一起打麻将,家昆则蹲在离麻将摊不远处磨刀。于是,一听到沙沙的声音,大家就知道家昆在磨刀。别人蹲在一起喝着啤酒吃着烤串扯着淡,他依然蹲在不远处,反复地磨着刀子,还经常眯起眼睛看着大街,似乎要随时注意,看看将要被他捅死的那个人,此刻是不是在大街上溜达。
家昆为什么要磨刀?镇子上的人能猜中七八分,却也有点迷糊。当然,为啥磨刀,只有家昆自己心里最清楚。两年前,家昆的儿子赵子豪十七岁,在读高二。有一天,赵子豪回家说,我不念书了。家昆说,不念书你干啥去?兒子说,我去欧达罐头厂。正在洗脚的家昆,一脚踢飞了脚盆,盆子里泼洒出来的水,把赵子豪的耐克帆布鞋完全打湿了。赵子豪一下子攥紧了拳头,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的两只眼睛似乎挤在了一起,已经棱角分明的脸,因此变得更宽。家昆看见赵子豪的肩膀抖动了一下,似乎在活动脖子。但是,赵子豪没有动,就站在那里,看着家昆,渐渐地眯起了眼睛。
家昆腿脚不便,因此洗脚的动作很笨拙。
刚才家昆在那里洗脚的时候,子豪已经看了半天,他坐在靠墙的黑皮沙发上,边刷手机,边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家昆,但家昆没有注意他。基本上,家昆从来不管儿子,不过,儿子赵子豪似乎很注意与家昆的父子关系,但凡做什么事,总要问一下家昆,比如,他十来岁的时候,会说,爸,我去买两包方便面,他不需要跟家昆要钱,他手里捏着足够的钱,而且也不是家昆给他的,但他还是要征求家昆的意见,似乎把这个爹很当回事。家昆一般都很不耐烦,挥手说,去吧。这是个不可能特别引起注意的习惯。赵子豪有时候也关心家昆的腿,比如,以前在镇子上读初中,每天回家,只要下雨,他就会主动把两片毡护膝拿给家昆,家昆也顺手就接过来套上,一切都顺理成章。相比别家的那些混账儿子,赵子豪可真算是孝顺,不知道家昆有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感到一丝得意。当然,赵子豪有时候也会征求一些比较重要的意见,比如说,爸,假期学校组织游学,你说我去不去?家昆就会不假思索地说,去问你妈。因此,赵子豪从家昆那里征求意见从来只会得到两句回复:一、去吧;二、问你妈。在这个家,腿脚不便的家昆,好像是一个形同虚设的权力机构,也好像是个被架空的元首,为了某种惯例对外界宣示合法性而设立,按部就班地维持着一个完整的家庭形式。怎么说呢,钱,说到底,全都是何美兰挣的;家,也可以说全是靠何美兰撑起来的。更何况,何美兰给足了家昆的面子,在人面前,总是说我家家昆如何,有时候,还假装他依然大权在握,经常会跟有求于她的人说:这事儿你得找家昆,我说了不算。如此等等。
那么,双腿一瘸一拐的家昆,算是这个家庭的功臣吗?这很难说,家昆以前是建房造屋的大工,用专业一点的称呼来说,就是所谓的工程师。在镇子上,也算是一个能把日子过好的角色,因此多少会赢得别人一些尊重。然而十三年前,也就是赵子豪五岁的时候,家昆的双腿被钢筋给砸坏了。照当时在场的其他工人描述,责任完全在家昆,作为一个大工,竟然连这点安全意识都没有,那天,“走路风摆柳”的韩玉淑,风姿绰约抛眉弄眼地朝家昆走来,手里拿着两包红塔山烟,说,家昆,我家的活儿啥时候能干上啊?家昆嬉皮笑脸地说,你比我还急。两个言语暧昧的男女,都在高声说话,不远处干活的人都听见了,跟着哈哈大笑,似乎都品出了其中妙不可言的味道。事实上,那时候操作吊车的小段一直在喊,吊在空中的钢筋圈已经在倾斜,但是家昆没注意到,韩玉淑惊叫的时候,家昆已经趴在地上了。换句话说,这嘴炮打的,真是代价太大了。
事情开始扯皮,结果弄得家昆的双腿也给耽误了。虽然最终还能直立行走,但他绝对干不了重活儿,也没法长期弯腰或者下蹲。家昆的活路越来越少。那时候,“可能会过上好日子”的家昆,还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一切才刚刚开始。一段蓬头垢面的日子之后,何美兰什么都没有说,把自己收拾整齐,去了欧达罐头厂。那时候的欧达罐头厂,也不过就是占地十几亩大的一个小厂子,一个看不出什么前途的草台子而已。何美兰在欧达罐头厂干了十几年,家昆窝在家里,晃荡了十几年,他学过修车,也学过焊工,都不了了之,全是因为那双腿。何美兰说,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因此,这个家,是何美兰撑起来了。家昆有吃有喝,也有老婆孩子,只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存在”着就可以了。
按照惯例,十七岁的赵子豪告诉家昆他不念书了要去欧达罐头厂,家昆的正常反应应该是:问你妈去。然而结果不是,家昆飞起一脚踢翻了脚盆,这个情绪表达得相当激烈,令赵子豪非常意外。由于事情过于反常,赵子豪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态度——他并没有那么尊重家昆,而且还相当地厌恶和蔑视。
不过赵子豪也没敢造次,一定是何美兰对他严格要求了什么。愣了半天,赵子豪走出了院子。家昆自己稳定了一下情绪,拿过拖把打扫洒在地上的水,等他打扫得差不多了,赵子豪又折回来了,说,我告诉你,这样的行为,我只容忍你一次,以后可别再抽抽了,实话跟你说吧,我吴叔哪儿都比你强百倍。家昆的浑身再次抖动起来,他抬眼看着儿子,慢慢地直起了身子,额头两侧也慢慢地有蓝色的蚯蚓隐隐在蠕动。家昆说,你再说一句?子豪说,我说十句也还是那么回事,这些年,要不是吴叔,还会有咱这个家?我妈这半辈子也不就白瞎了?大家给你面子,你兜着就是了,跟着吃吃喝喝,一辈子优哉游哉,你不抽抽,谁会说你啥?
家昆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闭合,似乎有一根大号的夹子别住了心口。他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捂着胸口,看着赵子豪甩着膀子走出了屋门。
何美兰好久没回家了,家昆到罐头厂去找他。罐头厂如今已经很大了,气势相当恢宏,连办公大院的门房,都相当严肃气派,门口的保安看着家昆,说,你跟何经理约好了吗?这个保安当然不认识家昆,因为他从来不去欧达罐头厂。家昆说,我是她男人,保安这才仔细地转头看了看他,然后露出了怪异的笑容,当然,也慢慢客气了很多,说,有事儿不能在家里说?是很急的事吗?
家昆第一次进何美兰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很明亮,有黑褐色的实木办公桌,黑色的真皮沙发,还有一个小套间,站在何美兰面前的时候,家昆不由自主地把头扭向门半开着的小套间。那显然是何美兰在欧达罐头厂的私人空间。何美兰看着家昆闪烁的眼睛,说,想看就过去看看吧,何必扭扭捏捏。家昆没有接她这句话,也没有动。何美兰说,赵子豪不想念就算了,我同意他来罐头厂,这孩子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让他先吃点苦头也不是坏事。家昆说,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何美兰说,那你为啥事儿?家昆说,我告诉你,老子要杀人。何美兰非常吃惊,她几乎脸色白了那么一会儿,然后抬手整理了一下头发,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说,你疯了吧?滚!赵家昆虽然说他要杀人,但他赤手空拳,显然没有任何杀人的准备,因此何美兰并没有太紧张,她一动不动地呵斥着他,你他妈走不走?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么大个地方,你也不瞅瞅你啥样?跟个老鼠似的,还杀人?你说这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不发虚吗?
晚上,何美兰回来了,她没开车,自己骑着自行车进了家门。家昆看见进屋的何美兰身后跟着人高马大的赵子豪。躺在床上的家昆本能地坐了起来,虽然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举动。何美兰没有看家昆,而是一脚踢在了赵子豪的腿弯上,说,跪下!赵子豪像是被打断了腿,耷拉着脑袋面朝家昆跪下了。何美兰脱下高跟鞋,换上了家里的凉拖鞋,声音低沉地说,你中午跟你爸怎么说话的?赵子豪没有说话,何美兰就脱下一只拖鞋,光脚站在地上,甩开胳膊把拖鞋拍在了赵子豪的脸上。
说不说?家昆浑身在被窝里哆嗦了一下。何美兰的声音依然在屋子里回荡。赵子豪说,我就是说让他以后别这样了。
何美兰说,一共说了几句?
赵子豪低着头,似乎是在一句一句地回忆。
家昆坐在床上,看着何美兰一起一伏的胸部,她依然穿着商务西装,那个他曾经相当熟悉的乳房,此刻像是隔着万水千山,当然,家昆没有心思想何美兰的乳房。
赵子豪终于开口了,说,就说了五六句。赵子豪的话刚落音,何美兰的拖鞋就接连扇在了他的脸上,啪、啪、啪、啪、啪、啪。然后,鞋掉在了地上,何美兰把脚套了上去。何美兰说,啥时候脸好了再出门,滚。赵子豪的左眼已经明显肿胀了起来,他没敢抬手摸自己的脸,弯着身子走出了屋门。
家昆一动不动地看着何美兰,只见她脱下了自己的西装扔在沙发上。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家昆下意识地往床里面挪了挪,何美兰说,家昆,你真要杀人?家昆转头看着墙上自己的影子,没有说话,他的双腿,似乎又疼了起来。何美兰说,你要真想杀我,就在家里杀吧,反正我已经回来了。这事儿闹在外面,多丢人啊,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家昆没有说话。何美兰叹了口气,说,有时候,我也想杀人,可是,我没杀人,咬着被子哭一晚上,早晨还得起来,孩子没长大,还这样不懂事,以后还要成家立业,再加上你这腿,后半辈子说长也够长的,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些?
家昆说,你说这些干啥?
何美兰说,我不跟你说这些,跟谁说?你该不会不知道,我辛辛苦苦是为了谁吧?这个家现在有吃有喝,你就不能好好生活着?
家昆把头转向墙面,何美兰却说,你是我男人,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一直把头别过去,连看也不看我一下?当年,是我看上你的,家里人怎么拦也拦不住,结婚前就跟你睡了觉,死心塌地跟了你。这个你不会忘了吧?我知道,这些年,你难熬,我也没那么好过,现在,日子终于有了点模样,你却想要杀我,是吗?
家昆觉得自己一直被何美兰逼向了墙角,他从被子里艰难地抽出腿,他打算下床。他边挪动身子边问,你什么时候走?
何美兰说,家昆,你要赶我走?
家昆说,你不是一直不住家里吗?
何美兰说,就算我有一段时间不住家里,这也是我的家呀,我晚上不走了,行吗?说着,何美兰脱掉了衬衫,接着,她把家昆往里面推了推,说,你就不知道让一让?家昆只好把身子往后缩了缩,何美兰弯腰脱下裤子,把裤子搭在床沿上,然后又解开白衬衫,此刻,她的上身只有一个乳罩。家昆看到何美兰,被乳罩托起来的乳房闪烁着丰满的光芒,难以置信的挺拔。何美兰说,你一天吃饱了到处瞎晃,不知道我有多累,你给我揉过一次肩吗?你是死人还是活人?
家昆还是起身下床了,何美兰吃惊地看着他,说,你干啥去?家昆说,我去上厕所。何美兰说,尿完尿回来给我揉揉肩膀。
挨揍之后,赵子豪和家昆的关系很紧张。赵子豪每天躲闪着家昆。好在家昆并不一直待在家里,连早饭也是在街上吃的。过了一周,赵子豪的脸完全好了,就有一个姑娘上门找他,那是他的女朋友,名叫菲儿。家昆不知道赵子豪和菲儿两人钻在家里,他稀里糊涂地推开门,就听见赵子豪的屋子里酣畅淋漓的叫声。家昆在院子里停住了脚步。屋子里也慢慢地安静了下来,此刻的家昆不知如何进退,于是便咳嗽了两声,他听见姑娘在问,是谁?赵子豪说,是我爸,你别管。家昆在院子里茫然地四顾了一下,又出门了。
家昆在院子门口看见赵子豪和那个姑娘一前一后地出门了,那个姑娘跟在身后,眼睛非常灵活地閃烁着光芒,她看起来十七八岁的样子,挺漂亮的。穿着一件浅粉色的T恤和浅蓝色的牛仔裤,屁股紧绷绷的。她看见家昆的时候有些躲闪,不自在地抬手整理了一下头发,侧着身子走得很快。家昆说,你女朋友?赵子豪没有理他,甩开步子走向摩托车。姑娘已经分开腿骑跨在后座上了。家昆觉得,赵子豪,这个混账王八蛋,无论如何也是自己的儿子,那鞋底子扇在他的脸上,家昆解气之后,心里还是有点难受,这个难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儿子像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替罪羊似的。他一直试图和解他们的关系。晚上,赵子豪回到院子,家昆正在给几盆大丽菊浇水,说,你以后可别这样了,何必挨这冤枉打?赵子豪没有接他的话,只是把自己的球鞋球衣都一件件地脱下来放在一个蓝色的塑料筐子里。家昆有些尴尬,而且又觉得有点生气,说,你以为是我跟你妈说的?赵子豪说,别这样装好人了,你不是要杀人吗?家昆浑身震了一下,他万万没想到,赵子豪竟然也知道了他“要杀人”的事,但他觉得不可能是何美兰跟儿子说的。赵子豪说完这句话,又补了一句,说,别以为我妈打我,我就怕你了,再说,你以为杀人就那么简单?你有那胆吗?活得好好的,反倒脑子烧起来了,不知道一天抽的什么风。我知道,你恨我妈,恨吴叔,但你就不怪你无能吗?人活在世上,谁没有点感情?跟着你吃苦受罪就是道德模范了?人世上的人,要是都像你想的那么单纯幼稚,人类早灭绝了。
赵子豪说完,踢了一脚院子里的一个塑料小凳子,光着背向洗澡间走去。有那么一瞬间,家昆甚至听见他好像在哼着曲子。家昆听到清脆的断裂声从自己的身体里传来。
去欧达罐头厂上班后,赵子豪几乎再也没有回过家。家昆也很少出门,他每天吃点饭,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有时候想得脑子天旋地转,像是喝醉了大酒。有一天,他忽然从睡梦中醒来,几乎要号啕大哭一场的时候,他决定试试自己的胆量。他买了一把半尺长的刀子,同时买了一个磨刀石。开始在院子里磨起了刀。但是他跟谁也没说这个事。有一天,邻居老王来借电动车,看见家昆磨刀,老王问,你磨刀干啥,这年头又不杀鸡宰羊。家昆说,磨刀当然是杀人了。老王说,你可别吓人。
也许是老王的这句话启发了家昆。他开始上街磨刀,不管走到哪里,他都随身携带着两样东西,刀子和磨刀石。
家昆的刀子磨了差不多快一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惊悚。人们看见他一声不吭地磨刀,啥也不敢问。后来,慢慢地便有不着调的人问,你这把刀还没磨好?家昆说,关你什么事儿?后来,家昆去羊肉馆吃饭,身上依然带着那把刀子,那把刀子就挂在腰间,老李嬉皮笑脸地说,家昆,杀了人,可就没有羊汤喝了,你还是把那把刀子收起来吧。天天打麻将的老郑也开玩笑,说,你把这刀都快磨没了,刀子是切东西的,一年四季也没见你切啥,老磨来磨去,不是在糟蹋刀子吗?秀英超市的司秀英,三十七八岁,长得有几分潦草的姿色,初中文化程度,也有点幽默感,她坐在超市门口的麻将摊边,别人开玩笑的时候,她跟着来了一句,说,这就叫“铁棒磨成针”。说完,她还意犹未尽地故意问,你们这些老爷们儿,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越磨越细,什么东西越磨越粗吗?大耳朵喜全嬉皮笑脸地说,你家那根铁棒多年不回家,你这磨刀石早长青苔了吧?司秀英朝喜全吐了一口唾沫,说,没了那把金刚钻,老娘还不做瓷器活了?
慢慢地,磨刀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当然,这件事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派出所的民警杨敬安把家昆带到所里,语重心长地说,你天天带着刀子瞎晃,你这不是在故意为难我吗?民警杨敬安给何美兰打电话,何美兰去交了罚款,把家昆领了出来。
回到家里,何美兰哭了,问家昆,你非要这样吗?家昆没说话,何美兰说,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杀谁,要说你打算杀吴登良,他现在一年也来不了厂里几次,你连他人也见不着,要说你打算杀我,我回家几次,睡着了你都不动手,你到底要干啥?我活在世上,让你这个大男人抬不起头吗?你要真打算杀我,给个痛快话,我晚上就回来,也不要你杀,我自己收拾自己,你杀了我,不还得偿命吗?子豪将来怎么办?说完何美蘭一头倒在沙发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不过,何美兰哭也没用,那把刀子被没收之后,家昆又搞了一把一样的刀子,带着刀子到处磨来磨去。他慢慢地有了酒瘾,人们终于有点担心了,不喝酒的家昆,大家也都不太在意,然而,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家昆,带着一把闪亮的、磨得越来越细的刀子在街上晃来晃去,你很难说没什么闪失。
盛夏的黄昏燥热悠长,鸽子飞上天空追逐晚霞,放学回家的孩子们在明亮宽阔的马路上追逐嬉闹,然后消失得干干净净。后来,天空中有一朵云好像爆炸了一样,它的碎片正在朝小镇的上空扩散蔓延。穿着一件背心的家昆,喝得酩酊大醉,看到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唯恐这个神志不清的醉汉伤到自己,这样,基本上就是家昆一个人走在越来越空洞的大街上。一阵凉风过后,秀英看见摇摇欲坠的家昆从自家超市门前经过,她站在收银台前,看着家昆横穿街道朝老戏台广场那边走去。那里有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台。
赵子豪开着何美兰那辆黑色大众,停在了秀英超市门口。赵子豪在秀英超市拿了一包芙蓉王和一盒杜蕾斯,司秀英指着街对面外摇摇晃晃的家昆说,喝得太多了,还拿个刀,迟早要出事。赵子豪扭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司秀英一边扫码一边说,去把你爸弄回家吧,这大热天的。赵子豪咧了一下嘴说,把自己搞成一个笑话,也是人才难得啊,真他妈丢脸。说完,赵子豪扫码付了款,走出了超市。看着赵子豪闪在阳光里的背影,司秀英叹了口气。
赵子豪坐在车里,拆开芙蓉王点了一支,他刚启动车子,就看见司秀英快步追了过来。司秀英低头靠着车窗说,子豪,还是过去看看吧。副驾上坐着一个紫色头发的女孩,桃红色的短裙几乎露出了白色内裤,女孩嚼着口香糖,口齿不清地问,看什么呀?赵子豪转过脸去,很酷很平淡地说,闭嘴。女孩切的一声,扭过头去看着窗外。司秀英说,子豪,听我的话。赵子豪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歪着脑袋转头看着司秀英,说,要不你去?我看你倒像个活菩萨似的。司秀英直起了身子。赵子豪踩了一脚油门,车子迅速地滑了出去。
司秀英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她看着远处的家昆。此刻,他背朝着这边,脑袋抵在一根电线杆子上,身子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司秀英目光所及之处,除了家昆,没有一个人。司秀英朝自己的超市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她看见家昆已经坐在电线杆子的阴影里,像是睡着了。她朝他走了过去。
司秀英站在距离家昆两步之外,叫了一声家昆,她看见家昆抬起头来,嘴唇发白,两眼直直地看着她,眼睛像是冻僵了。家昆艰难地撑了一下身子,依然那样看着司秀英,但是,他的眼球有了点活力,似乎在努力地辨认对方。司秀英说,家昆,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可你手里有刀子,我一个女人,胆子小,你能不能先把刀子给我?家昆含糊不清地问,你要说啥?司秀英说,你把刀子给我,我才敢说。家昆把手往斜挎在自己身上的帆布包里掏,他掏出了那把刀子。司秀英心里一阵哆嗦,她后退了两步。她看到家昆把刀刃捏在手里,把刀柄朝着自己。司秀英上前两步,弯腰快速把刀柄捏在手里,说,家昆,你瞧瞧,你这么心善的人,拿着这么个玩意儿到底干啥啊?司秀英拿着刀,飞快地走向垃圾台,几乎用尽全力,把那把刀甩了出去,她看见那把刀非常奇怪地扎在垃圾台后面的老槐树身上,震颤了好一会儿。
司秀英对家昆说,走吧,你跟我回去歇一会儿,我有事儿跟你说。家昆的眼睛已经活泛了许多,这会儿他大概已经酒醒了七八分。他盯着司秀英说,你要说啥?司秀英说,秘密,天大的秘密,你到底要不要听?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