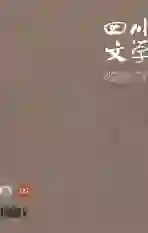美人鱼
2020-08-10田兴家
田兴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我还没说完,晓默就故作生气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总是讲到一半就停。我说,我得出去找吃的,我带来的东西都吃完了。晓默说,不就是吃的吗,我给你找去。说着她潜入水中,水面微微动,冒出一串气泡。大概半分钟,她浮出来,手里握着一条鱼,递给我。我看着她长满鳞片的下身,说,我怎么能吃这个。晓默笑着说,这有什么的,我自己有时候都吃。我仍然不接,她用眼缝看我(在黑暗中生活十八年,她的眼睛已经退化成一条缝),那表情好像在说,你不信吗?稍一停,她把鱼头伸进嘴里,在尖锐獠牙的咬动下,鱼冒出鲜红的血,尾部奋力地摆动。一分钟不到,整条鱼就被她嚼烂吞下去了,我惊讶得半张着嘴。晓默抹了抹嘴唇,说,味道还可以,就是比洞虾的浓了些。我说,你不是说平常都吃洞虾吗?晓默说,哪有那么多虾可吃呀,我得留一部分繁殖,所以有时候也得吃鱼。晓默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怪不得她能活到今天。我给她投去赞许的眼神,但不知道她能否看得清(或感觉得到)。她朝我笑笑,又潜入水中,不一会儿又浮出来,把一条挣扎的鱼递给我,比刚才的那条大两倍。我犹豫一下,接了过来,鱼尾拍打在我脸上,晓默笑起来。我把鱼头砸在洞壁的巨石上,鱼就不动了。接着我取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刮掉鱼鳞去除内脏,在洞口生起火,火上盖一块石片,把鱼放在石片上烤着。
我没想过我还会见到晓默。说实话,我都快十年没有梦到她了,但这并不怪我,要怪就怪时间。晓默消失的那年,我们都才十二岁,如今我已经三十,而晓默还是十二岁时的模样。那天下午来到洞里,看到水边坐着一位姑娘,凭着背影我就认出来是她,但让她认出我却费了一番工夫。晓默摸着我的左手说,你的第六根手指呢?我有些伤感,说,去医院切掉了,切掉以后我就经常感到孤独。晓默试着安慰我,说,孤独是常有的事,我还不是孤独,所以我常对着石头说话。顺着她的手,我看到一块蓝色的石头,洞里的石头都是灰色的,唯独这一块是蓝色。晓默说,它以前不是這样的,自从我对它说话以后,就慢慢变成了这样,对于石头来说,孤独才是最可怕的。想不到晓默对石头也有着独特的研究。其实我也研究过石头,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用马车从后山拉回一车车石头,建了几间房。我说,晚上我总是睡不着,墙壁上的石头一直窃窃私语,时不时还互相推挤,弄得房子摇来晃去的。晓默说,你当时应该告诉你爸。我说,告诉我爸有什么用,他拉回最后一车石头,马就累死了,从此以后他就听不见任何声音。晓默说,对不起,我们还是别谈论石头了。
你在发什么呆,我好像闻到一股奇怪的味。晓默推推我,我回过神来,鱼烤焦了,我赶紧过去翻动。晓默突然语速极快地说,是鱼烤煳了吧,我想起来了,这是煳味。我点点头。晓默瞬间哭起来,我疑惑地看着她。她边哭边说,我六岁时学煮饭,把一锅饭全煮煳了,我爸打了我一顿,打得我屎尿都出来了,我妈哭着把我抱去厕所,他一脚踢在我妈的屁股上,我妈一个踉跄,和我摔进粪坑里。我努力在记忆里搜寻,搜寻了一会儿,说,其实那天我听到你哭的。晓默止住哭声,擦掉眼泪,说,听到又怎样,也不能怪我爸,要怪就怪那时候的米太金贵了,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还记得我爸去上粮,粮库的人说我家的谷子不干,我爸争辩几句,被他们打了出来。晓默说,别提这些旧事了,一提起我就想哭。停了停她又说,不过哭哭也好,我已经好多年没哭,所以眼睛才逐日地缩小。
鱼烤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撕下一块肉塞进嘴里,味道鲜美。我撕下一块递给晓默,她没伸手接,而是凑过来用嘴咬住。晓默嚼两下,吐了出来,捧起一捧水漱口。我以为她是觉得烫,可她却说,我不喜欢这种味道,这是死亡的味道。我无声地笑笑,继续吃美味的鱼肉(我目前还觉得这是美味),最后我把整副鱼骨放进水中,它扭动几下,就往深处游去了。我趴下身去喝了几口水,感觉肚子微微的胀。晓默说,吃饱喝足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我想了一下,问,刚才我讲到哪儿了?晓默说,讲到你妈跑了。我有些尴尬,说,我的记忆越来越差,有时候刚说出口的话转瞬就忘。晓默说,不用担心,我们忘记的每一句话总有一天都会重新想起。我点点头,清了清嗓子,继续讲刚才的故事。
你还记得我家那匹马吗?哪匹?我家就只养过一匹马,就是累死的那匹,白色的。噢,想起来了,是跟西梅家买的,那时候还非常小,不能拉车。嗯,但后来长大了。我妈没跑之前,每天都割一箩草回家,马吃得肥肥胖胖的。我妈跑以后,没人割草,马天天都拴在竹林里。一天晚上,它咬断缰绳,就沿着竹子爬上去。这应该是你的一场梦吧?不是,马在梦中不可能笑的。它就停在竹子上,饿了就吃竹叶,吃饱了就睡,醒来就朝着我爸笑。有一天它把竹叶全部吃光,不得不回到地面上,我爸就给它架上车,每天教它拉一个小时的车。你偏离了重点,没讲你妈是怎样跑的。噢,这个,我妈生下我完全就是一场梦,有一天她醒来,觉得我不是她生的,就悄悄跟一个卖米粉的小商贩跑了。你爸去找过她吗?没有,我爸还希望她走远一点,因为那时候她已经病得很严重,常常在深夜提着镰刀念念有词,不时地放声大笑。这样说来,你是你妈的一场梦,可你妈怎么会随意抛弃自己的梦呢?晓默,你已经不了解人世,在人世里,梦醒来是很痛苦的。
晓默估计坐累了,浮在水中摆动着双腿活动身体。长时间在水中游动,她的双腿长满灰白色的鳞。稍一停,她朝我笑笑,潜入水底。晓默,晓默,你在哪里?我像当初那样呼唤。那时候晓默瞬间潜入水底,起先我还笑着说看你能憋多久,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一直没有出来。晓默,晓默,你在哪里?我惊慌失措地呼唤,没有任何回应。我也跟着潜入水底,一团一团的黑色从深处冒出来,拼命把我往上推,我喝了几口水,浮出水面。晓默估计被水里的怪兽吃掉了,我一阵恐惧,头发根立起来,哭着走出洞口。我们的两捆柴靠在洞边,我无法扛两捆柴回家,于是就放火把晓默的那捆烧掉了。晓默失踪的事情很快传遍整个寨子,年龄相仿的几个小伙子把我叫到一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纷纷问我。六指,你是不是先奸后杀?六指,你是怎样把她骗到洞里的?六指,做那事的感觉怎样?……大人们在我的带领下点着葵花秆来到洞里。晓默,晓默,你在哪里?只有回声在洞里古怪地响,渐渐变小。晓默的父亲和我父亲先后潜入水底,皆一无所获地出来。最后走出洞口,看到那捆燃烧成灰烬的柴,晓默的父亲才突然大吼起来,你怎么把她砍的柴烧掉了?我被他的声音吓得直发抖。我父亲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安抚道,小孩子懂什么,别吓着他,我让他赔你一捆就是了。水面平静,一丝涟漪也没有。晓默,晓默,你在哪里?我又像当初那样呼唤。晓默忽地冒出水面,朝我笑着。
你差点又把我吓坏了。我不过开个玩笑而已。当初也是开玩笑的吗?是的,但那时候不懂事,那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晓默她不知道那个玩笑给我留下好长时间的阴影。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那究竟是梦还是玩笑。肯定是玩笑,自从开了那个玩笑,我就再也不会做梦了,所以我才对梦如此好奇。你就生活在梦中,你还想做什么梦?我有些不高兴,转过脸去。晓默看出我不快,游回岸凑到我身边说,别这样,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不得不那样做。不会,我永远也不想明白。我堵着气,不理她。蜡烛就在此刻熄灭了,那块蓝色的石头极其耀眼。晓默说,我们还是睡觉吧,兴许睡觉能让我们开心起来。
晓默很快睡着了,轻微地呼吸。我一直睡不着,总觉得父亲在洞口朝里张望。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年轻时洞里没有水,有一次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有人无意中到洞里来,就看到了水。我们小的时候,时不时会有闲得无聊的人点着葵花秆来洞里探险(其实是洗澡),自从晓默在洞里失踪后就没人来过,我是在荒草杂木中走了一个小时才到的,衣袖都被刺刮破了几处,想不到一到水边就见到晓默(那时候我并没有惊讶,也没有害怕,在洞里遇到一个人总比什么都遇不到好)。原来晓默并没有失踪,只是开了个玩笑而已。我翻身坐起来,打燃打火机,转眼去看晓默,她伸手挠了挠额头,翻了一下身,继续睡。我的烟瘾又犯了(以前很多个失眠的夜晚,我就坐起来抽烟,有时候一直抽到天亮),但那天跑得急,只带了一条烟,都已经抽完。嘴里苦得难受,稍一停,我取出水果刀,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嚼,最后吞了下去。
我依旧觉得父亲在洞口朝里张望,便起身往外走去,洞口除了杂草和乱石什么也没有。天快黑了,天边浮着暗灰色的云,好像正往这边飘过来,风疯了一般地吹,忽左忽右,不时听到树枝断裂。我又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嚼,不小心割破手指,血不停地往外流。我回到水边,点燃一支蜡烛。不一会晓默醒了,她揉着眼睛问,你没睡?我点点头说,刚去洞口看,天快黑了,看样子要下雨。晓默突然看到地上的血,指着血问,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我说,开玩笑要受到惩罚的,我才不会开玩笑。什么惩罚?你自己还不知道吗?晓默转过脸去,寂寂的样子。我觉得有点过了,不该说这话气她。为了挽救,我把还在滴血的左手伸到她面前晃了晃,说剃头发不小心割到的,然后剃下一撮头发递给她,问,要嚼吗?像槟榔一样。她厌恶地推开。我说,不要生气了,生气会让人更加孤独的。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在想我爸我妈和我弟。那天见到晓默我就想给她讲讲她的家人,但她说不想听,怕听了以后会很痛苦。现在我犹豫着,还是给她讲了。你爸和你妈老了很多,但他们都过得很幸福。是吗?是的,你弟初中毕业去打工,几年后从云南娶回一个媳妇,生了个女儿,你妈每天都教她唱歌。唱什么歌呢?这,我没注意。晓默沉默着,稍一停唱道:木马木马摇摇,宝贝宝贝笑笑,快点快点跑跑……唱完后羞涩地笑着说,我妈以前教我的。停了停又問,我妈他们经常谈起我吗?我抬头望着洞顶,回想了一会儿,说,我好久没听到他们谈起你了,只是有一次听你妈说你弟的女儿长得像你,估计是你投胎的。我笑了笑,接着说,他们不知道你还活着。晓默抿嘴笑着,望向那块耀眼的蓝色石头,笑在她脸上静止了一般。我又剃下一撮头发,但已经觉得饱了,便把头发放进水中,一只肥胖的鱼张嘴咬住,转身游跑了。
我坐过去,抱住晓默。许久后她突然发笑,说,你好像是第一次抱我。我也笑笑,说,我以前对你没有过不轨的想法,包括那天和你进来洗澡。大概是因为那时候你还不懂男女之事。不,我只是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失去你,我就没有朋友了,当时他们都说我是怪胎,不愿意跟我一起玩。晓默抚摸我左手大拇指根处外侧,说,就是在这里吧,现在看不出这里曾经长着第六根手指。我说,现在的医学太发达了。你的手还在流血。不要紧的。不痛吗?不痛。我愣了一下,确实没感觉到痛。我突然怀疑,你的第六根手指是你自己切掉的。我笑着说,真后悔花钱去医院,早知道不痛就自己切了。突然听到牛叫马鸣,混乱成一片,我下意识地四处看。晓默笑着说,下雨了,只要外面下雨,洞里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我想起初中时看过很多关于神秘事件的书,看来那些书的作者不是乱编的。洞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估计外面的雨也跟着大了,好像还有风吹进来,很快蜡烛就灭了。我和晓默紧紧地拥抱着,我在黑暗中探寻到她的唇,吻了上去。
醒来已是中午,我来到洞口,只看到一半太阳,另一半不知哪儿去了。正感到疑惑,突然听到晓默喊我,我赶紧回去。她拿着两条鱼,递一条给我,我掏出水果刀,又准备开膛破肚。晓默说,把刀放下,像我这样。说着她咬下鱼头,嚼得咯吱响。我说,我不行。晓默指着我,故意用吓人的语气说,你敢动刀,就给我滚出去。我想,如果经常烧火烤鱼,烟上升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便收回了刀,朝晓默笑笑,学着她咬下鱼头,吃了起来。一条鱼很快就被我吃完了,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下咽。晓默看着我,满足地偷笑着。我用手把水撩在她脸上,她躲闪着,趁我不备把我拉入水中。我们嘻嘻哈哈地打起水仗,闹了一会儿都累了才停下。晓默说,讲故事的时间到了。我说,今天讲点什么呢?细想一会儿,我说,对了,我给你讲讲我爸。晓默点点头说,嗯,我觉得你爸的故事应该很神奇。
那天晚上为了庆祝拉回最后一车石头,我爸捧了两捧苞谷粒给马吃,马吃完后喝下半盆水,我爸把它关进圈里。我去马圈边撒尿的时候,看到马躺在地上,马一般不会躺下,除非生病或者特别累,于是我赶紧回屋里告诉我爸,我爸也睡下了,他说,没事,它只是太累了。第二天早上我爸起来,把我喊醒,问道,你今天早上听到鸡叫没有?我疑惑地看着他,那时候我还不会失眠,一般都睡得很死。我爸说,你喊我一声。我揉着眼睛,丈二摸不着头脑。我爸又说,我好像听不到声音了,你喊我一声,看我能不能听得到。我喊了几声爸爸。他问,你喊了吗?我点点头。我爸掏了掏耳朵,平静地说,真的听不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是的,他那时候表现得很平静。说着他走出房间,不多时听到他的喊声从马圈传来,说我们家的马死了。我赶紧爬起来跑出去,马闭着眼睛瘫睡在地上,我摸了摸它的脖子,硬邦邦的,应该是半夜就死去的。我才想起来,昨夜在睡梦中模糊听到几声马叫,我想那时候我爸就已经失聪了,要不他一定能听到声音并起来看,因为他的睡眠浅。
讲到这里,突然听到外面有说话声。我想,警察终究还是来了。苦笑着对晓默摆摆手,她用手指在嘴边嘘了一声,示意我和她搬开那块蓝色的石头。石头很重,我们用尽全力才移动了一点,我拼命地挤进去,脸部被擦伤。我们又用尽全力把石头合上,没合严实,有一条细小的缝,仍能看见外面。晓默把蜡烛吹灭,沉到水底去了。说话声越来越近,好像已经到洞口。女声:有人在这里烧过火。男声:早就跟你说的,经常有人过来,不用怕。我从缝隙往外看,黑漆漆的,但不一会儿,一束光射进来,很快一对男女出现在我眼前,穿着普通衣服,虽看不清脸部,但估计不是警察。女声:有蜡烛、烟头。男声:是来这里洗澡的人留下的。女人突然惨叫一声,我定睛看去,男人左手抓住她的头发,右手握着刀疯狂地刺进她的脖子。女人惊慌地求饶着,声音很乱,听不出她说些什么,求饶了几句就没有声息了。我想起阿杜,阿杜是个矮个子的女老师,那天我猛地抓住她的头发,取出水果刀刺进她的脖子,她就是这样求饶的。半分钟后她倒在我怀里,张大着嘴,眼睛惊恐地看着我。我很后悔,当时我应该把速度放慢一点,听听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听到水声,我回过神来,那个男人蹲在水边洗刀。清洗干净后,他换了衣服,把脏衣服盖在女人的身上,点燃,然后提着手电筒出去了。我很赞赏他的做法,当时我应该把阿杜烧掉的。如果烧掉就好了,警察会以为她是因火灾而死,我就不用逃了。可是如果选择那样办,我就不会在这里见到晓默。我顿时感到有些难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选择。
晓默浮出水面,撩水把火浇灭。我们又用尽全力搬开石头,我拼命地挤出来,又用尽全力合上。晓默对我说,你出去看看。我来到洞口,太阳恢复了完整,开始偏西,一个背影在荒草中渐行渐远。那天我离开阿杜的宿舍,太阳的位置好像就和今天一样。我走出空荡荡的教师宿舍楼,在街上看到几个住校生,估计是翻围墙出来的,他们正抽着烟,看到我后一溜烟跑了。那时候我无声地笑了笑,在心里说,以后你们再也见不着我了。晓默喊了两声,我才回过神来,回到她身边说,远去了。我点燃蜡烛,火只烧了女人的脚,烛光照亮她的脸,看样子四十来岁。晓默说,帮我搬去暗室吧。我抬着女人的头,晓默抬着脚,我们在水中往暗室游去。我的水性很差,喝了一口水,晓默则在前面轻而易举地游着。游了二十来米,看到一个小洞,晓默示意我进去,我钻了进去,看到里面坐着五副人体骨架。晓默说,忘记告诉你了,这洞里有过几次杀人案,尸体都是我搬进来的。我们把女人放到第五个骨架的旁边,给她摆好坐姿,然后晓默熟练地脱下她的衣服,笑着对我说,我穿的衣服都是这样来的。
晚上我和晓默相靠着坐在水边,我正准备给她讲故事,突然听到暗室里传来哭声。晓默说,刚死去的人觉得心不甘,都会哭。哭声轻微细小,却狠狠撞击人的心底。我说,我们过去安慰她吧。晓默坐着不动,说,还是别去了,她哭够了会自己停下来,安慰一个死去的人没用,而且你越安慰,她就越痛苦。我说,看来死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是用哭来表达痛苦。晓默说,我们哭过后,痛苦就慢慢消失,而死人哭過后,痛苦则慢慢传遍全身,所以身上的肉才会腐烂,最后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我突然无比激动,说,晓默,想着肉体一点点腐烂,骨架一点点露出,这是何等的孤独呀。是呀,痛苦、孤独和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晓默说着往我怀里蹭,我顺势把她抱住。很久后,死人的哭声才停止。晓默已经入睡,我把她放在水面,自己在石头上躺下。翻了几次身,一点睡意也没有,又开始感觉父亲在洞口朝里张望。我坐起来,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嚼。我越嚼越清醒,失聪后的父亲又浮现在我脑海里。
聋子,你也会砌墙?父亲嘿嘿笑。你这墙砌歪了,拉一根线吧。父亲嘿嘿笑。那人手舞足蹈地比划着,父亲摆摆手说,我用眼睛。说着他丢下烟头,把头靠在墙壁上,闭上一只眼睛,看了一会儿,取下一块石头,用锤和錾子修了几下,又放回去。聋子,你家六指考上高中了?父亲嘿嘿笑。别让他读了,让他去打工吧,能给你挣回很多钱。父亲嘿嘿笑。去报到的那天早上下着毛毛雨,我们扛着行李走到镇上已是两脚泥巴,父亲拉我来到草地上,我学着他把鞋的边沿在草丛中擦了几下,鞋子就变得干净了。我们坐班车到县城,问路走到学校,几个老师正在吃盒饭。一阵饥饿袭来,我吞了吞口水,才意识到已经中午。我和父亲把行李放下,远远地看着老师们,“报名处”三个字很显眼,我们不敢上前去打扰,心想等他们吃完饭再去。一个高瘦的老师注意到了我们,站起来招手,喊道,是报名的吗?过来登记。父亲看到老师招手,赶紧掏出烟,跑上前去分给他们,嘿嘿地笑着,我提起两袋行李跟上。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哼着苗族山歌满寨子转悠。聋子,什么事让你高兴成这样?我家六指考上大学了。聋子,你听到我说话了?我家六指考上大学了。聋子,别总昂着头,走路得看着路。我家六指考上大学了。聋子,这回你可以享福了。我家六指考上大学了。第二天早上父亲爬到山上找野蜂蜜卖,找到中午时分摔了下来。最先带来父亲摔亡消息的是一个放牛的小男孩,他喘着气跑回寨子,见到我时停下来,因惯性还险些摔倒,站稳后激动地说,你家聋子摔死了。最后,在高中班主任的鼓励下,我还是去办了助学贷款,踏上开往大学的火车。一个高中女同学去送我,她不停地挥手,跟着火车跑,但很快就被抛在了后面,她突然蹲下身去,蒙着眼睛哭起来。
我是被晓默摇醒的。我感到背上隐隐发痛,转身一看,才知道昨晚是靠着一块凸起的石头睡去的。晓默笑着说,快给我讲讲你的梦吧。我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做梦了?我醒来好久了,一直在观察你,发觉你的眼皮和嘴唇一直在动,这不是做梦是什么?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晓默是个聪明的姑娘,我甚至对她敬佩起来。我的梦中首先出现一匹白马,它在树林里神情悠然地啃着低矮的草。我想起我妈,她跑之前曾对我说,要是在树林里遇见白马,就追着它跑,跑到一座坟前,挖开坟,揭开棺材,里面就是亮堂堂的黄金。梦中的我有些激动,跺脚吓了马一跳,马拔腿往前跑去,我赶紧追上。跑到一座长满荒草的坟前停下来,我取出水果刀开始挖掘,最后挖到几根白骨,我知道是我爸的。白马突然朝着我大笑,我发现正是我家曾经养的那匹马。你说怪不怪?晓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我还是羡慕你能做梦,想什么就可以梦到什么。我觉得头有些沉,摇动了几下说,可是梦醒后的感觉不好受。晓默说,那就讲讲你的故事吧。说完她拍了拍我的肩,像是在给我安慰。我做了一次深呼吸,不知道讲些什么,又靠在凸起的石头上。靠了一会儿,我直起身来说,对了,就给你讲讲我的大学生活吧。晓默点点头。
刚进入大学不久,我好像患了轻度抑郁,觉得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我给那个高中女同学打电话,说我想退学。她也不善言谈,一直说,你千万别退,好好在大学里等我,我一定认真补习,明年九月份我们在大学校园相见。挂断电话后我哭了,比父亲摔亡时哭得还厉害。三个室友围拢过来,问我到底怎么了,我摇头不答。最后他们把我拉去烧烤店,说没什么事是酒解决不了的。你就是在大学里学会喝酒的?是的,还学会了抽烟。后来你和那个高中女同学在大学相见了吗?没有,她补习还是没考上大学,给我打电话哭了一场,去浙江打工,两年后就嫁在那边了。如果她考上大学,你就和她恋爱了。也许。那你和其他女生恋爱了吗?没有,估计是家庭影响了我的性格,我不会跟人交往,特别是女生,记得大四那年,有个学妹对我说想去镇远玩但没人陪同,我让她找她的同学陪,她说她的同学都去过了,我想了想说,镇远也没什么好玩的。后来呢?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你傻呀,竟然不懂她的意思?那时候确实不懂,但应该是我的钱包不允许我懂吧。我们沉默下来。年幼时,我家和晓默家是寨子里最穷的,别人家最起码在秋收时能吃上米饭,而我们两家秋收时吃混合饭(一半大米和一半苞谷面混合煮成),平时全吃苞谷饭。沉默许久,晓默说,你大学没谈恋爱,感觉孤独吗?我说,孤独,但有什么办法?晓默问,孤独的时候你梦到过我吗?我没有回答,陷入沉思。晓默好像有些不高兴,回到水中,慢慢地转着圈。稍一停,我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嚼。
晓默,我明白了,我们都是孤独的,因为我们被石头包围着,你看我们的上下左右都是石头,它们正逐日地朝我们挤压过来,总有一天会把我们的身体挤压破碎,然后我们就会在痛苦中消失,我们的骨头也会消失,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时间始终都是残酷的。晓默,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假想出来的,等有一天,假想不再存在,那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世界又回到最初的模样。晓默,整个人世都是一样的,在外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外面的人也会孤独,只是他们已经习惯,他们还刻意用石头建造成房子,生活在孤独中,特别是晚上,他们在孤独中做爱,在孤独中怀孕,产生孤独的下一代。晓默,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逃离不了孤独。晓默,你以为地球就不孤独吗,地球被那么多星球包围着,那些星球也是由石头组成,所以宇宙中孤独是无处不在的,孤独是永恒的,但仍有少数人不愿服输,一直在跟孤独抵抗,尽管这种抵抗犹如杯水车薪……
进餐时间已到。听到声音,我回过神来。晓默抱着一条硕大的鱼,对着我笑。你在胡思乱想什么?我摇摇头。看,我费了好大劲才抓到的。晓默腾出右手拍了拍鱼的肚子,鱼又奋力挣扎起来。我赶紧过去帮忙,但鱼挣扎得很厉害,我们无从下嘴。我一狠心,把鱼从晓默的怀里抢过来,把它的头猛撞在巨石上,撞了两下它终于安静了。晓默有点责怪我,一直说我不应该这样。尽管她心里不快,但我們还是一起把那条鱼吃完了。
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晓默突然问。我顿时一惊,想不到她会问这个问题。我对关于心理的字眼很敏感,这大概是因为我三年内跟五个同学闹了不愉快,和其中三个还打过架。有一天下午,班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心理学老师的办公室一趟。我当时心跳加速,反复问班长有什么事。班长说,没事,只是约你过来聊聊天而已。挂断电话,我坐在床上犹豫了十来分钟,还是忐忑地去了。班长和心理学老师正在说笑,我敲门打着招呼走进去。老师微笑着指指沙发让我坐下,班长起身去给我倒水,坐了一会儿他就借故走了。那是我跟老师聊天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是否喜欢这座城市聊到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临走时老师对我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跟我聊。我后来没有去找过他,我知道这是班长和他设好的圈套,他们把我当成了病人,虽然我知道这是好意的,但心里面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晓默摇摇我,说,发什么呆呢?回答我的问题,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我说,算是去看过一次。医生怎么说?也没怎么说,就是瞎聊而已。我不想谈论这些,赶紧转移了话题。
晚上我和晓默做了两次爱,我们的动作过大,她腿上的鳞都掉了好些。我背靠石头坐着,晓默蹭到我怀里,笑着玩弄我疲软的阴茎。烟瘾又发了,嘴里苦得很难受,我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嚼,不小心又把手割破了。我把几滴血滴在水中,一群五颜六色的虾围过来,有拳头般粗的,也有小指般细的,看着很可爱。很快血就被吸光了,我索性把手放进水里,让这些虾吸个够。晓默抬头看我,故意装作很厌恶地说,令人讨厌的烟鬼。我摸着她的肚子,笑着说,让人喜欢的美人鱼。晓默突然问,你说我会怀孕吗?我吞下头发,说,会,然后生下一群小美人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晓默咯咯地笑,轻轻捶打我的胸口。
晓默睡着后,我越发清醒,感觉父亲一直在洞口朝里张望。我逃到洞里之前,还是去坟边给父亲上香烧纸的,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烧纸的时候忍不住流出眼泪。我想把事情告诉父亲,但犹豫了一会儿没有说,说了他也听不到。我取出水果刀,依旧锋利无比,靠近刀把的地方还有一点血迹,我在裤子上擦净后又放回去。父亲的坟被杂草包围着,我想割掉杂草,但最终没有割,藏在其中,待香燃尽,就逃往洞里。我想,再过段时间得出去,悄悄买点香纸烧给父亲。
晓默醒来,惊讶地说,你昨晚上一直没睡?我神情迷茫地点点头。晓默说,你的头发都快被你吃光了。我本想开玩笑说头发是烦恼丝,吃光了最好,但没有说出口,我感到胸口很闷,心里一阵一阵地痛。晓默看出我难受,过来抱住我,抚摸我的头,说,别吃了,别吃了。我躺在晓默的怀里,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晓默把我喊醒,问,好点了吗?我坐起来,说好多了。看我确实比刚才好多了,晓默便笑着说,你刚才一直在说梦话,我好久没听到别人说梦话了,感觉好有意思。我也笑笑,问,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你说得吞吞吐吐的,好像是说冤家路窄。我开始回想我的梦,我似乎做了几个梦,其中一个梦梦到暗室里的那个女人,她用手堵着脖子的伤口,但血还是疯狂地冒出来。我说,我们去暗室看看那个女人吧。晓默说,别去了,快给我讲讲冤家路窄的故事。于是我给晓默讲了我杀害阿杜的经过。
刚讲完,听到外面有说话声,难道又是一场杀人案?我和晓默又赶紧移开那块蓝色的石头,我拼命挤进去后又合上,晓默吹灭蜡烛沉入水底。说话声越来越近,强烈的光射进来。我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嚼。石头依旧没有合严实,我从缝隙看去,首先看到一个光头男人,穿着红马褂,双手被铐在后面,由两个警察押着,后面还跟着好几个警察,有的拍照,有的做记录,我知道這是指认现场。一个警察问,尸体在哪儿?男人说,烧掉了。警察说,在哪儿烧的?男人指了指那天女人倒下的地方。警察问,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男人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把嘴里的头发吞下去,又剃下一撮头发放进嘴里,这是最后一撮了。一个警察四处张望,很快发现了缝隙,石头被搬开,强烈的光射进来,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大概半分钟,一个警察笑了起来,说,原来你在这里,我们找你好久了。他们把我全身上下摸了一遍,搜走水果刀和打火机。暂时没有手铐,两个警察把我的手反到背后,用绳子捆住,一左一右地押着我。
一个警察朝我吼道,嘴里嚼的是什么,吐出来。我准备吞下头发,他赶紧捏住我的脖子,另一个警察把一个塑料袋撑开,放在我下巴处,说,吐出来。我看到塑料袋是白色的,便把头发吐了进去。那个男人突然问我,你看到尸体没有?警察朝他吼道,闭嘴!我说,尸体被搬去暗室了。警察问,暗室在哪?我想用手去指,但发觉手动不了,便朝暗室的方向努努嘴。一个警察脱下衣服裤子,用绳子捆住腰部,把绳的一端递给另一个警察,朝着我努嘴的方向游过去,一会儿后听到他喊,尸体在里面。男人讲了他杀害女人的过程,我讲了搬运尸体去暗室的经过。领头的警察很快做出决定,由四个警察把我们押出去,其余的留下来处理尸体。我对警察说,我要跟晓默道别。警察问,晓默是谁?我说,晓默是美人鱼。我朝着水中喊,晓默,晓默,你在哪里?一点回应都没有。我说,晓默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她十二岁那年开了个玩笑,留在水中生活,变成了美人鱼,现在她沉在水底不敢出来,因为你们吓着她了。警察押着我往外走,我急得哭了起来,说,我一定要跟晓默道别,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押着我的一个警察说,走吧,听话一点,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晓默,晓默,你在哪里?我又喊道,还是一点回应都没有。那个领头的警察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里没有美人鱼,你只是产生了幻觉,快走吧,出去就好了。我仍不走,一个警察踢了我两脚,强行把我连拉带推押了出去。
走到洞口,那个男人突然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止住哭声,茫然地盯着他。他又说,我认识你,你是我女儿的班主任。我看着他,轻轻摇着头。男人突然兴奋起来,不断找话题跟我聊。他说,想不到我们俩会以这种方式在这里见面。我只顾往前走,没有回答。稍一停,他又说,都是因为我去投案自首,要不我们不会这么快就见面的。我来了兴趣,问,你是投案自首的?男人说,是的,我做了一整个晚上的噩梦,感到很痛苦,就去自首了。他又问我,你呢?你感到痛苦吗?我点点头。那你为什么不去自首?我没有回答,我又想到晓默,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男人是个话痨,又问我,那个女老师真的是你杀的?一个警察朝他吼道,你有完没完?我转眼去看着男人,说是的,那个矮个子的女老师,姓杜,大家都习惯叫她阿杜。刚才的那个警察又朝我吼道,闭嘴!我说,你就让我说出来吧,要不我心里很痛苦,我这几天过得像梦一样。押着我的一个警察和气地说,到派出所再说,到时候我们给你足够的时间,你想说多久都行。
我抬头看向远处,野草深处先后飞出两只野鸡。一阵风从山下吹来,野草发出轻微的声响。我一眨眼睛,恍惚看到一个老人和一匹白马,白马慢慢地吃着草,老人坐在一边悠闲地裹叶子烟。我再仔细看,老人已经点燃叶子烟,起身朝我招手,无声地喊着什么。稍一停,白马抬起头,直盯着我看,看着看着,它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责任编辑 杨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