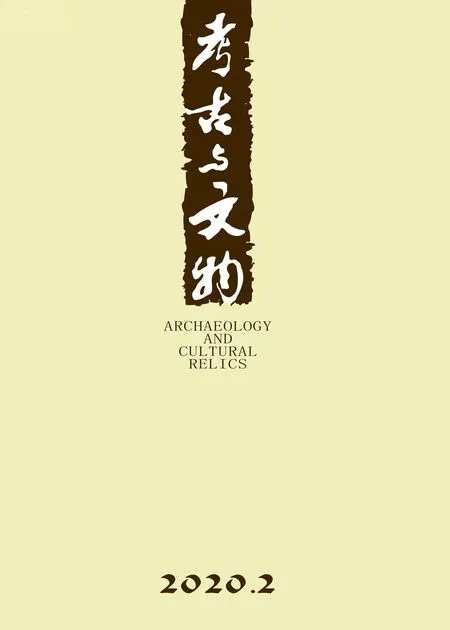试论两汉随葬车马明器
2020-08-04赵丹
赵 丹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明器为“有形无实之器”与“送死之器”,是指与现实生活所用器具有别,仿实用器制作而成,专门置于墓葬之中服务于死者的随葬之物[1]。车马器一般是指古代车及车马使用的器件,有的具有实用功能,有的具有装饰功能[2]。本文车马明器是指相对于服务现实生活中实用车马器具及真实车马而言,在墓葬之中,区别于实用车马或者代表真实车马而存在的,包括三个方面:随葬的车马器(实用或模型)、车马模型、车构件与车马饰件等。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车马明器随葬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出现,随着时代发展,车马明器随葬在内容上有所丰富,使用阶层有所扩大,功能及内涵有所改变。目前学术界对汉墓随葬车马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车马殉葬的相关内容[3],但未见有对两汉时期车马明器的专题性研究。本文就现已发表的汉墓发掘资料,试对汉墓中车马明器的使用及时代特点进行综合性探讨。不妥之处,以求指正。
一、汉墓随葬车马明器发现概况
根据现有发掘资料来看,汉墓中有随葬车马明器的墓葬较多。一般帝陵、诸侯王墓大都有随葬车马明器,列侯及其以下的大、中型墓葬亦有较多发现。
西汉帝、后陵陵园内的从葬坑与陪葬墓中多有发现随葬车马明器的现象,包括高祖长陵[4]、景帝阳陵[5]、武帝茂陵[6]、昭帝平陵[7]、宣帝杜陵[8]等。
诸侯王随葬车马明器的墓葬有:山东西汉齐王墓陪葬坑[9]、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10]、章丘洛庄汉墓[11]、曲阜九龙山鲁王或王后墓[12]、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墓[13]、济宁东汉任城王配偶墓[14]、济宁东汉任城孝王墓[15],江苏徐州狮子楚王墓[16]、拖龙山楚王墓[17]、龟山楚王墓[18]、驮篮山楚王墓[19],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墓[20],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21]、定县中山怀王墓[22]、鹿泉市北新城真定王及王后墓[23]、定县三盘山汉墓[24]、获鹿高庄常山县宪王墓[25]、定县中山穆王墓[26],河南商丘梁王墓葬群[27],广州南越王墓[28],安徽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29]、六安双墩1 号汉墓[30]等。
其它多为诸侯王以下的列侯及其他中型墓葬。车马明器随葬范围较为广泛,在辽宁、广州、安徽、广西、贵州、河北、江西、湖北、湖南、江苏、青海、甘肃、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皆有发现(图一)。从地域分布特点来看,北方地区较多,南方地区较少,汉代两京及其周边地区尤为常见。
二、汉墓各阶层车马明器随葬特点
两汉车马明器随葬于帝陵、诸侯、列侯与一般中型墓葬中,表现形式及其组合有所差别,展现出一定的特点。
(一)帝陵

图一 汉墓随葬车马明器分布示意图
目前,已发掘的西汉帝陵陪葬坑中,长陵有祭祀车马与大量鎏金车马饰件;阳陵南区从葬坑中发现较多的木马模型及车马器具;茂陵一号从葬坑有车和驾车的铜马、木马明器及车马器具;平陵及园外16 号坑有漆木车与木马,14 号坑中有木质的羊车;杜陵一号陪葬坑出土有铜、铁质车马器与彩绘明器车相配。
目前,所见两汉帝陵从葬坑中使用车马陪葬可分为车坑、马坑、车马坑、马厩坑等,真实车马、车马器、车马模型等同出中应是象征“厩”的内容[31]。帝陵的车马坑与其它陪葬坑共同构成不同内涵、形式多样的外藏系统。
(二)诸侯王墓
在两汉诸侯王墓葬中,车马陪葬形式有真实车马与车马器、车构件与车马饰件,及车马模型、车马器模型等。组合形式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真实车马与车马器共同使用(表一),同出于陪葬坑中。车马器的位置有两种,一种为车马器分布于车马身上;一种马身未佩戴马具和马饰,车马器单独放置。
第二种类型,在第一种基础上加上车马模型或有与之相应的车马器(表二)。一些墓葬之中车马模型与真实车马位于不同的位置。一般真实车马位于单独的随葬坑,车马模型位于单独的随葬坑或墓葬内部,二者随葬功用应有别。
第三种类型,车马器、车马模型、车构件与车马饰件等单独出现,代替真实车马随葬(表三)。随葬车马明器一般在墓室中有特定的位置。
诸侯王墓中有使用车马陪葬的第一、第二种类型在西汉早中期、西汉晚期前段盛行,晚期后段衰退,仅见北京大葆台有真实车马陪葬,其他诸侯墓葬中大多为第三种类型。总体趋势是至西汉中晚期之后真车马被车马明器取代。东汉时期诸侯王墓中基本不见真实完整的车马随葬,明确随葬车马明器仅见3 座。
诸侯王墓中随葬车马器的位置总体趋势是由墓外车马坑向墓室之内转移,主要集中出现在墓道、回廊、耳室、侧室或主室之内。相对于墓葬之外专门设置的车马坑,诸侯王墓室内专门随葬车、马或者车马具的地方称之为“厩”[32]。“厩”中一般随葬有真实车马或车马模型,如长清双乳山1号墓,墓道椁室之内有真实车马随葬;广州南越王墓,墓道与前室中各有一辆漆车模型,其中2 件当卢、2 件马衔及数量众多的马饰代表至少有两匹以上的马匹。

表一 西汉诸侯陪葬车马第一种组合类型
(三)列侯及其以下大、中型墓葬
目前,有5 处列侯级别的墓葬随葬有真实车马,同时出土有车马器,分别为:杨家湾4号墓[33]、仪征烟袋山一号西汉墓陪葬车马坑[34]、海昏侯墓[35]、蓝田支家沟汉墓[36]。其他列侯及贵族随葬车马以墓内随葬车马明器为主,车马明器数量多,形式多样,常与人俑或骑马俑等构成车马随葬内容。
常见构件有:车轮轴及其部件包括:辖、軎、轮、毂、轴;车盖及其部件盖弓帽、箍;马配件当卢、马衔、马镳、弓形器、衡末轭首饰;以及其它车身、马身装饰或功用类配件。根据列侯墓葬与其他大、中型墓葬中所使用车马明器的随葬组合情况,主要分为3 类。
第一类为车马模型随葬。根据材质可以分为木、陶与泥、铜质等三种。
1.木车马。有木马与木牛两种。如甘肃武威磨咀子48 号汉墓出土有彩绘铜饰木质轺车马一组;49 号墓出土有牛车3 组[37]。
2.陶、泥车马。如四川成都扬子山墓葬出土陶马车[38]。济南市北郊无影山西汉墓出土有陶车马模型一套[39]。西安世家东汉墓M169 出土有泥质模型牛车[40]。
3.铜车马。如贵州兴义汉墓出土铜车马一套[41],属于辎车[42]。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有铜马39 件、铜车14 辆以及完整的铜车马俑[43]。
第二类为车马器随葬,占多数。主要有铅、铜、鎏金与错金银、铅锡、铁质等5 种,车马器分为实用与模型两种。车马器构件多以铜质较为多见,其次为铅质,有的墓葬之中还出现多种材质的车马器共同使用的情况。

表二 西汉诸侯陪葬车马第二种组合类型
1.铅质。如西安东汉墓中出土铅车马饰件近50 件,有车軎、盖弓帽、衡末、衔镳等[44]。老河口九里山汉墓M89、M171 出土有铅车马明器,有盖弓帽、马衔、当卢、泡钉等[45]。
2.铜质。此类材质的车马器构件最为常见。如南阳一中M223 及M406 出土有铜质当卢、车軎、管、盖弓帽以及铅质车軎、盖弓帽[46]。
3.鎏金、错金银。如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墓室前部东厢出土鎏金车马器,有车轡、伞柄饰,车器与马器应代表相应的车马[47]。
4.铅锡质。如萧县汉墓出土有铅锡衔镳类(XWM22:1)车马饰[48]。

表三 西汉诸侯陪葬车马第三种组合类型
5.铁质。如咸阳师院科技苑西汉墓出土铁车马器,墓主为西汉晚期二千石高级官吏[49]。
第三类为车马明器与车马模型共出。如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4 辆模型木车和16 匹木马,前室北侧器物架下有铝车马器,均模筑,制作精细,小巧玲珑[50]。
列侯级别墓葬中,除4 座随葬为真实车马之外,其余皆为车马明器。随葬的车马明器一般置于墓内,有专门的耳室或侧室用于放置车马及相关随葬品。车马明器第一、二、三类皆有,材质以铜制或鎏金铜车马器、漆车马为主。
其他大、中型墓葬随葬车马明器材质多样,常见铜、铅或陶质,随葬数量及形式根据墓主经济能力而定。如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县令长)或富甲一方的大商贾,亦随葬有成套车马模型与相应的车马器明器[51]。
从地域分布与特点来看,北方地区较南方地区多见,且有所差异。南方地区中型木椁墓之中多随葬木质车马器或车马模型,应与地方葬俗有关,成套或制作精致的铜车马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北方地区列侯级别以下的中型汉墓中车马随葬多为车马器的形式,而且以西安与洛阳为中心的两京地区是车马明器随葬集中出现的区域。南方与北方汉墓车马明器随葬有别,除传统的丧葬习俗因素外,北方经济较南方发展繁荣,加之北方地貌较南方广阔、民族善骑射,以马或牛为劳力的车马为北方地区主要的交通出行与运输工具等因素,皆是南北车马随葬特征差异的重要原因。
真车马或代表真实车马表现殉葬习俗、社会地位及丧葬礼遇。如柿园汉墓中随葬车达20余件,象征马匹100 余匹,鎏金车马器以西排列有骑士俑,整个车的阵容前为导行车,中间为墓主人乘坐的车辆,后为小车随从,庞大的象征车马的存在可能主要为表达墓主的丧葬礼遇与社会地位,同时也是经济能力的体现。列侯及相关贵族随葬车马明器的数量与规模不及诸侯王墓,主要为车马器与车马模型,同时车马模型有马车及牛车两种形式。列侯级别以下的大、中型墓葬随葬车马明器数量明显较少,根据地位、财力及需求仅放置相应的车马明器。
三、继承与发展
商周时期随葬品明器化开始流行[52][53]。两汉时期的车马明器随葬内容多样,在继承前代车马埋葬等级制度的同时,在具体埋葬形式、内容上又有所演变。
(一)继承
商代车马器一般出现于车马坑与马坑之中,墓内发现较少,一般带车马坑的墓葬在墓内不随葬车马器,车马器类型相对简单[54]。西周时期墓葬中车马器的使用有相关规定:“无鼎小墓均无车马坑与车马器;一鼎至三鼎大多有车马器,很少有车马坑;五鼎或五鼎以上的墓,几乎都有车马坑,而殉车、马的数量也还各有等差”[55]。一些贵族墓葬中以随葬大量的车马器代替真实车马,等级高者随葬数量多,反之少。东周时期为车马器与车马模型随葬盛行阶段,形式及内容丰富,此时期车马明器随葬虽有进一步普及,但相比较西周时期而言,车马器在器类、组合及器形上有所简化[56];车马随葬亦有相关规定:九鼎墓中有单独的车马坑并且随葬车马器,三鼎至九鼎的墓葬中仅有车马器[57]。在战国晚期墓葬中车马明器随葬现象开始增多,内容上有所丰富,真实车马随葬趋于减少,表明真实车马殉葬制度的衰落,是车马殉葬制度由真实车马向车马明器的过渡阶段[58]。秦始皇陵墓东侧有真实车马殉葬,同时在车马陪葬坑有大型彩绘铜、人俑,真实车马加之陶质武士俑、战车战马及青铜车马器等[59]。
汉代高等级墓葬对前代车马明器随葬的等级性有所继承,同时显示出一定的时代特点。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社会自天子至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乘坐车马有严格的规定[60]。汉代车马随葬制度虽没有像西周、东周有严格的设置,但在汉宣帝和元帝时期,诸侯王墓之中大多随葬三套真实车马,说明此时期的诸侯王墓殉马是有所规定的[61],而不同级别墓葬中车马明器随葬规模和数量体现出较大差异。车马模型与真实车马共同使用,或以车马明器代替真实车马随葬是对秦及以前车马陪葬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早中期,帝陵、诸侯王与列侯王墓中有完整的真实车马,数量、品类、形式与组合等多样的车马明器应是配套使用,用于殉葬。同时,设置单独车马坑或墓内有特定位置随葬车马,有的还有御马俑,或者根据车马的功用配置相应的器物。如战车则配置兵器,仪仗出行则配置大量的人俑。总体来看,高等级墓葬车器、马器较为完备,车马饰件较多且精美,低等级墓葬以个别车器或马器代替整体。西汉中晚期以后,诸侯王墓与列侯王墓几乎不见真车马随葬,且一般不再有单独车马坑的设置。但车马模型、车马器明器在墓内有特定的位置,一般大、中型墓葬中车马明器与其它随葬品直接置于墓室,随葬数量及品类有一定区分,功能及内涵不及高等级墓葬,车马明器的存在更多的应是直接服务于死者,代表地下墓主衣食住行中的一种要素或象征性需求而存在。
(二)发展
两汉时期车马明器随葬与前代相比更具普遍化、渐趋明器化。西汉早中期,部分帝陵、诸侯王与列侯王墓表现以真实车马+车马明器或大宗车马器随葬为主,其他诸侯及列侯级别仅随葬车马明器,且数量与品类层级递减。西汉中晚期之后,诸侯王与列侯王墓车马明器随葬内容明显简化,常与偶人共同置于墓内特定的位置。普通官吏或大地主阶级在墓室内亦随葬不同材质、数量的车马模型或车马器,一般中小型墓葬中也发现有少量车马器的随葬。车马形式以车马器、车构件、车马模型、车马饰等单独出现并且逐渐明器化,车马明器随葬成为西汉中晚期及其以后车马随葬内容的主流。东汉时期,随葬车马器基本明器化,真马以马俑、马具或马器代替;真车以模型车、车构件或车器代替;真实车马器或以模型车马器所代替。
高等级墓葬内车马明器所在位置的相对固定。东周时期大多数的车马明器置于墓室之内,表明车马殉葬由墓外转移至墓内,是对前代车马埋葬制度的一大发展,但其位置并不固定。至西汉时期,尤其是诸侯王墓中随葬的车马明器,大多有其固定的位置,数量之多,具有相应的象征性[62]。受等级及墓葬建造规模的限制,列侯级别以下的一般官吏、豪强地主墓葬之中的车马明器则根据需要放置,主要与其它随葬品构成种类丰富的随葬内容。
完整车马表现形式增加。汉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墓中出现较多的车马出行图案,完整的车马在墓葬中表现形式有所转变。一些有车马出行图案的墓葬,同样有车马明器存在,如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中随葬有铁衔镳、车軎等[63],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中,既有车马出行图案又有随葬的木车马明器[64]。以上或可证明,汉墓中车马出行图案在墓中出现似乎并不意味着代替车马明器在墓葬中的作用。两汉时期车马形式以场景图像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出现于墓葬之中,与前代相比是汉墓车马随葬的一大特点。车马在墓葬中的表现形式出现多样化,最终发展为两大系统:作为图像出现主要满足思想方面需求,用具体图案体现希冀;作为模型明器或以部分代替整体,置于墓葬之内,与其它随葬品共同服务于死者。
随葬车马明器内容丰富。两汉墓葬中所见车马明器主要包括车马器,木、铜、陶车马模型,车马饰件以及与车马相关的器物等。另外,牛车模型的出现是汉代车马明器随葬的重要发展,丰富了车马明器随葬的内容。因此,墓葬中车马器不再单独指代表马车,也有可能是代表牛车的存在。根据文献记载,牛车最早是用于载物,西汉早期因战争、经济等原因,马匹数量减少,在高官贵族中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65],并有相关规定:“自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66]。如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墓,墓道中有车构件于牛群俑之后[67]。载人的小车多以马为劳力,拉货物的大车以牛为牵引,庶民之中乘坐亦主要以牛车为主[68]。东汉时期,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东汉末年牛车迅速发展成为高级的车型[69]。因此,墓葬中车马器随葬亦有可能象征牛车的存在。牛车的使用在汉以后有所延续,从汉末至魏晋时期,统治阶级时常乘坐牛车,后成为习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因袭不改。两晋南北朝贵族官僚墓葬之中出土有陶质牛车模型,或者以牛车模型为中心与陶俑组成的仪仗队等,显示出牛车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作用[70]。牛车延续至隋唐仍比较盛行,但至宋代之后趋于减少。
四、两汉车马明器随葬盛行缘由
(一)真实车马殉葬习俗的衰落
车马明器代替真实车马存在于墓葬之中,首先是源于真实车马殉葬习俗的衰落。车马殉葬习俗源于殷商时期,战国晚期趋于衰落。战国时期真实车马陪葬减少,车马模型及车马器开始在墓中出现并成为主流,陪葬等级弱化,失去其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性特点,有些大型的墓葬之中不再单独设有车马坑,且一些诸侯列国王室及高级贵族真车、真马为车马器具所代替,作为象征性而存在[71]。战国晚期真实车马殉葬减少,模型明器车马增多西汉中晚期之后,汉墓中几乎不见真实车马用于殉葬,且车马明器代替真实车马在不同阶层墓葬中的发现。
(二)随葬内容追求明器化
先秦及其以前,墓葬等级标准主要以坟丘大小、棺椁数量、礼器及车马等方面,至秦代兵马俑的随葬代表强权军队,大量俑的出现表示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转变[72]。“生死有别”的思想观念促使死后埋葬用具与生前有所区分,“事死如生”的观念又要求与生前所用之物高度相似,与生活实用之物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模型明器一经产生便迅速发展。西汉时期作为等级象征的标志主要凸显在丧礼制度、墓葬规模与形制大小、随葬器物的材质及其组合、随葬品的数量及质量等方面,同时随葬品各类明器品类增加。两汉时期墓葬的随葬品,“改变随葬的表现形式,贯穿等级关系,广泛使用明器,充分反映死者生前面貌,达到‘生死始终若一’的目的”[73]。各阶层墓葬中随葬车马明器,及高等级墓中以车马明器代替真实车马盛行,体现出车马随葬内容追求明器化;大量的人俑、车马明器以及其它禽畜模型、日常生活用品模型明器等以象征拥有大量财富。
(三)立法禁止
立法禁止是真实车马殉葬使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竟宁元年(公元前33 年)六月乙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初即帝位的汉武帝“奏可”。及至永始四年召言:“车服、嫁娶、埋葬过制”[74]。《太平御览·班彪上事》云:“吏民葬埋,有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以法禁之”。从目前汉墓中真实车马随葬情况来看,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有效的抑制了真实车马随葬,尤其是于高等级的诸侯王墓中较为明显。西汉中晚期之后,诸侯王墓中使用真车马陪葬走向衰落,此后墓葬之中真实车马陪葬少见,象征性车马陪葬较多[75]。西汉早期列侯级别仅见周勃、周亚夫墓,安徽六安西汉贵族墓,以及海昏侯墓中设有车马坑或真实车马随葬。西汉晚期及其以后基本不见真实车马陪葬,车马明器随葬代之成为主流。
五、结语
两汉车马明器随葬是继承秦及商周时期车马埋葬内容而有所发展,高等级墓葬中车马存在形式不同,功用可能有所差别,而真实车马与车马明器的组合具有等级特征。西汉早中期墓葬中随葬车马器器类丰富,随后又趋向简化,东汉时期逐渐减少并普遍明器化。车马明器中,尤其是车马器,成为较多中高级墓葬随葬品内容的组成部分。动物模型明器随葬的流行使单独的泥制或陶质的马更具普遍化;画像墓中车马图像又为车马在墓葬中存在形式增加新的内容。
总之,两汉墓葬在继承前代一些葬俗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丧葬观念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墓葬中随葬之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更具有丧葬特点。因此,车马明器代替真实车马存在于墓葬之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汉墓随葬品的特点为现实中大型者“微缩”、繁杂者“简化”,形式简化但总体内涵丰富,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及生活产品的复制亦更加满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目的。模型明器是汉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制”随葬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模型明器的存在。东汉时期模型明器繁盛,专门用于服务丧葬系统而存在,是丧葬文化发展的一大特点,奠定了此后中国丧葬文化随葬系统内涵的基调。
[1]蔡永华.试论明器在丧葬中的作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
[2]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C]//古代文明(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80.
[3]主要代表有:a.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J].文物,1992(2).b.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J].考古,2002(1).c.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J].考古学报,2006(4).d.高崇文.再论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J].考古,2008(11).e.刘尊志,赵海洲.试析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J].江汉考古,2005(3).f.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陪葬车马及相关问题探讨[J].华夏考古,2013(4).g.赵海洲.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7.
[5]a.王学理.西汉阳陵陵园考古有重大发现[J].考古与文物,1991(12).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J].文物,1992(4).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J].文物,1994(6).d.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M].重庆出版社,2001:3,9-12.
[6]a.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9.b.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J].文物,1982(2).
[7]刘卫鹏.西汉帝陵的陪葬坑[C]//秦汉研究(第4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152.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J].考古,1984(10).
[9]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J].考古学报,1985(2).
[10]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7(3).
[11] a.崔大庸.洛庄汉墓的陪葬坑和祭祀坑[J].寻根,2001(3).b.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8).
[12]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5).
[13]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3(4).
[14]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J].考古,1994(2).
[15] 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的发掘[C]//考古学集刊(第12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6] a.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博物院.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J].考古,1998(8).b.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8).
[17] 徐州博物馆.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2010(1).
[18] a.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J].考古学报,1985(1).b.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J].考古学报,1985(3).c.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J].考古,1997(2).
[19] a.李琳,甘晓妹.驮篮山汉墓惊现神秘陪葬坑.彭城晚报[N].2004―4―9,2-3.b.赵海洲.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表二.
[20]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8).
[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鹿泉市北新城汉墓M2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08(4).
[24]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50.
[25] a.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获鹿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获鹿高庄出土西汉常山国文物[J].考古,1994(4).b.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高庄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6]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 3 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3(11).
[27] 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J].华夏考古,1992(3).b.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9] 江苏省大青墩汉墓联合考古队.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J].东南文化,2003(4).
[3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六安市文物局.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C]//文物研究(第1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07-123.
[31]同[7].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64.
[33] 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10).
[34] a.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J].考古学报,1987(4).b.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市烟袋山西汉车马陪葬坑发掘简报[J].考古,2017(11).
[35] 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J].南方文物,2016(3).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5).
[37]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12).
[38]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18.
[39] 济南市博物馆.试谈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饮陶俑[J].文物,1972(5).
[4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34-435,717.
[4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J].文物,1979(5).
[42]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18.
[43]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J].考古学报,1974(2).
[44]同[40]:434-435.
[45]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安铁路复线九里山考古队.老河口九里山秦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43-247,333-339.
[46]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一中战国秦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68,203。
[4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萍乡市莲花县文物办.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70.
[4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22-323.
[49] 刘卫鹏.咸阳师院科技苑西汉墓葬的发掘和收获[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5).
[5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局.巢湖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45-146.
[5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25-526.
[52] a.张勇.明器起源及相关问题探讨[J].华夏考古,2002(3).b.何毓灵.殷墟墓葬随葬品冥器化现象分析[C]// 三代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75-382.c.郜向平.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J].考古与文物,2010(1):45.
[53] a.《礼记·檀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郑玄注:“言与明器同。”孔颖达疏:“孔子谓夏家为明器者,知死丧之道鄢。”b.李自智.殷商两周的车马殉葬[C]//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226.
[54] 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2.
[55]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212-214.
[56]同[54]:175.
[57]同[55]:262-266.
[58] 同[53]b:240.
[59] 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J].考古,2003(11).
[60] 范晔.后汉书:舆服志[M].中华书局,1965:3639-3659.
[61]同[3]a.
[62]同[3]g:143.
[63]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象石墓[J].考古学报,1980(2).
[6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5).
[65] 韩国河,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秦汉[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258.
[66] 司马迁.史记:五宗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04.
[67] 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碳墓发掘报告[J].考古与文物,1990(4).
[68] 王玉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207.
[69]同[42]:111.
[70]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说[J].考古,1981(5):456.
[71] a.刘允东.中国古代的车马坑陪葬[J].文物世界,2008(6):44.b.刘振东.中国古代陵墓中的外藏椁[J].考古与文物,1999(4):77.
[72]同[7]:155.
[73] 蔡永华.略论西汉的随葬特征[J].考古与文物,1985(2).
[74]班固.汉书:成帝纪(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2.
[75] 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