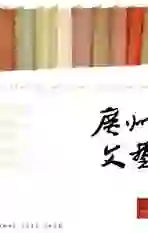丁酉年夏,过池上楼
2020-07-30池凌云
广州文艺 2020年7期
池凌云
南方的雨季刚过,
池上楼青瓦上的雨水也已干透,
砖缝里的青苔混淆了一个年代的
激情和冷漠,招徕过路的鸟儿,
那口著名的池塘隐藏在楼群中
散发淡淡的渴望,但少有人凑近细看。
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登池上楼,
曾有的几次都是陪伴远道而来的友人
我们置身于飞檐之下,感受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荒寂,
然后匆匆下楼,到院子里
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想象一千五百多年前
蓄了长长美髯的康乐公
带着心爱的曲柄笠与谢公屐
伐木开路,登峰顶,寻溪涧
写千锤百炼的诗赋,
最终惟有自然美景做伴,少有知音。
有人说他“终身一我”,
这其中的悲伤,不知诗歌能否拯救。
与其委曲求全,不如择一处绝壁
交谈。回想一个无法保全生命的
诗人的命运,头发不免黏湿。
但毕竟太久远了
他临终写下“斯痛久已忍”的圖景
我迟迟未能在脑海里补上,
还羡慕大自然给予他的补偿。
或许,落寞并不总是坏事,
适当的贬抑和受挫,
能换来另一种绽放。留给我们
浑浑噩噩的绚丽。
噢,那是多美的词语,在空气中
独自航行,我不得不构想
有一种所有色彩都得到平等喜爱的山水
存在于自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