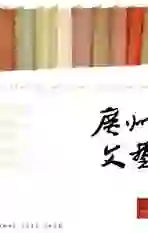荒草
2020-07-30宫敏捷
宫敏捷
丽萍告诉我们——女朋友和我:“你们看到凤凰加油站就下车,往前走五十米,有一个公交站,也叫凤凰加油站,我就在站台上等你们。”挂了电话,我们在广州流花汽车站,登上开往深圳的班车;一路摇晃着,差不多凌晨一点,下了广深高速,来到深圳關外的福永镇。
车上的人,都是像我们一样的南下人群。从家乡出发,不知转多少趟车,几经颠簸,累得像坨屎摊在座位上,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或者是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谁知道呢,离家那么远,城市那么大,车门一开,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没一个人能料想得到;只能屏声敛息,以不变,应万变。
107国道上没有路灯,黑漆漆的,大巴车幽灵一样行驶着。我们的老家,十里八乡才能看得到一个油站。按我的理解,一个福永镇,有一个加油站足够了,这个加油站,必定就是丽萍所说的凤凰加油站;所以我才会晃眼看到车窗外的黑暗中,浮现出“加油站”三个字时,激动地朝司机大喊,“下车,下车。”司机一脚刹车,把我们丢在路边。抬头一看,错了,是机场加油站,心里立马就慌了。
“你他妈有病啊?”女朋友说。
她不是真心要骂我,四周黑黢黢的,她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们并不清楚凤凰加油站在几公里之外,途经那儿的车辆,107国道上络绎不绝,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身后,机场加油站后面,一座小山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前面,宝安机场不停有飞机在起落,发出轰鸣声,还有一闪一闪的蓝光。从西南的小县城突然来到这样的地方,犹如进入到梦境。
我们在路边,黑暗中,相互沉默,又等了快半个钟,才来一辆大巴,将我们带到目的地。丽萍把我安排到五元店住,女朋友呢,对了,她的名字叫梅子,和丽萍是小学同学,被丽萍带到她们宿舍去了。其实没这必要,梅子我们很早就睡过了,丽萍不知道,我们又不好意思说。
第二天,丽萍请一天假,带我们找工作。她俩一早来五元店叫我,我在水龙头下接点水,捋顺乱糟糟的头发,跑下楼跟她们汇合。深圳是一个轻工业城市,女工需求大,梅子几乎刚转过一个街角,就被一家叫“中原”的丝印厂聘用了。跟她一起面试的,二十几个女孩,半小时不到,再出厂门,她们就都穿上有着蓝色条纹的短袖工作服,胸前挂着厂牌。工服又薄又透,能从外面看到每一个人文胸的颜色和胸部的轮廓。我偷偷告诉梅子,会不会太透了。她回我说:
“怕什么,人家不都一样穿。”
似乎只要是女工,不管胖瘦美丑,都会有一家工厂的大门向她敞开着。男工就得另当别论,没个一技之长,就会被人挑挑拣拣。除非招高端人才,工厂都懒得去人才市场。需要什么人,告示往门卫室的玻璃窗或外墙一贴,不出半小时,就会被务工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从初中生到大学生,一抓一大把。
当然,我找不到工作,跟这些都没半点关系,是我的身份证出了问题。它是临时的,只有三个月有效期,人事人员接过去一看,连大门都不会让我进,就一句话,“我们不招只有临时身份的人。”最为成功的一次,是一周之后——丽萍和梅子要上班,只有晚上不加班,才会有空出来见一下我,陪我在路边小卖部门前坐着喝一瓶汽水,五毛钱一瓶的可乐。梅子乐呵呵的,沉浸在有了工作的兴奋中,感觉不到累。只有听我说到找工作的艰辛,脸上才会浮现失落的表情——在凤凰工业区对面的新田工业区,我一再向人事小姐承诺,不出半年,就能把正式身份证拿来;她这才让我通过初试,放我进入人事部办公室填写《求职表》。随后,我们一起求职的差不多五十余人,来到工厂大门前的院坝里,站成一排,等待人事经理检阅。
他手里拿着我们填写好的《求职表》及身份证复印件,叫到谁,谁向前一步,接受他的各种询问。这是道流程,他至多是看看长相什么的,更多是显示他人事经理的权威;尤其当他说到如何严肃规章制度时。但叫到我名字时,他并不要求我向前一步,而是说:
“你,出去,”随即侧身对一旁的人事小姐说,“怎么搞的,你?这样的人也放进来。”
我唯一的选择,只能回家。
身上的钱差不多用光了,买上回家的车票,只剩下五十元。工业区里,有去六盘水的大巴。五十块钱,除去转车费,刚好够解决路上的温饱问题。梅子一个人来送我,也是在晚上。发车前,我们找了个僻静的角落拥抱和接吻,她哭得稀里哗啦的,还说:
“回去赶紧办证,我等你回来。”
梅子个不高,模样也不漂亮,圆圆的脸上还有细密的斑点。她沉静的性情中,又自有一种直指人心的灵性,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你,疼你,关心你,也死死地钩住你。
办证时间只需三个月,我再次回到深圳,却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只需六天时间;半年,得发生多少事情。
家里给了我回深圳的路费,打麻将输了,想再赢回来,却输进去更多,五六百吧。半年里,我都被这事困扰着——后来,向一个在菜市场杀鸡卖的同学求助,才得以解决——写给梅子的信中,我只字不提。我给她写了很多信,告诉她,我们那帮子高考落榜的同学,每天都是怎么瞎混的。
学生的身份剔除了,世界就会是另一个模样。家人会让你做这个,那个,做不好就得劈头盖脸骂你。旁人呢,每一个认识的,差不多都会为你操心,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逼迫你去思考各种问题。为了避开他们,我们早出晚归,白天在县城四周的山里钻山洞,爬树。我说的是我的同学们,钻山洞是为了进到里面跟女朋友亲热,爬树一般是为了吃上各种野果。到了晚上,我们把各自的女朋友送回到她们父母身边;一帮男生,会找地方躲起来,喝酒,打牌,唱郑智化的《水手》热望未来,也用他的《麻花辫子》发泄情绪。当一城的人都已入睡,我们还留在街上摔啤酒瓶子,听碎玻璃片在水泥路面上滑行时的“叮叮”声。
“哦……吼……”我们拖长强调,向着夜空发声。
我在信中告诉梅子,如果她在家,我们的日子差不离也是这样的;而这样的日子,我和我的这帮同学,高一时就开始过上了。我们这山里小城的世界,跟梅子置身的深圳,根本不在一个空间,从来都是这样。我们这个空间,你可以通过瞎混过完一辈子,深圳却不一样。我一周会给梅子写一封信,还偷偷去到建设西路76号观察她家人的生活,然后把各种细节告诉她。她从不回的我信,除了那一次。那一次,我告诉她,她妈妈得痔疮,住院了。她爸爸喝得烂醉,往医院送饭,在路上摔了个狗啃泥。
“我太忙了,忙得都没了时间去写信。”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没告诉梅子我的回归。
我到深圳的时间正好是大中午。
太阳明晃晃地烘烤着南粤大地,什么也不用做,光站着,也会大汗淋漓,再多站一会儿,就晕了;热气从身体有窟窿眼的地方,还有脚底板,灌进人身体里。大巴车直接把我放在凤凰加油站公交站。我爬上加油站后面那个缓坡,进入到工业区,在一家小卖部买了一瓶汽水喝下去。休息够了,这才用公用电话打给梅子,告诉她,我已经到深圳了。电话打到他们部门的办公室,让她的同事转告坐在流水线上的她。过了一阵子,她的同事再打回来,告诉我她说了什么。
“她说,”她的同事说,“她让我先骂你一句。”
“骂什么?”我还没搞明白情况。
“他妈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就来了。”她的同事说。随即又说:“这是她的原话。”
“还说了什么?”我说。
“她要你一边待着去,她晚上还得加班,晚上九点以后才能出来见你。”
我看了看表,要见到她,还得等上九个小时。我想把行李放到五元店去,立即着手找工作,却又怕丢了。那里面,南来北往的人进进出出,随手见到什么拿什么,一点也不跟你客气。这么想着,我放弃找工作的打算,又买一瓶汽水提着,在小卖部后面找一条小路,弯弯曲曲走到凤凰加油站后面一块开阔的空地里。空地杂草丛生,被加油站和油站边上的废品收购站隔着,在国道上根本看不着。
杂草这里压倒一片,那里压倒一片,像一个漩涡,连着又一个漩涡。草丛中,除了啤酒瓶和汽水瓶,更多是使用过的避孕套和揉成团的纸巾。可以想见,这片草地上,这片热土里,每天晚上,会有多少工业区里不加班的男男女女跑进来,在肉体的挤压、摩擦中,发出卑微的呻吟。杂草中除了垃圾,还能找到卷好藏于某处的凉席和衣物;是找不到工作,又没地方住的人藏下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去动这些东西,山南海北汇集起来的人民,在这一点上,有着朴素又动人的情怀。
我展开某一个人的席子,在阴凉处,用行李枕着,美美睡了一觉。睡着之前,我还预想了一下,半年不见,我和梅子的见面,该是如何感人的一个场景。我甚至想着,如果她是一个人来,我们还会在她回厂之前,再次来到这片草地,一解相思之情。不过,现实却不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九点半,我准时出现在中午打电话的地方。中午梅子交代,她会到那儿来找我。还没到时间,就看到他们三个人,丽萍、梅子,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高大的男子;男子走在他们两人中间,三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穿过人流,朝我走来。见到我了,梅子脸上的表情马上僵住,冷冷地说:
“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说不说,不都一样要来。”我看着她,想笑,没笑出来。
他们三人都穿着工服,看着有些傻气,但整洁,干净,有着一种来到世间走一遭,对许多我尚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情熟稔于心的气度。与之相比,我猥琐很多,浑身酸臭,衣衫邋遢,还滚了一身的草。思及这些,不免心生悲凉,再想到一个你所爱的人能给你这样的感觉,又凉下去半寸。
男女之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心如水一样,丢一个眼神进入,能看到涟漪,能知深浅,还能明辨水质的好坏。梅子可以带丽萍来接我,但还多带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老乡,我们厂的。”她这样给我介绍那个男子,却不告诉对方我是谁。我在一瞬间就把心放下了,就是不管不问、面对且接受一切的意思。家在几千公里以外,隔着一百八十多个日子,我得允许什么事情都能发生。
“你吃饭了没有?”丽萍问我。
“没有,”我说,“不饿。”
“那你先去旅店休息吧,休息好了,明天好找工作。”梅子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提着行李,跟在他们三人身后去到五元店里。他们只是在楼下看着我,我才开始爬楼梯,他们就离开了。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人流中。工业区里灯火辉煌,每一条道路,都挤满了穿着各种颜色工服、胸前戴着各种工厂标志的年轻人。站那么一小会儿,就能把各种方言听个遍。方言千奇百怪,与道路边上的工厂车间里,发出来的机器轰鸣声混杂在一起,成就一个超于巴别塔的神迹。我刚想转身进屋休息,又听到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低头看,是丽萍。她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子,袋子里鼓鼓囊囊的。
“我给你打包了个炒粉,还带了两个苹果。”她说。
我下楼去接过食品,向她真诚地道谢。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就站住不动,微笑着看着她。她又说:“别怪梅子,她耍小孩子脾气吧。”
“我知道。”我说。
丽萍说:“那你休息吧,我回厂了。”
“我想你帮我保管一下行李,”我赶忙说,“我找到工作了,再来拿。”
“好啊。”丽萍笑出了颗小虎牙来。
我上楼去到阳台上取下行李交给她。
看着丽萍再次走开,我真想叫住她,告诉她,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爱上她了。她很瘦小,脸上颧骨过高,按我们家里的传统说法,叫寡妇相。她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取下眼镜来,就是个瞎子。她的马尾辫,黄黄的,也不怎么讨人喜欢。可那一刻,她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这抵御了我心里不断积累起来的一些寒气。
我睡在五元店的床上,在一群陌生人的鼾声中想,她耍的是什么“小孩子脾气”呢;或许,她只是被這个花花世界迷住了。年轻好儿女都跑这儿来了,不管是生活还是爱情,她都有了无尽的选择性;或许,再过上几个月,我也会变得跟她这个样子。
第二天,找工作前,我去到梅子他们厂门前,想再看看她。很多时候,你去看某某人,就是去看看而已,跟你要看的人,可没什么关系,我那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我去看梅子,就是想在她身上发现某种变化,可以把之前和之后的她拼接成同一个人的变化;然后把自己的心气捋顺,继续过今后的日子。梅子知道我会来,她是我的恋人,依然停留在我心里最为柔软的地方。我们隔着她们工厂的大铁门说话。我赶过来时,她坐在厂门前的院坝里(这里也是他们厂的露天餐厅),跟昨晚见到的那个男子及许多同事一起,吃早餐。
“对不起,”梅子说,“我最近心情不好。”
我正要说话,她又说:“你不要问,什么都不要问,安心找工作吧。”
我点点头,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看着她。她比以前瘦很多,脸上的雀斑也更多了,也比以前黑,再就是,眼神没以前那么透亮了。以前,我可以在她的眼里看到我自己,我的身影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轮廓,是她眼里唯一的东西。而今,轮廓依然清晰,却被许多我不明白的东西缠绕着,我得去寻找,也不一定能分辨出自己来。我转身走开时,听见她在身后说:
“你的工作稳定了就来找我,这段时间我们赶货,天天加班,一点时间都没有。”
我回身,对她点了点头。
我认识一个男子,叫管勇,是我在深圳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他也是我的老乡。他很高大,近似驼背,眼睛和头发都黄黄的。他的眼角时常会有白白的眼屎,看着邋遢,这也是女孩子不怎么喜欢他的原因。
一家五金厂招搬运工,人事小姐懒得出来,让门卫把第一关。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门卫都先问一句:“你会说白话吗?”
“不会说白话的不要,”他问我时,眼睛冷冷看着我,并不接我递过去的身份证。又说:“你会说白话吗?”
对这个问题,我有些犹豫,不知道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按我们老家的说法,白话就是谎话,而说谎话的,都是骗子。保险起见,我回问他:“什么是白话?”
门卫不回答我,直接说:“下一个。”
“白話就是广东话的意思。”一个声音在身后告诉我,说话的就是管勇,回头看着他时,他顺溜着又说了一大堆。告诉我,很多工厂是香港人开的,香港人不会说普通话,为方便交流和管理,只得招会说白话的内地人。他还说,他看到我的身份证了,知道我们是来自一个地方的。我马上兴奋起来,阴霾散尽,有一种找到组织找到家的感觉。通过交流,管勇告诉我,他来深圳一年多了,一直在工地上干。工地太辛苦了,想在工厂里找一份不晒太阳不淋雨的工作,都已在周边几个工业区转半个月了。最后他告诉我,男孩子不好找,东华工业区那边,有一家东华电子厂,人事经理是我们老乡,可以随时进厂,但一人得一百元的介绍费。幸好,我身上仅存着两百元大钞,我们立即赶过去,交钱,办手续,一气呵成。再分头,他回工地,我去找丽萍,拿上各自的行李,当晚住进了东华电子厂的员工宿舍。我把东华厂的地址告诉丽萍,让她得空了就过去玩。
“好的。”她说。
丽萍站在他们厂门前,一直看着我走远。灯火阑珊,相看着,都影影绰绰的。
我们两个厂之间,至少隔着五里路,七八个工业区。
我和管勇在同一个车间,管勇分在包装部打包装,将成品运送到仓库去存放,坐着电梯,拉着拖车,楼上楼下地跑。我在制造部,不坐流水线,做杂工,香港人叫“什工”;负责用滑轮车从洗手间拉来清水,清洗整个车间里,用来存放半成品的天蓝色塑料箱子。箱子在流水线尾部堆放得整整齐齐,哪个流程的工人需要箱子了,招一招手,我赶忙给他送一个去。
我们的工作相对自由,也可以到处走动。流水线的人不一样,动作慢一点,制品就会堵塞,不会有人来给你帮忙,各自的任务,加班加点都得自己解决。上个厕所,也得等拉长有空了,给你顶着,才能走开。许多人干一整天,连个直着腰杆缓口气的时间都没。机器是冰冷的,人是麻木的,说起话来,似乎都很熟络,大部分都有着老乡圈子,但除非是亲人,不然,不会有人真心去关心一下你。
自己也上班,对流水线工作有了深切的认识后,我开始从梅子的角度,思考她的生活;尤其我离开的半年里,是什么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我没去找过梅子,她也没来找过我。我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重复前一天:早上七点起床上班,午饭后在工业区绿化带草皮上躺下休息半小时,又接着上班;晚饭后,还是在工业区的绿化带草皮上躺下休息半小时,又接着加班。每天睡下时,差不多也是午夜。如此往返,什么爱情啊,理想啊,全都是见鬼的东西,一点也不重要。
一个叫秋针的女孩,江西人,时常会过来找我说几句话。她在包装部做库存统计,也是可以楼上楼下到处跑的人,管勇介绍我们认识的。得空了,她就跑过来,跟我瞎聊。我得空了,也会过去跟她说话。更多的时候,她站在一旁,呆呆看着我。父亲是中学老师,会写毛笔字,过大年或哪家有红白喜事了,会找他写对联。平时手痒了,他就用废报纸练笔。没事,我也跟着他瞎比画一番。时间长了,成了一种习惯。秋针喜欢看我用指头当毛笔,蘸水在地板上写字。
有一天,她告诉我,昨晚她梦到我了。我写了很多她喜欢的字,要我送一副给她,我没给,还把写好的字全丢垃圾桶里。于是,她在梦里哭起来,醒过来,眼角还有泪痕。我想,她是喜欢上我了。在深圳,爱情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你都不用去考虑什么,跟着生活的节奏走就行。
我小心翼翼地跟秋针说话,把握着分寸,不能让她感受到,我也喜欢上她了。我是说,我还没有喜欢上她,不能给她错觉,至于以后,谁知道呢。看着她的时候,我想着的是梅子,我觉得,我和秋针之间的状态,或许就跟梅子和那个年轻男子一样,只是她走得比我要远一些。秋针皮肤很白,剪齐耳的短发,爱笑,一笑就有小酒窝。你什么时候看着她,她都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就是眼睛太小,嘴也太小。
大家熟络后,秋针就加入我们的行列,午、晚餐后,一起去到工业区的草皮上休息,慢慢吃着零食;其实是锅巴,管勇悄悄从饭堂的灶台上捡来的。黄铮铮的,嘎嘣脆。在之前,我们一般大大咧咧地躺着,让体力尽快恢复,养精蓄锐,应付晚上的加班。她加入后,就只能正儿八经地坐着聊天了,零食也是不能吃的。说各自家乡的事情,说各自都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有时她还会唱歌给我们听,她唱田震的《野花》和周华健的《风雨无阻》,管勇喜欢的是王杰的《心痛》,可惜,他还没经历过自己的爱情,唱不出那种味道。晚上不加班的夜晚,秋针还会买水果提着,来我们宿舍;话说是,要看我用手指头写字,但我在宿舍里只会看书,或听收音机;《夜空不寂寞》的节目里,主持人会读这样那样的听众来信,讲述的,也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她每次来,都坐我的床上,这意思,连管勇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