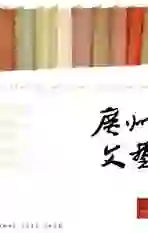圈
2020-07-30罗铮
罗铮
一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十一个,二十二个。二十二个!四岁的儿子重复了一句,笑容灿烂。从家里的阳台居然能看到这么多塔吊,真是一件兴奋的事。我只好挤出一丝微笑,算是对他数数精准的肯定。然而,内心依然忧虑忡忡。
起初,我也沉浸在乔迁的喜悦之中。海拔高了,离阳光更近了。可每当试图极目远眺,几个粗犷的钢筋水泥结构横亘于前,一扇扇窗户威风凛凛,组成一个庞大的扇形,压迫眼球,把天空割得四分五裂。这些由钢筋、水泥、瓷砖、工程管道、人造板、气味各异的油漆拼凑而成的巨大空间,硬生生从大自然的身体里割取出来,像一个个钢筋水泥的火柴盒子。它以这样的方式把人圈在里面,密不透风。除了散佚的灯光。这些人本来天各一方,只是因为一个金属结构成为邻居,咫尺天涯。
前几天,雪终于姗姗来迟。南昌城的冬日,总是给人一种即将落雪的假象,又每每失约。所幸,今年有了冻雨。饱满的颗粒砸在窗户上,响亮,自信。在这股强大的寒潮催化下,雪总算来了。路面,悄然铺上一层坚白的冰层。屋檐下,路灯外壳下,粗壮的树枝上,乃至挖土机的顶端,结满闪亮的冰凌,错落有致。城中迅速燃起一种罕见的冰冻美学。只是,人们纷纷紧闭门窗,猫进各自的金属盒子里。堆雪人、打雪仗的欲望,似乎也降至冰点。若是早些年,随便喊一嗓子,小伙伴们便蜂拥而至。不过也对,那时都是家属院,彼此熟稔,阳台也是敞怀的,雪花可以随性飘落。当然更关键的是,人们的内心几乎是不设防的。如今,气候变暖了,可人心呢?
仅仅待在金属盒子里,似乎并不能完全放心。铝合金窗早已成为标配,房门越发沉重,密码锁、指纹锁大行其道。好不容易出一趟门,总能在小区偶遇各色人等。西装革履的绅士,浓妆艳抹的白领,双手各拎一个打包袋的快递小哥,遛狗的全职太太,彼此眼神充满警惕。乃至进电梯时,都不愿先伸手,生怕暴露自己的楼层。人们正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圈起来,封闭在厚实的金属框架里,越圈越紧。海拔越升越高,身体和心灵都飘在空中,如何能感知地气?更可怕的是,这种远离地面的悬空,并未让大多数人觉得恐慌,而是趋之若鹜,无暇,确切地說是不屑,思考与大地和泥土的关系,麻木得令人恐慌。
从金属结构残留的角度里,二十二个塔吊正在张牙舞爪。它们的海拔随着空间的远离不断升高,“野心”昭然若揭。它们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圈里,围出一个个小圈。未来,还将有多少居民从四面八方汇入?还将有多少个新楼盘,上演争先恐后、摩肩接踵的壮观?无论是老城的置换者,还是乡村的迁入者,都将欣然接受被塞进金属盒子的命运,并以此为荣。
前日,翻看清朝时期南昌城的《三湖九津图》,我原先居住的三经五纬,竟只是西北角城墙边的一块荒地。可自打我记事起,三经五纬就是全城当仁不让的中心。近几年,又被广袤的新区取代。城市扩张的速度实在太快。若干年后,这个大圈必定还要继续延伸,再用成群的塔吊搭建更多的小圈,圈进越来越多的人。斯蒂文森曾说,人须有冬天的心境,才能看霜、看雪。是否可以说,人须有城市的心境,才能看圈、看人?
二
停下车。眼前的大楼庞然矗立。墙,粗壮,白得有些耀眼。二舅探出头,露出古稀老人的皱纹。跨入大门,瞬间袭来一股凉意。七八十平方米的厅堂,五米多的层高。厨房,卫生间,卧室,阳台,空间富余得可怕。除了一根晾衣竿悠闲搭在窗台边,三楼的区域充分闲置。天台极度舒展,几进邻家院落。眼前的村庄,钢筋水泥一望无垠。
这是我的家乡吗?乡邻们为何对高楼趋之若鹜?二十年前,两层的房子都难得一见,田野开阔,足够孩子们疯跑。可现今,村民对于空间的热爱似乎丧失了理智,原先谨小慎微的长宽高,放大成一个个不受约束的数字。容积率,采光,美观,搭配,在村里完全失效。乡村不是在城镇化吗?在城里,类似架构的商品房必定滞销严重。二舅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在外面,留下的独苗还在老屋翻修了新房,这些空间用途何在?
日头像一枚亮堂的银币,把阳光抹在鳞次栉比的屋顶上。三舅家的房子也翻新了,偌大的厅堂只有一组沙发,几组柜子,一个电视机和几张桌椅,空旷,甚至浪费。每层格局大致相同,老两口和两个儿子各占一层。小表哥还在哭穷。算了吧,这都可以当地主了。表妹怼得他哑火无言。
见母亲他们聊得火热,我出门走走。其实,小表哥或许并没骗人,做点小生意,打打零工,能挣多少钱。一层房子又不能卖,更何况小洋楼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终于拐进主干道——龙布镇唯一的主干道。每逢农历二、五、八,四面八方的商贩和农民挑着竹筐竹篓簇拥而来。于是,一个铺着鸡蛋、豆角、花生、鱼干,各类新鲜水果的集市形成了。天蒙蒙亮,吆喝声,还价声,交谈声,让龙布镇的分贝蹿升。每隔三天,就是一场感官的盛宴。可眼前的主干道,人迹稀疏,偶尔三两孩童或老妪闪现。T形辅路上,一字排开的石桌们不知所终,只见一个个用砖砌起的圆形结构,堆放着扫帚、抹布、麻袋、麻绳等物什,歪七倒八。人们的维权意识真是越来越强,连扫帚这类再平常不过的工具,都要专门圈个地方保护起来。噢,或许在意的并不是扫帚,而是地。就像一幢幢小洋楼。怎样宣示主权?除了用砖围起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围得越大越好,最好一丁点不浪费。
曾经浑然一体的乡村,正在被一个个“圈”割裂。人们执着于最大限度圈住土地,好像只有用砖砌得严严实实,才能确定为己所有。可同样被圈住的,还有人的内心。以往几乎路不拾遗,有时去街坊邻居家拿个东西,房门随意一带,忘了也就忘了。现在,铁门越做越高,有的还摆上两个石狮子,宫殿般气派。人和人之间,被密闭的空间隔开。乡村的生机和活力,也被圈得寥寥无几。偶尔邂逅的几个年轻人,脸上写满孤独、焦虑和紧张。孤独、焦虑、紧张,不是城市的特性吗?可为什么出现在乡下?难道在与城市相向而行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某些“恶习”?尽管我不愿相信答案,但如果不焦虑,不紧张,为何要把自己圈起来?
这会不会只是乡村走向城市的一股阵痛?我不得而知。主干道的尽头,是大舅的房子。果然不出意外,原先的老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崭新的三层洋楼,依坡而建,南北通透。二表哥的房子比邻而立。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二、五、八的集市上,肉,安放在哪儿?
三
长时间的雨季,人越发意兴阑珊。约定的菊花展,推而复推。好不容易放晴,一盆盆菊花涌现在广场,迫不及待。人,男女老少,摩肩接踵。并不宽敞的广场,顿时像一个下满饺子的蒸锅。
五颜六色的菊花从各地被征调,像是共赴一个约定。有的悬于梁上,有的嵌入铁架,有的坐在地上。白燕漫风,碧玉银凤,嫦娥奔月,仙露蟠桃,光名字就是一场盛宴。它们是心甘情愿的吗?恐怕未必。原本它们可能生长于大山,每日沐浴纯净的阳光,聆听溪水潺潺,无忧无虑。
它们是大自然的宠儿,却被外力强拉至一片几亩大的草坪,供一个个饥渴的眼神打量。它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阵势,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仿佛突然间全冒了出来。他们渴望进入这个被花围成的圈。站在圈内,尽管一股凶猛的窒息感袭来,但每张脸上都笑靥如花。赏花也成了一种奢侈。看花,还是看人?
渐渐地,机器成为城市的主旋律。层出不穷的机器抢占了大量的私人空间,人的生活每天被各种机器瓜分肢解。电脑,空调,电视机,iPad,iPhone,机器拥有的数量与质量成为生活水平的关键象征,人与机器相对的时间远远超过人们的面对面。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些新奇的机器登录生活。人与机器之间的智能界限愈加模糊。时间一长,或许人类本身都将被机器同化。
不过,一听到大规模菊花进入城市的消息,人们对于大自然的灵敏度貌似即刻恢复。他们从城中城郊专程赶来,是多么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呀,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菊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虔诚。花展总算暂时证伪了机器的万能。伟大的软件足以遥控卫星火箭,操纵飞机潜艇,但无法管住生命的本源舒展与审美情趣。菊花的种类与名称?如何摆放以优化审美?孩童的笑与成人的笑,男人的笑与女人的笑,背后隐藏着何种机缘?机器只能哑口无言。
尽管如此,人们刚从花展返回,转身又投入到机器的享受之中,接受机器核准的生活,甚至钻研机器的更新换代,似乎真要把机器变成统治世界的万能之手。一边沉浸于机器衍生的快感,对大自然不屑一顾,一边又把最平常的花草奉若掌上明珠,应当怎样理解这对矛盾的做法?或许只顾埋头赶路的人们,偶尔也会想起丢失已久的诗和远方,希冀一点心灵的慰藉,但根本无法停止近乎疯狂的脚步。一场菊花展,又怎能担此重任?
四
一个球,从发射器里喷射而出,砸在某个形状上。正方形,三角形,圆形。正的,倒的,斜的。里面装着数字。砸一下,形状抖一抖,数字也随之递减。直到减到零,形状一并消失。难度系数水涨船高,形状消灭越多,分数越高。直到某个形状升至顶端,游戏结束。
它有一个朴素而优雅的名字——最强弹一弹。精准诠释了它的内涵,弹。腾空,折射,自由落体,都是弹的结果。对了,它还有一个前缀词——天生就带着比拼的意味。时光,在一弹一弹间川流。
前不久,一款名为“跳一跳”的游戏横空出世,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每部手机。一个国际象棋小卒,在各種方块和圆柱体之间跳来跳去,几乎没有技术含量。手指的力度是唯一的技巧。可人们照样趋之若鹜,一有空便试试手气。你多少分,成了最时髦的话题。每周的排行榜上,总会出现几千分的“大神”。今年春节,夜幕笼罩下的乡村,“跳一跳”成了孩子们的主旋律。五岁的侄子挑落各路好手,荣膺冠军,惊艳众人。没几个月,在“跳一跳”被审美疲劳击退时,“弹一弹”应运而生。人,和他的眼睛、大脑、手指、神经系统,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无法自拔。这真的是放松吗?
前不久,网上流传一段视频。一条游轮,栏杆边拥着一群人,一名身穿豹纹上衣的女子情绪激动,哭天抢地,几次想越过栏杆跳下水去,幸被两名女子紧紧拽住。女主角似乎并不领情,让开,让开!视频长达一分多钟,豹纹女子一度濒临崩溃。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她的手机掉进了海里。至于这么激动吗?“我的孩子掉下去了!我的孩子……”噢,她竟与手机如此相依为命。
洱海的清静,被一部突如其来的手机划破。人的理智瞬间失常,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如今却并非个案。哪天自己没带手机,不也魂不守舍吗?手机悄然织起了一张网,日益繁密,把人们裹挟进来,进入一个既定的圈内。手机日益成为身体的一个器官。“低头族”已经不是某个群体的称谓,而是整个人类的代言。
地铁或公交车上,公寓楼的电梯里,机场、车站的大厅,医院候诊的走廊,单位食堂,“低头族”四处可见。尽管三令五申,可相当数量的驾驶员仍然接打电话,闷头看手机。斑马线上的行人同样不甘落后。是啊,网还在升级,扩容,买火车票飞机票,购物,交水电费,朋友圈里眼花缭乱,连现金都不用带了,怎么舍得放下呢?书被抛弃了,谁还有心情去看大部头的东西。朋友圈时常点个赞,却难得真正电话问候一二。家庭,学校,社会,逐渐被网一一瓦解。在网的圈笼下,人,彻底扭曲了。
迟早,“最强弹一弹”也会步“跳一跳”的后尘,变得门可罗雀。然而,心理学专家腾讯公司,必定又会设计出新的替代品。据说,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将实现wifi全覆盖。人们在手机与互联网的大圈里,只会越陷越深,越裹越紧。说不定哪一日,便完全沦落。
五
阳台上掠过两只小鸟。
这是十六楼,四周除了高楼,就是撕裂的天空。上次看到完整的天空,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向外望去,一层巨大的浅咖啡色油漆面,密集镶嵌着长条状的玻璃和乳白色的空调,像随时要倾倒过来。如果视角大致按一百二十度计算,这个油漆面至少占据了一半以上。剩余的几十度,依然是油漆面主打。白色,褐色,暗黄色,裹着烈日傲然耸立。唯一的纵深,塔吊们正在张牙舞爪,绿色的防护网密不透风。到了夜晚,像一群幽灵。小区的绿化显得孤立无援。
自打出了水痘,我成了重点照顾对象。由于病菌的传染性,我被牢牢圈在一百平米的金属盒子里。少用脑,好好休息。医生再三叮嘱。我只好减缓高速运转的大脑,静静看着,听着。只是一朝外看,不同种类的金属结构接二连三跃入眼帘,无法躲避。闭上眼,高架桥上的汽车呼啸而过。尽管隔着厚实的玻璃,每一辆的声音都清晰入耳。匆忙,焦躁。方向不明的电钻声劲头十足,仿佛随时会钻破某个墙面。钢筋的碰撞声时不时从某个工地传来。这是高速运转的声音,契合整座城市的节奏。我看不见麦穗在稻田里摇曳,听不见溪流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在离地五十多米的高空,我像被囚进一座空中楼阁,无所适从。两只小鸟,已经是上好的褒奖。
城市拥有一股前所未有的魔力。人们从各个村庄涌出,奔向一个叫做城市的目的地。写字楼灯火通明,深夜到家的白领第二天清早又是精神抖擞。无论白昼黑夜,都有人挥汗如雨。夜总会的女郎刚刚下班,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人就接茬上街。龙虾店、烧烤店的卷帘门才拉下,包子店、米粉店的锅炉迅疾开启。分秒必争,城市给所有居民上紧了发条。恨不得每天变出三十六个小时来。钱袋子越来越鼓,身板却越来越弱,猝死的新闻司空见惯。“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从容恬淡,恐怕只能封存在想象中了。
愣了好半天,我只好打开电脑。海量的网络信息扑面而来——高考状元出自哪所中学,世界杯哪支球队赢了,哪几个城市又开始“抢人大战”了,美国又和哪国开打贸易战了……手机铃声响了,一通电话过后,又把微信、QQ、手机报、新闻软件挨个点开。最后,万分纠结当中,还是戳了一下“最强弹一弹”,试试能否再创新纪录。时间任性地往前走,一不小心就超过刚才那些费力思考的用时。我又陷入了另外的圈。确切地说,我根本未曾离开。什么时候能跳脱出机器和网络织成的圈?手一抬,就是机器的领地。
关于这个庞大的世界,它是由若干碎片组成的。人,山水,花草,金属结构,机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网。但这些分散,独立,看似毫无关联的碎片,却拥有一种整体性,多元的整体性。它织起一个个圈,以独特的方式把经过筛选的零件装进去,形成一个个不被察觉的大型闭环。圈内秩序井然,相安无事。舒适,安逸,压抑,暴躁,都源自圈内释放的磁场。人们甚至感受不到边界,更无法跳出边界,只能顺着圈内的游戏规则行走。城市的圈,机器的圈,网络的圈,尽皆如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世界在圈与圈的交织中尽情舒展,阔步向前。世界并不是一元的,平面的,线性的,很多问题无法通过一元论解释清晰。当人们认定某种真相,也许只看到真相的一个切面。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人生的窥探,或许从一个个圈入手,能够获得一些新的切入点。每个圈,都是通往认知的窗口,至少,它是一种体察世界的方式,从这种方式出发,能够看到更丰富更宽广的事物。
我无法逃出这些圈。是的,我为什么要逃呢?我又能逃到哪儿呢?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