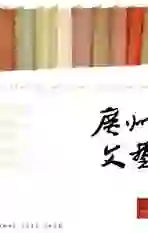贤士花园
2020-07-30李晓君
李晓君
琴声悠扬
每个周末,早上八点,我的楼上准会响起悠扬的钢琴声。至今,我没有与这位弹奏者谋面。只好在想象里,将她描述成一位长相不赖的女士。钢琴声时而如急促的瀑布倾泻而下,充满激情和力度,时而像草原上的微风,轻柔而悠长。每次弹奏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通常,这个时间我会赖在床上,直到睡意全无才起来。因为周末,是摆脱工作的时刻,睡一个踏实的懒觉,是对辛劳一周的奖赏。不知从哪天起,我的睡梦中出现了钢琴声,如雨点落下,也如阳光照耀。曲子是温暖的、悦耳的,我在半寐半醒、虚幻与真实之间醒来。聆听一支又一支曲子滑过耳际,熟悉又陌生。有些曲子似乎早有耳闻,有些则完全陌生。我在师范读书时,同学中有许多弹琴高手,那时的师范教育,注重人文艺术的全面培养,我将自己描述成整天在一种艺术的熏陶中并不为过。红墙碧树的琴房、妙曼的少女——那里似乎寄托着早年幼稚、朦胧的情感。我的懒觉是睡不成了,但我也不愿起来,便在床上,兀自“欣赏”这一段段乐曲。
这位弹奏者,只在每个周末上午时分,才那么真实地存在。琴声提示着她的身份——一个院校的音乐老师、青年(为什么是青年)艺术家、资深音乐爱好者?对音乐我不在行,我无从去判断这位女士(假如是)的艺术水准。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琴声优美、悦耳、温暖。在那些旋律中,我似乎聽出了人的喜怒哀乐,看到了群山大海、草原蓝天,也看到了潺潺流水、田园村舍,我感受到了春的芬芳秋的清凉,听到了奔流嘶吼和鸟鸣啾啾。我仿佛看到一双白皙、细嫩、修长的手,在黑白琴键上抚摸、舞蹈、跳跃,它们弹起、落下,有时像白鸽轻柔展翅,有时像鹰隼迅疾俯冲,我甚至看到了她的一头秀发垂泻而下,青丝勾勒出一张白皙、若有所思的脸。
她是我们小区众多住户中的一个。我与其中绝大部分无从交集,谈得上一无所知。我们唯一的共性便是栖居在同一片屋檐下。我们像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子民,但互不相识,也不交集。我们会去同一个农贸市场买菜,与熟悉不熟悉的商贩讨价还价。在同一个站台候车,脸上有着同样的冷静或焦灼。会去同一个湖边锻炼,或沿着玉带河漫步。我们不知互相的身份和姓名,这让我们轻松和心满意足。与我的童年不同,我的童年是在故乡县城长大,在街坊邻居的“亲情”中成长,在一个熟人社会,毫无秘密可言的人际网络中,开始形成对人和社会的认知。所有的温暖和羞耻都在其中获得,烙印般深刻。但现在,比如这个小区,我在其中居住五年与居住五天,是没有分别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会纵深展开,像一个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这是我们的幸事还是悲哀,无从知晓。时间会培养人的一种惯性,对他既有的生活方式加以固化和肯定,他处在这时间蛛网结成的茧中,慢慢变得惰性和麻木。他没有改变既有一切的勇气。
废名曾给鹤西写过一联:看得梅花忘却月,可怜人影不如香。很有意思的一副联,我是在格非写鹤西的一篇短文里见到。这是对人的状况一种生动的表达,顾此失彼、喜新厌旧、欢喜一场,只有经历了才会懂得其中的况味。废名笔下那个“莫须有先生”,好像没有随着时间而死去,还活在我们众人中间。我们从何而来、到何而去,为何来、为何去——说到底,别人是不关心的。我们在这世上留下点痕迹,譬如,我写过的那个制造点响动的借贷者,楼上的弹奏者,甚或我对他们的书写,也许被人看到、听到、读到,便烙印在他心里,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其实不是重要的。我们大部分人恐怕难以摆脱这样的命运——留下一鳞半爪的是幸运儿,更多的是灭影息身在人群中,如一滴水汇入大海,渺无踪迹可言。
我们都是梦中人,不愿醒来。这仿佛是无法质疑的。我们能够把握到的真实有限——当那些时刻我们悲欣交集,却又怀疑是在做梦。也许那睡梦边缘的琴声,会强化这一点,让人生出更多人生如梦的感慨。我闭着眼,却醒着,耳边流淌着倾泻而下的琴声,那天才之手谱写的旋律(他们想表达什么?),随着曲子深入,我目击到更多的场景、画面,我深入其中,徜徉、流连,久久不愿出来……但终有那一刻,琴声戛然而止,四周一片空旷。仿佛我听到的是梦中的乐曲。琴声逃遁得无影无踪,我兀自留在沙滩上,头顶是深邃的蓝,脚下是金色的月光。我躺在床上,又像躺在一艘空无一人的大船。
梦
我做了一个梦。我经常做梦,几乎每晚都有梦。我梦见在一个考场,面前支起一个画架,手忙脚乱地将画纸粘在板子上——老师分发了好几张纸给我,其中有一张是有编号的,但我看不清楚,几张纸上都已经被前面的使用者画满了(有水粉风景、素描人物),我花费了十来分钟都无法辨别,向监考老师提出疑问。他接过去瞄了两眼就把那张涂满颜料的纸给我。幸好这场考色彩,我带的水粉颜料可以将纸上的色彩覆盖掉。我小心地用夹子将纸固定在画板上,其实用透明胶带可能效果更好,于是去找胶带。我已经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来做准备,但似乎没有理出头绪来。我的隔壁考生——一个男孩,捂着嘴偷偷发笑。我听到老师焦急的声音,“先画起来”。是的,要先画起来。可是我的画笔找不到了,我在地上摸索,以便确定用哪一根来勾形,洗笔筒里的水污浊不堪,似乎只到了桶沿的三分之一处,我起身去装水。我记得考试时间是一个半小时,我掏出表来看,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我感到非常焦虑。起先我对这场考试蛮有把握的,色彩头像对于我来说似乎不是难事,虽然捂着嘴笑的男孩告诉我,考题是——他居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我,上面是几排合影(黑白色,像80年代的学生毕业照),其中第一排左四这个小指甲盖大小的头是个模糊的——在周围清晰的脑袋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像是照相时猛烈地在甩头似的。他告诉我,就画这个模糊的头。我的信心受到打击。我找出一支笔来,胡乱地在满是颜料的纸上勾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形来,然后把笔一扔,我知道,我无法完成这场考试了,完全不可能……我满头大汗地从梦中醒来。贤士花园的夜恢复了平静,我差一点坐起来,却仍然平躺在被子里,看到天花板,确定刚才的情景不是真的。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事后回想,也许是代替女儿的角色出现在考场上。那是考前的压力给造成的。
那个夜晚我没有睡踏实,我又做了一个梦。单位小肖告诉我,我们要到河对岸的茅棚里上班。什么,茅棚?这确定是真的?我想到办公室那些机器、文件,他们都将随我们到河对岸的茅棚中去。而单位的头头们,却留下来,其余的八九十号人全到河对岸去。那是一段不短的距离,也许只有电动车能派上用场。因为我们单位要拆除,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确实,它太陈旧了,是应该重建。后勤中心的人已经在开始筹划,怎么来搭河对岸的茅棚,他们提出了一个搭建两层的宏伟计划。这个梦没做多久我就醒了。哦,这又是一个梦,不是真的。工作同样给我带来压力。我的焦虑不经意间在梦中暴露出来。
这已是这个晚上的第二个梦了,但还没完。我出现在一个工地上,人来人往,一个大人物在巨幅图画前指指点点,似乎是一幅施工图,里面有隧道,前景居然是鸭群和牛群——它们从隧道口涌出来,中景是一些人物,远景有建筑、工厂、山峦。我提着一个铁桶,手里拿着抹布,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对着画面指指点点,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看到我并过来与我握手。然后他们走进去了。留下来的人在那里争吵,显然大人物对这幅画并不满意。这只是这个梦的前奏。我在惊愕中看到人们离去,才又提着铁桶往前走,扭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画的背面——一位女性,短头发、小脸蛋,粉色衣服,她坐在矮凳上,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瞟了我一下,我觉得那张脸很熟悉。我认出来了,是个同行。她说有几句话问我。周围人来人往、乱糟糟的。我和她去寻找一个僻静一点能说话的地方。我们来到一处,坐下,她劈面问我,说昨天和几个女作家在一起,她们说听到你说某某人的事情,想来求证一下。我惊讶地站起来,这完全是不实之词,况且,我讲什么话,她们怎能听到?她说,你在乡下说当然没人听到,你在城里讲,保准没人听到吗?况且,她说,她那个地方——西部某个省份,距离我们这里就是几十公里(实际在1200公里之外),保不准我说话的时候有人正好在我身旁听到。我质问她,是谁要这么说?她闭口不言,只拿黑白分明的眼睛瞅着我——言下之意,难道你心里还不清楚吗?我脑袋雷达似的快速搜索可能出现的面孔——这时我听到一阵响声,从梦里惊醒。原来手机设定的闹钟响了。
每晚,只要我的头一挨着枕头,梦就开始潜入我的脑袋。我发现贤士花园C栋1403室真正的主人不是我,也不是我太太和女儿,而是梦。梦主宰了这套居室,主宰了每个夜晚,而白天的所见,则为它的世界提供了素材。与其说我生活在这房子里,不如说是生活在梦里。每晚它以不同的面目、故事出现,并寄居在我身上。我只是它的房子而已。就像我和这房子的关系。可以想见,每晚小区要发生多少故事,已大大超过白天发生的那些事实多少倍。那些形象、故事,投射在夜的天幕上,简直灿若星河,像个奇观。各种各样的故事,披着梦的外衣,在颠倒的时空里穿梭往返,在那真正“自由的国度”生成、嬗变。我做梦,那是每晚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我不迅速将昨晚的梦记下来,也许什么也不曾看见,什么也不曾发生。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