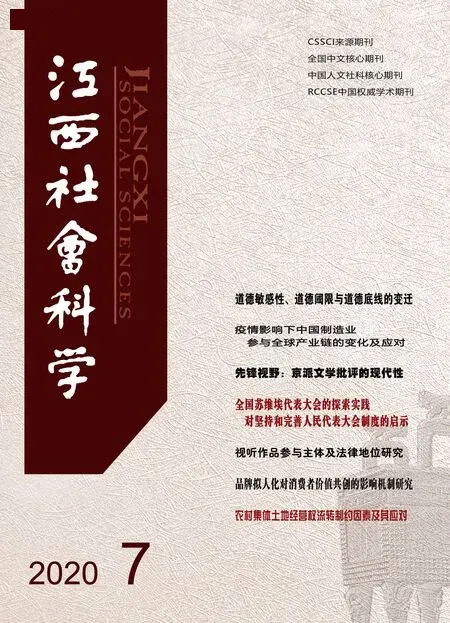城镇化驱动力与绩效逻辑
——以内陆省江西经济转型发展为例
2020-07-30李恩平
■李恩平
江西城镇化具有典型的沿海拉动与本地自发双轮驱动特征。近年来城镇化驱动力发生重要转型:省域城镇化利益机制由就业收入转向就业收入与消费利益并重,与沿海经济关系也由人财物的单向虹吸转向虹吸效应与产业转移承接并重,且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竞争加剧。其导致的城镇化绩效逻辑变化是:县域小城镇传统小型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竞争力持续下滑,省会南昌首位城市效应持续放大但面临内陆欠发达条件的规模绩效约束,近海城市赣州、上饶可能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因此,应优化南昌大都市的组团城市群格局,顺应首位效应,强化赣州、上饶的沿海产业承接功能,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转型。
作为内陆省区,江西具有较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城镇化格局。东南两面毗邻沿海省区,如何理顺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虹吸辐射关系,一直是江西发展战略面临的难题。
省会南昌位于省域中北部,但由于历史上形成了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南昌的首位城市辐射带动效应并不强,江西城镇化格局如何优化、城镇化的主战场和重心如何选择,省内一直存在矛盾、犹豫与争议。这在江西省城镇化的一些相关政策文件中表现很明显①,一方面,政府希望做大南昌,提升首位城市的增长极化效应;另一方面,又强调加强地级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提出加快县城和小城镇发展,这使得省域城镇化长期缺乏战略重心。
研究江西城镇化的文献不少,但多数文献聚焦于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关系。[1][2]李述、胡浣晨是极少数能从空间格局视角研究江西城镇化的作者,但李述的研究主要基于生态承载关系,胡浣晨的研究则主要介绍了新一轮的江西城镇体系规划,对江西近期发展动能转型未给予关注。[3][4]
近年来,江西发展的内外动能条件发生的重大改变为城镇化注入了新动力。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下,江西发展也进入由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2010年全省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2014年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50%。这使得城镇化驱动力发生了重大转型,乡城迁移由早期的单纯就业迁移转向包含居住生活在内的举家迁移,同时城城迁移加速。
随着全国沿海内陆经济关系优化重构,近年来,江西作为东南两面近海的内陆省区,与沿海发达省区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要改变。沿海主要发达城市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使得其对临近内陆地区的经济关系由早期的虹吸主导转变为虹吸与扩散辐射并存,这为江西城镇化注入了外生新动力。同时,基于产业升级需求,各省区对高端服务业集聚和高端人才竞争空前加剧,科教卫文等传统社会事业服务改革加速,在其他省区大都市多样化消费服务需求和多类型业务平台吸引下,近年来江西人才流失严重、高端产业发展不足,这使得城镇化规模绩效发生重大变化。
如何根据既有的地理资源条件扬长避短,适应省内外发展动能变化,优化和调整城镇化格局,是江西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试图从江西城镇化的基础条件、驱动力变化和绩效逻辑变化等三个层面,研究江西城镇化格局优化调整的战略方向,期望为江西城镇化战略制定提供一些理论支撑。
一、江西城镇化的基础条件
在国家经济地理的八大经济区中,江西属于长江中游的内陆省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不过近年来保持了较快经济增速,其城镇化基础条件算不上优越,但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
地处内陆但两面近海使得江西城镇化面临沿海发达城市拉动与本地市场自发的明显双轮驱动。江西是全国唯一一个两面近海且连接三个沿海省区的内陆省区,南邻广东、东接浙江、东南连福建。两面近海的地理区位使得相对于其他内陆省区,江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沿海地区影响更加突出,表现出明显的沿海城市拉动的输出型城镇化移民模式和沿海城市辐射带动型城镇化格局特征。沿海拉动与本地市场自发相结合的城镇化双轮驱动在江西表现得尤为明显。
省域辖区气候地理条件有利于中大型城市集聚,但内陆城市本质特征也使得首位大都市面临更高的通勤运输成本。江西境内地形地貌主要为丘陵平原,具有较低纬度的亚热带气候,这使得本地市场的多样化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特别丰富,有利于大中型城市集聚。但作为内陆省区,缺乏大型海港,省会南昌更位于省域中北部,远离长江航线②,相较于沿海省区及以长江港口为省会的湖北等省,江西首位城市南昌面临更高的通勤运输成本。
江西省会南昌的首位度并不突出,省域内已形成多个传统次级中心城市,部分城市还保留了一些“三线”布局的较高端生产型服务业。南昌为省域首位城市,但截至2018年南昌人口占全省比重仅11.4%③,属于内陆地区最低首位度的省区之一,南昌市常住人口规模也只有531.88万,城市规模也大大低于武汉、长沙、合肥等临近省会城市,属于规模较小的省会城市。除南昌之外,省域内历史上就形成了众多著名的次级城市集聚中心,如九江、景德镇、赣州、抚州、宜春等,近现代又形成了一批工矿业城市和铁路枢纽城市,如萍乡、新余、鹰潭、上饶等,全省已形成11个地级区划的地级中心城市。尽管江西近代工商业发展水平不高,但也在省会南昌以外的地级中心城市集聚分布了一批特殊类型的国家级科研教育等生产性服务机构部门,如景德镇的飞机制造研发、陶瓷陶艺研发,抚州、赣州的地质矿藏、有色金属科研机构等。
江西高端人口相对缺乏,省会南昌相对缺乏国家级大区域级别服务平台,因此,难以支撑大型中心城市集聚。由于历史原因,江西近代以来教育科研相对落后,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江西大专及以上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率为7.56%、研究生学历占比为0.15%,在全国31个省区中排名倒数5位。江西也是全国高等院校分布最少的省区之一,省内仅有一所211高校,没有一所985高校,没有一所中科院下辖研究所。在省会南昌,各类国家级、大区域级别服务平台也很少。人口相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必然影响消费结构层级,系列高端服务业需求不足,高端科研、服务平台缺乏,这使得高端服务业发展缺乏供给基础支撑,以高端服务为主导产业的大型中心城市难以集聚。
二、近年来江西城镇化驱动力的转型
历经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与全国大多数省区一样,江西内外发展条件正发生重大变化,省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驱动力正发生重大转型。
一是省域经济迈入由中等发展向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城镇化迈入快速增长2.0阶段,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入新阶段。
2010年江西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2018年达7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5],江西已经迈入中等收入或中等发展阶段,进入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2014年江西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50%,2018年达56.02%,按照S型城镇化水平的阶段划分[6][7],江西进入了快速城镇化的中后期即2.0阶段。在经济发展的转型跨越期和快速城镇化2.0阶段,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对于类似江西这样的后发地区,早期经济发展更多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仅仅是对工业化的被动适应,但进入中等发展跨越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
根据Annez and Buckley、周一星的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对数线性关系。[8][9]如图1所示,江西城镇化与人均GDP之间的散点图和对数线性趋势线表明,江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其对数线性趋势线拟合方程的R2达0.9562。对照散点图与对数线性趋势线,我们可以发现江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变特征。2001年以前,散点图基本位于对数线性趋势线下方,意味着实际的城镇化水平低于经济增长合意的城镇化水平;2002—2010年,散点图与对数线性趋势线高度重合,意味着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联动;2011年以后,散点图基本位于对数线性趋势线上方且呈偏离拉大趋势,意味着城镇化对人均GDP的拉动效应低于合意水平,城镇化集聚效应并没有被释放出来。

图1 1978—2018年江西不变价人均GDP与城镇化水平散点图
二是省内城镇化驱动力由早期就业收入利益主导转向就业收入与多样化消费服务利益并重,居住城镇化需求快速增长,城城迁移加速。
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城乡发展关系发生重大转型。农村经济商品货币化和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自给自足的消费便利消失。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低成本的市场且多样化的消费服务利益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利益差距从有利于农村转变为越来越有利于城市。也由于不同层级消费服务供给对最低市场规模要求存在差异,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消费利益差距也快速拉大。城乡利益差距的变化使得城镇化驱动力由早期就业收入主导转向就业收入与多样化消费服务利益并重,城镇化移民模式发生改变,由早期单纯就业移民即农民工个人进城打工转变为包括劳动人口在内的举家移民,居住生活城镇化与就业城镇化并重。根据李恩平的研究,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差距存在以大致50%的城镇化水平为拐点的先升后降规律,当城镇化水平突破大致50%拐点以后,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加速。[10]
江西城镇化人口迁移模式的拐点大致发生在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50%的2014年前后,由于缺乏各年度分年龄的城乡人口数据,我们以“城镇就业人口/城镇常住人口”比率来考察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城镇化进程差距④,“城镇单位就业人口/城镇人口” 比率拐点发生在2013年,“城镇单位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口/城镇人口”比率拐点发生在2015年,如图2所示。江西城镇人口比率关系变化表明,城镇就业人口占城镇人口比率已经跨过拐点呈现出右下方倾斜的趋势,这意味着城镇化人口中非劳动(就业)人口比率将呈逐渐上升趋势。

图2 江西城镇就业人口与常住人口比率变化
三是省域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经济关系也由早期单向的人财物虹吸转向虹吸效应与产业转移承接并存。
经历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我国沿海内陆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由早期单向的人财物虹吸关系转向虹吸效应与产业转移承接并存。一方面,沿海发达城市基于国际竞争压力存在产业升级需求,需要淘汰一些中低端产业实现腾笼换鸟;另一方面,长期经济集聚也使得用地成本和劳动成本迅速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和用地密集产业迫于成本上升压力,被迫实施产业转移。而内陆地区相对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宽松的用地供给,正好错位沿海发达城市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形成沿海内陆梯度产业转移承接。
从沿海省区产业企业集聚关系看,较大幅度的沿海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2010年以后,如图3所示,江西临近的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工业企业单位数在2010年均出现了大幅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统计口径变化),且2011年以后各年度工业企业单位数变化幅度很小,远没有2010年以前的增速,这表明这些沿海省区工业制造业企业集聚减少了,新增的工业制造业企业被转移到了内陆等其他区域。沿海内陆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也伴随了沿海内陆城镇化迁移方向的变化,内陆省区输出劳务即农民工跨省外出随着产业迁移出现回流,出现省区内家乡就近城镇再就业。

图3 江西沿海近邻广东、福建、浙江工业企业单位数变化
江西东南两面均毗邻沿海省区,是距离沿海发达城市最近的省区之一,具有最短的交通距离和最低的交通运输成本,更有利于沿海发达城市转移产业及与原转移地之间的商贸联系。因此,江西很容易成为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转移首选地,并且与沿海发达城市之间人财物虹吸与产业转移的双向经济关系更加突出。
四是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外迁和高端人才流失困境。
随着全国经济迈入转型跨越期,省区之间的发展竞争加剧,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竞争加剧。一方面,沿海发达省区迫于国际竞争压力,存在产业升级需求,希望通过普通制造业到高端服务业的升级占领高附加值产业链端;另一方面,不少内陆省区也希望通过高端服务业集聚实现赶超发展,江西毗邻的湖北、安徽等内陆省区纷纷提出建设光谷、硅谷,集全省之力,大力提升武汉、合肥等省会城市的高端服务业集聚。与高端服务业竞争相对应,无论沿海省区还是内陆省区,均展开了对高端人才的吸引竞争,纷纷出台各类颇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
在沿海发达省区和近邻内陆省区联合竞争挤压下,本就缺乏高端服务平台的江西竞争劣势更加明显,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三产占比47.35%,是长江中游四省中三产占比最低的省区。高端服务业竞争被挤压,必然也意味着高端人才的流失。如图4所示,无论相对全国还是长江中游地区,江西省大专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或长江中游)大专及以上人口的相对比率自2008年开始表现出持续性的明显下行趋势。

图4 江西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相对变化
高端产业集聚和高端人才集聚的外部竞争也必然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给省区内城镇化集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会降低城市集聚效率,使得单位人口和单位产出的城市拥堵效应增加,高端人才流失更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导致城市发展动能丧失。
三、江西城镇化驱动力转型引发的发展绩效逻辑变化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驱动力转型必然影响城镇化绩效关系发生变化。在新的驱动力条件下,一些城镇固有的资源约束、区位劣势等不利因素越来越凸显,发展动能耗竭,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一些原本未被开发的城市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逐渐凸显,城市发展动能转换,可能迎来城市快速增长的机遇期;还有一些城市可能需要对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重构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县域经济和小城镇传统小型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面临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的转型
中等发展到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是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在于城市集聚效应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转换及对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适应,更高层级的工商产业只有较大规模的城市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共享、匹配和知识技能的扩散与创新,但消费结构升级也为农村腹地的县域和小城镇带来新机遇。
县域经济和小城镇传统工业化发展动能快速耗竭。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一些农村腹地县乡小城镇依赖丰富的劳动力和临近的农产资源,建设发展了一批“小而全”的小型工业园区,壮大了所在县域的经济,但在新的发展驱动条件下,这些农村腹地的小城镇无论是生产集聚还是消费集聚,都因为市场规模狭小导致共享、匹配和扩散创新严重不足,小而全的传统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
消费结构升级又为县域经济和小城镇转型发展提供了机遇。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居民家庭对健康服务需求提升,对消费服务的绿色生态品质追求不断强化,一些山清水秀的乡村可能迎来生态养生服务业的发展机遇,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也必将快速增长。随着快速城镇化,农村人口减少和人均土地资源增长将促进农村经营方式发生转变,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和绿色农业将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部分没有区位优势的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竞争力可能持续下滑,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
在转型跨越期,大都市的集聚优势进一步凸显,次级城市竞争力存在持续下滑趋势。经济发展早期,由于产业结构层级较低、交通通讯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市场可达的区域范围有限,本地市场的城镇化和产业集聚更多地在较小区域范围内(如县域或地级辖区)发生;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层级提升、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市场可达的区域范围大幅提升,本地市场的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可以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如省级辖区)发生,集聚效应很可能使得更大区域范围内逐渐形成一个主要的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中心——首位城市所在的城市群或都市区,而(省级)大区域内原有次级中心城市可能迅速衰落。如日本、韩国在其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中后期均曾经历了首都都市区快速集聚、其他次级城市快速衰落的过程。日本东京都市区集聚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传统的次级中心城市,如广岛、大阪、京都等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持续衰落,韩国首尔都市区集聚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传统次级中心城市,如釜山、大邱、光州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出现了持续衰落。
江西属于内陆省区,其次级中心城市(地级市)的区位条件远远赶不上韩国、日本诸多具有良好水运条件的海港、河港城市。进入转型跨越期后,在省会城市南昌和近邻沿海城市的联合虹吸下,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可能持续下滑,特别是一些远离沿海城市的中西部次级中心城市,如萍乡、宜春、新余、景德镇等,发展动能衰竭,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
(三)省会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可能持续放大,但面临欠发达内陆条件的规模绩效约束
在转型跨越期,省会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持续放大。一方面,由于产业层级提升和技术进步,首位城市存在集聚效应的规模路径锁定优势,强者恒强;另一方面,南昌作为省会所在,全省行政资源的集聚必然强势吸引集聚全省人财物资源,更由于处在转型跨越期,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行政资源对服务业集聚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可以预期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可能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省内中高收入人口和中高端人才的快速集聚。但南昌城市集聚绩效提升也受到内陆区位和省区相对欠发达条件的约束。作为内陆型大都市,南昌无法像沿海城市一样分享大吨位水运的低成本利益,这使得城市对内对外运输通勤严重依赖陆上交通体系。随着城市规模增长,单位道路运输通勤承载呈几何级数增加,城市拥堵效应快速提升。
作为相对欠发达省区,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江西所能选择的就业结构从产业结构层级来说相对较低,低层级的产业集聚共享匹配所要求的本地市场规模并不高,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并不明显,难以抵消大规模集聚所带来的拥堵效应;另一方面,相对较低收入和较低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消费结构层级也相对较低,消费结构以相对较低成本的大众化商品服务为主,多样化的高端消费服务需求不足,大规模人口带来的消费市场集聚并不能带来过多的消费集聚利益,同样难以抵消大规模消费集聚带来拥堵效应导致的通勤运输成本上升。因此,南昌人口和产业集聚还需处理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所要求的最佳市场规模与城市总人口规模和总市场规模之间的分流问题。
(四)东南近海区域可能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机遇期
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转移进入新阶段,产业转移可能更偏好近距离的产业集聚集群分工。随着产业结构初步调整到位,沿海发达城市选择进一步产业转移的承载地,不再如早期几乎不考虑与母城市间的运输通勤距离和空间经济联系(如超远距离的大西南、大西北),因为被转移产业与母城市产业之间更紧密的前后向业务关系和商务往来,其转移承接地的选择必然更偏好空间距离更短、交通联系更便捷、经贸往来更密集的内陆省区近海区域。
江西东南近海区域对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转移承接具有更有利的区位优势,可能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机遇期。南昌尽管具有行政资源集聚和首位城市效应,但位于江西省中北部,其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距离超出了频繁业务往来和商贸关系所能承受的最佳距离。但东南区域的赣州、上饶分别连接广东、福建、浙江,是与沿海发达城市空间距离最短、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地级城市,它们将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⑤,未来5~10年内可能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承接机遇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考察了江西发展转型和城镇化驱动力变化,分析了发展转型和驱动力变化引起的城镇化绩效逻辑变化后,得出以下结论:(1)江西城镇化具有典型的沿海拉动与本地市场自发双轮驱动特征,首位城市发展不突出,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层级较低,高端服务平台相对缺乏。(2)近年来,江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驱动力发生了重大转型。省域经济迈入由中等发展向中等发达的转型跨越期,城镇化迈入快速增长2.0阶段;省内城镇化驱动力由早期就业收入利益主导转向就业收入与多样化消费服务利益并重,居住生活城镇化需求快速增长;省域与沿海发达城市间的经济关系也由早期单向的人财物虹吸转向人财物虹吸与产业转移承接并存,同时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外迁和服务人才流失困境。(3) 城镇化驱动力转型也导致发展绩效逻辑变化。县域经济和小城镇传统“小而全”的工业化发展动能耗尽,面临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的转型;部分没有区位优势的传统次级中心城市竞争力可能持续下滑,发展停滞、逐步衰落的风险加剧;省会南昌的首位城市效应可能持续放大,但面临欠发达内陆区位条件的规模绩效约束;东南近海区域可能成为最佳产业转移承接的近海发展地带,迎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集聚机遇期。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顺应首位城市南昌的极化效应,加快高端产业、高端人口集聚集群。在转型跨越期,首位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对省域经济的带动效应明显,省域经济发展应以省会南昌为中心,促进南昌与省域各区域之间的人财物流畅通。面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省域经济布局应加快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集聚,形成以南昌为中心的集群发展,以南昌大都市多样化的生产生活服务平台重构江西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的生存发展环境。
二是重构南昌大都市经济结构和空间格局,加快大都市区就业、居住、服务一体化的组团功能区和城市群建设。内陆区位及相对低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内陆大都市集聚的不利规模约束,需要都市区经济结构与空间格局联动优化来破解。按照产业层级差异,强化南昌大都市组团功能区分工,分别规划布局独立的组团功能区,最大化地发挥各分类产业内的集群集聚效应。
各组团功能区内就业、居住、服务平衡发展,大力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居民区与产业区临近布局,根据各组团产业就业人口结构特点,尽可能设计规划更贴近本组团就业人口需求的住房和社区服务,通过税费和限购约束跨组团就业人口的住房购置。
三是紧抓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机遇,将赣州、上饶建成与沿海发达城市紧密分工的近海次级城市集聚中心。赣州、上饶属于沿海发达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的中间地带,与沿海发达城市的空间距离短、经济联系紧密,又不受发达省区相对严格的生态保护和用地供应约束,还相对远离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是发达城市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应大力推进联通两城市沿海交通通道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进城市政府施政水平,努力提高城市营商环境,加强对主要沿海发达城市的政务商务服务,实现本城市在沿海发达城市的零距离全方位政务商务服务。
四是对省区内发展条件不充分地区适度收缩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的转型。对一些缺乏发展动能的、区位条件不理想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不再推行低效无效的本地市场产业转型,而是实施收缩发展,做好城市经济衰退后的人口迁转和维稳保障工作。
鼓励农村腹地县域小城镇由传统小型工业化经济向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新经济转型,除农产品加工外的工业制造业逐渐向省内主要大都市城市群迁转,鼓励利用优越的生态条件发展养生、养老经济,积极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绿色生态农业。
注释:
①参见赣发[2010]7号文、赣府发[2019]10号文、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文件。
②实际上,进入江西以上长江航线的航运价值并不高,铜陵以上长江港口均不具备万吨以上泊位通航能力。
③除特别说明外,笔者所引用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在线数据网http://data.stats.gov.cn/,部分较早时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④由于各年度统计口径差异,城镇个体就业人口数年度之间变化太大,因此笔者没有考察包括个体就业人口比率变化。
⑤实际上,近海发展地带可能在整个东南近海省区均存在,如:江西上饶、赣州,湖南郴州、衡阳、永州,近年来均成为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