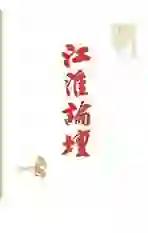政治场域中庄子式的人文化成
2020-07-23张榕坤
张榕坤
摘要:庄子在“天”与“人”两大基本维度上,自觉反思了先秦儒家在“外王”政治实践中成己成物的方式可能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人文化成的独特方式:以涵容虚静的“天德”为法,保有对恶者同情的理解与悲悯体贴,并通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心斋”工夫,将其落实于政治实践,这是成功化物的根基;继而,顺应“物性”与“物势”,与物宛转、因机点化,以巧妙的庖解之道完成对恶者的更新与转化。就此而言,“德合于天”前提下“顺物”且“因势”的文化治疗,无碍地贯通了“与天为徒”及“与人为徒”,成就了庄子式的人文化成,其中也蕴含着建构其内圣外王圆融之学的契机。
关键词:庄子;儒家;虚静之德;庖解之道;人文化成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3-0094-006
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道家哲学却历来被认为缺乏此一方面的积极思维,尤其在政治场域中,学者或片面强调其遁离时局的出世立场,[1]或仅认为其政治思想乃道德学说之余绪[2],抑或点出其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重建内圣外王之道[3],并试在内圣与外王之间寻求一种承续与融通,却并未深入阐发。[4]事实上,庄子已在《人间世》(1)明确提出“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乃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存在处境,且在具体的政治场域彰明了自身独特的人文化成,从而构成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具有进一步探究的价值。由于《天下》篇将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凝练地概括为“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超越与圆融,这两个面向实则共同构成了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因此,以“天”与“人”为基本立足点展开对庄子式人文化成的分析,无疑是一个合理的诠释方向。
一、庄子对先秦儒家人文化成之道的反思
先秦儒者企盼“为政以德”的王道理想能在政治场域实现,却常常不见用于统治者,尤其对当政的无德之君而言,其理想主义的政治实践更被斥为无稽之谈。在《人间世》,庄子特举了颜回劝诫卫君的寓言,在“天”与“人”两个根本向度上,借重孔子之言对颜回的教化之方做了深刻省察,提拈出先秦儒者由内圣走向外王时可能遭遇的困境。这表明庄子对儒家的人文化成之道确有自觉的省思,而这也成为庄子提出其思想创见的前提与基础。
在这则寓言中,卫君是恶者与政治权势(2)的象征,顏回则代表了施以仁义教化的儒者形象。颜回怀抱“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这一儒家式“成己成物”的道德理想,欲通过匡正卫君彰明仁义之道。对此,庄子借孔子这一代言人表明了基本立场:“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可见,庄子最重要的考量并非德性论意义上的价值理想,而是生存论背景下圆融而智慧的行为方式,在存己而立本的前提下,实现对暴虐卫君的有效救治,构成了庄子式人文化成的基要。进而,我们可在颜回提出的劝诫策略以及孔子的回应中,更清晰地体会庄子对先秦儒家人文化成之道的省察。类似《大宗师》中的“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在这则寓言中,代表儒家的颜回亦提出了“与天为徒”“与人为徒”及“与古为徒”三条原则。所谓“与天为徒”,即若童子之真,立公正允直之心以为大本;所谓“与人为徒”,即曲合外物,顺行人臣之礼;“与古为徒”,即以古人言教作为劝诫之据。三种策略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儒者面对政治威权中的恶者所运用的教化方式。但庄子认为,这一人、我二分前提下的化成之道,每一向度皆深藏着幽微之弊。我们顺庄子的思路依次省察如下:
首先,对于“与天为徒”,郭象注曰:“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婴儿之直往也。”[5]这恰恰代表了儒家式“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君子无畏之风:心中秉持廓然大公之理,可勇而无惧,依理直行,由此对失德乱政的王侯之势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与直谏。因此,他可不求人誉以为善,也不虑人以为不善,但由本心发而为言,这便是“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的正义坚持。然而,此理虽是应然的价值标准,但若抱持胜物之心,执于此理而不去同情地理解、体贴卫君,其结局一则将殉身于权势,二则反成为权势者的帮凶。这正是庄子指出的:“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人间世》)面对权势者的凌人盛气,最终难免顺从屈就,这无异于以水救水、以火救火,终将助势恶者,而难成化人之功。
其次,“与人为徒”是指行以人臣之礼,恭敬随顺以应物。然而,恭行人臣之礼并不意味着内心能真正的从容和谐,若显题化为劝诫的一种方法,反而会加重内心的患得患失而最终适得其反。台湾学者林明照指出:“这促使‘随顺成为他心中的一道指令,他必须时时督促他的行为符合这指令。于是,原本看似能求得和谐而平静的方法,反倒成了一道时刻令自己紧张不已的指令!”[6]由此可见,礼的作用被刻意提拈并策略化之后,非但不能成为心中自然流衍而出的行为,反而会因人的过于自觉而异化为心之束缚。
最后,“与古为徒”是说,劝诫并非一己独论,乃是依从古今共循的法则忠谏之而已。然而,在幽微复杂、人心惟危的政治局势与恶者强权的实存处境中,若颜回强以仁义绳墨之言呈于暴君之前,可能会被认为炫己之美德反显暴君之恶,从而导致暴君为保其名与之争斗,颜回将难免祸患。所以,庄子评论道:“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宣颖注曰:“有矜名争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即无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见信于人,则彼亦将谓汝炫美而掩己,必加害矣。”[7]正如夏桀杀关龙逄,殷纣杀王子比干,修身爱民、德性仁厚的贤良之士被杀只是因为桀纣怕其美誉显己之恶名。因此,庄子在后文感慨说:“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也就是说,虽然仁德深厚,不求声名,却不一定能使人信服,反可能伤及自身。
以上三点表明,颜回所代表的先秦儒者虽有“视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的道德理想与政治勇气(3),但其“以善止恶”的化成路径难免陷入规范伦理善恶二元对抗的格局,对善的执着与对恶的排拒使恶非但不能被有效转化,且可能在恶者的权势加持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具体而言,儒者虽“与天为徒”,直行天理善道,却执于善恶二元对立下应然的价值裁断,未能保有对恶者的安纳体贴与同情理解;虽“与人为徒”,恭敬行礼,却不能确保礼在君臣关系展开的特殊之势中不被异化;虽“与古为徒”,借古圣先王之言以资劝诫,却未能充分考量人心实则好名喜争,最终反会使自身在政治威权中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所以,庄子一语中的,指出儒者人文化成之道的弊病症结:“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也就是说,儒者的“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虽然托之于天、人、古,但致使内心“成法”太多。依照诸多成法施以仁义之教以拨乱反正,即便能够免罪,也“止是耳矣”,不能产生化物之功。
继而,庄子提出了人文化成的独有创见,其中蕴含了庄子式“天与人不相胜”之道在政治场域中落实的可能性。
二、庄子式人文化成的根基:
“与天为徒”的虚静之德
对于政治场域中的人文化成,庄子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人间世》)。也就是说,要想劝导卫君行善(“存诸人”),自己首先应有足够的德行修养(“存诸己”)。(4)在《庄子》全书,虽然无法寻得他欲图矫恶为善的理想坚持,但有相当多关于有“德”者“不欲正人而人自正”的论述。我们可先在普遍意义上简单说明对待恶者应当保有何种“德”,继而延展至政治场域,来考察其应用意义。
在《德充符》中,庄子描述了诸多极端丑陋者、肢体残缺者乃至犯罪受刑者却能内保其德的人,同时盛赞他们的德行将自然而然地产生使人倾慕、归附的无限光辉,乃至“正人”“化人”的神奇力量。那么,庄子所言的这种“德”具备怎样的特质?在其中一则寓言中,他提出人之德应如天覆地载般涵容万物: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 德充符》)
该寓言讲述了鲁国兀者叔山无趾求教孔子,孔子认为他前行不谨既已犯错受刑,现在来求教为时已晚。无趾认为天地无不覆载,即使自己以前有过错,仍可复补前行之恶,理应被德如天地的孔子接纳,而不是以其为兀者為由将之拒之门外,所谓:“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这就是说,天地可以涵容、宽宥一切(包括罪恶),人亦应保有如天地之柔量虚怀,以及广纳万物的大德。当吾人可以消解由成心裁判出的是非善恶的价值畛域,柔化强烈的道德主体“我”,先以虚怀敞开的态度感通、体贴、同情地理解恶者,方可消解与恶者的对立,进而才有对恶者施以救治之方的可能。以天地涵容万物般的虚量大德,保有对恶者深刻的理解纳受与“无弃人、无弃物”的慈悲爱怀,这是庄子所认为的对待恶者的基本态度。在外、杂篇,庄子由天地的涵容万物、虚怀若谷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天德”概念,并以虚静无为、淡漠自然描述天德:“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刻意》)“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天道》)由此可见,“虚”为天德的核心特质,人应当以之为法。概言之,庄子期待吾人首先能以天德之“虚”对待恶者,“与天合德”便构成庄子式人文化成的枢要与根基。
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考察颜回劝诫卫君的寓言,来看这一理念的应用意义。在否定了颜回的方案之后,庄子提出“心斋”这一“存诸己”同时可以“存诸人”的修德方法。对于“心斋”的义涵,他首先精要地指出“虚者,心斋也”,继而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释:“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据此,对“虚”的含义分析如下:
首先,“名”为有“迹”(实),“无感其名”为“虚”。庄子主张“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身在政治樊笼之中,一方面不宜以善名或恶名去裁定他人,不先入为主地设定对象为“恶”,而应敞开自身能容善恶的若谷虚怀;另一方面,自身也当与善恶之名保持距离,避免“德荡乎名”。正如吕惠卿所论析的:“德者,内保之而外不荡者也,不荡则无所事名。溢而为名……则彼亦以名胜我矣。则是名也者,相轧也。智出乎争,则彼亦以智与我争矣。”[8]也就是说,即便自己为善并非逐名,亦要避免德形于外而固著成一种善名,而使己之美名显出他者之恶名,防止跌入双方继之以智相斗的危局。
其次,“有心胜物”为“实”,“无心知止”乃“虚”。庄子主张“入则鸣,不入则止”,所谏之言能被领受则言,不能被领受则适可而止,万不可强人就己。这一方面符应了天德无心化育万物、“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基本特质,即便对人文化成来说,也应以因循为本,不能刻意造作,不可行则止;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有德者虽然不否定恶者为“恶”的存在实情,却可清明洞察对恶者的强力规劝并不能使其由衷悔过,所以,有德者不存强为之心,反能以涵容万物的天地德量给予虚怀容纳。
最后,“有方有谋”为“实”,“无门无毒”为“虚”。庄子主张“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钟泰解释道:“‘毒谓药也。名曰医门,名曰用药,则讳疾者之所避也。卫君不见其过,而将乘人斗捷,其讳疾忌医甚明也。惟无门,则无往而非医也。无毒,则无往而非药也。如是,则讳无所用其讳,而避亦无得而避矣。”[9]如果颜回一开始便打着“行医”的名号,并且准备好了所用之“药”,那么讳疾忌医的卫君必然趋避之、打压之,乃致与之争斗,颜回根本无从化人。反之,如果一开始不立“医门”之名、不备应对之“药”(“无门无毒”),入于其中,在物势发展的“不得已”处(“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全无刻意地因势起化,在时机适宜的时候施以救治“良药”,方能在保全己身的前提下,巧妙地化恶于无形无迹之中。
基于以上对“虚”的分析,我们才可理解庄子何以用“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再次强调“心斋”的基本精神。前人学者常从“人为”(为人使)与“自然”(为天使)的角度说明庄子主张顺应自然而为,但未过多留意句中的“伪”字。关于“伪”,《康熙字典》云:“《说文》:诈也。《书·周官》:作伪心劳日拙。《说文》:从人为声。徐曰: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故人为为伪。”[10]庄子的深意,在于表明如果不能虚明其心,有意为之却不能取法天德,那么,即便出于正义而为,从最终结果来看,一则将枉费苦心,徒增劳顿;二则适得其反,行之以善却弄巧成拙,难成化物之功。
至此,可借上述分析反观先秦儒家的化成方式。儒者的人文化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这一理想主义的道德信念,而庄子式的人文化成之所以有不同的理路,在于庄子更侧重思考君臣互动的政治实践中所展开的“势”,并对人的经验认知心有深刻的洞察、反省与警惕,因此会将人文化成置于“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意义脉络中进行考量。他主张在“存诸己”的基础上,以更加智慧的方式“存诸人”,兼顾并周全“存己”与“存人”,以保持两者完满而圆顿的平衡。这同时表明,庄子的本意并非只求“与天合德”以“存诸己”,明哲保身地“澹然独与神明居”,他还须进一步在实质上完成对恶者的医治与救赎。
三、 庄子式人文化成的落实:
“与人为徒”的庖解之道
庄子主要以遮诠的方式说明了对待政治权势中的恶者应当保有天德之“虚”,可分为“无感其名”“无心知止”及“无门无毒”三个方面。同时,他也对如何化恶为善做出了某些积极的暗示,比如“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对于这一主张,庄子在《人间世》的第三则寓言“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一节做出了更深入的说明。该寓言的背景是,欲救国于危亡的颜阖要去辅佐、教化“其德天杀”的卫灵公太子,然而,不能省察己过并讳疾忌医的卫灵公太子,很可能会起忿恨之心,迁怒于颜阖,或将以权势杀之。因此,颜阖之傅卫灵公太子,与颜回之劝导卫君,事件背景几乎无异。同时,颜阖也向庄子的代言人蘧伯玉提出了请教。我们可将庄子的观点厘清如下:
首先,庄子开宗明义地点明一大前提:“正己身”,所谓“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对个人而言,所谓正,即不偏左不偏右,不偏执一端而行中道。在《养生主》,庄子已明确提出应“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王船山释曰:“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者也。”[11]句中的“督”,本指人身的督脉,它不左不右,中空能容众多支脉汇流,由此可形成贯通生命全体的气化景观。也就是说,不可执于定名所裁定的善,也不可执于定刑所裁定的恶,而是让善恶都能安顿在包容涵纳的“虚”德之中,恶才有进一步被转化与更新的可能。这也是上节我们论证的核心内容,此乃庄子式人文化成实现的根基。
其次,在“正女身”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阐发了化物之道。他说:“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这段话的含义是,外表上要恭敬顺应(“就”),内心要去调和诱导(“和”)。恭敬顺应但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就不欲入”),否则便失劝诫真义;调和诱导又不能太过张扬(“和不欲出”),否则会被视为博取名声,易招杀身之祸。由此可见,庄子一方面确立了形与心应当顺之和之的总体基调,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其分寸与尺度,从而彰显对价值原则的坚守,表明对恶者的虚怀涵纳并非善恶不分、一味纵容。这也展现了庄子“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化物本怀,即在“保身全生”与“化恶为善”之间寻得妥善的周全与动态的平衡。
最后,庄子对如何化物做出正面的阐释,即顺性起化、因机以导。其言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赵虚斋注曰:“婴儿、无町畦、无崖,是形容无知妄为之状。彼方如此,我且顺之;到有可觉悟处,就加点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无疵之地。螳螂怒臂,喻小材自矜,以当大事,鲜不败者。养虎、爱马,义自显明。”[12]也就是说,纵使卫灵公无知而妄为,起先仍不可有所违逆,姑且许之顺之(5),否则将如螳臂当车,自矜其材,不知力所不及;又如养虎爱马者,若妄出己意,不顺物性,则会“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纵有主观美意,仍会为虎马毁伤,所以,必须谨循虎马之习性以为则,“时其饥饱,达其怒心”地养虎、顺应马之本性地爱马。同理,只有顺性而动、因势利导地转化外物,才能以曲成与善调的智慧化恶为善。顺物性而动不等于放纵其恶、任其无知妄为,而是在时机适当、机缘恰合时见缝插针、因机点醒,在“有可觉悟处”加以点化,使其“躍然醒悟”,如此便是付化物于无迹、寓有方于无方之中。此处的“可觉悟处”便强调了“机”之重要,善因物性,同时善因时机与情势以起化,才可能产生“达之,入于无疵”的自然化导之功。在此过程中,要时时保有戒慎恐惧之心,怵然为戒,不可自恃相习已久而妄出己意,所以,庄子开宗明义地強调“戒之,慎之”。
此处宜与儒家的化成之道对比,借以澄清庄子式人文化成的特质。《孟子·梁惠王下》亦记载了孟子循循善诱,顺物性、因时机劝导齐宣王行王道之事,似乎与庄子顺性起化、因机以导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庄子而言,孟子的教化仍属人、我二分前提下“技”的运用(只是一种化成技巧与方略),而未达“道”的高度。正如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纵然庖丁解牛的过程如何出神入化,在面对文惠君发出“善哉!技盖至此乎”的惊叹时,他并不归因于技艺的高超,而答之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与道阶位的差别在于德,即生命主体的修养境界。前文述及,庄子是以虚静无为、自然淡漠的天德为法,以此作为人文化成的根基。在此意义上,庄子与孟子教化方式的不同在于前者可在“虚己”的前提下涵容覆载,不居善恶两造,亦无矫恶为善的刻意“为之”之心,因此可以消解自身的善恶固著,产生对恶者的倾听包容与感同身受(某种意义上的“与物一体”)。也就是说,首先打破物我壁隔,与外物一气共感而全然体贴其存在情境;进而以“无己”的姿态“达之,入于无疵”;最终可以无丝毫刻意、自然而然地“化物”于无方之中,如同庖丁十九年后“忘我”而游刃有余,解牛而刀不伤。由此而有的人文化成,才可避免以正义之善自矜自恃,而能循虚以行、因势利导。由此也可明了,“与人为徒”的庖解之道只有在“与天为徒”的意义脉络中才能被正确理解。
“心斋”工夫所言的“虚己”是不断消弭自身私意固著的过程,同时也是更为真切地体贴物性及物势的过程。“虚”的结果并非仅是一虚灵明觉的纯粹境界,从而纯有“全生保真”之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使心产生对物性及物势更为澄澈而专注的觉照力(“虚室生白”),并由之采取因物付物、恰到好处的因应活动,以一巧妙而迂回的庖解之道寓“化成”于“无方”之中。它不显强烈的为善动机,亦无明确的治疗策略与技巧,而是虚怀顺物、因势利导以成化物之功。如同庖丁解牛之刀,以无厚的刀刃循顺牛身骨骼与脉络的条理走势(“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宛转其间(虚明之心随顺外物之性及时机情势而调之解之),最终不伤其刀(保真、全生)地使牛“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成功化物)。这也是心斋之“虚”在凶险难测、变幻不定的政治场域中呈现的神妙的化物之功:“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人间世》)
由此可见,与儒者“与天为徒”及“与人为徒”的人文化成方式不同,庄子式的“与天为徒”乃是消解了心中应然的价值裁断,侔合天德之柔量虚怀的广覆涵容,因而对恶者可生出遍润感通又慈柔悲悯的道德情感(6);庄子式的“与人为徒”,乃是因物付物,应不同之机、不同之境而随缘起化的庖解曲成,这是深刻洞悉物性与物势之后既可存己又可存人的应物、化物之方。“与人为徒”以“与天为徒”为前提,“与天为徒”终须落实于“与人为徒”而获得真实的人文本质与现实效力。在此意义上,两者完成了圆融的统合,并彰显庄子式内圣外王的人文向度。
四、结 语
在“天”与“人”所展开的视域背景中,庄子自觉省察了儒家人文化成之道的局限,指出儒者过于重视道德主体对理想价值的主观弘扬,少有对非与恶的同情感通与慈悲爱怀,欠乏在政治场域中对物性及物势的体贴洞悉与精微察识。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了独特的存己存人之方,彰显了道家式的人文化成。具体而言,庄子参赞包容涵纳、虚静无为的天德,在施行教化的过程中,能以体谅欣纳、一体涵容的天德之善对待恶者,其中深蕴着“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伦理关怀与人文精神;在对恶者柔怀纳受的前提下,进一步以“虚己”的心斋工夫(“存诸己”),消解既成的价值裁断与善恶固著,以“无我”的姿态迂回宛转地游刃于外物之中,以巧妙的庖解之道实现对恶者的转化与治疗(“存诸人”)。这一寓有方于无方、无心而成化的方式,表征着庄子实有对人文化成的自觉思考与独特创见,同时也可为建构庄子式内圣外王的圆融之学开辟一条新的可能之路。
注释:
(1)本文所引《庄子》原文,均只标篇名;若无特殊说明,皆依据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2)杨国荣强调了“势”作为具有普遍内涵的哲学范畴,与个体在社会实践结构中的“位”相联系,并具体体现在政治实践过程。它不仅指君臣互动过程中所据之“位”,并展现为独特的政治格局与态势,同时也作为行动和实践的背景和条件,体现于事物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参见杨国荣. 说“势”[J].文史哲, 2012,(4): 83-91。庄子的寓言将君臣关系与善恶关系紧密结合来阐发人文化成之道,意在强调外王政治的实现必须考量君臣结构,并结合具体实践活动中两者的互动情势。
(3)杜维明认为先秦儒家的“抗议精神”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政治批判,二是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批判,三是文化传承、文化批判精神。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M]//杜维明文集(第五卷).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59。虽然《庄子》全书亦流露出一种批判主义精神,但是,这一批判精神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品格仍是道家式的,与先秦儒家的“抗议精神”有本质的不同。
(4)“存己”并非仅为生存论意义上的免患自保,而有“定”己以立“本”之义。盖庄子首明:“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人间世》)对此,王先谦引成疏云:“道在纯粹,杂则事绪繁多,事多则心扰乱,扰则忧患起。药病既乖,彼此俱困,己尚不立,焉能救物?”[清]王先谦集解,刘武补正,沈啸寰点校. 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32。心志纯一,本立则道生,方可有救物之力。在此意义上,“存人”则是“存己”基础上对恶者的拯救与治疗。
(5)钱澄之注解道:“惟就与和,然后人乐与处而可以施吾之教。‘就,则前所谓‘达人气;‘和,则‘达人心也。就者使之可亲,而入则为所狎矣;和有潜移默化之机,而出则为所觉矣。达之入于无疵,因而利导之。”由此可见,“正汝身”前提下的“就”与“和”,可创造一和豫气息,使卫君乐与吾处,便于因机施教。[清]钱澄之. 庄屈合诂[M]. 合肥:黄山书社,1998: 69。
(6)史泰斯认为,道德行动只能立基于道德情感,只有“宇宙万物一体”的冥契意识(mystical consciousness)才能生发诸如感同身受、同情慈悲等“爱”的感受,因此成就了真正伦理关系的价值基础。参见[美]史泰斯. 冥契主义与哲学[M]. 杨儒宾,译. 台北:正中书局,1998: 447。事实上,保有如天覆地载般涵容虚静之德的至人,已然体证到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存有实相,由此生发的道德情感,应与史泰斯所说的“冥契意识”同质。
参考文献:
[1]劳悦强. 人间如森林——《庄子》内篇中的政治辩说[C]//屏东教育大学中文系.东亚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2:189-222.
[2]鄭开. 道家政治哲学发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9-22.
[3]陈赟. 庄子哲学的精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01-220.
[4]赖锡三. 道家型知识分子论——《庄子》的权力批判与文化更新[M].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1-42.
[5][晋]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 南华真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8:80.
[6]林明照. 先秦道家的礼乐观[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133.
[7][清]宣颖.南华经解[M]. 曹础基,校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30.
[8][宋]吕惠卿. 庄子义集校[M].汤君,集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9:63.
[9]钟泰. 庄子发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5-86.
[10][清]张玉书,等,编纂. 康熙字典[K].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1-42.
[11][清]王夫之. 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9:30-31.
[12][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M]. 张京华,点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8.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