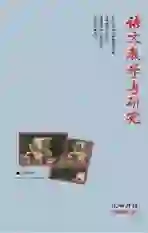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贬谪诗文艺术特色及情感类型
2020-07-18杨丽莹
杨丽莹
贬谪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惩罚制度,指臣子或因上谏冒犯统治者被放逐,或因党争失败、小人构陷等原因调任至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所谓“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困顿的谪居生活没有造成中国古代文学土壤的贫瘠,反而孕育出不少动人心魄的佳篇。尚永亮教授曾言“一部中国文學史,很大程度上是由迁客骚人的低吟高唱所构成”。[1]经过一代代迁客骚人的创作积淀,贬谪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主题。而一些经典的贬谪文学作品,始终活跃在各版本的语文教材中,如《记承天寺夜游》《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琵琶行》和《赤壁赋》等。这类贬谪文学作品在文学涵泳、文化思辨与现实教育方面都有较高的价值,值得语文教师特别关注与钻研。
一、教材中贬谪文学的艺术特色探析
语文教材收录的贬谪文学作品多语言凝练、结构严谨、手法精巧,有着丰富的文学涵泳价值,是古代诗文中的上乘之作。教师在面对这些贬谪诗文时,除了孤立地、具体地钻研每一篇课文之外,还要建立类文意识,在宏观上把握这一类文的艺术特色。这有助于加深教师对课文的解读深度,拓宽教材中贬谪文学作品的授课思路。下面笔者将从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的常见意象、用典类型和独特的地理书写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常见意象
叶朗认为“意象世界必然是带有情感性质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2]。诗人常借“象”委婉地表达言不尽的“意”,读者透过“象”能感知到他们隐秘的精神世界。贬谪文学中的意象是打开贬谪文人心灵世界的钥匙。教师在执教贬谪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把意象当作抓手,让学生借此更好地进入文本,体会诗文情感。笔者整理了中学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常见的意象:月、江水、扁舟、香草、子规、孤鸿、风雨、杨花。
“月”在教材贬谪诗文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第一,月是寄寓相思的凭信。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与张若虚的“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异曲同工。第二,月体现了诗人的旷达与平和。这在苏轼的诗歌中体现得较多,在《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少不了平和、安宁的月的影子。明月始终悬挂在夜空中,不论寒来暑往、朝代更迭,它阴晴圆缺始终如一。相较于人有限的生命,诗人面对这轮周而复始的明月,自然会生出了超越空间束缚的愿景。苏轼是个达观的人,他在被贬谪后不断调整,终于如愿驰骋在山水间,获得精神的祥和与宁静。相对的,有的诗人从不断阴晴圆缺的月象中,看到的是孤寂与清冷。第三,“月”也寓意了人生的不圆满,如苏轼的“缺月挂疏桐”和张孝祥的“孤光自照”。贬谪文人常饱受远离亲朋与国都的痛苦,贬谪文学先天就带着一丝孤独的生命底色。他们在偏僻的地方遥望一轮明月时,或许会对仕途生出几分幻灭之感。
与之类似的是“江水”和“扁舟”。《论语》中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诗人们常用“江水”寓指时间的永恒。一江滔滔河水,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止。“一杯还酹江月”之所以引人无限遐想,“江水”意象积淀了丰富的内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扁舟”在《赤壁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用来表现个人的渺小。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写于诗人因谗言被罢官,途径洞庭湖之时。他说月光照拂的湖面三万顷,而自己只有“扁舟一叶”。这里诗人同样借扁舟喻个人的渺小,以展现自己在世上的无力感。这里还要提一句,“扁舟”有时还隐含一种向往归隐的意向。范蠡棹一叶扁舟消逝于江湖,给予了后代文人无尽的遐想。贬谪文人在政治受挫后,归隐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选择。苏轼也写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句子,张孝祥身处范蠡隐去的洞庭湖,未必没有一丝隐意。
“子规”也是贬谪文人笔下的常客。蜀王杜宇相传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夜夜哀鸣啼血,“子规”喻极度的哀痛。李白听闻王昌龄被贬时想到的景象是声音凄凉的杜鹃;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他听到的也是令人忧伤的子规声。文人对贬谪的惊惧,造成了他们在使用意象时常不自觉地想起死也不甘的杜宇,仿佛自己的心也随着声声子规啼血。
“香草”意象的产生便与贬谪文学紧密相关。“香草美人”的传统由贬谪文学的代表人物屈原开创。屈原在《离骚》中大量使用了各类香草意象,以“茝”“蕙”“荷”等喻指高洁的品格。同为贬谪文人代表的柳宗元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传统,他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用到了“芙蓉”和“薜荔”两个意象,也以香草自喻,来表明自己对节操的坚守。
(二)用典类型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事类”是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3],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援用古代相类似的事件来辅助表达情意。刘勰“事类”的概念其实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援用古代的历史事件,一是直接引用前人或书籍中的文字。本文所说的“用典”指的是“事类”的第一种情况。通过整理,笔者发现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用典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伤己型用典,多怀屈原贾谊。
感怀伤己是贬谪文人共有的情感基调。后代被放逐的士大夫,很容易与历史上被贬谪的名士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诗人们在诗歌中除了常用屈原的典故,如“湘水无情”,还经常缅怀贾谊。贾谊继承了屈原的骚赋传统,被认为是自屈原以后贬谪文学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他曾被贬长沙王太傅,有三年谪宦经历,途径湘水的时候想起同样被贬的屈原,作了名篇《吊屈原赋》。刘长卿一生也两次遭贬。他被贬谪长沙后望着同样的湘水,写下了《长沙过贾谊宅》这首七律来追悼贾谊。他借贾谊和屈原的典故,表达了自己被贬的伤感。七年级下册有一首同题材的诗——李商隐的《贾生》。两位诗人都吊贾谊,引典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意在表现政治才能无人赏识的忧伤。
第二类,励志型用典,好引三国人物。
三国风流人物在中学语文教材选录的贬谪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较高。部分贬谪诗人在现实中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只能将希望寄寓到虚无的文学世界中。他们向往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三国名士般傲视群雄,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刘梦得被贬,在被多次的羞辱后,借“诸葛庐”和“子云亭”的典故激励自己身处斗室亦不能屈服。居陋室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已是不易,坚守节操、只与志趣高洁的人来往更让人敬佩。陆游在《书愤》中也用了诸葛亮的典故明志,以此展现自己渴望为国效忠、浴血沙场的豪情。苏轼也曾以孙权自比,来表现自己的抖擞面貌,着实进行了一番自我感动。此时的苏轼对仕途还抱有一丝希冀,所以许下了“遣冯唐”之愿。而在《赤壁怀古》中,苏轼对周瑜典故的情感态度变得更为复杂,诗人既崇拜羡慕周郎,亦感叹如此风流人物最终也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三)地理书写
在贬谪文学作品中,地理坐标常有独特的空间隐喻和文化内涵。曾大兴认为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各具特色的地理空间,“既有客观世界的投影,又包含文学家的主观想象、联想和虚构,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也是地理思维与文学思维的统一”[4]。也就是说,诗文中所提及的地理坐标,常常不仅指向现实中真实的地点,还被赋予了一些额外的情感隐喻。
在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中,“五溪”本身不仅指今天湖南黔阳一带这个地方,还隐含了一份不舍与怅然之情。学生多从“左迁”“子规”和“愁心”等词语中感悟到诗中愁绪。但若隐去题目和前后文,我们能否单从这个句子里体味到一丝不舍与怅然呢?明代屠龙在《彩毫记·妻子哭别》中写“别亲知,走天涯,过龙标、五溪,我怎顾得路崎岖”。人尚未启程,仅仅只是想到亲友要前往“五溪”“龙标”就已忧心忡忡。这种情感跟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就感到强烈的担忧并急忙写诗劝慰非常相似。一个文人对地理环境的书写,可能是他个人审美趣味的体现。但针对相近的地理坐标,如果多个文人出现了相同的情感倾向,那这背后可能隐含着一些关于地域文化的默契。“龙标”“五溪”地处偏僻,路途遥远,行旅在外实属不易。蒋长栋曾在《王昌龄龙标之贬考论》[5]中考据,王昌龄此次被贬应于天宝七载九、十月出发,大约在第二年春末或夏初才达到龙标。刘禹锡在《读张曲江集》中亦言“逐臣不得与善地,多五溪不毛之地”。因此,“五溪”在文人的潜意识里已经与荒僻遥远相关联,这个地点本身就带着一层怅然若失的意味。
在教材选录的贬谪文学作品中,韩柳笔下的“岭南”也是富有隐喻性的地理坐标。中国自古有南贬的传统,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官宦自然是避之不及。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立志“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们,对岭南的书写常带有贬义意味。韩愈被贬“潮州”后有“好收吾骨瘴江边”。他从岭南的瘴气里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直接点出了岭南环境的恶劣,读来颇让人惊心。柳宗元亦有“岭树重遮千里目”之句。诗人登上柳州城楼远眺,却只看得见重重叠叠、烟瘴缭绕的荒山。这些绵延不断的山峦不仅断送了他的仕途,还阻隔了他与友人的情谊,仿佛是一座囚笼让诗人寸步难行。
此外,柳宗元还花了大量笔墨对“永州”进行地理书写,完成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永州的奇山异水有时在柳宗元心目中是凄寒可怖的存在,比如《小石潭记》中的“其岸势犬牙参互,不可知其源”。一些学者将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解读为“贬黜生活的象征”[6]。柳宗元笔下的山水呈现出一种无人欣赏的状态。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解读。在“永州八记”的其他几记中,柳宗元笔下的山水也常常是幽深怪异的,时有“深林”“回溪”和“幽泉怪石”之语。而且永州多火灾,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永州寓所“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几次火灾无疑对困顿的柳宗元是雪上加霜。永州凄清可怖的印象是他作为贬谪文人在遭遇交游受阻、亲友离世、永州寓所四次大火等重重伤害后,心理感到孤独、被遗弃的写照。总而言之,贬谪诗人对地理环境的书写,常常流露出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倾向。如果说“五溪”是旅人充满未知的天涯,“岭南”就是让迁客惊惧的囚笼,那“永州”便是被弃者无人问津的寓所。
二、教材中贬谪文学的情感类型归纳
贬谪是古代文人心中共同的隐痛。不同时代的迁客骚人,总能产生一些精神上的共鸣,达成情感态度上的默契。贬谪者在诗文中呈现的情感态度,除了受性格影响外,还可能受政治环境、经济收入、谪居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贬谪文学作品最终所呈现出的情感态度往往是复杂的,是作者主客观世界相互交织、激荡的写照。笔者归纳出四种教材中贬谪文学作品主要的情感态度类型。这些情感在同一篇课文中可能同时出现。笔者希望借此为教师厘清作品情感层次提供一点帮助,而非倡导教师将诗文放入情感类型的框架中去。教师要从文本出发,再对具体的文章进行反复揣摩、品析,感受每篇贬谪诗文的独特魅力。
(一)讽刺奸佞,幽怨不平
在古代中国,被政敌构陷是文人被贬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受到诬陷的官宦失去统治者的信任,被流放或贬谪自然满腹牢骚、心存怨怼。因此,贬谪者常在诗文中讽刺趋炎附势的小人、埋怨君主识人不明。讽刺奸佞、幽怨不平是贬谪文学最原始的情感态度类型。这在贬谪文学模式的确立者屈原的《离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后代贬谪文人或多或少继承了“忧愤怨刺”的传统。
《离骚》虽然创作时间存在争议,但其产生与屈原的流放经历定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言,“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我们在《离骚》中至少可以读出两层情感基调。第一层是屈原对君王不贤明的埋怨。屈原的“美政”思想對君主有很大的期待,他希望楚王可以选贤举能、除奸佞,复兴楚国。但现实是残酷的,楚怀王并不是屈原理想中的君主,顷襄王亦不是。第二层是屈原对君主身边小人的强烈鞭挞。“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屈原认为君王身边的人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扰乱了君主视听,所以国家遭受了严重的伤害。真正忠君爱国的自己,却因为高尚的品性不为小人所容,这是莫大的讽刺。他的笔下时刻洋溢着幽怨不忿之情,诗人偏要作不群的“鸷鸟”,绝不作阿谀奉承之态,即使身死亦不妥协。
后世的许多文人都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在被贬谪后也借诗文来倾吐心中的怨愤不平。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就是一个例子。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写出了“密雨斜侵薜荔墙”的诗句。这个句子颇有屈原离骚风韵。作者以香草自比,细密的雨象征了朝中佞臣权贵。“斜”字非常巧妙,写出了对方来势汹汹之感,又体现了自己受攻击的无助。然而即使对方声势再浩大,密雨也无法毁灭自守之人。总而言之,讽刺愤慨与幽怨不平是中学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最常见的情感类型之一。这与屈原开创的“骚赋”传统密切相关。
(二)坚守冰心,且济天下
因仗义直谏或不愿与人同流合污被贬谪的文人,在遭遇苦难时常常不仅不会退缩,反会生出“穷且益坚”之感。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不少贬谪文学作品都体现了作者虽身处逆境,却不忘坚守节操的情感态度。这些作品除了表现诗人对自我高尚品德的坚守,还可能体现了士大夫要时刻不忘兼济天下的更高追求。体现了“坚守冰心、且济天下”这类情感态度的代课文,有《陋室铭》《梁甫行》《岳阳楼记》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
教材编者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赏析部分评价:韩愈“左迁”后,没有屈服于失意的现实际遇,反而愈发激亢,誓要将一腔不平诉诸笔端,颇为坦荡豪迈。韩愈因为谏迎佛骨,朝夕之间被贬潮州。韩愈深知自己年事已高,可能此去山高路远的潮州不能安然归来,但他仍表达了自己九死未悔的决心。他甚至在蓝田见到孙湘时发出更加悲壮的“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誓言。现实中的政治磨难不仅没有让韩愈退缩,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强化了他对自己政治节操的坚持,让诗人的贬谪命运更添一丝悲剧性。
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安徽和州,并屡次受到和州知县的刁难,被迫搬了三次家。面对前两次搬家,“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重在表现自己不忘政治初心,不屑于向对方屈服,尚比较平和。直到第三次被迫搬到一间斗室,刘禹锡才忍无可忍写下了《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刘禹锡对弄权者的挑衅,也是他“贫贱不能移”的自励。“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体现了他不愿屈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我们两相比较,会发现如果说他前两次搬家的态度是无视弄权者,不屑与小人辩驳;那“无白丁”就是毫不留情地直面讽刺。被压迫得愈狠,愈会给贬谪文人以正面的心理暗示;文人越是被排挤,越要坚持操守、不改初心。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则更多体现了士大夫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执着。“先忧后乐”的思想源自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当然,孟子意在谈如何做一个好的君主,他说这段话的目的是规劝君主施行仁政。而范仲淹将这种思想延续到了志在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心济天下的士大夫身上。朱熹曾夸范仲淹在通晓经义后常诵读“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类句子,是一个“慨然有志于天下”的读书人。这种情怀在他被贬后所作的《岳阳楼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范仲淹在这篇课文中,高度赞美了与他遭遇相同贬谪命运的滕子京。巴陵郡在滕子京的治理下变得井井有条,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范文正公心目中,滕子京既不是因被排挤出政治中心感怀自伤的迁客,也不是在山水间慰藉身心、获得暂时精神愉悦的谪人,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品德高尚之人。前面两种人本质是独善其身,他们沉溺在个人的喜怒哀乐之中。在范文正公心目中,滕子京的高尚在于他即使被贬是失意落魄之人,也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不论身居何处,他始终不放弃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行动了,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话只短短七字,却是本文在情感表达上至关重要的一笔,既表达了对滕子京的敬佩,也勉励自己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怀兼济天下之心。
(三)观照自我,孤寂怅惘
“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士大夫神圣的理想,莘莘学子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舉,入庙堂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对这些文人来说,贬谪带来的生命体验是深刻而极致的。首先,被贬意味着他们要饱经颠簸,前往千里之外的南方。南方瘴气严重,在医疗卫生水平较差的古代,被贬文人在路途上有丢性命的风险。其次,南贬意味被排挤在政治主流之外,他们的前途充满了未知,这极大地阻碍了文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重要的是,一些被贬者的罪名多为政敌恶意罗织。政客断章取义、故意歪曲式地解读诗文,除了让无辜获罪的文人们名誉受损,还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新党收集苏轼的诗作,曲解其包藏祸心、对君不忠,制造了差点要了苏轼性命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虽逃过一死,但这段经历无疑对他造成了不小的精神伤害。他初到黄州仍对这桩冤案心有余悸,我们从八年级下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寂寞沙洲冷”中,能读到诗人灵魂深处的恍惚与孤寂。一些文人在被贬谪后变得格外敏感多疑,在一段时期内会沉溺在对自身的审视与观照之中,常对自己的境遇表现出消极的思考。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孤寂怅惘的情感基调。
在教材选录的贬谪文学篇目中,体现这类情感的代表性古诗文还有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柳宗元在《小石潭记》的前面部分花了不少笔墨写小石潭水声的清脆悦耳、小溪的蜿蜒曲折。试想如果是陶渊明来写小石潭,他可能会由此生发出对深林野趣的欣赏、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但突然被贬永州的柳宗元全无这种闲情逸致,他的内心是愁闷辗转的。永州的山水只能给他暂时的慰藉,并不能抚平他精神上的伤痛。无人欣赏的景色时刻提醒着柳宗元他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山川风物背后隐藏了无限的失落。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言“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这种被遗弃感不仅源于仕途受挫,还来自于现实交往的困境。他的身体状况也并不乐观,自述“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温饱”。所以,他面对这寂寥的山水再也忍不住了。他不忍再看,笔锋一转,以小石潭环境“悄怆幽邃,凄神寒骨”为由迅速离去,赋予了这篇文章浓郁的孤独凄冷色彩。
我们发现,小石潭再美,都无法真正进入柳宗元的心灵世界,因为他更沉浸对自我的观照中。这点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7]颇为契合。按理说多人跟随柳宗元游览小石潭,作者不应感到清冷才是。但作者却因为“凄神寒骨”迅速逃离了小石潭。或许,他真正躲避的是心理上的那份被贬谪遗弃后无可消除的孤独。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与其说是用来欣赏观照的客体,不如说是作者用来调节愤懑情绪的载体。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强调了审美主体地位。对他来说,他在小石潭停留得再久,恐怕也难从景象本身体会到寻访游玩的妙处。小石潭更能引起他灵魂共鸣的,是“不可知其源”的恐惧和无人涉足的孤独寂寞。在某种意义上,贬谪文人从山水中感受到的孤寂怅惘,是他们沉溺于观照自我、强调审美主体地位的结果。
(四)忘情乡野,闲适自得
徐复观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8]中国传统文化受道家思想、禅宗的影响,对山水有着强烈的偏好。人们喜爱自然中的山水,并且将山林当作自己的情感寄托。不论在现实中贬谪文人们如何困顿难行,他们一旦走进自然中,都能够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之所。这里所说的自然世界不一定指深山野林,还可能泛指古朴自然的农家生活。初中教材中的《游山西村》,高中教材中的《赤壁赋》《新城道中(其一)》《游沙湖》和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自然的喜爱,表达了诗人享受乡野村居生活,闲适舒畅的情感态度。
陆游任职期间,因为支持将领北伐,在军队战败后被主和派弹劾归乡闲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游写下了《游山西村》。作者笔下的乡野生活和谐,村民淳朴热情、安贫乐道,诗人对这种生活的满足与向往表露无遗。除了与农人的交往令人愉悦外,山水也让陆游感到兴奋。他从村野中甚至看到了无限的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是作者给自己的鼓励。山水成功慰藉了他失意的心灵。陆游从乡野中获得了平静,并与农人许下了“闲乘月”的约定。这里的“闲”不仅指陆游身体得空,更暗示了他希望以后能像这次出游一般,获得精神上的闲适惬意。
被贬谪的苏轼在游览山水时,更加尊重客体的审美性,让自己向自然事物靠拢,并从中体悟到超然自得的乐趣。苏轼本身是一个达观的人,他在黄州的山水中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周瑜、曹操即使当年风流得意,也终被历史的洪流吞噬,成为一朵浪花。作者借此安慰自己不必过于在意现实中的得失。接着,他又在自然事物中看到了真正的超越时空的永恒:只有一轮明月,阴晴圆缺周而復始;一河江水,从古到今潺湲不绝。于是苏轼将自己的精神提高到了更虚无的境地,在精神上与山水融为一体。通过忘情山水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人格、获得精神自由的方式,延续到了他晚年的谪居生活中。苏轼晚年被贬谪到岭南时,创作了不少和陶诗,曾在《和陶游斜川》中言:“谪居淡无事,何异老且休……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从这首诗中,我们发现苏轼对自己晚年谪居乡野的生活状态是满足而享受的。他面对一江春水,只想乘一叶扁舟随意行止,无所羁绊。现实中的年老体衰、政治不断受挫并没有打击到苏轼,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尊陶”意识。他对陶渊明所代表的隐逸精神充满热情。如果说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面对一江水月的心情还存在几分争议,那么他在年老时再观山水所作的这首贬谪诗,则无疑全然是平和与闲适了。
三、结语
贬谪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贬至偏远之地,不仅给贬谪者带来了经济、环境、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更对被贬之人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贬谪者在遭受身心双重打击的同时,也被激发出一些特别的生命体验。这些体验往往让文人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拓宽了文人观察生活的视野,也带来了新的创作灵感。所谓“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困顿的谪居生活常常不仅没有造成文人创作能力的枯竭,反而孕育出不少动人心魄的佳篇。经典的贬谪诗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占了一定的分量。在艺术特色方面,“月、江水、扁舟、香草、子规、孤鸿、风雨、杨花”是教材中贬谪诗文常见的意象。诗文用典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伤己型用典,贬谪诗人多借屈、贾感叹自身怀才不遇。第二类是励志型用典,贬谪文人喜欢从三国风流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此外,贬谪文学作品中的地理书写常暗含诗人的情感倾向。在情感态度类型方面,在被贬之后,有的诗人将自己的一腔愤懑投注笔端,在高声的怨刺中宣泄心中不平;有的诗人将目光转向了内在世界,沉溺于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审视,长时间处在孤独郁闷的情感中;还有的诗人从执着走向了超越,利用山水游记、农家生活闲笔慰藉受伤的精神,在自然世界中寻求自由与解脱。教师在执教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时,不仅应深入研读每一篇具体的课文,还应建立起类文意识,在宏观上把握该类文的艺术特色与情感态度类型。这有助于教师进行深度教学,引导学生更好地探索贬谪文人的冰雪精神。
注释:
[1]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11.
[2]叶朗.美在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9.
[3]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3.
[4]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
[5]蒋长栋等.贬谪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76.
[6][美]司马德琳.贬谪文学与韩柳的山水之作[J].文化遗产,1994(4).
[7]王国维著.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7.
[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