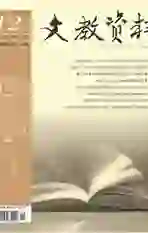拉康主体理论视域下对《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解读
2020-07-14李康杰
李康杰
摘 要: 拉康提出自我与主体存在想象性建构。作为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体现在与周围主体的差异与相似等种种关系中。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著作《道连·格雷的画像》,通过画像这一镜像符号,体现小说主人公道连·格雷以及作者王尔德本人的主体形象建构与分裂。这种主体,形成一种拉康式的悖论发展,在建构中不断分裂,又在分裂中不断建构。这种悖论式主体的形成,不仅体现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还体现在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关系中。
关键词: 拉康 主体 《道连·格雷的画像》 王尔德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爱尔兰(当时隶属英国)作家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是唯美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品,小说主要通过对美少年道连·格雷的形象变化及他者的言辞行为的描述,呈现出王尔德所秉持的享乐主义人生信条和唯美主义艺术观念。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将画像这一象征符号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能得到更好的解读。主人公道连和画像之间存在着主体与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并形成拉康主体悖论式的发展,这种主体性反映出奥斯卡·王尔德对自我主体身份的建构和探索。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小说中的主体性,尝试更深入地解读《道连·格雷的画像》这一文本。
一、自我与主体的建构与分裂
道连·格雷的人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在与画家巴兹尔和亨利勋爵的相识后,巴兹尔为他作画,亨利为他塑魂。道连的人生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父母身份地位悬殊,母亲出身贵族,父亲只是落魄穷小子,他们的爱情遭到反对,最终以父亲被外公所害,母亲随之殉情画上句号。独留道连一人被外公收养,外公与道连的关系冷淡,几乎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道连可以说成长在一个缺爱的环境之中,没有人让他意识到自我,或认识自我、建构自我,他的自我身份一直处在滞后性或者缺失性的状态中。直到遇到巴兹尔和亨利勋爵,巴兹尔为他画像,亨利勋爵在旁称赞,这种他者的赞美和凝视,让他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像时,“好像第一次才认识自己似的”“他恍然大悟似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美貌”[1](22)。正如幼童第一次看到镜映一般,他开始作为一个主体并首次把一种自主的思维知觉为其自体,并感受到了自体的存在,认识到了自我的主体性和审美价值。
拉康镜像阶段的主体认识到自我是通过差异性和同一性建构的,道连认识到自体的这种同一性亦是通过差异性来确立的。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具有自恋性质的,如同纳西索斯(Narcissus)般顾影自怜,当道连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画像时便爱上了这幅画像,爱上了画中这幅年轻美貌的面孔,他说道:“只要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该多好!为了这个目的……我愿献出我的一切!我愿拿我的灵魂去交换。”[1](22)他渴望将这种想象性的镜映形象永远留在其自体的身上,但这种主体的建构被镜映(画像)这个诱饵所欺骗,使“主体以与自己有别的形象为中心,通过只能回归他者的形式,在自我疏离的道路上接受终身背负的想象性自我”[2](59)。小说带有哥特式神秘色彩的叙述让这一想象成为可能,道连的人生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道连的主体外貌与画像中的镜映自我发生转移,从此画像逐渐变化衰老,道连的身体却青春永驻。道连成为一个想象中的自我,但这一自我不仅仅是主体的建构,更是与主体的分裂,欲望的实现使身体这一视觉形象青春永驻,但这一视觉形象却是透过他者欲望的凝视建构的,这种建构实质上是一种主体与自我的分离和割裂。这一主体从想象界通过画像这一能指实现到象征界的转化,就主体与个体而言,拉康的主体是“去本质化的”(de-essentialize),主体是他人即大他者的建构,个体是自我的建构。但这种自我的建构受制于他者的影响,因此人是无法脱离他者而存在的,这种全然主观性的建构是不存在的,但道连的问题在于无法摆脱这种自我建构的全然幻象,沉醉在他者凝视下的自我幻象,并通过这一幻象与最初和谐的自我构建形成分裂。拉康指出:“主体借以超越其能力的成熟度的幻象中的身躯的完整形式是以格式塔的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获得的。在这种外在性里,形式是用以组成的而不是被组成的,并且形式是在一种凝定主体的立体的塑像和颠倒主体的对称中显示出来的……这个格式塔通过体现出来的两个特征,象征了我在思想上的永恒性,同时预示了异化的结局。”[3](91)从这点上看,道连最后悲剧性的死亡从他意识到这种自我后就已埋下了伏笔,自此道连的主体便一直处在一种灵魂肮脏却外表靓丽的异化状态之中直至毁灭。
在小說中画像所代表的青春美貌是一种幻象,是道连的主体与画像(视作小客体)的“不可能的”关系,小说中将主体与欲望的客体满足了其可能性,幻象被设想是可以实现主体欲望的场景。画像正如拉康的小客体是那个剩余、令人难以捉摸、令人难以信以为真的东西。小客体通过画像成为青春美貌的象征,形成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换,只作为自我的主体已被置换到我的主体。正是这么一种虚假之物,驱使道连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以享乐主义为信条肆意生长他者的欲望,道连的自我与主体都变成一种大对体的凝视(gaze of the Other ),从而与最初的主体割裂,建构出一个分裂的自我。这种建构是悖论式的存在,既使道连认识到了自我,这种自我的认知又将主体与之分离。
二、画像的符号含义
正如拉康所说:“主体是一个能指对另一能指所表征的东西。”(the subject is that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one signifier to another)。“能指并不是标记失去、欠缺的事物的符号,而是把消除行为而残留下来的自身的痕迹交给为未来”[2](103)。在小说中画像作为能指符号一直推进情节的发展,当代英国艺术史学家诺曼·布列逊认为“绘画艺术的认同行为是指产生意义而非知觉意义的过程。凝视行为可以不断地将绘画的形式转化成意义,而这种转化难以阻挡”[4](349)。拉康的镜像理论特别强调视觉的作用,我们对于自我的建构是通过视觉观察(误观察)在镜像阶段的想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种建构是不稳定的,拉康认为镜中的幻象同时带来了自我的异化。同样,在小说中自画像的形式使道连认识到“我”作为一个整体符号时,主体与自身便不再和谐了。这种自我的形成由于画像这一能指符号的介入标志着对自己的沉迷与异化同时开始,尽管道连的真实身体与画像存在明晰的空间联系,但这两者却分处于不同的位置并导致了“我”的分裂。画像成为主体与在镜像阶段丧失自我发生际遇的潜在场所,成为脱离以主体意识的异化为前提的完整性的假象符号。
道连的画像这一符号在小说中实现了由小他者(little other)到大他者(capitalized big Other)的转变。“小写的‘他者始终指涉着想象的他者。我们把这些小他者看作是完整的、统一的或是一致的自我,并且把它们看作是给我们赋予了完整存在感的我们自身的映像”[5](94)。在小说中,巴兹尔给道连·格雷作的画像即是让道连假定会完全满足自己欲望的镜子阶段的介入他者,与此同时道连也将自己看作这个他者欲望的唯一对象,所以画像承载了想象性他者的欲望。但主体的欲望与大他者是难解难分的,主体与镜映(画像)产生想象的二元对立由亨利勋爵的介入打破,道连的主体由想象界迈入象征界,由此画像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大他者的作用得到体现,“大写的他人于是就是那个由讲话的我和听话的另一个组成的地方。……反过来,这个地方延伸到主体中所有由言语的法则统治的领域,也就说远远超过了从自我那儿得到指令的话语的范围”[3](416)。由此可知,“大他者则是我们无法与自身的主体性进行同化的绝对相异性。大他者即是象征秩序”[5](94)。象征秩序可以说是主体的语言,欲望的表达来自语言的言说,但这种言说体现着周围人的辞说和欲望,正是经由他们的辞说和欲望,主体才能内化并扭转为自我的欲望。亨利勋爵的辞说和欲望对道连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道连的为人处事受到亨利价值观的深度影响,亨利人生享乐的信条植栽在道连的潜意识中,并潜移默化地通过画像体现出这种变化。画像最初象征的年轻美貌代表着亨利所赋予道连的欲望,亨利的欲望与愿望便经由语言流进了道连的骨血。道连的欲望由亨利勋爵这一他者塑造并形成,而画像则是这个欲望的表现,抑或者通过大他者并于在大他者的关系中而形成,由此欲望的等价物即画像跟亨利勋爵的无意识辞说构成了道连·格雷这样一个丧失了自身的缺失的主体。正如拉康式的主体在本质上是“虚无”(nothing)一般,道连的画像也在包含的意义中最终在结尾恢复如初,因此丧失了一切拥有的意义和本质,由此完成一个能指链到另一个能指链的滑动。
借用拉康对需求与要求作出的区分,画像完成了从需求(need)到要求(demand)的转变,体现在它的使用价值被交换。道连用外表的美貌和人性的沦落做交易,签下浮士德式的交易,在这个过程中画像的存在成为一种欲望,与此同时構成了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网络的索引。我们在要求某个物品时,最终目的并非用它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确认他人对我们的态度[6](6)。画像所代表的美貌并不是仅仅用来满足道连的“需求”,更是确认他人对他的态度,如小说中写到他人对道连的态度是:“他纯朴的脸上总有一种申诉的表情。只要他在场,他们就会回忆起自己失去的天真,并无不感到惊奇,这人如此迷人,如此高雅,却能不受这个肮脏而又声色犬马的时代的污染。”[1](106)由此可以看到画像的符号象征已内化在道连身上。画像作为一个参考的符号,将道连所做的恶都在画像上留下了痕迹,正如小说最后道连看着画像认为“画像给他的情绪增添了忧郁。无数快活的时刻,只要一想起它就兴味索然。这东西像是他的良心。不错,已经是他的良心了”[1](184)。此时,画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占据了他的主体,画像抑或是良心所留下的痕迹体现出道连在道德上的沦落、内心上的丑恶及他人对道连态度的逐渐变化。这种双重符号意识下的变化,体现了画像这一符号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变化。从这种立场来说,画像便充当故事真正的主体,这幅画像是故事中真正的主体间关系的模式,画像是一份象征契约,是一个能指,画像这一能指占据着主体,正是这种能指把道连这一主体写入象征秩序之中。
三、外界对主体欲望的建构
欲望不是事先赋予的,而是后来建构起来的。欲望是事先被赋予的,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对象,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这种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为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欲望[6](9)。寻觅欲望就是欲望的实现,欲望的实现并不在于它的全然满足,在于一种拉康悖论式的欲望:欲望是逐渐建构起来的,欲望在于自身的延展和扩散。道连与亨利勋爵的交际使他一步步走进欲望的循环,例如道连对上流社会的迷恋、深入乃至难以逃脱。这种欲望的循环使他进入了一个与最初目的相违背的异化阶段,他最初是追求美的,但等外貌的美得到后,不仅没能完善他,反而最后使他迷恋上了丑恶,走向了欲望循环圈中的另一端,正如小说描写道:“丑恶曾一度让他讨厌,因为丑恶给人一种真实感。而现在却因其真实,反觉得可爱了。”[1](153)这种欲望的建构在小说中正是亨利一类的他者所赋予主体的。
道连的欲望充斥了整个主体,欲望的建构通过外界、他者的凝视完成。“主体透过群体的眼睛审视自己,并极力争取群体的爱戴和尊敬”[6](176)。画中的道连自我可以说是想象界的自我,这一自我同时代表着他者,并分裂了我的认知。镜中自我是不断作为标准的客体,通过他者的认同和客体的变化形成自我的主体意识,并最终让想象的自我进入象征界,使目的与目标发生割裂:目的在最终欲得,目标在整个过程。“这种驱力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目的(即完全的满足),而在于它的目标,最终目标是不断地复制欲望,是回到欲望的循环之处。快感便是来自于不断重复的循环运动”[6](5)。道连回到自身的年轻美貌即是一种快感的循环运动,道连在内在性(道德)本我的随性解放和外在性(美貌)自我的完美建构,带来一种本我和自我之间快感与沦落的极端性审美快感。但这种快感来自于自我和本我之间原有的不平衡的平衡性,是主体剩余快感的恐惧客体,道连越是恐惧画像变化带来的不安,越是变得肆无忌惮地纵恶享受。如同“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7](6)。这种痛苦的不安反而带来一种受虐式、审美式的快感,使道连陷入西西弗斯式的自我论证与过程的重复之中。
拉康曾提出康德即萨德,在康德伦理学体系曾提出婚姻是对“两个成年异性签署的彼此使用性器官的合约”,亨利勋爵这一形象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亨利勋爵对婚姻的轻蔑,以及他对爱情、对人生都围绕着享乐主义,正如他认为:“唯有享乐值得有理论。”[1](66)更提出“现代道德就是接受自己时代的准则。我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人接受自己的时代的准则是最不道德的表现”[1](66)。亨利勋爵对道连来说便是一个如同萨德般的存在,即使道连决定“他会拒绝诱惑。他再也不见亨利勋爵了——至少不再听他的话,那些难以捉摸的有毒的理论”[1](77),最终无法抵挡这种潘多拉魔盒式的诱惑。道连欲望的异化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超越的,这种异化表明欲望本身是一种缺失。正是通过亨利勋爵这一他者,道连作为主体才确立了自己在社会象征秩序中的位置,亨利勋爵赋予了道连主体象征性的欲望,正是透过亨利勋爵的欲望,道连自身的欲望才得以建立。
道连主体的建立主要建构在这种与外界的关系之中,通过一种连续的异化与分离进行主体化过程。道连这一主体是替代性的,外界的欲望几乎填满了道连。只有在小说的结尾,即道连将匕首捅向画像,自己却倒在血泊的时候,才最终承担起了自己作为主体的责任。道连·格雷的悲剧,如拉康分析哈姆雷特这一形象般,可以说是一个主体被悬置于大他者的时间之中的悲剧。
四、王尔德的自我建构
如果说在小说文本中道连的形象受到他者的建构的话,那么不同的是在现实叙述中道连的形象则受到王尔德本人的建构。王尔德的自我建构是偏向于主动性的,是一种对自我的审美性建构,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可以说是一幅为他自己所打量的文学理想形象,是王尔德的自我构建与审视,书中的形象和人物观点都体现着王尔德的思想和个人生活。福柯曾提出:“我们必须审视理解那些审慎的和自愿的实践,人们通过它们不仅确定了各种行为的规则,而且还试图自我改变,改变自己独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和反映某些风格标准的作品。”[8](112)福柯的这种把自我活成艺术品的观点与王尔德不谋而合,除了相同的观点外,在生活中这兩人同是性少数群体。王尔德本人是一个同性恋者,作者在塑造作品时会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生活折射到作品之中,因此他书中人物的自我建构与他本人的自我建构都不可避免地与性少数群体有密切关系。《道连·格雷的画像》写于一个同性恋被禁止的时代,王尔德本人因为与同性恋人波西(道格拉斯)的关系被告入狱。《道连·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所有作品之中最明显涉及同性恋主题的一部,甚至小说主人公道连·格雷的命名与其情人之一约翰·格雷也有着密切地关系[9](72-73)。王尔德在狱中给恋人的信中曾写道:“我的人生有两大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进牛津,一是社会送我进监狱……我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太典型了,以至于因为我的乖张变态,为了我的乖张变态,把自己生命中好的变成恶的,恶的变成好的。”[10](76-77)
《道连·格雷的画像》的结尾具有明显的哥特式风格,故事的结尾荒诞离奇,在道连将刀刺向画像的时候他却倒在了血泊,以恐怖奇异的哥特式效果收场。“哥特式小说的奇怪命运承载着英国同性恋这一社会角色的变化,早期的哥特式小说的奇怪命运在十九世纪成了一种表现贵族同性恋角色的方式。而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之后,‘贵族角色已经变成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同性恋男性最重要的可用角色。这种哥特式的不可言说属于贵族的同性恋风格在二十世纪之交,伴随着恐同风格席卷了中产阶级,带来了复杂的政治效应。而《道连·格雷的画像》则成了或被用作同性恋风格和行为的指南手册”[11](117-119)。从这一角度看,王尔德作为受过顶尖教育的中产阶级,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让王尔德声名狼藉的诉讼官司源于他同性恋人的父亲对他的言语羞辱,这场官司可以看做王尔德的自我选择和建构。“在某种程度上,王尔德之所以沦为牺牲品,不但是出于昆士伯里父子的故意,也是他自己的故意。他倾向于自我背叛,他把它看成潮涨,然后会有潮落”[12](589)。朱迪·巴特勒曾提出:“同性恋的职业化,要求某种程度的表演和对于‘自我的制作,这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尽管这一话语声称它先天真理的名义‘代表了自我。”[13](335)王尔德这一主体可以看作一个自我的表演性的建构,王尔德的主体是通过反复的表演行为和话语建构起来的。同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是通过反复的表演行为和话语进行建构。正如王尔德认为小说中的三个角色折射了他自己的形象。他曾向一个记者解释道:“我自己认为自己是巴兹尔·霍尔沃德;世人以为我是亨利勋爵;道连是我想成为的人——也许是在他的时代。”[12](432-433)
剧场与扮演息息相关,阿兰·布莱(Alan Bray)曾指出,英国伦敦的剧场是英国同性恋亚文化群的一个集中地[14](147)。剧场被看作同性恋亚文化的存在地,王尔德本人也是一名相当出色的剧作家,与其小说的塑造有着紧密的联系。《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有着大量的剧场的描写,其中道连与西比尔的恋情的始末全部贯穿于剧场之中,可以看到剧场与小说主人公的关系、剧场与王尔德的关系及小说主人公与作者王尔德的虚实关系,都体现出相关的融入和建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虽然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出来的,即以上帝视角来叙述出的,但这种叙述方式似乎显得较为公正和客观,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以隐形的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述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叙事性投射(narrative projection),例如在小说中关于画像的变化,是道连自己觉得画像要吞噬他,这是道连个人的叙事性投射,也就是说是他把自己恶的欲望和实现投射在画像上身上。但当这种恶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他的自我与主体出现间性,这种间性最终导致主体与主体的欲望客体发生矛盾性间离,主体的欲壑难填终致分裂性的自我毁灭,道连生命的主体性已被欲望客体带来的死亡所遮蔽。
将道连的人生际遇同王尔德本人进行联系,可以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同从落魄底层跃至上层,人生都秉持着享乐和唯美的信条。从这个角度上,小说体现了王尔德的个人投射,他通过作品创作建构并审视了自己,并通过对道连悲剧性命运的揭示写出了对自己所秉持的享乐主义的惩罚的预见。
五、结语
拉康悖论式的主体与王尔德塑造的角色及本人有着双重性的建构与分裂。这种主体与主体欲望的客体的间隙如芝诺论证阿基里追龟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陷入一种主体的悖论,即主体无论如何努力自我建构,都逃不出欲望客体的掌心。即这种自我建构造成自我分裂,在这一过程中,王尔德用作品和自体勾画出痛苦、恐惧、极端,并最终汇聚进非理性主义思潮。王尔德用唯美主义文学在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间搭建了桥梁,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重估一切价一般值,认识到理性只是手段,生命才是目的。不同的是王尔德用《道连·格雷的画像》和自我主体对生命进行回答,以享乐主义的思考和至美追求的价值在人类主体的探索进程中写下独特的一笔。
参考文献:
[1][爱尔兰]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M].黄源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法]拉康(Jacques Lacan).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美]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英]霍默.导读拉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6][斯洛文]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8][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杨霓.王尔德“面具艺术”研究王尔德的审美性自我塑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0][英]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汉英对照[M].朱纯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11][美]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12][美]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逆流,1895-1900[M].萧易,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3][美]葛尔·罗宾(Gayle Rubin),等.酷儿理论[M].李银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4][美]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M].赵炎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指导老师:郭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