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游文史 重度青春
2020-07-14程毅中
程毅中

24年在文史馆重度青春
我在中华书局退休之后,于1995年12月应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对我来说,是我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的一个新岗位,也给了我继续学习、继续工作的好机会。因为我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履职后馆领导就分配了几项工作给我。一是协助吴小如先生编内刊《诗书画》的文字部分;二是参与审读《世纪》的清样;三是承担了馆员文选《崇文集》初编和续编的责任编辑工作。
这是我本职工作的继续,也是向前辈老馆员学习的机遇。他们是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我有幸阅读他们的著作,聆听他们的高论,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和见识。在编辑《崇文集》时,我跑了几个图书馆,搜集前辈老馆员的文章,顺便把他们的著作目录都记录了下来。后来编辑诗选《缀英集》的时候,我就推荐了不少散见于各处的诗篇。我本想编一个老馆员著作书目的初稿,做了一些卡片,最后移交给中华诗词研究院备查了。我也写过一篇《张伯驹与辛卯重三承泽园禊集》(《中华书画家》2015年8期),为馆史做了一点补充。
2007年前,我们的《诗书画》每年都要征集馆员的新作,我自己也总得交几篇诗和文章。还曾与《人民政协报》合作,提供馆员的文章,设了一个《文史余谈》的专栏,可惜不久就停了。中央文史馆对我个人的研究工作,给了许多支持。2015年特为我聘了一个助手,帮我通读《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修订本的清样和校注《宣和遗事》里的《李师师》篇;2016年又资助我《宣和遗事校注》的项目,至今已完稿待印。24年来,我在文史馆度过了第二个青春。
为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言献策
馆员虽然没有固定的调研报告任务,但也负有建言献策和咨询的责任。在多次国务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总理都一再号召我们要建言献策。我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及有关文化建设较为熟悉,也有兴趣,因此曾屡次写出建议或报告提交国务院领导,总能得到及时的批示。我最受鼓舞的是2014年2月提出的《关于古籍数字化需要加强统筹工作的建议》,刘延东副总理及时批转给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同志,立即推动了古籍数字化工作的进度。中国出版集团抓紧了这项工程,大力支持了有关的出版单位,就迅速见到了成果。
我在学习使用数字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益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认识到古籍数字化是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新事物,是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其意义将会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需要由政府部门来做全面的统筹工作,所以大胆越位,提出了一知半解的建议。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策划下,中华书局就迅速行动,以古联公司的《中华经典数据库》为基础,加快了工作进度,并联合了巴蜀、齐鲁、华东师大、辽海、天津古籍、凤凰等六家出版社,扩展了收书范围,陆续完成了四期数据库,于2017年1月正式上线,产生了很大影响。继而又扩大联合,加入了三晋、上海书店、岳麓、三秦、上海辞书、安徽教育等出版社的合作,到2018年底完成了第六期数据库,并升级出籍合网。现在已经收书2694种,达到了12.5亿字。上线之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赞赏。我曾参与过一些活动,也有一分成就感。
当然,古籍数字化的课题很多,前途很广。我还要呼吁,在经过机构改革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下,希望继续开展大联合、大数据的工程,在已有的《中华经典古籍库》之外,不妨推动第二、第三个古籍数据库,比如以上海古籍为中心再建一个数据库,以匡现有人力、物力之不足,不妨求大同而存小异,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竞赛性的合作,分工式的联合,这恐怕还是需加强统筹工作吧。
铸造出版业的“中国品牌”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我在學习之后,就针对前两年有些出版社片面追求速度、扩展数量的偏向,5月14日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关于出版业加强质量检查和适当减轻负担的建议》,国务院领导很快就批转给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负责同志。领导部门也一再指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动优化升级和融合发展,持续提高优质出版产品供给,实现行业的良好发展。
出版业在 2017年就初见成效,全国共出新版图书25.5万种,较2016年降低2.8%;重印图书25.7万种,增长8.4%,首次超过了新版图书。重版书的收益也超过了新版书。这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新成就,正是从数量的增长转向质量的提高,逐步由出版大国发展为出版强国。2018年更进一步压缩了书号,提高了重版书的比重。当年的业绩也强调了质量的提高,以三十种好书作为标榜了。因此我就更有信心,继续向青年编辑们解释这一种“中国工匠”的精神,在2018年5月18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采访中提出了“取法乎上,精益求精”的理念。
参与《通览》编纂学在其中
中央文史馆最大的科研项目是《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由袁行霈馆长主编,各省、区地方文史研究馆合作分编的。中央馆有好多位馆员参加审编,我也有幸参与了。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学习的机遇,从头学习了文学史以外的多种学科,也了解了当代的多处地方的特色文化,大开了眼界。
我分工联系安徽、上海、江苏三地的编委会,因为我是江苏人,有义务为家乡和邻居多做点工作。我比较关注的是原属江苏而今归上海的几个县,一再建议要分工合作而避免争夺。第一部开始试点的是安徽卷,我多次参与讨论,反复提出建议,最使我感动的是安徽卷主编郭因先生,当时年逾八十而认真、勤快、虚心、谨慎,耐心地反复修改,九易其稿,这种敬业精神是最值得我学习的。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是21世纪初的一项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我为之付出了五年内的一大半时间,融合在五百多人的大集体里,做成了一件大事,这是我的荣幸。
研习传统诗词传播“诗教”
我在文史馆工作中,还有一项收获,就是重新写作传统诗词,参与了当代诗词的学习和研究。我少年时代曾学写过旧体诗,在“文革”中已把以前一些“吟风弄月”的诗稿都毁弃了。改革开放后,又偶尔写一两首酬世之作,只是自娱自遣而已。进入文史馆后,参与编辑《诗书画》的文字部分,每期都要发些传统诗词,后来又参与编选馆员诗选《缀英集》。我受到许多前辈馆员的熏陶启迪,又拿起笔来学写已成鸡肋的旧体诗词,主要是还想探讨一下诗体发展的历史过程。有一回,马凯同志不耻下问,写了《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文稿,发给袁馆长、孙机先生和我征求意见;在筹建中华诗词研究院前,又找了我们好几位馆员进行座谈,继而又聘请多位爱好诗词的馆员为诗词研究院顾问。我从中得到了鼓舞,重振了信心,再一次投入了传统诗词的学习,特别是对当代诗词的学习和研究,有机会与当代的诗人和研究者讨论切磋,因而积极参与诗词研究院的许多活动。当我年过八十后,文史馆为了照顾我们年老体弱,减少了资深馆员的活动。但我还努力响应诗词研究院的召唤,尽可能参与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己似乎也略有寸进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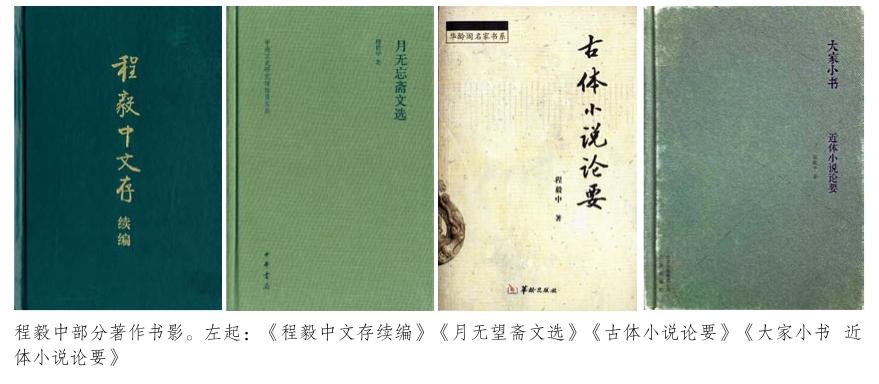
2015年6月,中华诗词研究院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研究”课程,我受诗词研究院的委派,去上海復旦大学讲了《楚歌与七言诗的传承》《歌行体与长篇叙事诗的演化》两堂课,同时参加了“首届中华诗词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据主持课程的黄仁生教授说,听众反映还不错。后来我的讲义和论文,也公开发表于中华诗词研究院和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华诗词研究》学刊上。作为兼任诗词研究院顾问的馆员,也算出了一分力量。
2018年4月,中华诗词研究院与北京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诗词创作与赏析”专题研修班,我也应邀去讲了一堂《格律诗的吟诵》。我一向认为,对少年儿童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最适宜的是“诗教”,而诗教最适宜的方法是吟诵,而吟诵的要点是辨别平仄,而辨别平仄首先是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基础知识。2009年我曾撰文提议,要把诗词格律和吟诵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并传承下去。因此我特别愿意去讲这样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