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和参与的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建设
2020-07-14施晓平
施晓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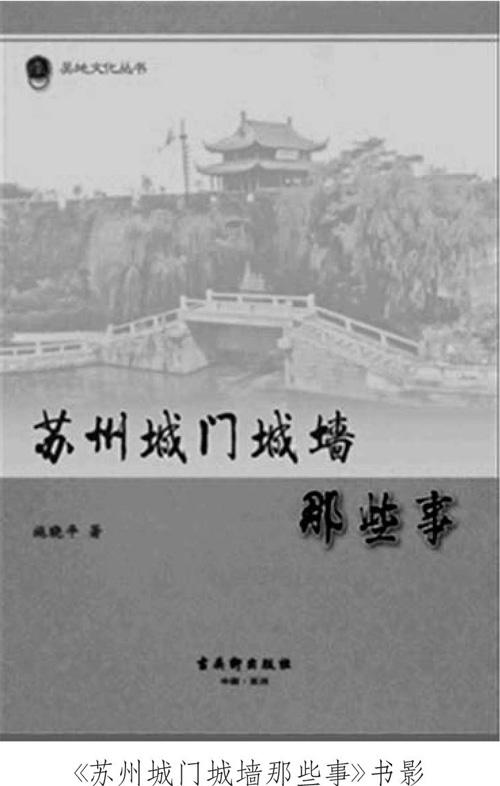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在如火如荼推进,苏州段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在宝带桥附近出生、喝运河水长大、长期和大运河打交道的苏州人,我见证了40多年来大运河苏州段的发展变化,并参与了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建设的报道和文化挖掘工作。
见识运河
1972年我生于苏州葑门外小集镇郭巷。这里离葑门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相传系苏州外城(郭)所在地,因此得名“郭巷”。集镇一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东南面有尹山湖,东北面、北面有独墅湖、黄天荡,西面约1.5公里处就是大运河,运河水通过集镇北面的斜港河(东西走向)、东港河(南北走向)、西栅口港(东西走向),流到我家老屋后面的郭巷街河里,再向东注入尹山湖。
斜港河向西穿过大运河,就是举世闻名的宝带桥,以及因孔子弟子澹台灭明而得名的澹台湖,再向西则是东太湖湖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东太湖湖湾水域宽阔,大量运河水通过这里,或通过胥江、吴淞江等江河流入大运河。因此,斜港河送至郭巷集镇的大运河水,实实在在流淌着太湖水的“基因”。
我小时候,郭巷街河水体清澈,鱼虾众多,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时太湖和大运河的水质之佳。此外,每年汛期,郭巷街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清代石拱桥泰安桥桥洞段,从东向西的手摇船往往过不了桥洞,尽管船夫们已经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由此可见当时的大运河水量之充沛。
受大运河宽阔的水面阻隔等因素影响,郭巷集镇一直到1983年3月15日才通上公路、公交。在此之前,郭巷的對外交通以水路为主,出行基本靠坐船,连办理婚丧喜事也是如此。要坐公交车的话,必须向西行走到一个叫“红旗渡口”的地方,摆渡到运河西岸十苏王公路公交站点(位于宝带桥南500余米处)搭乘,返回时亦是如此。郭巷集镇通公路后,由于到苏州城需要向南绕道尹山桥,多走约3公里路,因此许多骑自行车去苏州城里的郭巷人,仍喜欢选择到红旗渡口摆渡。
我还清楚地记得,十来岁时的一个夏天,祖父带我到苏州城里白相(苏州方言“玩”的意思),晚上去观前一家影院看了场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没有到红旗渡口的公交车了。这时祖父恰好碰到一个熟人,是在电影院附近一家单位看门的。祖父跟熟人说明情况后,熟人将我们带到他的宿舍,安排住下。当夜因为蚊子叮咬,我和祖父没睡好,凌晨3点多就迷迷糊糊起身了。告辞熟人后,我们才发现,这个时间点也是没有到红旗渡口的公交车的。但我们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于是就摸黑行走。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宝带桥北端,这时天已经放亮。我一见宛如卧波长虹的宝带桥就兴奋起来,想在上面走走,但同时又想知道这座古桥一共有多少个孔,就央祖父走西侧的十苏王公路桥,边走边点桥洞,我自己则直接在宝带桥上走过。会合时祖父告诉我,古桥一共有53个桥孔,我这才第一次知道了这座举世闻名的桥梁的“家底”。
1987年9月至1990年6月,我在大运河以西10余公里处的木渎中学求学,平时住校,休息日则骑自行车回家,红旗渡口、宝带桥、十苏王公路都是我的必经之处。这段经历,让我多次饱览了宝带桥一带大运河的优美风景,看到了十苏王公路两旁成荫的梧桐树、榆树,也看到了波浪滚滚的大运河水。当然,由于当时沿河建有化工厂,加上来往船只众多,螺旋桨不断卷起水底泥沙,大运河的水质已经不尽如人意了。
就在木渎中学求学期间,苏州开始了城南运河的改道工程。根据《吴中区志(1988—2005)》记载,改道工程让大运河从苏州古城西南面的横塘镇大庆桥直接向南,到石湖北侧后向东直达宝带桥,再向南回到原有航道,全长9.3公里。这样,大运河就绕过了苏州古城区,减少了轮船噪音对护城河两侧居民的影响。整个工程历时5年有余,1992年6月25日竣工,同年7月16日通过验收并正式通航。工程同时对十苏王公路改线7.342公里,1991年10月8日十苏王公路苏州城南改道段暨长桥正式通车,宝带桥北侧河口同时破土开坝,至此,苏州城区至郭巷之间的来往需要向西绕道东吴塔,圈子兜得更大了。直到1996年9月,大运河东岸吴东路通车,这种现象才得以改变。
1999年5月我成家后,就住到了吴中区城区,但单位在苏州工业园区一所中学,上班时仍要经过大运河原有河道旁。记得有一天大清早,我路过运河西侧某化工厂时,看到工厂通过闸门向外排放污水,导致运河西半侧河水和东半侧河水颜色一灰一白,像两块不同颜色的布南北向并排延伸,空气中则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酸味。
解读运河
我和大运河苏州段的第二段因缘始于2002年。当时,我已成为苏州日报报业集团《城市商报》的一名记者。因为工作需要,我对运河苏州段进入了“了解她、解读她、传播她”的新阶段。
那时候,苏州启动了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这是苏州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十五”期间中心城市重点建设的十大工程之一,也是一项集城市交通、防洪、生态绿化、景观、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全长约17公里,基本沿护城河及灭渡桥至北干河之间的大运河故道展开。从现在的情况看,此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国家启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之前,苏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展的一个先行先试行动。
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于2002年5月24日正式启动,分三期实施。到2005年12月,经过一、二期的建设,苏州已基本形成一条沿护城河两侧各100米、凸显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园林和东方水城特色的景观带,“觅渡揽月”“金门流辉”“旧城堞影”“耦园橹声”“烟霞浩渺”等48个景点布局其间,以水系和城墙体系串接,构筑起以“金阊十里、盘门水城”为主的西部功能区、“吴门商旅、都市驿站”为主的北部功能区、“城市山林、枕河人家”为主的东部和南部功能区。如果把古城比作苏州的头部,那么,经过整治而变得一年四季常绿的环古城地区,就是绕在头部的一条绿色项链。护城河上的巍巍桥梁、岸边的斑驳城墙经过整修,显得传统而典雅,让这里文化味十足。从此,环古城地区成为苏州人漫步休闲的自然生态圈,也成为苏州古城又一张景观名片。环古城风貌保护带三期工程于2011年1月起进场施工,当年完工。
配合环古城风貌带工程建设,苏州文物部门2004年还开展了阊门遗址抢救性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汉代遗物,既为重修阊门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苏州古城历史的悠久。
凡此种种,我都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报道。
这期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私人纪念品埋入重修城墙一事。那是2004年初,姑胥桥东北堍一段城墙开始修复。我报道这一消息后,报社总编辑突发奇想:能否埋一些纪念品在这段城墙内,让后人见证这段历史?为此,我查阅了资料,发现把纪念品埋入地下、留给后人的做法,国内外都有先例。于是,《城市商报》4月18日以《让后人见证古城沧桑巨变 重修城墙能否埋入私人纪念品》进行了报道,引起当时苏州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见报当天(星期日)就得到批示:“可批准有关方面研究”,并提出了有关纪念方式的设想。5月初,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指挥部对“重修城墙埋入纪念品”一事进行了讨论。考虑到其他纪念品不易保存,而将创意刻入城砖则可较好解决这一问题,也更有纪念意义,指挥部决定遴选55句有创意的话刻在城砖上,铺砌在姑胥桥东北侧或阊门段的城墙上。之所以遴选55句,主要是因为当年苏州正好解放55周年。
创意语句通过《城市商报》进行了征集。入选的句子中,我记得最牢的是苏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办公室(后改名为市非遗办)主任龚平的一句:“亲爱的未来市民,相信苏州将来以加好。”这段文字下面还用国际音标进行了注音。“以加好”是吴语,意思是“更加好”,所以一些专家称赞:这句话不但可帮助未来市民用古老的吴侬软语读出先辈的祝福,也可为未来学者提供一个研究吴文化发展的实例。
2012年3月31日,我从《城市商报》转岗到《苏州日报》。从此,我对大运河苏州段的解读就更多了。
此前的2008年3月,大运河申遗工作已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启动。换岗第一天,我就接到任务,采访来苏考察大运河申遗准备情况的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一行。励部长一行先后考察了山塘街、虎丘、盘门、宝带桥、东山镇陆巷古村等文物推荐申报点,对苏州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并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
2012年9月28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會资深顾问、世界内河遗址首席专家米歇尔·科特也来考察大运河苏州段申遗工作。由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也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唯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单的审定和评估,因此,此次专家考察对大运河苏州段申遗乃至中国大运河申遗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又进行了报道。
配合申遗工作,我还以主力记者的身份,参与了2014年6月11日至22日《苏州日报》开展的“一条河·一座城”行走苏州运河遗产系列报道。整组报道既涉及苏州大运河历史沿革、变迁、苏州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还有列入申遗名录的苏州段运河遗产情况,最后以《中国大运河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苏州古城申遗梦圆》终结,前后共10篇稿子,几乎每天一篇。稿件除刊登在《苏州日报》上,还提前在苏州日报APP、官方微博、微信、苏州日报文艺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发布,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阅读方式读者的需求,为申遗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这组采访报道节奏快、强度大,而且碰到了不少困难,但我们乐此不疲,也收获颇丰。比如写历史上的虎丘塔时,我们多方寻找,找到了家住虎丘山下、时年95岁老人郁文剑、81岁老人夏友良,得知他们小时候去虎丘塔时,塔身外面裂缝和窟窿随处可见,塔顶还出现了大窟窿,吓得他们不但不敢爬上去,就连靠近塔身都很紧张;写宝带桥时,因周边村民已经动迁,我们在当地社区干部的带领下,赶了好几公里路,到红庄新村才找到了88岁老人马永昌,采访到了日军当年在桥上开汽车的内容;在写吴江古纤道的时候,我们又多方打听,终于在吴江区平望镇梅堰三官桥村找到了老纤夫朱根林,听他讲述拉纤情况,还拍下了他模拟的拉纤动作……这些鲜活的资料,让我们的报道吸引了众多读者。
苏州纳入大运河遗产的范围,包括山塘河、上塘河、胥江、环古城河四条运河故道,山塘历史文化街区、虎丘云岩寺塔、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全晋会馆四个运河相关遗产和盘门、宝带桥、吴江古纤道三个运河水工遗存,遗产区面积6.42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6.75平方公里,比原先设定的苏州古城申遗范围还大。因此,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也意味着苏州古城申遗的成功。这是苏州的智慧,也是上上下下不懈努力的结果。为帮助人们了解这一情况,2014年7月4日,我又以《大运河苏州段入遗比当初古城申遗范围还大》为题,在《苏州日报》“文化访谈”专版进行了阐述。
与此同时,我还受邀在苏州图书馆的“苏州大讲坛”上主讲苏州城门城墙历史、故事,每月一次,连续9次。因为苏州城门城墙和护城河密不可分,所以我讲课中涉及了许多大运河的内容。事后,我在讲稿的基础上进行充实、调整、补充,形成书稿,于2015年3月出版个人首部著作——《苏州城门城墙那些事》。
参建运河
2017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打造展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关于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中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批示,为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
此后,全国相关地区开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则被苏州市吴中区文联引进,从事文艺交流、管理等工作。从此,我从原先的“贩卖式”解读、宣传大运河苏州段,转向“自产式”参与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的建设,开启了我和运河的第三段因缘。期间,我深入挖掘大运河苏州段沿线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参与规划方案编制,积极提交政协提案……这些举措虽然不是直接参加建筑工程,却是推进建筑工程的基础,也助推了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灵魂的塑造。
其中,2017—2018年我承接了苏州高新区《文蕴高新》系列丛书之一《运河流芳》的撰写任务。那段时间,我利用晚上和休息日,对大运河苏州高新区段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浒墅关八景和蚕桑文化、枫桥街道的贺九岭和寒山岭、横塘的驿站和亭子桥、玉雕高手陆子冈、跨越三个世纪的人瑞李阿大等,并多次前往实地踏访、采访知情人士,多方征集老照片,最终胜利完成撰稿任务。2019年,在苏州市第十二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中,《文蕴高新》系列丛书成功入选。
2019年,我又根据吴中区文联主席团要求,担纲大运河文化带吴中段历史人文特辑《吴运流长》的编撰工作。吴中区委宣传部、区大运办对此书高度关注,将其列入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五个一”文化活动(“五个一”中的“一本书”)。
由于大运河吴中段的文字记录相对较少,名门望族外迁较多、后人难以寻找,而且动迁启动早,特辑的撰稿工作面临很大困难。幸而经过召开座谈会、区作协微信群发布信息、吴地历史文化研究会会议发布信息、约请文史作家等途径,最终有10余位作者(包括本人)参与到编撰工作中来。大家深入实地反复调查,在宝带桥畔寻觅诗情,在大运河边采撷珍闻,并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找线索,加上以往的积累,辛勤笔耕、反复修改,最终如期交出了文稿、端出了特辑。此书在2020年元旦的“新年走大运”第三届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八城新年行走活动(苏州地区活动)上首发。
我还受邀参与了《大运河文化带(吴中段)规划设计》的编制。2019年初,规划方案在向吴中区领导汇报时,区领导要求加强大运河吴中段的资源挖掘、特色挖掘,并建议设计人员找我“取经”。于是,我义务参与到设计方案的编制中,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不少独家资料和建议。随后,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目前已基本定稿,将作为指导性规划,指导全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工作。
2020年初的吴中区两会上,我作为区政协委员,又在区政协领导们的指导下,以《大运河文化带(吴中段)后续建设和发展的建议》为题,参加大会联组发言。由于内容较多,规定发言10分钟,我实际发言15分钟,但会后多位领导、委员说,这个发言是全场发言最精彩的一个。
鉴于大运河文化带吴中段核心监控区位于吴中经济开发区、吴中高新区,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为了将更多历史文化信息留存给后人,为大运河文化带吴中段建设添砖加瓦,2020年两会期间,我还提交了《关于加强蠡墅、郭巷集镇历史遗存保护的建议》,最近被确定为2020年吴中区政协领导督办重点提案。
如今,每次经过宝带桥,看着水质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的大运河,我就会想到,流淌不息的大运河哺育了我,也给我提供了学习和施展身手的舞台,我应该感恩大运河、回报大运河。
(责任编辑:巫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