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汉·祀汉·去汉
2020-07-14李庆西
李庆西
建安二十五年(改年延康,220),汉献帝禅位,曹丕登阼成为魏文帝。自此,讨伐黄巾以来延绵不止的战乱渐而定格为三国鼎峙格局。献帝去位,实际上给刘备腾出了陟升空间,翌年刘备在成都即皇帝位,承汉立国。东吴孙权其初玩暧昧,既向曹魏称臣,第二年又自立年号,实不甘居藩国地位。在蜀汉立国七年之后,孙权升坛称帝。

按旧时帝王纪年,三国历史应该从魏国建立算起,终结于吴国灭亡,按干支纪年恰在两个庚子年之间(220-280)。然而,至魏延熙二年(晋泰始元年,265),司马炎以晋代魏,便是下一个朝代肇始—蜀汉已于两年前亡于魏。东吴尚在苟延之中,但看陆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似亦难以割据为存在。这样说,三国从头到尾只是四十五年(220-265)。
这四十五年或是这六十年,魏蜀吴三国从建立到终结,实际上各有不同的国家构想与话语内容,三方之间的战争乃至不同的建政理念,自是國家话语的各自表述。三者在追逐疆域和帝国集权统治的过程中,或是消耗了自身而走向衰亡,或是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是非成败转头空”,归根结底亦是坠入某种话语迷思。

魏:从禅代到禅位
如果不是关羽“大意失荆州”,恐怕不会很快形成魏蜀吴三方掎掣的鼎峙之局。建安二十四年,曹孙两家联手除去关羽这肘腋之患,各自额手称庆。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孙权即“上书称臣,称说天命”,进劝曹操做皇帝。曹操竟不领情,到处跟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略》)按《通鉴》胡三省注,炉火喻指汉之火德(以阴阳五德之说),孙权欲使曹操加其上,自是居心叵测。胡注又谓,曹操是拿这个话头探试众人之心。当时一班曹魏重臣不乏乖巧者,如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都亟劝曹操登皇帝位。但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没有确切解释,也许是想等灭了刘、孙再晋大位,也许他亦满足这种周公居摄的地位。第二年,曹操就死了,结果是他儿子曹丕做了皇帝。
不过,曹丕践祚的方式稍显特别,不是直接废掉汉献帝,而是不嫌其烦走了一道禅代程序。这番过程《文帝纪》未作详述,以献帝册诏宣告逊位,就算交代过去。但裴注引《献帝传》状述其事,连篇累牍皆是新君旧君与诸臣互动的繁文缛节—臣下不断上奏劝进,献帝本人更是一再申明汉祚已终,从虞舜之义说到各地出现之祥瑞,无非说明禅代之事已是天命所归。曹丕则是效仿“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一再辞让,最后才吐出一个“可”字。

走禅代程序,不能完全视为权力转移的一种伪饰形式(汉廷早为曹氏挟制,以魏替汉并未真正发生权力转移)。但汉魏之禅代并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表面文章,而恰恰是以这种方式昭示天下,曹氏从刘姓天子手里接过了汉家江山(虽说实际上并未完整地占有)。这不但是作为一种合法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国家让渡的消息,旨在杜绝刘备、孙权以恢复汉室的名义兴兵作乱,尤其是借以褫夺刘备承祧汉祚的资格。
简单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非是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两种模式。就实际情况而言,曹丕不具备秦灭六国而混一天下的实力和勇气,以禅代上位必是当日最优选项。这里不能不说到汉末乱局中的一个特点:自讨黄巾以来,虽说天下分崩离析,诸镇大佬中亦不乏有人欲伺机称帝,却并未出现将矛头直接指向朝廷的造反者,各方名义上仍是拥戴一个名义上统一的汉王朝,打成碎片的国土仍是抟成一个国家。所以,以魏替汉的禅代,也就是汉帝将普天之下的王土让渡于这个新的帝国,这里边自然包括曹魏未能实际控制的疆域。

禅让,或许亦可归入霍布斯和卢梭所说的那种“社会契约”。但在中土史官的书写中,譬如司马迁记述五帝时期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出现契约另一方的原始主体,王权只是产生于贤能人物自身的道德与才干,故而亦只能在王者之间转手。同样,在《三国志》和裴注所引诸史中,这类契约并不考虑“社会法人”之外的底层士民,所谓“天下大势”,只是综合大小军政集团之“公共意志”做出的判断。像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那些著作在关于国家建构的解释中,往往考虑到民众和士卒在整个共同体中的存在—这不能说只是启蒙主义之后的认识,因为他们引述的事况来自诸如恺撒和塔西佗一类文字记载,甚至早在色诺芬《长征记》里就有士兵参与表决的“游动的共和体制”。
尽管历史进程大率投射于帝王叙事,其背后则有多种因素凑集的合力在推动。史载曹丕升坛受禅后,环顾身边的大臣,感慨而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文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他有何感悟?此际他想到的当然不会是国家形成的原始契约,但是作为新旧君主之禅代不仅仅是代理人交易,抑或使他领受名义之后的立名之义。
当然,魏国既建,自有旧邦新命之义。曹氏集团由藩府之先军性质转变为“国家”,亟须改变战时状态的施政方式,恢复正常秩序,进而打造一个恢弘的国度。从曹丕承祧魏王后发布的一道政令来看,当时已有重建国家的若干思路,其令曰:
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秋七月)
按皇帝和帝尧故事,要求为政者“广询于下”,百官各司其职,广开言路,着眼于制度、礼乐、政务建设,这显然是儒家先贤的治国要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强调“军法”自有针对性,战乱以来军士扰民是一大祸害,游兵散勇更造成社会不安。不仅规束军士,曹丕登基后又严厉打击民间滥用暴力的寻衅滋事,其诏令曰: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春正月)
曹丕在位不足六年(220-226),检视其事功,主要在内政方面。为数不多的几次用兵是平息内乱和征讨鲜卑轲比能之类,重点在于安内攘夷,而不是与蜀、吴争夺地盘。其后明帝曹叡亦大体沿循这一方针,仅有的几次主动出击,也是因应诸葛亮北伐和吴军不断袭扰淮南的局面。总之,曹魏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军事上主要以守土防御为主。从文帝、明帝本纪来看,他们在位期间,相对比较关注农耕与民生,如黄初三年、太和元年、青龙元年各有“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之举,同时又对“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发放口粮或免除租赋。曹魏沿袭两汉“赐民爵”政策,是其建国初期鼓励孝悌力田的举措。
除了务实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帝开始,已着手铺陈作为国家精神建构的宏大叙事。虽是偃武修文,也轰轰烈烈像是搞运动。概而言之,一是修礼乐,一是筑宫苑。

早在建安十八年,曹操册封魏公之时,便已始建魏社稷宗庙。在魏蜀吴三者中,唯独曹魏最注重庙祭,这亦显出它与蜀汉、东吴那种草创之国不同之处。文帝登基在冬十一月,来年春正月便郊祀天地、明堂,恢复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的古礼。是年又下诏奉祀孔子,“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黄初五年,设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明帝对祭祖和祀孔亦毫不懈怠,太和二年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四年又下诏:“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尽罢退之。”将儒学作为选拔官员的门槛,是对设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制度的重大修正。从曹操的法家实用主义到曹叡重启王教的“尊儒贵学”,是一道渐变的轨迹,从中不难看出曹氏祖孙由先军政治转向礼治国家的努力。
曹丕受禅后定都洛阳,开始经营宫殿、园林和都城建设。黄初二年筑陵云台,三年穿灵芝池,五年穿天渊池,七年筑九华台,开大治宮苑之渐。曹叡在位十三年(226-239),更是大兴土木,在洛都建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又修复毁于火灾的崇华殿,整饰陵云台,起陵霄阙、承露盘和圜丘。不光是洛阳,还重修许昌宫苑,起景福殿、承光殿,等等。明帝在工程建设上豪掷人力财力,自然惹来史家非议。作为反“浮华”的君主,又何以如此奢靡?这事情不能仅从贪图享乐的角度去理解,建筑本身亦是精神建构,对君主而言,那些巍峨壮丽的宫苑正是打造想象的大国威仪的标本。都城宫苑工程作为国家话语的视觉表达,跟祭天祀祖、尊儒修礼这类节目实是相为表里。笔者在《三国宅京记略》(原刊《书城》2018年5月号,收入《三国如何演义》,三联书店2019年)一文中对此有过分析,这里不多说。但看《明帝纪》文末评曰,陈寿赞赏曹叡“沉毅断识”,有帝王之概,同时亦指出其堕入帝国迷思之溺惑—本是旰食之秋,“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
明帝时,最大的军事行动是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从景初二年(238)正月至十一月,四千里跋涉,往还近一年。之前青龙二年(234)四月,诸葛亮出斜谷,明帝以掾佐孙资之策,诏司马懿“坚壁拒守”,不予主动进攻。孙资对各方势力消长有一个基本判断:“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魏志·孙资传》裴注引《资别传》)王夫之称赞其“早决于大计于一言者,收效于数十年之后”,这正是曹魏应对蜀汉北伐之长期战略方针(《读通鉴论》卷十)。

用兵谋国之事一概托付司马氏,朝廷自然省心。不妙的是,却使代理人渐然坐大。
明帝之后,是三位闇弱的少帝,即齐王芳、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然而,曹魏这等大国已非弱主所能统驭。齐王芳企图遏制司马懿,却力有不逮,为时亦晚。嘉平元年(249)春正月,年迈的司马懿趁车驾谒陵之际,发动阙下政变,翦除大将军曹爽及其党羽,从此司马氏父子挟天子挟太后成为常例。老司马最后一次出征是嘉平三年解决王凌之叛,而高贵乡公时期又相继发生毌丘俭、诸葛诞反叛,都未能撼动司马氏。曹髦是三少帝中独见血性者,甘露五年(260)五月,竟独自率宫中百余僮仆讨司马昭,丧于贾充门人剑下。本纪中有不少篇幅记述曹髦造访太学,与诸儒讨论《周易》《尚书》《礼记》之事,其“才慧夙成,好问尚辞”,是个好学而风雅的主儿,其兴趣原本在于修明经典、广延诗赋、玩习古义。
曹奂被扶上帝座大概是早有设计,五年后亦即咸熙二年(265),禅位于晋王世子司马炎(晋武帝),本纪谓之“如汉魏故事”。其在位时,邓艾、钟会灭蜀,曹魏帝国开创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个宏大的帝国以禅代始,以禅位终,尧舜之德背后是浇薄与血腥。
蜀:遥领与征伐
曹丕成为魏文帝的第二年,刘备也赶紧做了皇帝。如果说魏国合法性来自献帝禅让,刘备则以血脉“祚于汉家”,他在登基文告中不但宣示其“率土式望,在备一人”之嗣国资格,更是谴责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云云。曹魏大费周章搞了一场禅代大戏,还是没能堵住蜀汉建政之路。不用说,刘备祚汉的资格在其刘汉之姓,此为立国之本。后来刘备病笃之际,召诸葛亮吩咐后事,有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蜀志·诸葛亮传》)这话听上去很是恳切,他那个儿子若是不成器,诸葛老弟不妨取而代之。后世学者对此有种种解释,或以为刘备托孤乃诡伪之辞,更常见的说法是诸葛亮“两朝开济老臣心”,足见其贤良忠恪。诸葛亮是否粹然出于尽忠之心并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毋须讨论—那个昏聩的刘禅才是蜀汉的命根子,若是庙堂上换了外姓人,“祚于汉家”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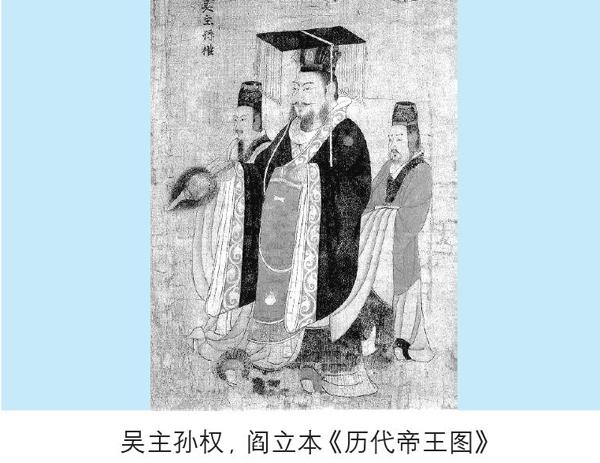
因为“祚于汉家”,刘备自建国起就申述自己继承汉室之权利,理所当然认为普天之下皆为其汉家领土。尽管蜀汉仅占据汉末十四部州中的一个益州,只是偏安一隅,但其存在并不只是一个割据政权,其数十年间始终持有大汉王朝的帝国心态。
这种心态需要精神空间来安置,不能为疆域所限,因而以想象超越现实,自是拓展蜀汉帝国最方便的路径。譬如,其分封诸王便采取一种“遥领”方式,将封地一概置于魏国境内。据《蜀志·先主传》,刘备称帝后,于章武元年(221)立刘禅为太子,随后分封诸子,立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作为封地的鲁、梁二郡国都不在蜀汉所控制的地域,鲁郡属兖州(治今山东曲阜),梁国属豫州(治今河南商丘),跟益州都隔着万水千山。既是遥领,自然不可能“之国”,却是表示主权所有的一種话语方式。另,《后主传》建兴八年(230),刘永、刘理的封国又改徙别处,因为前一年与东吴约盟“交分天下”,考虑到鲁梁二地将划入双方拟定的吴国界内,便将鲁王永徙为甘陵王,梁王理徙为安平王。甘陵,即冀州清河郡(治今山东临清),安平郡亦属冀州(治今河北衡水),依然都在魏国境内。
以遥领方式主张领土主权,是蜀汉一大创举。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滑稽,却不能简单地视为官样阿Q,这种虚封虚设背后有着王权神圣理念的支撑。蜀汉与曹魏之立国,都是你死我活的排他性设计,必然是承祧与禅代的话语撕搏。其实,蜀之承祧,魏之禅代,都是各自强说,献帝让位无非迫于曹氏威逼,而刘备说到底亦非汉室合法嗣主(参见拙文《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原刊《读书》2015年第5期,收入《三国如何演义》)。但因为曹氏是外姓,这事情在蜀汉这儿就演绎成忠/奸对立的叙事,虚妄的道德感亦便转化为义愤填膺的政治正义。所以,作为主权宣示的遥领,不但具有挑衅性,亦体现了无远弗届的精神扩张。
若干年后,刘先主这套遥置路数,亦被后主刘禅照式袭用。后主有七子,除太子刘璿外,其余瑶、琮、瓒、谌、恂、虔六子皆有封国,《后主传》记述如次:延熙元年,立刘瑶为安定王(安定郡属雍州,治今甘肃镇原县);十五年,立刘琮为西河王(西河郡属并州,治今山西汾阳);延熙十九年,立刘瓒为新平王(新平郡属雍州,治今陕西彬县);景耀二年,立刘谌为北地王(北地郡属雍州,治今陕西铜川),刘恂为新兴王(新兴郡属并州,治今山西忻州),刘虔为上党王(上党郡属并州,治今山西长治)。毫不含糊,这六王领地也都砸到了魏国境内。反观曹魏诸王封国,却无遥置之说。曹操分封诸子尚在魏建国之前,无论始封还是追封,其二十四子封地皆在自家境内。曹丕建国后所封八子,亦尽如此。曹魏注重实际的制度安排,不屑隔空虚占地盘。
蜀汉不仅诸王封地搞跨境,以敌国州郡遥置封疆府署,抑或是作为对臣下的特进奖赐。如《蜀志》各传见有以下数例—
《马超传》:“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
《李恢传》:“[章武元年]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
《魏延传》:“[建兴五年]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姜维传》:“[延熙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
凉州在魏国境内,与益州西北接壤,让马超、魏延、姜维这类骁将遥领其地,或许可以给对方造成边防压力。交州乃东吴地盘,李恢“领交州刺史”,正是蜀汉与东吴交恶之时,其遥领实有针对性。
这种遥领制度大概由汉末署置混乱状态而来,早年刘备就曾被表授遥领之职。据《先主传》,献帝兴平元年(194),曹操征徐州时,刘备率部数千人支援陶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其时豫州刺史为郭贡(见《魏志·荀彧传》),陶谦表授刘备豫州刺史,并非取而代之,是给刘备安排一个官阶而已,故胡三省注称“私相署置者也”。豫州本治谯县,而刘备领刺史却驻屯小沛,其领而不治说明只是虚衔。后来,刘备与吕布交恶,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先主传》)。实际上这回亦是虚授。刘备被称为“刘豫州”,就是这两度遥领豫州的缘由。
然而,蜀汉的遥领已不是早年方镇混战时期的赠官赐爵,实是刚烈而悲情的政治话语,贯注着“惧汉邦将湮于地”的危机意识,用以提醒臣民,大片国土还在篡盗者手里!这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肌理和织体。当然,这番话语不能只是玩虚的,要使复兴汉业的帝国大梦获得持续效应,还须借以战争做进一步表达。这一点,诸葛亮自是了然于心。
刘备死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传》),诸葛亮决计付诸军事行动。他知道,如果长期偏安一隅,不但“恢复汉业”成为空谈,自家这块地盘亦恐将不保。其《后出师表》有谓:“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这说得很清楚,明知敌强我弱,硬着头皮也要咬人家几口。
所以,平定南方四郡之后,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便投入了进攻魏国的北伐事业—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总称为“六出祁山”,实是胡乱命名,其征伐路线并非都在祁山方向,亦另由散关、羌道、斜谷等处向北楔入。综而观之,北伐是一种袭扰性打法,每每“粮尽而退”,都未能向关中推进。如此杀进杀出,耗至十二年秋,诸葛亮身殁,方告停歇。其连年征战,却寸土未得。为何屡出而无功,史家讨论此事各有说法。陈寿归咎其将略不足,而麾下亦无韩信那样的名将。其实,胜负结果应在武侯预料之中,毕竟国力相差悬殊。其执意伐魏,不在于军事上有多少胜算,实乃政治正义所驱使,出于一种心结和义愤—蜀汉既以延续汉祚为立国之由,就没有理由跟曹魏共存于天下。笔者分析,从蜀方征伐路线和部署来看,诸葛亮并无明确的战略意图,其征伐本身就是目的,乃以进攻姿态作为政治诉求(见拙文《秋风五丈原》,原刊《书城》2020年5月号)。
武侯去后,蒋琬、费祎先后接任军国大事,便将原先北伐中原的宏大计划压缩为“分裂蚕食”的边境战事。费祎说:“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他们明知北伐已无意义,但并不声言放弃,依然伺机而动,只是将诸葛亮那种袭扰性进攻变成了规模更小的袭扰。
蒋、费的继任者姜维在小说里被描绘成最后的悲剧英雄,从延熙元年(238)“数率偏军西入”,到景耀五年(262)再出陇西,跟曹魏周旋二十多年。按毛宗岗夸饰之语,姜维是“九伐中原”,但观其出兵方向大多在祁山以西,比诸葛亮北伐路径更加远离中原。唯独延熙二十年,自骆谷出秦川,是逮着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其时淮南诸葛诞兵变,三辅守军调往寿春平叛,关中一时空虚。即便如此,亦未能真正对长安构成威胁。姜维累年征战,大率辗转天水至陇西一带,尽在曹魏军力最薄弱的地带下手,可见“恢复中原”之说只是悬置嘴上的目标。关于当日情势和姜维的心态,笔者亦有专文评说(见拙文《托国羁旅,孤獨与悲情》,原刊《书城》2018年7月号,收入《三国如何演义》),此不赘述。
从诸葛亮到姜维,蜀汉北伐三十余载,疆土毫无拓展,却不改初衷。其国策背后清楚地呈现“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理念,亦让人感受到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悲情心态。事情显然不能仅着眼于其军事意义,更重要的是,同仇敌忾的征伐本身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让国家永远处于战时状态,并以其不断强化的正义论,产生了克里斯玛式的感召力。一种自我煽情的政治正义而本质上属于扯淡性质的国家话语如何产生有效性,这是一个典例。
事实上蜀汉是三国时期内政最稳定的一方,相比魏吴两国,少有内讧和反叛,更无权臣篡夺之事。刘禅作为三国最无能的君主,偏偏是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前后四十一年)。蜀汉之败,败于国势凋敝。连年征战,国家岂能不凋敝。有趣的是,这个最先出局的失败者,给后世留下了虽败犹荣的神话,更借以文学叙事建构了某种影响久远的政治伦理。
吴:听于神,浮于海
何时称帝,孙权好长时间沉吟不决。蜀汉既建,直接跟曹魏死磕,东吴这边便大有回旋余地。《吴主传》谓:“自魏文帝践阼,[孙]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魏黄初元年十一月,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其时孙权尚甘居藩王地位。裴注引《江表传》:孙权诸臣认为不应受魏封。孙权则谓:“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这话里是以刘邦自诩,其受封只是权宜之计。孙权还特意找星算家看过星象,确定了一种“先卑而后踞之”的策略。裴注又引《魏略》曰:
[孙]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为卑则可以假宠,后踞则必致讨,致讨然后可以怒众,怒众然后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
孙权“深绝蜀而专事魏”,是因为荆州之事,关羽死在他手上,刘备必然要找他复仇,这时候只能先傍住另一头。可是,此一时彼一时,曹丕称帝第三年的十月,孙权竟以黄武建元,撇开了魏之黄初年号。之前,曹丕要拿吴太子做质子,孙权不肯遣送,双方几乎闹掰。东吴上半年大破蜀兵,孙权已变得很有底气了。此时东吴尚为藩国,其自立年号,不啻是挑战宗主国的权威。《通鉴》胡三省注曰:“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这是跟曹魏争抢“承汉”的轮序。
是年九月,魏方曹休等分三路来伐,孙权一方面让部下临江据守,一方面“卑辞上书,求自改悔”,自是缓兵之计。《吴主传》谓:“初,[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故随后几年间吴魏双方逐渐进入开撕阶段,据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东吴记事,黄武二年至七年双方军事行动如次:
二年三月,魏军退。六月,将军贺齐等破魏蕲春,获其太守晋宗。
三年九月,魏主来伐,至广陵,临江而还。
四年十月,魏主复来伐,耀兵广陵而还。
五年七月,遣将侵魏江夏,围石阳,不克;还。
七年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八月,将军陆逊大破休于石亭。
自与曹魏绝交以来,孙权的一班大臣纷纷劝即尊号。《吴主传》接连记载吴地各处出现祥瑞,如黄武二年“曲阿言甘露降”,四年“皖口言木连理”,五年“苍梧言凤皇见”,八年“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八年四月,孙权终于称帝,改黄龙元年(229)。这是魏文帝御宇九年之后,明帝登阼亦已两载。跟魏蜀两国不同,孙氏将建国的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天命,其登基的祭天文告中特意强调“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干脆抛开汉业之因缘,声言“惟尔有神飨之”。
君权神授不是什么新命题,曹丕和刘备登基时也都扯上天意作为包装,可是孙权之“神飨”绝非装饰性辞藻,而是直接用它拉黑了世俗的王权统绪。提出“去汉”之说,实有如宣告“苍天已死”,既是否定魏之“代汉”合法性,也褫夺了蜀之“祀汉”的权利。这时候孙权已抛开七年前自立年号时“承汉为土德”的思路,干脆代之以一种神创说。
《吴主传》记录了作为神谕的祥瑞之物不断出现,如:嘉禾生,甘露降,赤乌集,黄龙见,神人授书……这些现象预示着天命神明之应,亦是国家话语的重要构成。在孙权及其身后三嗣主采用的十八个年号中,大多取自这类符瑞(如黄龙、嘉禾、赤乌、神凤、五凤、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似乎一切历史活动都围绕神迹而展开。譬如,嘉禾五年改元之事,传中有如下说明:
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
曹魏之王权建构亦夹杂此类受命符瑞的故事(如青龙见摩陂井中而改元),但其痴迷程度远不及东吴,而蜀汉则几乎不问天命。读《三国志》诸帝王纪传,各自叙事模式实大相径庭,概乎言之,曹魏践行王道之职,蜀汉贯以正邪之论,东吴则悬于天人之际。孙权的国事充满了各种留予后人猜详的隐喻,其生前三立太子,身后是两度废立之局……因为据于神的想象,不在乎什么现实羁绊。孙权死的前一年,派官员迎神人王表之事,神神叨叨,语焉不详,让人更觉匪夷所思。时谚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裴注引孙盛)其实孙权一开始就是“听于神”的神谕主义。
其实,孙权本人就是神话的主人公,自有超越魏帝蜀主的气场和境界。主人公将退场之际,那些符命自然就成了失落的凶兆。《吴主传》记述了那种惊悚场景,大风卷地,江海涌溢,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
汉末以来,各路豪强都是战国纵横家的路数,但要讲身段灵活,没有谁比孙权玩得更娴熟。赤壁之战就是拽上刘备才赢了曹操,后来又依傍曹操夺回荆州。现在,他以天意宣告汉祀已绝,却并不拒绝与祀汉的蜀方结盟。早在黄武二年冬,东吴刚与曹魏交恶,诸葛亮就看出东朝风向又转了,便派邓芝来重修旧好。第二年夏,东吴则遣张温使蜀,全面恢复邦交正常化。黄龙元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来庆贺孙权践位,乃有“参分天下”之议—以司州函谷关为界,东边归吴国,西边归蜀汉。这已不是遥置遥领的节目,直接从纸上瓜分了魏国。这时候,孙权的立国思路已从绝蜀事魏完全转向联蜀抗魏了。
蜀汉以魏地分封诸王,无疑给孙权一种启示。孙权七子,太子登和次子虑早夭,后立幼子亮为太子,其余四子封国皆在魏境。赤乌五年(242),立孙霸为鲁王;太元二年(252),立废太子和为南阳王(南阳郡,魏荆州治,治今河南南阳),孙奋为齐王(青州齐国,治今山东临淄),孙休为琅邪王(徐州琅邪国,治今山东临沂)。孙权分封诸子在吴蜀“参分天下”之后,这些遥领之地按双方拟议归属东吴。
孙权死后,继位的孙亮未及成年被孙綝废黜,拥立的孙休死得也早,其在位时只是封了废帝孙亮黜为会稽王(扬州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后来大臣们再搞废立之局,废了孙休的太子孙,孙皓封他为豫章王(扬州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会稽、豫章都在自家地界,那是要找个地方安置废帝和废太子。至于孙皓诸子,先后封国三十余者,封地散布于汝南郡、梁国、陈郡(均属豫州)、东平郡、陈留国(均属兖州)、天水郡、武威郡(均属雍州)、中山国(属冀州)、代郡(属幽州)等处。孙皓即位时蜀汉已亡,旋而司马氏以晋代魏,其所封皆为晋国地域。
至于虚置境外府署,东吴丝毫不让蜀汉。如黄武初,朱桓领彭城相,贺齐领徐州牧;黄龙元年,全琮领徐州牧;孙休即位后,丁奉领徐州牧,陆凯领豫州牧;孙皓即位后,陆抗领益州牧(见《吴志》各传)。除陆抗遥领之益州已是晋国地盘,其他所领州郡均在魏国。此亦可见,东吴战略的既定目标就是对抗那个北方大国。
遥领之外,孙权还有另一种跨境的想象,那就是企图在曹魏身后建立自己的实体藩国。孙权黄龙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派校尉张刚等往辽东联络公孙渊。嘉禾元年(232)春,又遣将军周贺等乘海往辽东。这回因携带大批随从,不便穿越魏国地界,只能走水路。周贺虽被魏将田豫狙杀于青州海岸成山角,但他的船队应该是抵达了辽东。是年十月,公孙渊即派人来东吴,“称藩于[孙]权,并献貂马”。翌年三月,又派张弥等一干文臣武将出使辽东,“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公孙]渊”。如果《吴主传》所言不虚,不妨想象那万人船队是何等规模。持节出使的太常张弥带去孙权诏书,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封公孙渊为燕王(裴注引《江表传》)。倘若辽东真成了东吴领地,可想而知,曹魏便是腹背受敌。历史的轨迹或许就是因为某个末流角色而发生转折,就在关键时刻公孙渊突然翻脸投魏,杀了孙权的使节,让孙权苦心经营的封藩计划彻底落空。史书记载此事过于简略,《吴主传》只说“[公孙]渊斩[张]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至于如何让随从的万余军士缴械入彀,想来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
辽东这一步踏空,却也有意外收获,辽东郡北边玄菟郡的高句骊王位宫愿为东吴藩国(《吴主传》裴注引韦曜《吴书》),总算让孙权的大国战略在北方获得呼应。
公孙渊的背弃让孙权怒不可遏(《江表传》载其诏书称“气涌如山”),打算亲自蹈海远征辽东,被尚书仆射薛综等谏止。之前,顾雍、张昭等老臣都认为辽东归附之事不靠谱,再三劝谏,孫权不听。没有人能够理解孙权的战略构想。他登基当年便迁都建业,显然是便于出海的考虑。他瞧不上蜀汉北伐那种边境打劫,一心要构筑向海外扩展的宏大帝国。
孙权登基第二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兵万余出征夷洲和亶洲。夷洲即台湾本岛,亶洲应是今之日本(《吴主传》谓秦皇遣徐福求仙之处)。不过这次海上冒险并不成功,只是从夷洲掳得数千人而已,终未能抵达亶洲。后来卫温、诸葛直竟以“违诏无功”被诛。但据《吴志》陆逊、全琮二传,征夷洲之役,目标还包括珠崖(汉武帝时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后废弃),二将无功而返,是因为“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吴主传》又谓:赤乌五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史书没有详述海南岛民归化状况,但自建安十五年以后孙权已将交州收入囊中—其地域不仅包括今之两广,更延至今越南中南部。黄武五年,吕岱督交州军事,平息士徽之乱,收复九真郡(今越南清化省一带),巩固了南越领地,并将扶南(柬埔寨古国)、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堂明(老挝古国)等外藩纳入职贡(参《吴志》孙权、士燮、步骘、吕岱诸传)。
从北方高句骊到南方交趾,以及一次次“浮于海”的外交与征伐,很难说是基于浪漫无边的征服心理还是某种畸变的忧患意识,总之是将叙述者带入不可解脱的帝国迷思。问题在于,这部“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罗曼司太过偏重神话与想象,所有那些宏大而虚幻的叙事总是难以转化为现实的辉煌,很容易湮没于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帝国的覆灭,另一方面自是由于本文未及叙说的那些烛光斧影的宫斗戏码。东吴的将军们一直试图越过庐江、淮南,寻求楔入中原的路径,却始终未能突破北兵的防线。“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直至千年之后才让人重拾忧伤的记忆。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