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型塑“中国”
2020-07-14葛兆光
葛兆光
引言:为什么笔谈?
有一段时间,我对前近代日本人和朝鲜人互相交流中国印象的文献很感兴趣,在这些文献里面,很多是当年留下来的笔谈。他们为什么不用嘴说要用笔谈呢?直接说话不是更方便吗?
原因很简单,日本人、朝鲜人在传统时代各有口语,口语讲是一回事儿,但官方文书和典雅书写,却往往通用汉字书写。大凡上层精英,包括僧侣,都识得汉字,也都能用汉字表达。《宋史》里说,宋太宗时代(也就是十世纪后期),日本僧人奝然来中国,“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就算没有通事(也就是翻译),通过手写,他们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和中国人沟通。这些不同国度的人见了面,嘴上说不通,却能用手写,写下来的这些纸片就是“笔谈”,这就好比下围棋叫“手谈”一样。所以,后来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者也好,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好,琉球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好,安南派往中国的使者也好,都要选择能汉字书法和通中国文言的读书人。举一个例子,朝鲜宣祖二十二年(1589),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朝鲜国王选择赴日使者,就十分谨慎地吩咐说:“闻倭僧颇识字,琉球使亦尝往来云。尔等若与之相值,有唱酬等事,则书法亦不宜示拙也。尔等其留念乎?”意思就是说,对外的使者必须精通汉字书法,还要能写汉诗,才能应付往来,不至于丢面子。这就像我们现在外交官要懂外文一样,那个时代,安南、琉球、朝鲜、日本,虽然各有各的方言,但正式的文书和典雅的交流,还就得靠写的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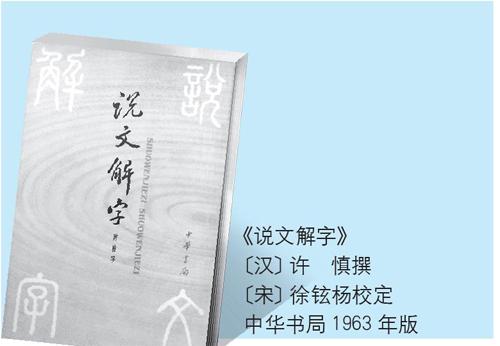
其实,不光是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外国”,就连传统中国之内,各个地方口音不同,像福建人或广东人讲话,河南人河北人不懂,山西人陕西人讲话,云南人广西人也听得困难,可是写成汉字大家就恍然大悟了。所以有人就说,汉字对于东亚来说,就好像古代欧洲通用的拉丁文,在罗马帝国时代以后通行整个欧洲。也有人说,汉字对于中国来说,是钢筋水泥里的钢筋,把中国这么复杂、这么广袤的疆域浇筑成一块混凝土。秦始皇统一中国,加上后来汉帝国形成大一统,靠的就是几招,在郡县制基础上,“行同伦”“车同轨”,最重要的就是“书同文”。“书同文”就是全国用一种文字,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官员民众都看得懂,能交流,于是才能形成政治共同体,也才能促成共同体意识。如果再扩大到东亚,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就發明了一个“汉字文化圈”的概念,用来说中古东亚的文化共同体。可见在历史上,汉字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东亚也有很大的重要性。
不过,汉字还是对汉族中国最重要。毕竟日本、朝鲜、琉球、安南这些地方,本来就各有各的语言,历史上他们虽然也借助汉字,但是时间长了,终归言文要合一。所以,当这些地方民族与国家独立的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就要凸显各自的文化和语言。逐渐地,朝鲜发展出了谚文,日本使用了假名,安南则有了汉喃,而琉球深受日本影响,在明清两代,口语就通行了日本语言,十九世纪并入日本之后,当然就更通行日语。特别是最近的若干年来,这些国家的汉字文化更是逐渐淡化,所以归根结底,汉字还是对于汉族中国以及汉族中国文化,意义最为重要。
所以,我们就把它视为(汉族)中国文化的一个要素,在这里进行一番简单的介绍和讨论。
一、从图画到文字:从甲骨文时代说起
汉字—当然,太早就说“汉”字,也有一点儿问题,因为在这些文字被发明的时候,还没有“汉”—什么时候产生的?现在还有点儿说不太清楚,因为不断的考古发现在挑战现成的历史观点。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陶罐上的刻符,是图画还是文字,还是从图画到文字的中间阶段?也还没有定论。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其中一个,有人说是“炅”,有人说是“旦”,也有人说是“日月火”,还有人说是“日月山”,究竟是不是?也不知道。不过,都没有疑问的成熟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殷商甲骨文才重新被人们发现。这个重新发现的故事很神奇。据说北京的一个大学问家王懿荣生病配药,这药方需要用“龙骨”,家人从药店买来“龙骨”。很偶然地,精通文字之学的王懿荣发现“龙骨”上面有字,于是追根寻底一番之后,发现这些龙骨来自河南安阳,而安阳就是殷商古都之一,所谓“殷墟”,据说是武丁之后王族的墓葬之地,随葬的物品中,就有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牛肩胛骨。这就是殷商的甲骨文。它们大多数是占卜刻辞,这些刻辞可都是成熟的文字。

我们来看甲骨上的几个字。“牛”字,就是牛的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犬”字,有脚、头和尾巴,有点儿像一条狗的侧面;“其”(箕)字,就像一个竹子编的撮箕;“刀”字,就是画一把刀的样子;“来”(麦)字,就像一棵垂着穗的庄稼。不过,千万别以为殷商甲骨都是象形字,实际上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远远脱离了文字最初的阶段。按照传统的说法,象形的往往是最早的“文”,后来,章太炎他们就管它叫“初文”,因为它常常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符号。
后来,在“文”的基础上衍生了好多“字”。“文”是初文,那什么是“字”?“字”的本义就是在家生育孩子,所以“字”是一个房屋下有一个孩子。相对“文”是最初的文,“字”就是后来衍生的字。像“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就是说,“旦”字是太阳和大地(日、一)的会意,表示天明。像“牛”,加上一个房顶(宀),就是“牢”,不光指牛圈,也可以象征关人的牢房,引申为画地为牢的界限;当然,如果同样是房顶,下面有个猪(豕,读作史),那就是“家”,可能那时候猪圈和人的住宅常常在一起?而那个“刀”字,有人为了表示锋利的那一边儿,就在“刀”的锋利一面加个点儿,就成了“刃”;而一个“犬”,配上各种声音符号,就表示和狗同类的动物,像“狼”“猫”等。像“其”,为了专门表示簸箕、畚箕,就加上一个“竹”写成“箕”,簸箕不都是竹子编的吗?而“其”则挪作他用,成了指示代词,表示“那个”。
上面讲的从“牛”到“牢”,就是后来六书里面讲的“会意”;从“刀”到“刃”,就是六书里面讲的“指事”;从“犬”到“狼”,就是六书里面讲的“形声”;从“其”(箕)到“其”,就是六书里面讲的“假借”。关于“六书”,我们一会儿再讲。古人说,“文”是仓颉造字时代的初文,这些“文”通过会意、指事、形声、假借等造字或用字的方法,就滋蘖出“字”,所以,中国汉代的辞典就叫“说文解字”。而从每个“文”中生出来的,与它意义相关的那一大批“字”,往往在古人心目中,就算是同一类事物。统率这组“字”的“文”,在后来就被看成是“部首”,率领这些字的头头。这个部首衍生的这些“字”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
所以,从早期文字里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蛮能反映古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因为它就是古人对万事万物的分类和理解。比如“示”这个部首下的各种“字”,往往和祭祀相关,而“玉”这个部首下的各种“字”,则和各种各样不同的玉石相关,“牛”这个部首下的各个“字”,就代表五花八门不同毛色大小公母的牛。你从这类字的多少,就能察觉古代人对万事万物了解的重心和偏向。比如,《说文解字》的“示”部居然有六十二个字,可现在,除了“社”、“祈”、“神”、“秘”(祕)、“祖”、“祝”、“祥”、“禁”、“福”、“祸”、“斋”(古字作斎)、“禅”这十二个字还常用外,其他的都几乎接近绝迹,就连这十二个字也改变了一些意思,否则恐怕也会被打入冷宫。可是,古人创造了示部这么多字,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字字有其用途。原来,古人重视祭祀,大至祭天地,中至祭祖先,小至祭灶台,名目繁多。为了区别这些不同的祭祀仪式,便有了这些不同的示部字。已故的诗人兼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就说过,本来“卜辞的‘示字,应是石主的象征”。据说,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宗庙中或祭壇上设石主(后来又设神主或立尸)作象征的习俗,所以,“示”就跟古代的祭祀和神灵有关系了。它与天象中的“电”组合为“神”,与筑土为坛的“土”组合为“社”,与手持肉的“”组合为“祭”,与神主牌位的“且”组合为“祖”,与奉酒尊祈福的“”组合为“福”,与奉玉于器中的“”组合为“礼”,而“祫”是“大合祭先祖”,“禘”是王正月郊祭天及先祖。你从这些今人已经很陌生的字里,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也可以证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古话。如果说,从汉字的衍生发展中我们大体了解的是古人“怎么想”,那么从某一类汉字的多少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想什么”。也就是在文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在文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代中国生活的重心和兴趣,难怪有人说,从古代文字中可以看出一部部古代中国的“文化史”。
四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周祖谟先生给我们讲《说文解字》,他的课讲得很有意思。有一次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字,上面加一个“口”,就成了新的字。不光如此,如果口朝上,就是“兄”(祝);口朝后,就是吃完了不再吃的意思,也就是后来的“既”(已经);如果口朝前张大呵气,就是“欠”,打哈欠的样子;如果在人头顶上加一横,就是“天”;如果在人下面加个脚(止),就是“企”,企就是站,香港人广东人现在还说“企”;当然,加一个“目”,那就是看见的“见”;如果这个“目”倒下来了,想睡觉了,那就是“卧”。他说,一个“文”生出无数“字”,通过用字的指事、形声、会意、假借等途径,慢慢分工、分化、滋长、变异,经过甲骨文、金文、六国文字和秦小篆,到汉代隶书,文字由简而繁,逐渐变化、孽生、滋长,人们就有了足够表达各种思想的成熟的文字。
二、说“文”解“字”:何谓“六书”?何谓“部首”?
那么,汉字的造字用字是怎样的?汉字怎样表达万事万物?
最早对汉字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叫许慎,他是东汉的一个大学者。他为了给读书人读经典提供文字语言基本知识(那就叫“小学”),编了一本辞典《说文解字》。现在来看,是他最早介绍了汉字造字或者用字的六种方法(六书),也第一次全面对通行的汉字做了声音和意义的解说,也是第一次给汉字做了一个分类。
也许有人会说,《说文解字》有什么了不起,这不就是一本字书吗?可是,它的意义可不比一般的辞典。
这里得先讲一下汉字的特别之处。要知道,在世界所有语言文字中,大概只有中国至今还使用着从象形符号直接衍生出来的文字,其他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早就已经消亡了。且不说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就是亚洲的日文、韩文,也逐渐变成了拼音文字。大家知道,拼音文字和它所表示的事物现象,已经相去甚远,“词”与“物”之间脱钩了,关系几乎很难解释。所以,有的学者就说,语言文字只是“约定俗成的、任意的符号”,根本无法探究早期人类创造文字时候的原初思想。可是汉字却不一样。比如说,英文的“sun”,为什么用这三个字母来表示太阳,这似乎没法解释,但汉字“日”,古代作“”,一看就知道这是太阳的象形。英文的“east”,为什么要用这四个字母表示东方,恐怕也没法解释,但是,汉字的“东”,古文作“”,分析一下就知道,这是太阳从树木中升起,那太阳升起的方向就是东方。这样,汉字就为我们了解古人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我们了解自己的语言特征提供了一条坚实的路径。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了解汉字的最重要的大门,大门一侧是汉字的古代形态,大门的另一侧是汉字的现代形态。打开了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从古到今、顺利地弄清汉族中国的语言与思维特征。

《说文解字》收录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另外还有一些重复的、别体的,这里就不说了),这些字按部首分成了五百四十部。我们要说,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第一,把字按部首分类,这是许慎《说文解字》的一大创造。所谓“部首”,前面说了,就是每一类字有一个可以统辖它们的首领字,这个字常常是这一类字的“文”,也就是意义来源(当然,偶尔体例不纯,也有音符),就是“意符”。用现代通行的话来说,“意符”就是表示意义的偏旁,比如“噤”“听”等字的部首,就是“口”,因为和嘴巴有关,所以凡是和“口”意义有联系的字,都归在这一部首里。许慎认为,这些部首和宇宙天地间事物的门类是一致的,部首将文字分为五百四十类,天下事物亦是五百四十类,文字在部首下有条不紊,正如天下的事物各归其类,有条不紊。第二,《说文解字》在每个字的开端标注了篆体字形,这也很重要,因为它能给后人指示一条通往更古老文字的途径。《说文解字》不仅保存了秦汉之间通用的篆体,还收集了逐渐消失的“古文”(六国文字)和逐渐滋生的“或体”“俗体”(汉代民间流行的文字),这等于为我们展示了战国到汉代丰富的文字资料,而这一时期又恰是汉字形态变化最大的时代。通过《说文解字》可以追溯与破解更早的甲骨文及金文,如果没有它作为中介,也许,我们将无法解读那些与现代汉字差异极大的古文字。这就好比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发现,对于破译古埃及文的意义。第三,对于现代人最为重要的,是《说文解字》对每个字的解释和分析。《说文解字》中记录了大量词汇的古义和古音,比如“自”的古义是“鼻也”,原来就是画的鼻子的样子,人习惯用手指着鼻子,就是在说“自己”;“听”的古义是“笑貌”,我们就知道,它的意思和嘴巴有关,是笑嘻嘻的样子,而“斤”只不过是表示这个字的声音。这里顺便讲一句,我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凭着现代的印象去解读古代汉字。
但是,《说文解字》解释和分析的最大意义,是它肯定了“六书说”对于汉字分析的作用,并在《说文解字》中运用它,对每个汉字的字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析,从而使人们了解每个汉字的字形结构及字义来源。所谓“六书说”,是指汉字的六种构字法:
(1)象形。就是用简化的形式画出它所表示的事物,如“犬”作“”、“人”作“”等。
(2)指事。就是用一个抽象的符号在所表示的事物上标志出它的所指,如“本”字就是树根,所以在木(树)下加一道来表示根部,刚才我们说的“刃”也属于这一类。
(3)会意。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某种含义的字,如前面说的“牢”是用“宀”和“牛”合起来表示关牛、羊的地方。
(4)形声。就是用一个表示意义的形旁和一个表示声音的声旁合成的字,如“伟”是“从人,韦声”,又如“江”是“从水,工声”。这类字后来占的比例最大。
(5)转注。关于转注,古今说法不一,可能是指可以与形旁互训的字,可能是同一部首内衍生变化出来的字,也可能是指形体变化但意义相同的孳生字(许慎举例“考”“老”)。
(6)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表示这个意义的一个字,便用一个同音字来充当这个字,如来来去去的“来”,是用本义为麦的“来”字充当。前面我们说的“其”,就用原本是簸箕的“其”借代。
这六种构字法虽然还不精确,但大体总结了汉字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种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运用了这些构字法,对每一个汉字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字义的由来。
在漢族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汉字虽然几经变化,篆变隶,隶变楷,但是几千年一直延续下来,这在世界上很罕见。更重要的是,它还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使得汉族中国人有一些思维习惯,似乎和其他民族不太一样。
三、通过汉字: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与表达
那么,为什么说通过汉字思维和表达,就形成了汉族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这里只能简单讲。
第一,刚才我讲到,汉字从象形的“文”,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字”,形式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大篆、小篆、隶书,一直到楷书。尽管离开它早期模样已经很远,但是,毕竟单个汉字还是残存了某些具体形象和意义,比起使用纯粹表音符号,文字和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文字,还是不一样。汉字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可是,通常表音文字,像拉丁文以及后来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也可以包括现在的日文(假名)、韩文、蒙文等,却只有音、义两个要素。这种单音节的方块字,使得文字的使用者,对于万事万物往往习惯直观感知和形象表达,不太擅长悬浮在半空,纯粹抽象地表达和运算。《老子》说,“始制有名”,文字是把世界呈现给我们的一套象征,每一种文字都以一种方式来描述和划分万事万物,人在学会并且习惯这种文字时,就自然地接受了它所呈现的世界。
有人说,汉字是偏重于“看”的文字,西文是偏重于“听”的文字,这有一定道理。和世界其他文字系统相比,汉字恐怕是唯一没有发生过根本质变的。如果我们同意,思想是以语言和文字进行的,文化是依靠语言和文字传递的,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语言文字系统,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儿汉字,在历史上长期地延续使用,肯定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也就是汉族中国人始终不习惯和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习惯使用纯粹而抽象的符号,甚至总觉得,文字和事实之间是重叠的、相连的。我们不妨看一看几千年的中国,为什么对于文字似乎总有一种神秘和崇敬的态度?从文字形状中进行训诂、解释和揣测,依靠文字(名)来整顿社会(实),借由文字形象进行联想,通过文字形状构造神秘图符,一直到由文字形状构造来预测吉凶,无论在“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中,文字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
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胡适一九二八年写的《名教》,他说的“名教”,就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他说,中国一是相信“名就是魂”,二是相信“名有神力”,三是相信建立社会秩序需要“正名”。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比如人的五行中缺什么,就用带什么偏旁的字来命名,就可以补救命运的缺失;比如把仇人的姓名字样写在纸上,用刀砍用针扎,就不仅可以出口恶气,还能够报仇生效;又比如通过文字标语或者在标语上给姓名打叉,就能够诅咒和消灭敌人。所以,战国时秦国打仗,就有《诅楚文》,古代治病,除内科、外科之外,还有专管念咒的“祝由科”。古往今来中国人对于文字过度依赖和过度迷信,以为文字就是事实本身,文字背后就是力量,这是一种文化传统。
第二,汉字的衍生和分类,塑造了汉族中国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这就要再次说到许慎的部首了。后来人可能觉得,这只是文字分类的“部首”,但在古人心目中,部首这些“文”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就等于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已故的郭宝钧先生统计过《金文编》中,“衣”“食”“宀”三部中的字,指出甲骨文中,衣部只有一个“衣”字,但到了金文中已经有了十二个从衣之字,而《说文解字》更增至一百一十六字;食部之字,甲骨文中仅有“食”字,到金文已有十字,《说文解字》中有六十二字;“宀”部之字,甲骨文中有“家”“宅”“室”“宣”“向”“安”“宝”
“宿”“寝”“客”“寓”“宗”十二字,但金文中却有三十六字,《说文解字》中则有七十字。在这些“字”的滋蘖过程中,你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和知识里面的万事万物,是如何被文字表述、分类和整合的,这就是“正名”。古人所谓“名正言顺”就是说,文字(语言)通过分类在整理人的知识。在汉字同偏旁(部首)的字里,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人的“分类”观念与西方或近代的所谓科学“分类”有一些不同。汉字常常是凭着对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的。
举一个例子。例如“木”作为“类名”,本来是植物的抽象名称,在“木”为意符的字中应该都是树木,如“梅”“李”“桃”“桂”等。但是,实际上在汉字中,“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树根)、“末”(树梢),可以是以树木为原料的建筑部件及各种用具,如“柱”“楹”“杠”“栅”,还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栠”(木弱貌)、“枖”(木少盛貌)、“朵”(树木众朵朵)、“枉”(曲貌)、“柔”(木曲直)、“枯”(槁也),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有关,但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特别是刚才提到的“东”,本来是“日在木中”,象征太阳初起的方向,“木”最多是一种背景,但也因为一种联想,而归入了“木”一类,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在后来的五行思想中,人们就把“东方”与“木”也连在了一起。
给事物分类就是奠定知识秩序,奠定知识秩序就能型塑思想世界。纷纭复杂的世界在思想上被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的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联系。我研究思想史,在我写的《中国思想史》里,曾经用几个在后世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概念为例,讲过这个道理。第一个是有无的“有”字。有学者指出,殷商卜辞中以“又”表示“有”,这已经是引申义,“又”本义原是右手,从右手的便利到佑助,再到领有的“有”,这是文字意义的延伸。但是,据说殷商之“又”只是暂时的领有,最多是神明的护佑,而在西周金文中蘖生出“有”,是既从“又”又从“肉”,表达了对实际物事的领有。于是,从“右”“又”到“有”,在文字的衍生中,意义也在延伸,而它们在字根上,又都和右手的“又”保持了同“类”的关系;第二个是思想史中很重要的“理”字,据说它从“玉”得义,第一个意思应该与“治玉”有关,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就说:“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它出现了第二个意思,引申为把土地分成小块,像《诗经》中《节南山》的“我疆我理”,《江汉》的“于疆于理”。如果说这还没有越出“剖析”的意义,那么,第三个意思就开始越出界限,段玉裁说,“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从“天理”再联想下去,万事万物都有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于是,这个“理”字就贯通了相当多的领域,成了一个大概念。当人们用“理”来理解各种现象和事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玉”的纹路、土地的沟洫甚至文章的气脉,变成一套互相贯通的隐喻系统。它使得汉族中国文化中,形成一种超越事物门类来联想的思维习惯。
第三,汉语的句式显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惯常思路。尽管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由于刻写或铸造不易,常常简化,但是,汉字(汉语)的句法确实比较简单。这些简单的句式要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常常一半要依赖阅读者对这种表达方式的习惯和熟悉,才能补充完整。所以,它既不像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被动主动、因果关系、过去现在未来时态,也不像现代汉语,极力建立完整的、表述充分的主谓宾定状等句法。有学者就指出,在早期汉字中有很多简略的句式,比如,主谓可以颠倒,使动、意动的句子没有明显标志,句子可割裂等。即使在后来的汉语尤其是书面文字中,语法关系也常常不那么严格和细密,表达者常常省略或颠倒,然而,通过“以意逆志”,阅读者也总能明白。这是否反映了古代中国思想的感觉主义倾向?
正因为汉字表达与思维的长期延续,由于无需严密的句法就可以充分表现意义,句法的规定性、约束性相对比较松散,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思想传统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语言本身是思维的产物,也是思维运算的符号,如何表达与如何理解,本来需要有一种共同认可的规则。但是,当文字的图像意味依然比较浓厚,文字的独立表意功能依然比较明显时,就可以省略一些句法的规定和补充,凭着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共同文化通感,他们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顺便说一句,在哲学领域里面,西方人常常讨论“Being”的意义。这个“Being”,中文很难翻译,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翻译成“是”,有人还翻译成“此在”;但是,它在西方思想世界是一个关键词,因为世界如何被呈现,万事万物如何被命名,人类怎样认知这个现象世界,都追溯到这个“Being”。这有点儿类似老子追问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中的“道”和“名”。
不过你注意看,古代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在意“是”“在”这樣的概念,这和汉字的思维和表达有没有关系呢?这扯得太远了,就此打住。
四、书同文:“中国”的形成
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天下,除了北方的匈奴、南方的西南夷之外,他采取了“书同文”的方式,废除互有差异的六国文字,统一用秦的小篆。汉承秦制,文字逐渐简便,渐渐又形成了通行的隶书,真的形成了一个“汉字共同体”。因为这时候有了大汉帝国,所以,我们就可以正式把这些文字叫作“汉字”了。
“书同文”真的很重要。其实,不要说春秋战国,就是到了秦汉时代,各个地方的语言还是不一样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怜爱”这个意思,东齐海岱之间叫作“亟”,秦晋之间也叫作“亟”,陈楚江淮之间(也就是南方)叫作“怜”,宋卫邠陶之间则叫作“怃”或者“煏”。又比如“害怕”这个意思,河北一带叫作“谩台”,齐楚之间叫作“胁阋”,南方两湖一带叫作“嘽咺”。再比如有关女子的“美丽”,江淮南方一带叫作“娃”,河南河北山西一带叫作“艳”,湖北河南之间叫作“窕”,而陕西山西,有的地方叫“好”,有的地方也叫作“窕”。再说“大”和“多”,齐宋之间叫作“巨”或者“硕”,这和我们说的“硕人”“巨多”还连得上,可是楚魏之际,“多”就叫作“夥”(伙),这就是《史记·陈涉世家》里面说的“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自己也解释说,“楚人谓多为夥(伙)”。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来自一本叫《方言》的书,是西汉末年大学问家扬雄编的,记录各地语言,全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据说,古代中国从秦朝以前就开始,每年政府都会派“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大概是为了大一统做准备吧。
秦汉时代,中国逐渐形成基本轮廓,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在“九州”基础上逐渐拓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统一天下,“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个时候“中国”比起《禹贡》所叙述的“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来,虽然在西南、南方和东北方略有扩张,但核心区域仍然大体相当;到了汉代,帝国的控制范围,西面到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为海岱、江浙。与秦帝国相比,西汉最重要的疆域扩张是汉武帝时代,一方面在西北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设西域都护府,西北边疆由此向外延伸;另一方面打通西南通道,相继设立越雋、沈黎、汶山、武都以及益州,这使得西汉“中国”又向外拓展了很大一块。
可是,地方大了,怎么管呢?世界上很多的古代帝国,控制的区域不小,可是往往有“统一”没有“统合”,像古代波斯帝国就是这样。可是在中国,“行同伦,车同轨,书同文”却很重要,它把“统一”发展到“统合”,特别是核心区域,除了依靠秦汉政治制度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之外,在帝国内部建立统一制度和统一文化,依靠的政策之一就是使用统一汉字。我们现在出土的好多汉代的文字资料,遍布汉帝国各地,北边到河北(定县八角廊),西边到敦煌(敦煌悬泉置),南边到湖南郴州(苏仙桥,汉代桂阳郡),东边到连云港(尹湾)。而且各种类型的文献,都用一种文字,无论是写在帛书上的,比如南方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还是写在竹简上的,像远在西北居延出土的汉简;无论抄写的是经典(像河北定县出土的《论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周易》和《老子》),还是实用医书(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引书》和《脉书》),特别是各种公私机构的文书与信函,都用的是汉字,这些汉字就把整个帝国连成了一个世界。
当然,文字之外,还有语言。从古到今中国为什么要推动“官话”“国语”或者“普通话”?还不是因为中国疆域太大,各地方言不同。虽然都是中国人,闽越人未必通晓川滇之言,北方人难懂瓯闽方音,所以,只能推行一种共同的文字语言来互相沟通,让各地人都觉得自己讲的是一种语言,是一个国家的国民。隋朝的陆法言编《切韵》,其实也是为了南北如果统一,各地人能掌握共同语言声韵。不过,古代不容易,现代可以靠普通话,用广播电视和教育机构来普及,可是在古代中国,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时代,主要就只能靠共同文字,也就是“书同文”的汉字来互相理解了。
因为这是“看”的文字,可是,如果是“听”的文字,在拼写不同方言的时候,必然还是不同的符号组合(欧洲各国语言就类似这一情况),那么,它怎么能“书同文”,使得不同方言区都能共同理解呢?显然,只能是“看”的汉字,才能超越不同方言,让各个区域共同使用。是不是汉字对于形成中国的意义很大呢?
五、书法与诗文:汉字的文学艺术
汉字的使用让汉族中国人形成一些思维习惯,比如习惯于联想,很注重感觉,不是那么讲究严密的逻辑(时态、因果等)。这是一种文化,文化没有好和不好的分别,我只是说,这是一种传统留下来的习惯。但是,它也使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很特别的文学艺术,最突出的一个是诗歌,一个是书法。
关于书法,我这里不多说。虽然世界上所有文字都有如何写得更美的技巧,但是写字成为一种很大的艺术门类,倒是中国特色。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书法史之类的书。这里我多讲几句汉字和诗歌的关系。三十年前,我写过一本讲诗歌的小书《汉字的魔方》,原来最开头有一节,叫作“汉诗是汉字写成的”,这好像有点儿讲废话,汉诗不是汉字写成的,难道还是外文写成的吗?所以,后来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我就把这一节删去了。不过现在想想,这个道理还真得好好讲一讲。就是因为我们用汉字,汉字又是一个个的方块字,每一个字有它独立的形、音、义,我们的诗歌才会有对偶、平仄、格律,而且还会衍生出回文、藏头、对联等文学形式。
汉字对于中国文学,实在很重要。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史记》里面记载飞将军李广的那一段,“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这一段非常精彩地呈现了传统汉字汉语的特色。李广出去打猎,看见草里面的大石头,以为是老虎,就给它一箭。“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八个字,你用英文或者现代汉语重新写一遍试试,恐怕字数会多很多。特别是最后两个字一句,生动地呈现了猎人视觉中的先后过程,先是射中了石头,然后看到箭头没入石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石头。这八个字不光简练,而且一读还能体会到身历其境的紧张,以及恍然大悟之后松一口气的感觉,这一方面是凝练紧凑的汉字的缘故,另一方面是阅读汉字文章的人联想的缘故。另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读过杜甫的《旅夜书怀》。它的第一、第二句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不用任何动词和形容词作谓语,直接用名词拼合成句,可是它的意思,靠着读者联想也能呈现。既可以理解成,微风吹拂长满细草的江岸,高高的桅杆耸立于夜空中的船上;也可以理解成,微风吹拂着岸上的细草,船上高高的桅杆耸立在夜空。这就是汉字诗歌常有的特殊句法,后来唐代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元代马致远《天净沙》里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也是一样。接下来第三、第四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五五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非常整齐。只有十个字,意思却很多,由于星辰“垂”在平野上,更显出平野的“开阔”,由于月光“涌”在江面上,更显出江水的“奔流”,而且“垂”字和“涌”字,虽然一向下,一向上,但都和平野、大江成为直角的对映,而且一静(垂),一动(涌),也相映成趣。为什么唐代诗歌好?原因之一就是,到了唐代,诗人已经把汉字汉语的这些特点琢磨透了,在写诗的时候,充分发挥了方块的、单个儿的、有声调的汉字特点,创造了魔方一样的律诗绝句,所以它叫“近体诗”。
前面我提到过我的老师之一,也就是已故的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这里讲一段和他有关的故事。当年,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招生出考题,出了个对对子的题目,他出的上联是“孙行者”,让考生回答下联。据说只有周祖谟先生答的他很满意,就是“胡适之”(据说答“祖冲之”也是可以的)。这个试题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陈寅恪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字《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来回答外界的质疑。他说,他之所以用“对对子”来考察学生,其实就是想找一个形式简单,又突出“与华夏语言文学之特性又密切关系者”,因为对对子可以考察出学生对汉字的虚实、平仄的掌握,也能够间接了解他读书多少,思想有没有条理。几十年以后的一九六五年,他又再次解释说,他出题的时候是受到苏东坡两句诗的启发,“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这两句诗里,后三个字是非常绝的对子,不仅“行”和“退”都是表示行走的动词,“者”和“之”都是虚字,而且“韓”字和“卢”字其实有关系,因为“韩卢”是《战国策》里记载的一条狗的名字,而且平仄一一相对,所以这两句“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而他期待的答案“孙行者”对“胡适之”也一样,孙和胡,就是“猢狲”,也和“韩卢”一样,是一个动物名称。
这种看上去是一种“奇技淫巧”或者“语言游戏”,但是它确实反映了汉字的特征。所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借用这种汉字的特点,逐渐突出了对偶、平仄、颠倒、错综,以及在对偶平仄的基础上发展成近体诗,也就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之类。关于古代中国诗歌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不妨看一看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
六、汉字文化圈?
在一开头我就说过,汉字很早就陆续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和越南,虽然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官方的、正式的、典雅的书面文字,还是汉字。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式公文,像国书之类,必定用的是汉字文言。日本当年往来日中之间,他们自己的官方文献,无论是朝廷的“宪法十七条”还是官方史书《日本书纪》,都仿效中国的格式,用汉文书写。宋代之后,日本与中国交往,为了外交文书典雅,就常常请禅宗和尚代笔,还让禅宗和尚当使节,因为他们在学习禅宗知识的时候,都要用汉文读书,所以汉文功底很好;朝鲜和日本之间互派使节,也要用典雅的汉文撰写国书。十五世纪(1458)琉球郑重其事铸造的“万国津梁”铜钟,上面的铭文也是汉文:“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而他们的文学呢?上层的、文人的、典雅的文学,还是写汉诗,学杜甫,学白居易,一直到明治时代,文人学者如果不懂汉字不会汉诗,就显得没文化。甚至他们的姓名字号,也得用汉字,找一些高雅或者有来历的字眼儿,像“豹轩”“如翁”“寒竹”“茂卿”,等等。所以说,这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可是,当这些国家一方面开始产生民族独立意识,要凸显自己特别的文化,一方面需要向下普及知识,追求说话与书写同一,也就是“言文合一”,就开始淡化甚至取消汉字。比如朝鲜,在世宗二十六年(1444),也就是明朝正统九年,朝鲜国王就颁布了《训民正音》,大力推广谚文,谚文就是有音无义的朝鲜拼音文字。当时,有一个叫崔万理的三品官儿就反对,他说这很危险,因为推广了这种文字,就违背了“华制”。什么是“华制”?就是书同文的以华夏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他说,只有蒙古、西夏、日本、西蕃(西藏)才另有文字,但凡是另有文字的,都不是文明人,“是皆夷狄耳”。可见文字是一种很重要的认同纽带和文化联系。可是,不光是朝鲜在李朝开始推广谚文,日本根据汉字创造假名,安南在较晚的时候用喃文(后来更改用表音文字)。到了现在,韩国、朝鲜和越南都不用汉字了,日本虽然还保留了“当用汉字”,但是也渐渐少了,而用片假名直接表述的英文词汇越来越多;越南后来干脆就用拉丁文拼音了,乍听上去,好像调调儿还挺像两广粤语的,但是写下来,你一个字也不懂。一九九三年我第一次去韩国,满大街还是汉字,从朝鲜国王的行宫景福宫,到后来被烧掉的大汉门,一路上看过去有很多汉字招牌,恍惚之间似乎还在故乡。第二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每天看日本的报纸,满纸汉字,尤其是《读卖新闻》头版的“天声人语”栏目,就算不懂日文内容,但用汉字的这四个字,怎么看怎么有深意。可是过了十几二十年,我几次到韩国,渐渐地汉字几乎全部消失,看着满眼的韩文成了睁眼瞎,不由得生出一种异域的陌生感。日本也差不多,再拿起报纸,汉字越来越少,洋文越来越多,可洋文还不是洋文,是用片假名拼出来的洋文,更是两眼一抹黑。越南就更麻烦了,十年前我去河内和西贡,除了原来的寺庙、孔庙这些还有几个汉字之外,其他清一色都是拉丁字母,他们那儿出版的学术书,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书。
所以说来说去,其他地方虽然曾经用过汉字,但是不一定非得用汉字,还是汉族中国人离不开汉字,用汉字思考,用汉字书写,用汉字表达。不信你仔细想想,你思考的时候和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说汉语?所以我说,汉字,通过汉字思考,以及用汉字表达,呈现出汉族中国人的一些思想和文化特点,真还是汉族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七、普通话与简化字:两难的选择
汉字承载着汉族中国文化,也影响着汉族中国人的思想,还型塑了汉族中国的文学艺术。可是,这种文化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中国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的汉字和汉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和汉语,和先秦、秦汉、唐宋甚至是明清时代都不太一样,虽然都是汉字和汉语,但是现在我们习惯的汉字和汉语,不仅由于历史变迁,以及蒙、元、清时代的语言冲击,在语音上有很大变形,而且更重要的是到了近代,经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有了三个很大的改变。
首先,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界限开始消失,虽然这种“言文合一”使得知识更容易普及,语言更贴近生活,但也使汉字原本承载的一些传统文化因素越来越淡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猛烈冲击了传统书面文字,也就是文言文的权威。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提高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加强现代国家中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但是,如果不能适当保留和吸取传统时代文言的典雅和精致,客观上也造成了新旧文化的断裂,也导致了现代白话的粗糙。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有教养、有文化的表达。可是,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分别,同时也使雅、俗文化不再有分别。这里的好处,是体现了“平等”和“亲切”,不再需要端着架子咬文嚼字,就像《镜花缘》里面君子国酒保说的“酒要一壶乎”“菜要一碟乎”那么酸溜溜,但它的问题就是原来汉字文言里面的典雅文化也随之流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文书也不那么庄重了,特别是电脑普及、网络流行,所有的文化格调都湮没在网络中了。比如,过去人写信,正事儿说完了,最后嘘寒问暖来两句“足下作归省计否?新凉入序,寄语加餐”。这话说得多好。可如果用现代白话来说,而且说得白一些,那就是“你还打算回家乡看看不?秋天天气凉了,你老兄多保重”,意思一样,可那韵味就差了许多。再比如苏轼的《水龙吟》,一开头两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是不是很有意境?可如果用通俗白话来说,那不过就是“(这杨花)像花儿又不像花儿,没人觉得它落下来有什么可惜的”。我常常很生氣的是,学生给我写信,既没有抬头,末尾也没有署名,事儿说完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其实也就是原来传统的雅文化渐渐淡去了。大家如果对传统文言和现代白话的问题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张中行写的《文言与白话》。
其次,现代汉语羼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
我有一个切身感受,我当年当农民是在苗族地区,除了一位生产队大队长懂汉语,所有人都不太懂汉语,很长时间里面,苗族人表达他们的生活世界,用苗语是足够的,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的苗语不够用了,于是苗语就不断掺入很多汉语词汇,再表达出来,新一代苗族人感受的和表达的世界,就和原来老一代的苗族人不一样了。
现代的汉族中国人也一样,通过已经改变的现代汉语,理解、想象和表达出来的世界也与过去不一样了。今天的汉语从晚清以来,先是从日本转手进口了很多新词,接着又接收了好多来自西方的新词,像“经济”“哲学”“科学”等。后来世界变得更快,无论报纸、书籍、信件、说话,一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花样翻新充斥在我们的眼睛里,像“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一直到“下岗”,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世界。即使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像西文那样的句法,“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猫”(modem)这样的进口词,使得我们眼前的世界大大变样了。
第三,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现代文字和传统汉字之间距离更拉大了。传统汉字也就是繁体字,和原来的字形、字义关系更加紧密一点。简体字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比如借鉴、鉴别的“鉴”字,早期是一个弯腰的人(人),加上一个大大的眼睛(目),看一个装满水的器皿(皿),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人在水中看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脸干不干净,好不好看,有没有疤痕,借着水面一看就知道,所以,这就是“鉴照”“借鉴”“鉴别”,老话说,以水为鉴,以铜为鉴。后来加上一个“金”,写成“鑑”,只不过是因为后来镜子都是铜镜,所以加上一个意符。可是,现在写成“鉴”,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不清楚了。这样的演变之后,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可能发生了问题,至少是淡化了。
这不止是繁体与简体两种写法上的差别,也是如何面对现代知识和文化传统的两难问题。承认现代并且面向未来,我们说应当简化汉字,使得知识容易普及;但是回顾过去,我们也觉得应当传承历史,保留传统文化。爱书法的人总觉得繁体字好看,简体字不好看,其实,繁简之间,并不是美丑那么简单的。我们看一个例子,一九五五年,原来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读到《汉字简化方案》,就痛苦地说:“文字改革之谬妄,吾侪言之已数十年。最主要者,汉字乃象形,其与拼音,至少各有短长……中国人以数千年之历史习俗,吾侪以数十年之心濡目睹手写,尤能深窥其价值与便利处。”“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以文字本质之不同,养成中西人数千年不同之习性……昔人谓‘中国以文字立国,诚非虚语。而文言废、汉字灭,今之中國乃真亡矣。”
他当然是一个比较顽固的文化保守派,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也反对提倡简体字,这当然并不一定有道理,因为时代变了,现代国民不可以这样抱残守缺。可是,他为什么把繁体简体变化的意义讲那么重?其实,就是担心人们使用简体字,离开传统时代的典雅和教养越来越远,以至于传统中国文化因此坠落失散。所以他说,“简体俗字之大量采用”,将导致“所谓中国人者,皆不识正体楷书之汉字,皆不能读浅近之文言”,最终连四书五经、韩文杜诗也无法读,因而“五千年华夏之文明统绪全绝”。
这话对不对?我并不完全赞同,我们还需要继续讨论。
本文系作者给《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增订本新补写的一章,由于是大学生通识课的讲课稿,所以保留了讲课的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