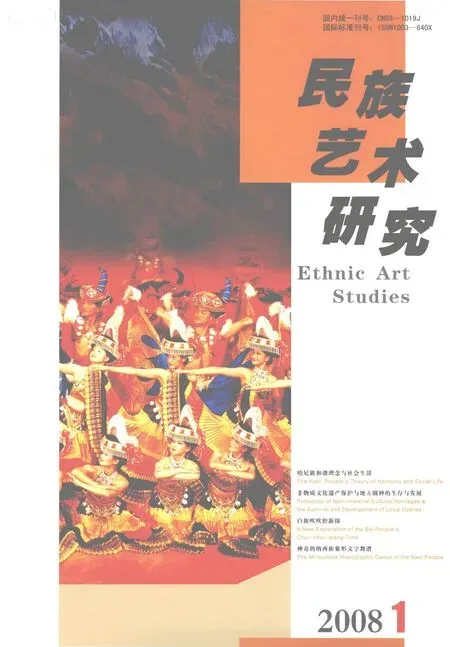中国音乐传承民族志的研究背景与书写
2020-07-12张应华
张应华
所谓 “音乐传承”,可以理解为 “一切音乐的教与学”,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教育学科 “母语教育研究”①关新:《中华文化为 “母语”的音乐在京研讨会纪要》,《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第27-29页。进程和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学术界往往将 “音乐传承”界定为 “民间音乐的教与学”,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间音乐 “本我”传统的自然传承;二是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民间音乐传承,即所谓的国家、学者等 “他者在场”的现代性传承。
中国当下的音乐传承民族志②音乐传承民族志是本文首次采用的一个学术概念,主要指向以 “民间音乐的民间传承”和 “民间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承”的专门性的民族志叙事与研究。研究是在民族志研究的影响下,基于音乐民族志与教育民族志的交叉综合研究。20世纪以来,民族志书写大体上经历了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三个总体递进阶段。③关于民族志书写历程,高丙中从学科史的角度认为民族志书写历程可分为 “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 “反思民族志”三个时代,参见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8-63页。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因而这里将借用朱炳祥的看法,将民族志的书写历程分为 “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和 “后现代民族志”三个阶段。参见朱炳祥:《三论 “主体民族志”:走出 “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39-50页。在此语境中,音乐民族志选取民间音乐文化为对象,表现为相互交叉、彼此相关、各有侧重的 “宏观→微观→微观+宏观”的规范范围、“客位→主位→主位+客位”的学术立场与 “比较→描述→描述+解释+比较”的描写方式①杨民康:《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论的回顾与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天籁)》2009年第3期,第1-8页。。
教育民族志多为学校教育的微观研究,内容涉及学校、教师、学生、课程、教学等等方面的个案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就其方法论而言,可划分为描述教育民族志、解释教育民族志和批判教育民族志三种类型,②巴战龙:《教育民族志:含义、特点、类型》,《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0-13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教育民族志研究的论域逐渐拓展到以 “文化”看教育的视界,关注不同文化现象中的教育问题,其中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传承问题是其论域中的一个重要视域。③陈学金、滕星:《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几个根本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64-69页。教育民族志方法论观念以及对于民间文化传承问题的研究视角,直接引导着音乐传承民族志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对于民族民间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的民族志研究,但是当下的音乐传承民族志并没有涉及学校教育体制内的有关学校、教师、学生、课程、教学的个案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因而,从具体的研究实践来看,我国当下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主要脱胎于音乐民族志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的 “母语”音乐文化教育大讨论之后,在音乐民族志、教育民族志的双重影响下,亦表现为描述、解释、反思等三种书写方式。
一、中国音乐传承民族志的研究背景
就中国当下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的文化背景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解读: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深厚而又久远的传承历史传统;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学术思潮;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理衍变;现代社会语境中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实践。
(一)民族民间音乐久远的传承历史
从事音乐传承的民族志调查与书写,总是基于这样一些民间事实和思路假定:在我国,不同的民间社会拥有诸多各不相同的民间音乐形式和品种,这些民间音乐形式与品种在不同的族群、区域等文化传统中均有着本原的文化根基和久远的流变历史;那么,根基如何持守?传统如何继承?均是民间社会自在自为、各有特点的传承观念、传承机制、传承习俗以及习得行为方式所使然。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总是依靠“传承”而得以存在,得以穿越时空,延绵至今。尽管我们没有能够在相关实物、相关文献中梳析出某一民间音乐有关古代传承的确切实证材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相关的口头传说中,或者在当下民间社会有关民间音乐传承观念、机制以及具体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中,领略到 “传承”这一行为方式对于民间音乐文化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流播至今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曾长时期对贵州苗族民间音乐进行田野调查,调查中收集到多则有关苗族音乐起源、音乐民俗、音乐传播等方面的历史信息的口传资料,虽然这些口头传说没有直接描述苗族先民的民间音乐传承行为方式,但是它强化了苗族人传习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信仰与信心,使之代代传习,延绵不绝。④张应华:《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往往将民间音乐的传承行为作为其 “田野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操作。众多的民族民间音乐调查发现,当下民间社会自在的传承观念与自为的传承机制均是 “祖先”遗留下来的。苏毅苗的田野提供了滇南彝族尼苏·花腰 “祭竜”仪式音乐的传承机制,她发现,“民间层面的家传、师传以及社会传承等,是尼苏·花腰固有的、传统的传承机制。”⑤苏毅苗:《地域性非遗音乐的 “多维”传承体系解读——滇南彝族尼苏·花腰 “祭竜”仪式音乐的传承方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17年第2期,第90-97页。王凤刚、杨正伟、吴一文、覃东平①参见王凤刚:《苗族古歌的传授风俗》,《民俗》(第一集),黔东南文艺研究室,榕江县民委编印,第67页;杨正伟:《苗族古歌的传承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22-24页;吴一文、覃东平:《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参见樊祖荫:《中华文化母语与专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王耀华:《20世纪中国高等院校传统音乐教学的回顾及其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赵塔里木:《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谢嘉幸:《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研究评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3期;冯光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等人对苗族古歌的传承行为进行了田野调查,揭示了苗族古歌师徒传承机制的 “祖训”:如吉日拜师、吉日开授、竹片传歌、只授 “歌骨”等等,这些“祖训”表达了苗族古歌的功能 (祈福纳吉)、苗族古歌的神圣 (传说歌神住在 “竹房”里)以及苗族古歌习得行为的继承性(传承 “歌骨”)和创造性 (创演 “歌花”)特点②张应华:《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深入,学界亦对民间音乐的习得方式进行了专题性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呈现了民间社会多样性的习得行为方式,归纳起来有 “口传” “神谕” “剽学”“体验”“谱传”等等。“口传方式”是民间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可表述为“口耳相传、口传身授、向无曲谱、改调歌之”的即兴性、身体性以及创造性特征。③朱结琼:《“口传心授”的多重解读》,《人民音乐》2016年第6期,第38-40页。“神谕方式”多为民间祭祀音乐的传承方式之一,即经由 “神话”或者 “梦境”而习得,是一种 “顿悟”的习得方式。④角巴东主:《“格萨尔”神授说唱艺人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1-124页。蒲亨强则发现了另外一种民间习得方式—— “剽学”,“剽学基于兴趣爱好的学习动机,与德国赫尔巴特 ‘以多方面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学说相通。”⑤蒲亨强:《“剽学”——值得注意的民间音乐传承方式》,《中国音乐》2002年第1期,第23-24,43页。“体验”与 “感悟”密切相连,多为民间班社师徒传承机制的习得行为方式,可表述为 “在创演中体验,在过程中感悟”。⑥张应华:《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与传承》,《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06-113页。在民间器乐、民间戏曲、民间说唱等表演行为的传习中,多采用谱传 (文本)与润腔(口传)相结合的方式习得,谱为框格,以润腔表现多样性的创造。⑦王先艳:《论民间器乐传承中的念谱过程及其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93-105页。
(二)“母语”音乐教育的学术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音乐教育界展开了音乐教育的比较研讨,在讨论中发现,中国音乐教育在国际音乐教育的比较中 “主体性”缺位。⑧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思考》,《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因而,回归、重建中国音乐教育的主体性成了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的主题。
1993年,全国教育科学 “八五”课题组与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举办的 “中外艺术教育比较专题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与会代表提请学界重视和关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问题,引发了建立自身音乐教育体系的文化思考。⑨谢嘉幸:《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研究综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3期。随后,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自己的 “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和民族音乐教育体系”。⑩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当代音乐教育学的重要观念之一就是 “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和 “实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
何以建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有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必须切实可行地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 “根文化”。樊祖荫、王耀华、赵塔里木、谢嘉幸、冯光钰、管建华①参见王凤刚:《苗族古歌的传授风俗》,《民俗》(第一集),黔东南文艺研究室,榕江县民委编印,第67页;杨正伟:《苗族古歌的传承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22-24页;吴一文、覃东平:《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参见樊祖荫:《中华文化母语与专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王耀华:《20世纪中国高等院校传统音乐教学的回顾及其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赵塔里木:《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谢嘉幸:《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研究评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3期;冯光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等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针对中华文化母语在音乐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危机、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缺失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讨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1995)的中心议题,至1999年 “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呼和浩特)的召开,一时间,“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建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问题”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教育的“主调”。《中国音乐》编辑部以 “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 (1995)和 “国际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 (1996)为题,连续两期刊发文章讨论 “母语音乐教育”问题,营造了一个母语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的良好的学术、理论氛围。
(三)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衍变
20世纪60年代后,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密切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有解释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思潮。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是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的代表人物,在以马林洛夫斯基 (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为代表的经典人类学研究转向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他对我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其所著的 《文化的解释》 (1973)和 《地方性知识》 (1983)两本论文集中。在 《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他认为 “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符号的和解释性的,作为人类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是解释性的”,①王铭铭:《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看到了解释者主体性的客观存在,承认在写作时的主体性的参与和解释。格尔兹的研究显示了对 “远方异文化知识”的迷恋,他的描述是一种地方性参与观察的 “民族志”,往往用 “深描”的方式对当地人的阐释进行再阐释。格尔兹提出的 “地方性知识”,对当代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着重要启示,管建华等人曾撰文予以积极评介:“‘地方性’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理念是紧密相连的,是对‘异文化’‘边缘文化’和 ‘女性文化’‘亚文化’‘微观文化’等研究的重视。”②管建华:《后现代人类学与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
后现代人类学思潮以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和《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两本书为标志。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通常以反思传统民族志和倡导实验民族志为特征,他们质疑传统民族志的客观性,认为马林洛夫斯基等人所提出的经典理论无非是人类学学者学术雄心的主观臆断,这种主观的臆断往往使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偏离现实,③瞿明安:《西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评述》,《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从而提出“实验民族志”的写作范式,力图在大的区域、民族和全球的政治经济场合里,强调从在异文化的描述中引申出对 “自我”社会的深度反思,并延伸至全球规模的文化批评。④王铭铭:《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20世纪90年代,汤亚汀对西方后现代人类学思潮以及后现代音乐人类学思潮进行了引介,他分别在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宣言》(1997)和 《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1999)两篇文章中,对西方后现代音乐人类学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地介绍。⑤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在以上汤文的译介中,我们看到学者们对音乐与人、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视,以及对音乐在建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的重视,这些学术思想将音乐置于整个文化网络中,探寻它的文化价值和 “人学”意义。
(四)现代社会语境中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传承实践
这里所说的 “教育传承”是指学校课程体系中的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现有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学校教育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1956年秋,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在专业高校探索少数民族音乐的教育教学。⑥雍谊:《访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班声乐专业》,《人民音乐》1963年第1期。1957年秋,内蒙古艺术学校宣告成立,开启了专业学校的 “潮尔”教学。⑦乌兰杰:《蒙古族 “潮尔”大师——色拉西》,《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1960年,新疆艺术学院设立民族器乐演奏专业,将新疆少数民族乐器引入高等专业教育层次。⑧肖学俊:《对新疆艺术学院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回顾与思考》,《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1960年前后,在 “贵州大学艺术系里,苗族芦笙就作为一种器乐专业,开设了选修课,并有相应的专职教师。”⑨隶月等:《贵州民族音乐教育述略》,《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0年第4期。
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传承”的真正创建。在专业教育教学实践方面,贵州大学先后开设了 “芦笙班”“侗歌班”。①隶月等:《贵州民族音乐教育述略》,《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0年第4期。1984年广西举办了首届 “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经过两年多的专业培训、艺术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②范西姆:《为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开拓新路——记广西少数民族歌手班》,《民族艺术》1986年第4期。1985年,西藏大学将 “扎木念琴”引入学校教学。③马可鲁:《西藏自治区音乐教育概况》,《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在普通音乐教育方面,中小学校的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传承也在逐步拓展,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出现了 “乡土教育”的萌芽,其初衷是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间音乐引入中小学校课堂,利用学校教育这一阵地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其中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推进的侗族民歌进课堂是比较典型的事例。④普虹:《民族音乐与 “双语教学”——关于新时期民族音乐传承的心得》,《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
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传承一方面扩大办学规模并使之制度化⑤隶月等:《贵州民族音乐教育述略》,《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0年第4期。;一方面在教学中总结经验,进行反思和调整⑥赵塔里木:《新疆高师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一个误区》,《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众多民族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高师音乐专业教育逐渐引入当地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传承成为民族地区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同时,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传承开始进入高校普通大学生的公共音乐课,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的高校中作为一种地方文化修养进入课堂教学,⑦杨殿虎:《谈民族师专公共音乐课的设置》,《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标志着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作用和意义逐渐得到公众的认可。⑧黄乃星:《南方少数民族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价值》,《民族艺术研究》1998年第6期。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则编写乡土教材,或实施 “双语教学”将本地区民族音乐引进课堂。⑨陈强芬:《营造民族音乐教学氛围——把乡土音乐引进课堂教学的尝试》,《湖北教育》1996年第2期。
二、中国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的三种书写方式
上述音乐传承的民间历史传统、音乐教育的文化思潮、音乐人类学的学理衍变以及现代社会语境中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传承实践等等,导引着民族音乐学者或音乐教育学者逐渐聚焦于民族民间音乐传承行为的田野调查,以民族志的方法描述、解释、比较与反思当代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观念与行为方式。
我国当下的音乐传承民族志调查与研究脱胎于一般的音乐民族志调查与研究。如果说在一般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中,音乐传承只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话,那么,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则是以音乐传承为主线的文化研究,在这类民族志的研究中,往往以“音乐传承”为核心,去观察、体验、感悟和理解它 “是什么”“为什么”“谁在做”“为谁做”“怎样做”以及它的历时性衍变问题、共时性流变问题与现代性调适问题等等。因而在方法论上,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和一般的音乐民族志研究一样,同样受到西方认识论哲学与西方民族志学术理论衍变的影响,经历了从 “宏观”到 “微观”再到 “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规范范围的衍变,从 “客位”到 “主位”再到 “主位与客位双重视点”学术立场的衍变,以及从 “比较”到“描述”再到 “描述、解释与比较三重表述”书写方式的衍变。当然,这种衍变并非是替代性的,而是相互交叉、彼此相关或各有侧重,总体上可以分为描述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解释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以及反思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三种研究和书写方式。
(一)描述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书写
本文使用的 “描述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来源于 “描述教育民族志” (descriptive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这一概念,依照巴战龙的理解,描述教育民族志常常暗含 “结构-功能论”的趣旨,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基本研究取向。⑩巴战龙:《教育民族志:含义、特点、类型》,《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0-13页。“科学主义”的方法来源于欧洲近代认识论的 “主客二分”观念,它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思维观念的能动性,以本质主义的观点去观察 “客体”的结构与功能,试图建构或丰富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科学主义者 “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一种以客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用格尔兹的话说,是 “第三人称的、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①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 “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24页。
本人曾采用这种方法论观念于2005年前后对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及其传承进行了实地观察和民族志书写。②张应华:《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与传承》,《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06-113页。在文本中,本人完全采用的是描述性的方法,首先把石阡木偶戏的戏班及其班主、管班、各行当演员、伴奏人员、随行学员作为客观观察的对象,在客位的观察中试图分析戏班的历史沿革和内部结构,并试图在描述内部组成人员的职能分工和传承行为中的角色关系的基础上,探析它的结构及其功能。其次,该文本的书写方法完全是第三人称的,戏班是 “我”观察的对象, “我”与班主、管班是分离的,“我”在外部 “客位”地观察他们,描写他们,“我”采用的是一种纯然的客观性思维,目的是寻找一种纯客观的感知经验。
杨民康对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与方法进行了详细地回顾与分析,参照他的观点,描述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属于 “微观视角”的规范范围,其学术立场以 “客位”为主,书写方法是 “描述性”的。他回顾了中国大陆的音乐民族志研究历程,提出中国大陆第一阶段层次的音乐民族志研究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研究观念来源于西方二战前后的人类学,是从客位切入音乐本体的表征层次;之后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进入,受解释人类学学理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音乐民族志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层次,即主位体察(可能从音乐本体,也可能从相关文化入手)的中间层次;大约1990年代以来,音乐民族志研究表现为第三个阶段层次的特点,即换位思考,将音乐更多地作为 “文化”进行透视性研究的内隐层次。③杨民康:《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论的回顾与展望》,《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8页。
因此,尽管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脱胎于音乐民族志研究,但在方法论观念上却晚于音乐民族志,也就是说,描述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依然是新世纪之交的重要书写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 《乌图阿热勒村蒙古长调民歌传承的考察与研究》等文本的书写中得以体察,该文本发表于2007年,作者采用客位观察的方法聚焦于调查对象的形态本体特征及其传承,以微观的视角,从研究者本人的 “主体性”出发描述了该村长调民歌内容方面的分类和应用方面的分类,以及历史上宫廷、寺庙、民间传承机制和当下家庭、民俗与其他社会活动传承机制、“口传”行为方式的特点等等,④夏敏:《乌图阿热勒村蒙古长调民歌传承的考察与研究》,参见管建华主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234页。可以说,这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 “描述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文本,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的基本理论。
(二)解释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书写
解释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类似于解释教育民族志 (interpretative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其理论基础是解释学的。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创立了哲学解释学,他认为理解不是认识论的,而是人的本能,是一种本体论的活动,解释就是通过对 “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 “存在”的理解。在此过程中,研究者的知识 “前结构”具有必然的合法性。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则认为人类历史是在演进和流变中,由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一种 “效果的”历史,真实的理解是各种不同的主体相互 “视界融合”的结果。格尔兹将解释学引入民族志的研究,“这种研究追求的是 ‘视域的融合’,从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同时赋予客位解释的合法性,注重从本土概念和地方性知识中提炼人们赋以文化以意义及其方法。”⑤巴战龙:《教育民族志:含义、特点、类型》,《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0-13页。解释教育民族志以及解释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采取就是这种方法论观念。
杨晓对小黄侗寨 “嘎老”传承的考察与研究①杨晓:《小黄侗寨 “嘎老”传承的考察与研究》,载管建华主编: 《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可以视为 “解释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在该文本中,多次出现 “小黄人说”“依照小黄侗语方言”等小黄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发言”,同时还十分详细地记录了侗歌传承的现场过程,以此作为小黄侗歌传承的主体性展示和主体性解释的 “文化现场”。从方法论上来看,这是作者对于小黄侗歌传承生态环境和 “上下文”的 “深描”,如同解释人类学的文本一样,作者紧接着将其作为研究者解释的基础,对研究对象的 “解释”再一次进行 “解释”,在再次解释中体现了研究者的主体观念与研究对象的主体观念之间的 “视界融合”,最终提炼出小黄侗歌传承的本土观念和地方性知识,即小黄侗寨特有的自然习得、嘎老传承的行为方式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隐喻:共生与互惠的内部关系以及本土与外乡的族群认同。
朱玉江对于淮剧的学校传承的民族志调查②朱玉江:《江苏盐城淮剧音乐传承的考察》,载管建华主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96页。也可以视为 “解释性”的,其采用的策略是问卷调查、访谈调查与课堂教学体验。作者深入到盐城中小学、艺术学校、老年人群体中的淮剧传承的课堂现场,在现场发放试卷,聆听淮剧课堂教学过程,试图通过问卷分析、访谈分析以及教学现场的主体性行为对淮剧的传承策略进行 “深描”,获得学习者的主体性解释,此为其一。其二,这里的主体性解释并非是该文本写作的最终目标,而是作者在主体间性的视域中建构自己的“解释”的一个维度。也即是说,盐城淮剧学校传承的调查研究最终被放置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予以讨论,作者带着理性主义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文化危机的 “忧思”进入田野,在作者看来,这种 “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是当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知识语境”,因而作者的 “忧思”即成了作者的主体性 “知识前见”或 “理论假设”,其文本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 “视界融合”,即研究者持有的 “前见”与传承者的 “解释”之间的 “视界融合”。依照杨民康的观点,上述杨文与朱文的研究仍然是 “微观”的,采用的是 “主位+客位”的学术立场,描写方法则是 “描述+解释”的,说明 “解释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并没有如同当时音乐民族志的研究那样,走向 “宏观+微观”的“描述+解释+比较”的多文化事项多点动态比较研究,比如同一音乐事项的民间传承传统与现代教育传承行为之间的 “差异性”和“相关性”的比较研究等等。
(三)反思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书写
反思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后现代人类学的影响下展开的调查和研究。实际上,我们不能将 “反思性”看成是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的 “阶段时序”特点,因为 “反思”其实是一种思维结构或者一种学术信仰,从古至今一直贯穿在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之中。这里提出的 “反思性的音乐传承民族志”,实际上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以及后现代人类学语境中的一种写作方式。
后现代哲学是针对现代性哲学而滥觞的,它们是一对不弃不离的 “欢喜冤家”。③贺来:《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一对欢喜冤家——对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辩证关系的思考》,《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第30-37页。现代性哲学坚持本质,后现代哲学则反对本质主义;④毛崇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23-28页。现代性哲学坚持基础,后现代哲学则反对基础主义;⑤赵光武:《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34-40页。现代性哲学坚持理性,后现代哲学则反对理性主义;⑥文兵:《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22-28页。现代性哲学坚持真理,后现代哲学则提出相对真理的概念。⑦陈金和:《罗蒂的真理观及其后哲学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22-25页。因而,“后现代”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以反思、怀疑为特点的批判精神。后现代哲学催生了后现代人类学,高丙中划分了民族志研究的三个时代,其中第三个时代是 “从反思以 ‘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民族志被置于反思的维度,人类学家开始将自己的学术活动 “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关系中”①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8-63页。反思或自我反思,批判或自我批判。
我在苗族社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总是怀揣着 “音乐”(Music)的概念,以音乐的音高、节奏、音色、旋法与曲式来观察和理解苗族民间社会以 “声音”为主要媒介的那些行为方式,我们将其称之为 “苗族音乐”。但是在后现代哲学看来,这是基础主义的思维和观念,基础主义认为世界上的文化均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永恒不变的、具有普适价值和意义的统一的基础,一切学科的研究均要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这就是我们带着 “Music”的概念进入田野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苗族民间社会类似于 “音乐”的概念是 “gol hxak(意为 ‘唱歌’)”,我开始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在 “反思性”的思维中建构文本,重新思考 “苗族音乐”的概念,因为它的界定决定了当代苗族社会的音乐传承观念与行为。实际上,“苗族音乐”是一个现代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反映了现代专业音乐的音乐本体观。在这一音乐本体观的影响下,其当代的传承与传播行为也是围绕着它的形态和本体展开的。②张应华:《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7页。有学者认为,我的这一文本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实验音乐民族志研究;多元主体共存的差异性对话研究;通过边缘反观中心的缺失;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对话。③管建华、欧阳平方:《全球化视野下的 “地方性音乐知识”研究——张应华 “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述评》,《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16年第3期,第130-133页。
反思必然反观,即是通过异文化的特征及传承研究来反观自我音乐教育的缺失。这种反观性的反思书写,集中地体现在近几年来管建华展开的有关东方音乐文化调查研究的民族志书写中④如陈国符、管建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CARE的人类学考察》,《中国音乐》2013年第4期,第38-41页;杨静、管建华:《东南亚三国音乐教育的人类学考察: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突围》,《中国音乐》2013年第4期,第29-31页;杨静、管建华:《印度学校音乐教育之旅》,《中国音乐》2014年第2期,第85-94页;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15-25页;管建华:《多为视野下土耳其玛卡姆音乐 “韵味”的思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15年第4期,第109-117页。,这些民族志文本表现出以下共同的特征:即研究的视角是 “宏观+微观”的,学术立场是 “主位+客位”的,描写方式是 “描述+解释+比较”的,是从现象学解释学认识论出发的对话与理解的民族志研究,是通过东方社会音乐教育的异质性,来反观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缺失的系列民族志研究。如在 《多维视野下土耳其玛卡姆音乐“韵味”的思考》一文中他写道:“本文介绍土耳其玛卡姆音乐的 ‘韵味’及其音乐表现形态,并将此与中国与印度音乐的 ‘味论’及其音乐的哲学美学认知方式”联系起来,其目的是 “力图引起人们对于东西方音乐哲学美学差异性的关注,以期对中国音乐传统流派风格 ‘韵味’的当代文化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⑤管建华:《多为视野下土耳其玛卡姆音乐 “韵味”的思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2015年第4期,第109-117页。再次进行思考。
余论: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的走向
在上述的回顾中我们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提出 “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以来,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论域,分别从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反思性研究入手展开田野调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过往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民间传承”的行为方式,聚焦于现代社会语境中民族民间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承实践。它脱胎于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但较少与教育民族志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理论相链接。基于此,当下的音乐传承民族志研究亟须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完善:
1.在学科建构上,还需全面吸纳音乐民族志与教育民族志的理论成果,在音乐民族志研究与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交叉点上寻找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 “音乐教育民族志”的理论体系。
2.在研究对象上,应在音乐民族志论域的基础上综合教育民族志的论域,从以往民族民间音乐的民间传承研究以及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传承研究走向一切音乐教育活动的民族志研究,重点研究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课堂、音乐教师以及学生的音乐学习生活、愿望、策略、观念等等;
3.在研究观念上,应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前人研究观念与方法的理论桎梏,从科学主义民族志、解释人类学民族志以及后现代民族志走向更为多元的、更为宏观的理论建构。
4.在文本书写上,应沿着以往 “描述+解释+比较”的描述方式继续前行,放弃文本写作的 “工具论”观念,将文本的书写视为文化的 “对话”,即在文本中进行多主体对话、多主体理解,通过对话达到理解,在相互理解中创生新的意义,抑或将上述三重描述修订为 “描述+对话+理解+创生”四重描述。
5.在研究目标上,应从以往的描述、解释以及反思走向反观,即在现象学解释学的视域中,通过异质性音乐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反观自我,从而实现 “反观性的音乐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文化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