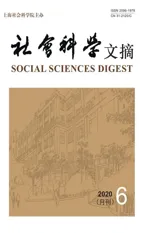70年来变文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20-07-09张涌泉
文/张涌泉
变文是我国失传已久的一种通俗文学体裁,自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被发现以来,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00多年来,变文的研究始终是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最为热烈且成绩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年,成就尤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
敦煌变文100多年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50年和后70年两个大的阶段。前50年,变文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战事延绵,所以系统、深入的研究还谈不上。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以后,随着国学的复苏并持续升温,变文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变文研究的成绩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1.“变文”的含义。“变文”是一种久已失传的文学体裁,传世文献中未见流传。所以当人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零散的变文写本时,不免感到生疏和隔膜。首先让人费解的是“变文”的含义。为什么叫“变文”?“变文”的“变”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的难题,至今似乎仍未找到大家都满意的答案。现在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大约魏晋以后,人们把表现佛教故事的一幅或一组绘画或塑像、浮雕称为“变”,后来又双音化作“变相”或“图变”,为同义复词;“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原本也是指组画,其字义渊源于变化、变现、变异等;“变相”是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画,“变文”本是“变相”的说明文字,类似于连环画的脚本,后来“变文”脱离“变相”而独立,便演变成为一种通俗文学体裁。Дх.11018 +BD11731+P.5019号正面为《孟姜女变文》,背面为《孟姜女变相》;P.4524号正面为《降魔变相》,背面为《降魔变文》,正是“变文”“变相”配合使用的实物佐证。
2.“变文”的类别。变文写本大多数是残卷或残片,没有标题;一些原有标题的卷子题名又有着变文、变、因缘、缘起、讲经文、赋、话、诗、词文、传等差别,即使仅有的八九种原来以“变文”或“变”题名的作品,也往往前题后题不一,甲卷乙卷有异:这种纷繁的情况,就给变文的鉴定带来了困难。所以当人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零散的变文写本时,隔膜和误解自然在所不免。1931年3月,《小说月报》刊布郑振铎的论文《敦煌的俗文学》,较早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后来郑氏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用“变文”作为敦煌所出讲唱文学作品的统称,含括讲佛教故事和非佛教故事两大类,其下统辖了讲经文、缘起、传等一些类目。王重民认为“讲经文是变文中最初的形式,它的产生时期在变文中为最早”。至于“因缘”,与“变文”异名同实。潘重规先生指出:
变文是一时代文体的通俗名称,它的实质便是故事,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赋、传、记等等不过是它的外衣。……变文所以有种种的异称,正因为它说故事时用种种不同文体的外衣来表达的缘故。(《敦煌变文集新书·后记》)
这是潘氏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3.综合研究。敦煌变文研究的前50年,除聚焦“变文”的名称、类别外,还对变文的来源、文本属性、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以及相关作品的演变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代表性论文有向达《唐代俗讲考》、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国学季刊》1937年第2期)、关德栋《谈“变文”》(《觉群周报》第1卷第1—12期,1946年)等。敦煌变文研究的后70年,除发表了更多专题性的论文外,还出现了一批硕博士论文及学术专著,如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四川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巴蜀书社2000年出版),荒见泰史《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复旦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李小荣《敦煌变文》(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等等,从原来的专题研究转向了系统、全面的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提升。
4.文本的整理刊布。敦煌变文文本的整理刊布,几乎是和敦煌变文的研究同步展开的。1924年,罗振玉辑印《敦煌零拾》(上虞罗氏印行),其中有“佛曲”三种(即后来收入《敦煌变文集》的《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文殊问疾)》《欢喜国王缘》等三种),这是国内外最早刊布的变文作品。稍后刘复辑《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5年刻本)、向达辑《敦煌丛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号,1931年)、许国霖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敦煌变文作品。此外,一些书刊杂志上也陆续校录刊布过若干篇变文作品。这些工作虽是零星的、不完整的,但为日后编辑比较完备的敦煌变文的校录本准备了条件。
1954年,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收录变文作品38篇,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的敦煌变文专集。其中所收既包括《目连变文》《降魔变文》这样写本本身标有“变”或“变文”字样标题的文本,也收有《妙法莲花经变文》《父母恩重经变文》等标题为编者拟定而后来通常定作讲经文的写本,首开把讲经文归入变文专集的先河。
1957年,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合编的《敦煌变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国内外公私收藏的187个写本,详加校勘,整理出变文作品78篇,堪称是自有敦煌学以来敦煌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但该书录文和校勘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
1984年,台湾潘重规先生推出了新一代的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该书以《敦煌变文集》为基础,校正了原书的一些录文错误,所收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如俄藏《维摩碎金》《双恩记》《维摩诘所说经讲经文》《十吉祥讲经文》、日本龙谷大学藏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盂兰盆经讲经文》等)。
20世纪80年代末,周绍良、白化文等先生出版有《敦煌变文集补编》,增补的敦煌变文共15种,该书后附写本图版,便于读者图文对照,这是体例方面的一个创新。
1990年,项楚撰《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巴蜀书社);200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增订本(2019年重版),共选入敦煌变文44篇。本书是按照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叙例”关于整理敦煌变文的计划和步骤之二“选出最优秀的作品,加上简明的注解,供一般读者使用”而写作的,“包括了变文中思想和艺术比较杰出的名篇,也兼顾了不同体裁和不同题材的各类作品”。该书“校释精详”(吕叔湘、江蓝生《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创获甚多,即使对专门的研究者也很有参考价值。
1997年,黄征、张涌泉撰《敦煌变文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在《敦煌变文集新书》的基础上篇目有所增加,并对原有的一些篇目作了调整,实收86篇。《敦煌变文集》出版后,学术界发表了数百篇(部)对该书校录的商榷批评文章(著作)。《校注》汇集了1989年底以前变文整理校勘的成果,在俗字的考辨和俗语词的解释方面很有创获。
此外,其他一些敦煌文献的整理本,如伏俊连《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涌泉主编《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及正在陆续出版中的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也从不同角度收录过若干变文的校录本,可以参看。
问题
如上所说,变文研究的后70年出现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一些汇编之作,颇为世人所瞩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汇编之作还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重要的如以下三点:
1.全集不全,亟待增补。近70年来,在敦煌文献大多没有影印出版的情况下,敦煌学界在变文文本的汇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应予充分肯定。但限于条件,现有的敦煌变文专集所收主要来源于英、法、中三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部分藏品,未能收入的变文写本仍然很多。现在随着这三大馆藏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品的全部刊布,加上北京大学、中国书店、首都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天津文物公司、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及甘肃、浙江藏品和台湾“国家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杏雨书屋等公私藏品的陆续出版,变文写本的数量大大充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有待增加的变文写本已达近百号之多,卷号已达《敦煌变文集》等书的二分之一强。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力量,对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图版作进一步的全面普查,相信还会有新的发现。
2.校勘注释,颇有疏失。敦煌变文来自民间,成长于民间的土壤,其中有着大量“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言俗语;同时由于变文基本上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不但充塞着大量的俗字、别字,讹、舛、衍、脱的情况也随处可见,而且有着许多殊异于今日的书写特点。这种繁复的情况,就给变文的校勘和整理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加上此前主要依以为据的缩微胶卷、《敦煌宝藏》的影印本效果不尽理想,进一步增加了变文校录的难度。所以尽管现有的一些敦煌变文专集的编校者都是海内外久负盛名的敦煌学专家,但这些专集在校勘注释方面都还存在或多或少的疏失。如下例:
《敦煌变文集》卷二《秋胡变文》:“(秋胡)叉手启孃曰:‘……儿今辞孃,远学三年间,愿孃赐许!’其母闻儿此语,不觉眼中流泪,唤言秋胡:‘汝且近前,听孃□之语。……’”其中的“三年”《敦煌变文汇录》以下各家皆同,《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又进而据文中“远学三二年间”“三二年间,定当归舍”等语,于“三”下拟补一“二”字。查原卷S.133号背,所谓“三”字底卷实作“”(下附底卷截图1),当是“一二”二字,各家录作“三”一字,其实不妥(比较下附底卷首页截图第2—7,六个“三”字皆作“”形,上部横画较短)。故原文既不是“远学三年间”,也不是“远学三二年间”,而是“远学一二年间”,“一二年”文义顺适。

图1 S.133号背《秋胡变文》截图
又上例末句缺字符《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选注》同,后书又拟补作“孃”字;《敦煌变文汇录》作“有”;《敦煌变文校注》称原卷作“一勾”二字,录作“一句”二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录作“苟”一字,又于其上拟补一“不”字,皆不确。查原卷S.133号背,“孃”下底卷确有“一勾”字样(上附底卷截图之8),但其上有涂改,似已涂去,应不录。
3.早期成果,尚待采纳。《敦煌变文集》自1957年问世以后,有关的商榷、补校论文(论著)就达近200篇(种)之多,《敦煌变文校注》已把其中的多数意见予以吸收采纳;对一些误校误说,也作了必要的批判,以免谬种流传。但在《敦煌变文集》出版之前,在变文写本的校勘整理方面,其实已有不少成果,重要的如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刘复辑《敦煌掇琐》、向达辑《敦煌丛抄》、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等。这些书因其成书较早,且多系直接据敦煌写本原卷迻录,所以在文字的校录方面有其佳胜之处(有些原卷残破严重的写卷,甚至有某些字句这些校录本校录时尚存而今本原件已破损残缺的情况),很值得重视。然而这些早期的辑本,《敦煌变文集》以后的各敦煌变文专集基本上都没有参校,《敦煌变文校注》也没有列入引用文献目录,不免时有遗珠之憾。比如下面的例子:
《敦煌变文集》卷二《秋胡变文》:“纵汝在外得达,回日□岂得与吾相见?”“日”下的缺字符《敦煌变文集新书》等以下各家皆同,而《敦煌变文汇录》不录此缺字符。查底卷S.133号背“日”字在行末,其下有一顿形笔画(上附底卷截图之9)。古代写本抄手为保持卷面整齐,经常采用在行末加字或添加符号补白的方式,以便行末抄字看起来与上下行大致对齐,不致长短错落。此处的顿形笔画正是抄手用作补白之用,《敦煌变文汇录》不录此符号是也,而后出各家未能采择,失之。
展望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叙例”中说:
我扪整理敦煌变文的计划和步骤,拟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一、校印本。把敦煌所出变文和与变文有关的资料,迻录校勘,排印成为一个最完备的汇编本,供研究和阅读古典文学的人使用。二、选注本。从校印本内选出最优秀的作品,加上简明的注解,供一般读者使用。三、影印本。将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罗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专门研究的人使用。
王重民等先生60多年前提出的这一宏大规划,其实只有第二项因项楚《敦煌变文选注》的高质量出版而完美收官;第一项,虽然敦煌学界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出版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校注》等汇编之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书离真正的“最完备的汇编本”都还有距离;至于第三项,迄今大抵仍付阙如,只有周绍良、白化文等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末附写本图版,作了初步尝试,可惜所附均为黑白照片,而且有的照片系据其他书转印,清晰度较差,质量难如人愿。
其实,第三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由于变文写本整理校勘特殊的复杂性,误录误校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前贤曾对《敦煌变文集》等专集提出过大量的商榷、补校意见,由于这些专集没有附列图版,提出商榷意见的作者多数也没有去核对敦煌写本原卷,因而所作的考订有如猜谜射覆,猜对的固然有之,猜错的也不在少数。事实上,不少错误是校订者误录造成的,如果覆核一下写本原卷,就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如能核对显微胶卷,可能效果更好”。现在,虽然绝大多数敦煌写本文献现在都已经出版了影印本,但这些专集动辄数十百册,读者自备不易,而且多系黑白照片影印(写本中大量的朱笔符号在黑白图版中难以显现),效果要打折扣,加上与敦煌变文相关的写本散在各家馆藏,寻检不便。所以,为方便读者,增加可信度,在变文录文后附上图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有鉴于此,在项楚先生亲自擘画领导下,本人参与组织编纂的《敦煌变文全集》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之中。我们试图把《敦煌变文集》编者设想的“校印本”和“影印本”合二而一,在对公私收藏机构所藏敦煌文献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收入所有变文文本,并汇集前贤的整理校释成果,汇校汇注,同时附列全部彩色图版,推出一部图文对照的真正的敦煌变文“全集”。只有在这样高质量的全集基础之上,敦煌变文研究才能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