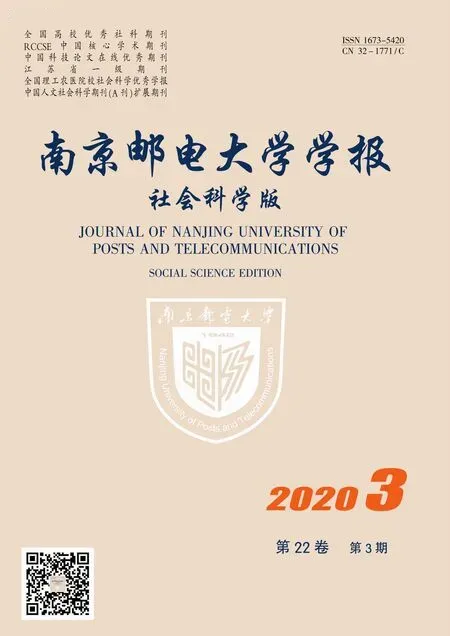论吴聿《观林诗话》的诗学观
2020-07-08何泽棠
何泽棠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吴聿,约1148年前后在世,著有《观林诗话》一卷。该书共115条,涉及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陈师道、贺铸、汪藻等诸多诗人及相关的诗作,主要以北宋诗人为主,偶有论述唐人、唐诗甚至汉、晋之诗事,偏重于用典、考据,夹以记叙轶事趣闻,又论及音律、字词、对仗等创作技巧。诗话条目间未形成严格有序的系统,仍保留了“以资闲谈”的功能和特点,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观点和诗话理论,是现存宋代诗话中值得研究的对象。
郭绍虞先生所著的《宋诗话考》中,记述了《观林诗话》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作者的生活年代、传世版本、主要内容等。郭先生指出,《观林诗话》的传本颇为稀少,其他书籍亦较少称引此书。(1)郭绍虞.宋诗话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55.
《四库全书》收录的《观林诗话》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聿之诗学出于元祐,于当时佚事,尤所究心。”[1]1785《四库全书总目》论及《观林诗话》,多从考证时事、辨误方面进行,最后总结道:“皆足以考证。在宋人诗话之中,亦可谓之佳本矣。”[1]1786
蔡镇楚先生的《中国诗话史》述及《观林诗话》,称其论诗以苏黄为主,多考证唐宋大家诗句,间述轶事,评介较为中肯。(2)蔡镇楚.中国诗话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115.
吴文治先生在《宋诗话全编》的前言中总结:“吴聿《观林诗话》,论诗以苏、黄为尚,颇有江西习气,用事、造语,皆所究心,而尤以考证事典见长。其考证诗歌用典,或述用事所由,或纠诗人之误,或订正语句谬传,大抵翔实有据。”[2]前言21
夏云壁先生的《读<观林诗话>札记四则》一文,从用典之正误的角度,抽取《观林诗话》中的四则,结合其他文集、书史进行辨述,(3)夏云璧.读《观林诗话》札记四则[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72-77.没有过多地涉及《观林诗话》的诗学观。
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中指出:“是书所论较偏考证,间述佚事,盖犹沿宋人笔记之体,与专主论诗者不同。”[3]本文不以《观林诗话》的考证、述佚事为研究对象,而是研究其“论诗者”。虽然吴聿不像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的“优柔感讽”说、“余味”说、蔡絛《西清诗话》的“情致”说、陈善《扪虱新话》的“格高”论、“韵胜”论那般提出了核心的论诗观点,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便是受苏轼、黄庭坚等诗人的影响较深。因此,本文将先从江西诗派强调“夺胎换骨”“以俗为雅”、用典及具体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出发,总结《观林诗话》的主要观点;次及作家作品论、文体论等,从这些方面系统地梳理《观林诗话》的诗学观,以挖掘出吴聿的诗学理论,分析其中的理论价值。
一、对江西诗学的继承
(一)“换骨”式的立意
立意,为作诗之首要。《观林诗话》论及立意,首先推崇立意拔俗。以第二十八则为例,该则指出:“前辈作桃花、菊诗虽多,而未见拔俗者。……然世复盛传一联,云‘陶令归来惊色变,刘郎去后笑开迟’。亦未为胜,但‘陶令归来’、‘刘郎去后’,乃切对也。”[2]2734这说明,吴聿对诗歌立意的要求是别出心裁、超凡脱俗、不落窠臼,方为上品。至于“陶令归来”“刘郎去后”虽然对得工整,乃求变、求“活”的范例,但整体立意仍逊一层,没有达到吴聿的期待。
黄庭坚等诗人强调立意要超出前人,他在《再次韵(杨明叔)》的诗序中指出:“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4]进一步来说,“以故为新”体现为“换骨”法。《冷斋夜话》里有记载,“山谷云:‘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5]16具体而言,“换骨”法就是重视诗作之意,以“意”为诗歌之“骨”,引用前人之立意,转化为自己的诗歌主旨,并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现。如此一来,即可适当地弥补诗人才学、经验、情感的不足。此乃宋诗所建立的法度之一,同时也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学观点之一。受此影响,吴聿也强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再追求立意的创新的“换骨”法。
《观林诗话》第五十二则:
东坡云:“醉眼炫红绿。”此乃“看朱成碧颜始红”换骨句耳。[2]2737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是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中的句子,表现了主人公眼花耳热、面如渥丹、不辨颜色的半醉状态。苏轼将李白的七言句浓缩为五言句,意思差不多,但语句更凝炼,是“换骨法”的典型表现。
《观林诗话》第九十八则:
鲍照云:“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盖以此也。[2]2745
吴聿说“盖以此也”,指的是黄庭坚的“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化用了鲍照诗句。吴聿说得很简单,认为这是黄庭坚等人倡导的另一种创作方法——“夺胎”法。《冷斋夜话》又云:“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5]16即揣摩出原作的意思,然后赋予它更深刻的内涵,将其意境升华。鲍照的《代东门行》用了《战国策》中的“惊弓之鸟”的故事来衬托“倦客恶离声”,表达了离别时的伤感,感情非常强烈。相比之下,黄庭坚的《题阳关图》更加含蓄,将离别断肠之意通过淡淡几笔渲染出来。黄庭坚捕捉到画作者的意趣,以“无声亦断肠”点染这种忧伤,反用鲍照之意,却比鲍照诗的意境更高一层,这是典型的“夺胎法”。尽管吴聿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仍能说明他崇尚江西诗派的创作理念。
(二)分析用典的巧妙之处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指出:“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6]614唐朝杜甫、李商隐等人的诗歌创作擅长用典,北宋的苏黄诗风更以“用事押韵”为工。受此影响,宋代诗话中不乏关于“无一字无来历”的记述。在《观林诗话》一卷中,论及用典的条目近四十则,约占全卷总数的三成,既涉及了古代诗歌典故的出处,也讨论了当代诗歌用典的出处,可见吴聿对用典方法的看重。就《观林诗话》中所讨论的诗人而言,其中多论苏东坡用事的出处,亦可见吴聿对于苏轼的推崇。除此以外,《观林诗话》还就用典的巧妙之处进行了分析,第七十四则:
半山《酴醿金沙》诗云:“我无丹白看如梦,人有朱铅见即愁。”孙思邈云:“苟丹白存于心中,即神灵如不降。”其用事精切如此。[2]2741
吴聿只是简单评论“用事精切”,却未详细说明。孙思邈说的“苟丹白存于心中,即神灵如不降”,是指如果有丹白一类的东西存于胸中,就会导致真感不应、真灵不降,是求仙学道者的大忌。王安石反用其意,意思是说自己心中不存丹白,所以视酴醿如梦。王安石尽管是反其意而行之,却恰到好处地表现酴醿、金沙二花同时盛开,自己却看花如梦,不受尘杂之事干扰的清静状态,用典十分精确切题。
第九十四则:
陆龟蒙《谢人诗卷》云:“谈仙忽似朝金母,说艳浑如见玉儿。”杜牧之云:“粉毫唯画月,琼尺只裁云。”“美似狂酲初啖蔗,快如衰病得观涛。”涪翁:“清似钓船闻夜雨,壮如军垒动秋鼙。”论用事之工,半山为胜也。[2]2744
这一则中,吴聿看似只论用事。然而他没有明说的是,这四组诗句主题相近,都出自诗人与朋友之间的寄赠和答诗。这些诗句都用比喻表达了收到对方寄来的诗文后的美妙阅读感受。吴聿的真实目的在于,在主题与句式相近的前提下,比较它们的比喻水平与用典水平。
陆龟蒙评论对方寄来的诗,谈仙说道,便如见道教传说中的金母;描写美人,便似仙鬼题材中的玉儿。这些只是寻常比喻,不足为奇。
在杜牧之前,骆宾王用过“画月”、李义府用过“裁云”,都是用以形容女子的妆饰。杜牧《赠张祜》的“粉毫唯画月,琼尺只裁云”是暗喻,说的是张祜描写云、月等景物,如画工裁缝一般,经过精心剪裁,巧夺天工。这种比喻十分贴切。杜牧也用了“画月”“裁云”二词,但与前人的用法不一样,这两句仍属独具匠心之作。
“美似狂酲初啖蔗,快如衰病得观涛”是王安石《次韵酬宋玘六首》里的句子,“狂酲”出自《庄子·人间世》,谓有商丘大木,“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不已”。“初啖蔗”与“狂酲”合用,来自《汉书·礼乐志》里记载的《景星歌》中的一句,即 “泰尊柘浆析朝酲”,“柘浆”是用甘蔗汁制成的,用来治疗“酲”这种酒醉之病。“衰病得观涛”来自枚乘的《七发》,有吴客以观涛之奇,起楚太子之病。王安石并不是普通的用典,而是将这几个典故组合在一起,表达了读诗后的振奋。
“清似钓船闻夜雨,壮如军垒动秋鼙”来自黄庭坚的《和答任仲微赠别》。这两句没有用古代的故事,而是用了前人的词汇。上句出自杜牧《独酌》中的“何如钓船雨,蓬底睡秋江”。下句的“秋鼙”出自孟郊《猛将吟》中的“秋鼙无退声”。这些词汇用来形容诗人收到任仲微诗时既清越又雄壮的阅读感受,十分准确,但只是普通的用典,不似王安石那般有变化。
因此吴聿从用典的技巧出发,认为“用事之工,半山为胜”可以成立。如果不局限于用典的技巧,那么杜牧的用意象进行比喻并不亚于王安石的用典故进行比喻。这一类的比较,主观性较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亦可以看出吴聿受苏黄诗风的影响,格外重视用典。
(三)“化俗为雅”
上文已引黄庭坚在《再次韵(杨明叔)》诗序中的原话:“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可见“以俗为雅”是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观。
唐诗多以丰神俊骨、神采华章著称,但也不乏“元轻白俗”之作。宋代诗话作者对唐诗轻俗的一面经常予以批评。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就对元、白、张、王乐府言尽意尽、过于通俗、毫无余味的一面加以斥责。
宋代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而杜甫的《缚鸡行》等作品同样是以俗入诗,因此宋代诗人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后人对此评价不一。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批评道:“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7]
然而苏、黄等宋代诗人并非简单地使用俗语,而是强调“化俗为雅”,重点在“雅”而不在“俗”,强调的是“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复斋漫录》列举了这一诗法的实例:
谚云:“情人眼里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鹅毛,物轻人意重。”皆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谢陈适用惠纸》云:“千里鹅毛意不轻。”[8]
俗语的意思众所周知,用语也很朴素。经过黄庭坚的点化之后,立刻变得新警。黄庭坚强调了“情人眼里有西施”的重点在于“称心”,这是原语中容易被忽视的。“意不轻”三字凝炼,与“千里鹅毛”组成七言句,不仅字数少于原来的两个五言句,而且句意更加警绝。这样的改造,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一脉相承的。
《观林诗话》同样讨论了对俗语的使用,请看以下几则。
第十四则:
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着易过。周美成诗曰:“冬曦如村釀,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非惯饮茅柴,不能为此语也。[2]2731
第十六则:
涪翁《读中兴碑》诗云:“冻雨为洒前朝碑。”《楚词》云:“使冻雨兮洒途。”故张平子赋:“冻雨沛其洒途。”旧注云:“冻雨,暴雨也。”巴郡暴雨为冻雨。[2]2732
第二十则:
梅圣俞诗“莫打鸭,打鸭惊鸳鸯”之语,讥宣守笞官奴也。陈无己《戏杨理曹》诗云:“从来相戒莫打鸭,可打鸳鸯最后孙。”又与宣守诗云;“一为文俗事,打鸭起鸳鸯。”皆用此也。然“起鸳鸯”三字亦有来处,杜牧之云:“织篷眠舴艋,惊梦起鸳鸯。”[2]2732
这几则提到的诗句,或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平凡无奇、琐碎常见的田园农家事物,如“鸭”“鸳鸯”,或是取用俗俚之词语,如“茅柴”“冻雨”,使得诗作语言平易通俗,浅显易懂,十分具有烟火气。同时,平淡寻常的物事、情境在诗中雅化,去除了俗陋之气,给人以别具一格的审美体验。正如诗话第一百一十一则所述:“虽是鄙语,亦殊精绝。”[2]2747用字虽俗,意却高雅,强调了“化”字。另外,诗话第六则有关俗语“羶根”的论述,还出现了“来处”一词。“以俗为雅”,亦讲究来处,或取其言词,或取其故事,或取其用意,又或者是综合而用之。这直接说明了《观林诗话》对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的强调,甚至连俗语也讲究出处。
二、写作技巧论
宋代诗学非常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黄庭坚特别倡导作诗的“法度”。而关于作诗技巧,《观林诗话》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涵盖了章法、对仗、音律等方面。
(一)对仗
《观林诗话》讨论了有关“对仗”的诗学内容,推崇奇巧、婉曲、工致之对。
对偶最初以“丽”字来表示,丽,两也,本意指的是两张对称的鹿皮。《文心雕龙·丽辞》指出,造化万物,都遵循成双成对的原则。“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6]589延伸至诗歌,律诗的对仗之联,亦可称之为“丽辞”。
1.推崇工整的对仗
《观林诗话》第四十四则云:
半山诗有用蔡泽事云:“安排寿考无三甲。”又用退之语对云:“收拾文章有六丁。”东坡诗有用屈原事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又用郑康成梦对曰:“忽惊岁在己辰年。”皆天设对也。[2]2736
吴聿说的“天设对”,指的是巧夺天工的对偶,但没有进一步对其说明。宋诗强调“以学问为诗”,喜欢用典,这对律诗的对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句用典,下句也必须用典,反之亦然。上下句所用的典故,其类型应当相似,内涵的文化价值也必须相当,否则就会如失衡的天平一般不协调。吴聿列举了王安石、苏轼的两首七律挽词,认为用事以对,上下句不仅意义相对,用典的分量也旗鼓相当,工巧有如天成。王安石的诗句出自《河中使君修撰陆公挽辞三首》之三,上句用了《后汉书》中《管辂传》的“吾背无三甲,腹无三壬,不寿之兆”。下句则用了韩愈的“仙官勅六丁,雷电下取将”。不仅词性、意义相对,而且分量相当。

2.“假对”(借对)
除了普通的对偶之外,唐宋诗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对偶技巧。吴聿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假对”。第二十五则云:
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严光钓濑喧。”此以杜与严为人姓相对也。又有“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此乃以朱云对白日,皆为“假对”,虽以人姓名偶物,不为偏枯,反为工也。如涪翁“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尤为工致。[2]2733
该则讨论的是“假对”(借对)的一种,即以人之姓名与物名相对仗。“杜若”的“杜”,本可作为人的姓氏,在此取它的另一个意义——作为香草的杜若,仅仅借“杜”的字面与下句严光的“严”姓相对。另一个例子是借用西汉人物朱云的“朱”姓的字面,与下句表示颜色的“白”字相对。这是杜甫以来律诗里惯用的手法。经过杜牧、黄庭坚等诗人的使用,技巧越来越成熟。黄庭坚诗中的“九方”是复姓,仅以其字面与“千里”相对,富有技巧性,很是工整别致,具有独到的艺术魅力。
3.另一些奇特的对仗
第三十六则:
秦太虚用乐天《木藤谣》“吾独一身,赖尔为二”。作六言云:“身与杖藜为二,影将明月为三。”真奇对也。[2]2735
这里秦观不仅化用白居易的《木藤谣》,创作出 “身与杖藜为二”,而且进一步发挥想象,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浓缩为“影将明月为三”。两句不仅对偶,还有递进的关系,隐隐有流水对的风采,所以成为“奇对”。
第三十七则:
乐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窕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渔父词》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然新妇矶、女儿浦,顾况六言已作对矣。[2]2735
这里提到了黄庭坚化用白居易诗句之意作《渔父词》,结合上文论及的江西诗派的“换骨法”,可见其可以进一步用到对偶中,令“换骨”无处不在。 “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中的“新妇矶”“女儿浦”都是地名,出自顾况的 “新月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黄庭坚将六言句中的四字词改用在七言句中,节奏更紧凑。总而言之,将顾况诗与白居易诗的意境融合在一起,境界更高。
(二)音律
《观林诗话》中,吴聿谈论到“音律”时,所秉持的主张与“对仗”类似,均推崇工巧别致而不失自然。
周颙、沈约、谢朓、王融等文学家发现并逐步完善声律,追求声律的变化、和谐。唐宋以来众多诗话中,有关“声韵音律”的记述,比比皆是。蔡絛《西清诗话》即有“诗之声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语工夫,各有微妙”[2]2493的说法。
1.“双声”与“叠韵”
《观林诗话》第二则:
谢灵运有“苹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浅。”上句双声叠韵,下句叠韵双声。后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杜荀鹤“胡卢杓酌春浓酒,舴艋舟流夜涨滩”,温庭筠“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老媪宝藁草,愚夫输逋租”,皆出於叠韵,不若灵运之工也。[2]2730
《文心雕龙·声律》:“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6]552按沈约与“永明体”以来的平仄规律分析的话,谢灵运诗中的“苹萍”“清浅”为双声,“沈深”“菰蒲”则为叠韵,双声词与叠韵词之间均由一个去声字隔开,平仄交替相对,整齐而又富于变化,读起来圆润流畅、铿锵顿挫。双声叠韵的上句与叠韵双声的下句两两相对,其中的名词与名词、动词与动词也是一一对应,无论在音律上还是句法结构上都紧密贴合,滴水不漏,工巧别致且清新自然,浑然天成。杜甫、杜荀鹤、温庭筠等人的诗句,正如吴聿所说的,虽然也出现了叠韵,如“卑枝”对“接叶”、“薜荔”对“菰蒲”、“藁草”对“逋租”,但是却没有双声,做不到谢灵运那般双声与叠韵错综出现,平仄相协。至于杜荀鹤的“胡卢”“涨滩”,还没有出现在对偶两句的同一位置,效果就更差了。
2.押险韵
《观林诗话》中,与音律相关的还有押韵用韵。诗话第十二则提到了押险韵的问题:
东坡和“辛”字韵,至“捣残椒桂有余辛”,用意愈工,出人意外。然陈无己“十里尘沉不受辛”,亦自然也。[2]2731
吴聿只指出了苏轼的“捣残椒桂有余辛”用意工巧,陈师道的“十里尘沉不受辛”胜在自然。吴聿没有说的是,这两句同押“辛”字韵,属于押险韵。所谓“险韵”,是指韵脚是僻字,前人少用,不容易组织意义连贯的诗句,更难写出佳句,因此一般的诗人慎用险韵,甚至是避用。然而苏轼在《再和曾子开从驾二首》这组和答诗中,面对无法避开的险韵“辛”,能将这个韵脚与《离骚》中的“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联系起来,用典工巧之余,将很难处理的“辛”字赋予了香草的气味,精妙自然,出人意表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极见艺术功力。至于陈师道《马上口占呈立之》中的“廉纤小雨湿黄昏,十里尘沉不受辛”,同样押了险韵,但不像苏轼那样用典,而是借景抒情,小雨浥润了黄昏,令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气息,甚至连泥尘也没有散发出刺激的气味。这样一来,巧妙地将“辛”字融入诗境中,隐去了雕饰的痕迹,浑然一体,犹如天成。这两个例子,对险韵的处理方法虽有所不同,但效果俱佳,是成功的范例。
3.重复用韵
第七十八则提到的是重复用韵的问题:
沈休文《钟山应西阳王教》一首五章,第四章用两足字韵。上云:“多值息心侣,结架山之足。”下云:“所愿从之游,寸心於此足。”一章才四韵,而两韵同一字。又陆士衡《拟古》一篇,用两音字。前云:“思君徽与音。”后云:“归云难寄音。”东坡一诗用两耳字。云:“二义不同,故得重用。”又涪翁一诗压两朋字云:“大府佳友朋。”“归鸟求其朋。”又有一诗用两扁字韵:“责任媲和扁。”“持断问轮扁。”自注云:“复有此一韵,事异似不类出此也。”[2]2742
一般情况下,同一韵脚在一首诗中只能出现一次。但如苏东坡所说,一个字,使用两次,分别表示两重不同的意义,那么可算作两个韵脚,至少不能看作重用。沈约与陆机的诗歌都是这种情况。
至于黄庭坚的诗句——“扁”字韵的两句,出自《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王世弼的原作这般押韵,黄庭坚的次韵诗也不得不如此。黄庭坚自注云:“复用此一韵,事毕似不害。”[4]555与吴聿所述略有不同。这两个“扁”都是人名,一指扁鹊,一指《庄子》中的轮扁。既然二者不是同一个人,黄庭坚说“不害”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另一组重押“朋”字,且两处意义相同,就不值得提倡了。
三、作家作品论
《观林诗话》提及的作家、作品颇多,依旧是以笔记闲谈的形式记录下他所熟知的某些诗人、诗作的风格特点或是趣闻轶事,时而记述自己的心得体会。主要形成的诗学观点可分为“才气论”“风骨论”“以意为先”“工巧妍丽”四种。
(一)作家论
《观林诗话》论述作家及其相关创作与事迹,并不执着于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品格、文气等的优点、缺点进行系统、完整的评论,亦未将其分成流派以别类,多是即兴发挥的记述,言明其作品影响范围时亦只提及寥寥数人,行文之间暗合《文心雕龙》之论,重视诗人之才气与风骨。
首先是重视诗人之才气。宋诗有“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特征,其中又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观林诗话》称赞李元亮兄弟数人为“隽才”,第九十九则:
乐天云:“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文,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故东坡有“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之句。然乐天既知韦应物之诗,而乃自甘心于浅俗,何耶?岂才有所限乎?[2]2745
这一则的主要讨论对象是中唐诗人韦应物与白居易。前文已述,吴聿认同黄庭坚等人“化俗为雅”的主张,对未能“化俗”的白居易诗持否定态度。吴聿引用白居易对韦应物五言诗的推崇,并转述苏轼对此的肯定,由此对比白居易与韦应物的成就,得出白居易因才力有限,因而自甘于浅俗的结论。吴聿的观点未必恰当,白居易的七言诗中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优秀作品;五言闲适诗中亦有《问刘十九》《官舍小亭闲望》等佳作。虽然部分闲适诗与讽谕诗确实有过于浅俗之病,但不可以因此全盘否定白居易的诗歌。由这一则的论述可以从侧面看出吴聿对“才力”的重视。
其次是关注诗人之风骨。第八十九则:
《树萱录》云:“杜工部诗,世传骨气高峭,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又唐人谓李贺文体,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2]2743-2744
这一则所引《树萱录》之论,出自唐人;唐人论李贺之诗,则出自《旧唐书·李贺传》,此处著述虽非吴聿本人的观点,但二者皆论风骨,组合在一起,可见吴聿对风骨的推崇。同时,该观点与《文心雕龙·风骨》中的追求是一致的,《风骨》篇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6]513
杜甫诗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推崇,但论者却较少注意杜诗的风骨。一般论者,从诗歌内容出发,或推崇杜甫忠君爱国,谓之“诗圣”;或谓杜诗反映现实,谓之“诗史”。若如江西诗派,将杜甫奉为始祖,则从诗歌创作技巧方面,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学其章法、句法、字法、对仗、拗律等。元稹、秦观等则谓杜诗乃集大成者,兼诸家之长。一言以蔽之,为“沉郁顿挫”,但不及其风骨。至于李贺的诗歌,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认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9]这里只看到了李贺诗与《离骚》的联系,甚至认为李贺诗义理不及《离骚》。其余论者,则将李贺诗视作意象险怪、诡异之类,强调其诗境幽奇冷艳,甚至称其为“诗鬼”。
吴聿这一则的论述却独辟蹊径,从新的角度审视杜甫与李贺诗歌。杜诗固然面面俱到,但突出其“风骨”,有利于读者抓住重点,发扬杜诗中能体现“盛唐气象”的一面。特别是《树萱录》已经失传,相关言论有赖于吴聿的记述方能流传至今。至于李贺诗,《旧唐书》所论有利于读者品味其如万仞绝壁般的风骨,发现李贺诗在凄艳诡激的外表之下蕴藏的苦闷、激愤的情怀,进一步发掘李贺诗的价值。如此来看,吴聿《观林诗话》的这一则功不可没。
(二)作品论
《观林诗话》专门论述作品的条目有数则,强调意境,既重自然浑成,又重工巧、妍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气概。
第一百则:
颜鲁公云:“夕照明村树。”僧清塞云:“夕照显重山。”顾非熊云:“斜日晒林桑。”杜牧云:“落日羡楼台。”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严维“花坞夕阳迟”也。[2]2745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引梅尧臣的言论说明“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梅尧臣举严维的“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为例,评论为“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2]215吴聿也持相同的态度,认为杜牧、王安石等人描写夕阳之诗句,都不及严维的“花坞夕阳迟”。此句自然而意境深远,一轮红日缓缓落下,与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夕阳虽美,终究是迟暮之时,光景难堪,不得长久,惹人伤感。此时对自然的感受、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慨叹,往往会提至新的高度。而其余的“夕照明村树”“夕照显重山”“斜日晒林桑”“落日羡楼台”和“返照媚林塘”,共同之处在于着重描写夕阳,余晖勾勒出山林草木楼台之轮廓,光影交错,颜色分明,均给人以明媚之感。“明”“显”“晒”“羡”“媚”皆不及一个“迟”字自然且触动人心。刘攽《中山诗话》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2]442可见刘、吴二人对意境的追求是相同的。
吴聿又喜好发掘工巧、妍丽之诗句,《观林诗话》第一百零四则:
乐府有风人诗,如“围棋烧败絮,著子故衣然”之类是也。然或一句托一物耳。独杨元素《荷花》借字诗四韵,全托一物,尤为工也。诗云:“香艳怜渠好,无端杂芰窠。向来因藕断,特地见丝多。实有终成的,露摇争奈何。深房莲底味,心里苦相和。”[2]2746
这一则论述的是宋代诗人杨绘的《荷花》,吴聿评论“尤为工也”,但语焉不详。此诗借鉴了南朝乐府的双关手法,但又富于变化。南朝乐府喜用“谐音双关”,如这一则所引“著子故衣然”的“衣”,双关“依然”之“依”。然而南朝五言四句的乐府,因篇幅所限,往往以一句或一联描写一物。杨绘此诗借鉴了双关的手法,如以“丝”双关“思”,而且全诗八句都围绕荷花展开,每一句都紧扣荷花,实属难能可贵,表现力极强。
第一百零五则:
这一则评述欧阳修写春景之句皆为“丽句”,可见吴聿对纤巧流丽的风格亦能接受。在其他多则的论述中,“尤为工也”多次出现。这个“工”不仅是修辞上的“工巧”,也是诗意、境界上的“工巧”,即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既得“骨气奇高”,又显“辞采华茂”,从中可见吴聿的艺术追求。
四、文体论
《观林诗话》并无太多直接涉及文体的讨论,不似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严羽的《沧浪诗话》那般对文体、诗体进行专门专项的分类和记述,提及的诗体主要有“应制诗”以及“联句”,共两类。
(一)应制诗
关于“应制诗”的是第一则:
汉武《柏梁台》,群臣皆联七言,或述其职,或谦叙不能,至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则又有规警之风。及宋孝武《华林都亭》,梁元帝《清□殿》,皆效此体。虽无规儆之风,亦无佞谀之辞,独叙叨冒愧惭而已。近世应制,争献谀辞,褒日月而谀天地,恐不至。古者赓载相戒之风,於是扫地矣。[2]2729-2730
吴聿举例追述了汉代南朝时期的应制诗有规儆劝谏之风,无谗佞之辞,感慨宋代的应制诗陷于谄媚,不复古人之风气。
受重文抑武、党派争斗和文字狱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宋代的文学氛围不似前朝古代宽松,但不能以此为据推断宋代的应制诗即是谗言媚上之作。应制诗服务于帝王,内容多以歌功颂德为主,但诚心恭维不等于拍捧奉承。判断谀词与否,为君主的学识水平、审美趣味、性情及当朝的政治氛围所影响,也同诗人的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有关,更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联,不能一概而论。下面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寇准的《应制赏花》与欧阳修《应制赏花钓鱼》均是描写赏花钓鱼之时盛大繁华的场面,一派富贵平和。这在应制诗里是比较多见的。《礼记·乐记》有“治世之音安以乐”的说法。从这两首诗中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升平优容之气象,宋仁宗时君臣关系非常和睦,为后世垂范,又何以见得是谀辞媚上呢?另外,北宋应制诗中还有一些关怀民生之作,体现了宋诗亲近平民俗事的特点,有民本情怀。因此,吴聿所论有片面之嫌。不过,他强调应制诗不可佞谀,出发点是可取的。
(二)联句
“联句”见之于《观林诗话》第六十五则:
刘向《列女传》,以为《式微》之诗,二人所作,一在中露,一在泥中,卫之二邑也。或者以为联句始此。[2]2739
西汉刘向所作的《列女传》认为《诗经·邶风·式微》一诗为二人合作而成。诗话里还提到,有的人以为《式微》是联句的初始。对此,吴聿并没有发表更多的意见,仅是记录。此外,也有其他观点认为,《柏梁台诗》才应该是最早的联句诗,该七言诗分别由二十六人各出一句联接而成,且每句用韵,被后人称为“柏梁体”。
五、结语
总的来说,《观林诗话》论诗重典故,亦重技巧,且十分推崇苏轼,多称引苏轼之诗句,亦倾向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本文从四个角度对《观林诗话》的诗学观进行了梳理,在系统分析的同时力求保持其论诗体系、论诗主旨的完整性与统一性。
全卷诗话,一方面讲究用典,偏重考据,重视字句和故事的出处,并分析诗句的化用,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又赞成“以俗为雅”,以俗入诗,为宋代诗歌注入新鲜活力,并使其有别于唐诗之丰神俊骨。另一方面偏重考证讹误,且论述诗人之轶事趣闻,记录诗歌的创作背景,间或鉴赏诗句妙处,分析名物与地理,保留了“以资闲谈”的特点。创作论方面,主要论及了立意、对仗、音律等三个方面,主张立意拔俗与“换骨法”,不论是对仗还是音律均追求工巧别致而不失自然。作家作品论方面,关注诗人之才气风骨,重视作品本身的意境、自然及工巧妍丽,强调作诗须以意为先,又论及了应制诗与联句两种文体。以上这些,对于研究江西诗派乃至于整个宋代的诗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