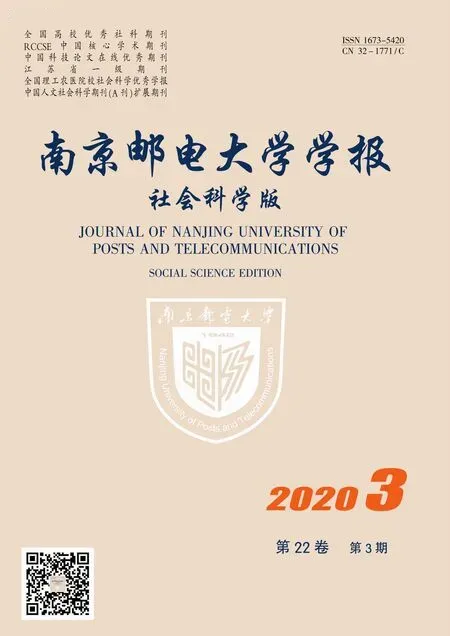从乔叟到狄更斯的犹太人书写
2020-12-13黄莹
黄 莹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犹太人物形象——从14世纪乔叟笔下“女修道士的故事”中的犹太人群体,到16世纪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再到19世纪狄更斯笔下《雾都孤儿》中的犹太贼窝窝主费金,均带有显著的种族特征:长袍着装,隔离的居住环境,靠放贷为生的营生手段,被基督徒憎恨的社会处境,毒害社会的罪恶行为,以及最终受到的严厉惩罚等。这种模式化的犹太书写通常被中外批评界认为是这些作家具有“反犹主义”立场的主要依据。就乔叟的“女修道士的故事”,弗里德曼(Albert B.Friedman)从乔叟维护了社会对犹太人的仇恨[1]127,法兰克(Robert Worth Frank,Jr.)从乔叟身处中世纪反犹文化的“现实”(given)[2]177,法兰登堡(Louise O.Fradenburg)从乔叟文本的意识形态的角度[3]76,阐释并表明乔叟存在反犹主义观点。就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除非既瞎又聋又哑,否则任何人都能看出莎士比亚那宏大、模棱两可的喜剧《威尼斯商人》无论如何都是一部彻底的反犹太主义作品”[4]171;国内学者王九萍也从夏洛克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业已形成的反犹主义的角度,认为莎士比亚将中世纪基督徒那种偏执、强烈的报复心理强安在夏洛克身上是极其不公正的反犹体现[5]17。斯通(Harry Stone)[6]228、乔国强[7]63、福尔曼(Nadia Valman)[8]176及陈后亮[9]152均认为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犹太人物费金进行的无意识再现,是狄更斯反犹主义倾向的体现。
然而,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三位作家笔下的模式化形象同时具有微妙的复杂性差异。本研究基于文本细读,结合历史史实,在回顾中世纪后期到近代英国社会宗教与社会背景的同时,分析这些犹太形象,探究模式化书写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文本中模式化书写之外微妙复杂的差异性及不同时期三位犹太人物的形象变迁。这些形象所反映的,一方面是英国社会长期的制度性歧视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偏见传统,另一方面是作家人性关怀的自觉选择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以及英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对待犹太人态度的逐步转变。
一、模式化的犹太形象与集体无意识的英国社会种族偏见传统
(一)乔叟、莎士比亚及狄更斯共同的模式化犹太书写
14世纪的英国作家乔叟(1340—1400)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借女修道士之口,讲述了一个基督教儿童被犹太人残忍谋害的故事。其中的犹太人是作为群体形象出现的。他们住在亚细亚一个大城市里,“另成一区,依仗着财主从事盘剥暴利,为耶稣和他的信徒们所痛恨”[10]193,只因基督徒歌咏队的一名童子每天往来犹太居住区时,大声颂唱赞美圣母的歌曲,犹太人便雇凶将其谋害,割破他的喉咙并将他抛进臭坑。事后圣母显灵,犹太人罪行败露,“市长把每个预闻这件凶杀案的犹太人都处以苦刑……用野马拖曳他们,然后依法吊死”[10]195。
到了16世纪,莎士比亚(1564—1616)延续了这种负面的犹太叙事,其塑造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日后更是演变成了英国文学作品中高利贷商人的原型。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夏洛克这一犹太形象,精明狡猾,靠放债集聚了财富,但一贯为主流基督徒社会排挤和侮辱,商人安东尼奥会无缘无故地辱骂和踢打他,其他基督徒也经常谩骂他为“犹太狗”。因此,夏洛克利用安东尼奥为好友借债之机,佯装慷慨不收取利息,但却签约规定,逾期不还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整整一磅白肉”[11]160。然而,夏洛克的残忍要求最终被法庭巧妙地驳回,不仅如此,他还被判处没收财产,“改信基督教”[11]206。
夏洛克奸猾负面的犹太人形象到了19世纪被狄更斯(1812—1870)的《雾都孤儿》进一步固化。小说中,犹太人费金住在伦敦一个最为肮脏和破败的地方,以控制儿童偷盗为生。在绑架少年奥立弗的过程中,他吝啬、贪婪、毒害儿童身心的形象在狄更斯笔下栩栩如生。在小说的叙事中,费金同样是个不断受到社会排斥的对象,他的基督徒同伴赛克斯或者直呼他为“老犹太”,或者辱骂他为“魔鬼、混蛋或野狗”;法庭的旁听观众对他也是极其“厌恶”和“不耐烦”[12]369。费金最后同样被“判处绞刑,就地正法”[12]371。
纵观六个世纪间英国文学中的这三个犹太形象,他们的外表、职业、性格及社会地位流于一套固化的模式,全部被置于故事矛盾冲突的唯一对立面,最后都受到了严厉处罚。虽然批评界已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这种模式化犹太书写达成共识,但是否就此给作家们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却一直存在争论[13-15]。如果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宗教、历史及其制度性歧视的角度进行探究,可以发现英国社会由此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种族偏见传统,应该是这种模式化犹太书写的深层缘由。
(二)对犹太人长期的制度性歧视及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偏见
根据美国犹太问题专家法恩(Henlen Fein)的定义,“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指的是“一种针对犹太群体持久而潜在的敌视性的信仰结构,包括个人的态度,神话、意识形态、民间传说和意象所表现的文化,以及社会和法律歧视、对犹太人的政治动员、集体或国家暴力等行为,所有这些导致了或者旨在导致仅因种族原因而隔离、驱逐或摧毁犹太人的行为”[16]3。尽管“反犹主义”这一术语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但是对犹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偏见、仇恨或歧视,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被犹太人陷害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因此被认定犯了弑神罪(deicide)而受到基督徒的仇视[17]32。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贝拉(Steven Beller)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基督教必然的组成部分。自犹太人拒绝承认“拿撒勒的耶稣是基督”这样的基督教基本认知开始,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仇视实际上已不可避免。作为弑神的“杀死基督者”(Christ’s Killers),犹太人从属而凄惨的存在,见证着漠视基督的神性真理的后果,最终也将见证“耶稣再次降临世界”(the Second Coming)这样的神性真理。因此,犹太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容忍的小众信仰[18]13。
至中世纪犹太民族更是到了被仇视的境地。以色列临床心理学家兼作家福尔克(Avner Falk)认为,中世纪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历次危机加剧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猜疑、恐惧和歧视心理,“恐慌的基督徒确信是犹太人在他们的水井中下了毒,这才导致数百万人相继死去”[17]34。中世纪晚期的基督徒的确受到很多疑虑和恐惧的困扰,“他们害怕他们称之为撒旦和路基菲尔(Lucifer)的魔王(Devil),他们将犹太人想象成魔王的子孙,他们还将反基督教的人臆想成魔王与犹太妓女的子嗣”[17]7。
对犹太人仇恨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发生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时,大批暴民借“杀死基督者”之名开始谋杀犹太人,仇恨的情绪愈演愈烈,最终变成了疯狂的妄想。12世纪中期,人们开始谴责犹太人谋害基督徒儿童用于祭祀;13世纪中期,这种妄想和非理性的情绪更是演变成了“血祭诽谤(blood libel)”——人们指责犹太人用基督徒儿童的血烘焙逾越节的面包。尽管少数神学界和社会权威人士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但多数人的沉默导致这种谣言被社会广泛接受,所谓 “血祭诽谤” 的受害人也被奉作了天主教堂的圣徒[18]13-14。
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社会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限制了犹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权利。犹太人的从业限制越来越多,使得大量犹太人集中到了放贷这一行当[18]14。因为基督教原则上禁止信徒借贷收息,很多需要资金的基督徒不得不同犹太人打交道,但借贷不仅没有为犹太人赢得爱戴和同情,反而加剧了仇恨:“借方发现贷方的‘得’是建立在自己的‘失’上时,便自然将收息视为邪恶之举——更何况对方是异教徒”[19]238。
受到犹太人与基督徒的信仰冲突,中世纪黑死病等原因招致的恐惧性偏见和怀疑,犹太人不得不从事令人讨厌的借贷职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犹太人最终于1290年被完全逐出英国。该项禁令直到1656年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才得以消除。因此,英伦三岛有近40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犹太人居住。
据这段史实判断,无论是乔叟还是莎士比亚,应该都没有与犹太人直接接触的经验,乔叟笔下犹太社区谋害基督孩童的犹太群体,以及莎士比亚笔下一心要割取基督徒借贷人一磅肉的犹太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都不可能源自个体的直接经验,而是源自间接传说或属于一种文学想象,“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主流文化对犹太人的那种鄙弃、歧视及忌妒的心态”[5]17,带有对犹太人厌恶和偏见的英国社会的传统特征。
在狄更斯时代的英国,犹太人的境遇虽然已经比乔叟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正如狄更斯为《雾都孤儿》中恶棍费金的书写所辩称的那样,费金之所以被定位为犹太人,是“因为在该故事发生的年代,情况不幸恰巧如此,罪犯几乎无一例外地总是犹太人”[20]269。费金的原型正是当时报纸报道的一位买卖赃物的名为所罗门(Ikey Solomons)的犹太罪犯[21]75。狄更斯将《雾都孤儿》中矛盾的对立面定位成一个犹太罪犯,应该是在“按照既有范式很便捷地塑造一个坏人形象”[6]233,这样的犹太人物书写,同样是“英国社会对犹太人的传统偏见,以及习惯于丑化犹太人的英国文学传统所造成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22]101。
尽管如此,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从乔叟到狄更斯,这些犹太形象在延续传统特征的同时,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隐匿的差异化叙事,通常被突出的模式化书写所掩盖,因而通常为批评界所忽视。
二、模式化书写之外的差异与作者的自觉选择及社会变迁
(一)乔叟“以恶治恶”的结局安排与对社会反犹情绪的客观性消解
在乔叟的《女修道士的故事》中,犹太人的群体形象更多是作为基督教殉教的背景而存在的[13]65。犹太人的形象仅仅是一种整体而笼统的群体符号:独居一区;以放贷为生;受魔鬼撒旦蛊惑,为信仰谋杀了基督徒儿童;被残忍地用野马拖曳,然后被吊死。乔叟将犹太人安排在矛盾的对立面,其原因在于前述基督教历史,以及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这一方面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偏见影响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故事的一些细微的选择和处理入手,能够找到一些不同的解读。国内学者汤玲等即从乔叟时代基督教会分裂、腐败、无能的历史,故事讲述者的不可靠身份,以及低层次的“圣母奇迹”的文学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乔叟旨在表达的是对基督教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社会盛行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的猛烈抨击[23]145。
而单从故事文本本身分析,也同样可以看到乔叟对社会普遍的反犹情绪进行的客观性消解。诚然,犹太群体在这样一个“圣母奇迹”的短小故事中是一种矛盾对立面的存在,他们因信仰冲突谋害了基督徒儿童。然而,乔叟在这个本应彰显圣母慈悲的故事的结尾,却安排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极其残忍的结局:市长将“每个预闻这件凶杀案的犹太人都处以苦刑”,“用野马拖曳他们,然后依法吊死”。这样滥用惩罚、“以恶治恶”和酷刑报复的叙事,在乔叟模式化犹太书写的同时,客观上部分消解了针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偏见。
(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之辩与对犹太民族的矛盾性同情
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同样有着针对犹太人矛盾而复杂的心理体现。一心要割取基督徒借贷人一磅肉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有着比表面“反犹主义”的叙事更加深层、隐性的复杂性。固然,犹太人夏洛克依然是反面的执着逐利的高利贷商人形象,但究其原因,一方面,16世纪的欧洲仍然延续着对犹太人的从业限制,从而导致了犹太人谋生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当时……借贷有很大的风险,利息免不了会很高”[24]147,因而夏洛克对于金钱执着的形象有着现实的基础。
此外,尽管莎士比亚在剧中尽力将基督徒安东尼奥塑造成一个多情尚义、具有古罗马侠义精神的正面形象,然而他也多次描述了安东尼奥当众无故辱骂夏洛克的情景,这样的叙事与将安东尼奥作为“一个心肠最仁慈的人”[11]190的设定明显构成了矛盾。而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叙事中的反面形象夏洛克,尽管唯利是图、感情冷漠,却是个言行一致的守信生意人:他借贷规范——评估风险、签订合约、履行合约;在诉讼失败、遭法庭判决罚没财产时,他签字认罚;他坚守犹太教义,不与基督徒同餐以避食猪肉;他崇尚勤奋,“容不得懒惰的黄蜂”[11]170,反感做事慢腾腾、白天也睡觉的仆人。这种看似矛盾的叙事,呈现的是作者对犹太人弱势社会地位的矛盾的同情心理。
这种矛盾的同情,在夏洛克坚持执行借贷合约的叙事中有着更多的印证。一方面,夏洛克是个不听任何人劝阻,一心要割取安东尼奥一磅肉的残忍的人;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在剧中对夏洛克这种一意孤行的报复行为给予了充分的铺垫和辩解。首先,在与安东尼奥签订合约之初,夏洛克并未料想到安东尼奥的全部商船都会出事从而还不起借款,他原本只是想借机嘲弄安东尼奥也有用他“盘剥得来的腌臜钱”[11]157的需要。其次,夏洛克坚持这一场对他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11]198,主要原因是对安东尼奥久积的怨恨和反感。安东尼奥只因夏洛克借钱给人收取利息,就一贯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对其当众辱骂、羞辱,骂他是“异教徒,杀人的狗”[11]159,把唾沫吐在他的犹太长袍上。为此,莎士比亚在剧中借夏洛克之口进行了诘问:“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11]180最后,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夏洛克的女儿不仅偷拿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违反教义与一位基督徒私奔。因此,尽管知道割取一磅肉对于他来说毫无经济利益可言,可夏洛克还是拒绝了几倍的利息赔偿,一意要对基督徒世界施以报复。但一个靠“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11]159的守信的放贷人,一个长期被基督徒无故侮辱的对象,一个看着女儿携款与基督徒私奔的犹太信徒,其采取的疯狂报复行为已经被莎士比亚给予了一丝理解和同情。
莎士比亚对于犹太民族弱势地位的同情,对种族平等的支持,在夏洛克遭受侮辱时所进行的机警沉稳的长篇雄辩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11]180-182
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在剧中借威尼斯城的社会和法律制度为犹太人夏洛克的行为进行了背书。虽然犹太民族的特色仍是“忍受迫害”[11]159,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仍常遭到歧视和辱骂;虽然威尼斯的法律仍有非常严厉的针对异邦人的违法裁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置”[11]205,而夏洛克也正是因这项法律规定而招致了财产的罚没。但夏洛克还是可以正常从事放贷生意、集聚财富、购房居住、雇用仆人,皆因威尼斯的法律规定了各国人民可以来往通商,“异邦人应享的权利”[11]192保障了威尼斯的繁荣。夏洛克坚持进行诉讼,认为只要付出代价,威尼斯城的法令就应判决给他应得的东西,而如果威尼斯公爵不能保障异邦人享有的权利即属蔑视宪章,自己有权“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11]198。犹太人夏洛克甚至能够正面谴责基督徒在蓄奴问题上的伪善行为。因此,该剧同时反映了16世纪欧洲社会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变迁和进步。
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描绘高利贷商人夏洛克的时候,一方面,受欧洲传统文化对犹太人歧视及嫉妒心态的影响,塑造了一个贪婪吝啬、视财如命、偏执且具有强烈报复心理的犹太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对犹太人的弱势地位表示了同情,并借威尼斯社会的法律制度对族裔歧视和蓄奴等社会弊端进行了批评。
(三)狄更斯赋予犹太恶棍的人性与对基督教济贫院的反讽
如果说14世纪的乔叟在其叙事中对社会普遍的反犹情绪进行了客观性消解,16世纪的莎士比亚借犹太人物之口对他们的际遇表示了矛盾的同情,那么到了19世纪的英国,狄更斯更是赋予了其笔下犹太人物费金传统负面形象之外的一丝人性。
在对费金的人物刻画上,狄更斯着力描绘的是一个构成故事矛盾对立面的社会底层罪犯的形象,费金的肮脏、贪婪、残忍仍为叙事的重点。但同时,狄更斯在书中不吝笔墨描绘了费金贼窝的日常饮食:费金在小说中的出场,即是手拿烤叉在锅里煎着香肠的形象;奥立弗刚到贼窝,费金立即分给了其一份奶油面包、煎香肠和热乎乎的掺水杜松子酒;仅就费金手下少年们的日常饮食,狄更斯在叙事中提及的具体食物名称就包括了面包、火腿、啤酒、香肠、杜松子酒、咖啡、糖、热面包卷、水煮牛肉、葡萄酒、兔肉饼、绿茶、干酪等。然而,反观奥立弗先前所居住的济贫院,以及九岁前在麦恩太太寄养处的饮食叙事,便能够发现其中鲜明的反差——无论是在济贫院还是在寄养处,低劣且稀少的饮食使得奥立弗整日“一副饿痨相”[12]8。济贫院每天只有三顿稀粥,“每个孩子分得一汤碗粥,绝不多给——遇上普天同庆的好日子,增发二又四分之一盎司面包”[12]11。小说中奥立弗想多要一点稀粥但被当众鞭打的情节,呈现的是济贫院孤儿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狄更斯以这种看似无意的饮食叙事安排,呈现出费金贼窝和基督教济贫院的对照和反差,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极大讽刺。
同样的对照和反差,也表现在孤儿和少年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基督教济贫院,处理孤儿事务的教区干事邦布尔一贯是“一副狰狞可怕的脸色”[12]17。孤儿们的世界“黑暗而孤独”[12]13,孤儿们整日拆着旧麻绳,靠稀粥孱弱地活着,但每晚仍必须为那些所谓养育他们、照应他们的人祈祷。而狄更斯笔下的费金虽然教唆少年为其偷盗,但也会将熟睡的奥立弗“轻轻地抱起来,放到麻袋床铺上”[12]52。费金贼窝中少年的日常可以是“开心地大笑”[12]120,自由地调侃,喧闹地游戏。费金贼窝中基本的人性是基督教济贫院世界所缺乏的。这种隐性的对比,呈现的是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时期基督教社会和济贫法改革的极大讽刺:如果一个社会底层的犹太罪犯的世界都能比基督教自鸣得意的慈善济贫院更为人性,那么,基督教社会的弊病已经到了非纠正不可的地步[25]84。
狄更斯笔下犹太人费金细微的人性化形象的呈现,同时反映了19世纪英国社会对于犹太人群体的进一步宽容和理解。贝拉的研究发现,至18世纪中期,欧洲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居住在隔离的社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仍然低于基督徒,甚至至18世纪末,在欧洲的多数地区,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仍被依据传统基督教反犹教义征收特别税、受到特别禁令的限制。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开始对犹太人相当宽容,这种宽容甚至到了“利犹太人”(pro-Jewish)[18]16的地步。尽管社会上仍然存有一定程度的反犹情绪,但英国犹太人在19世纪早期的地位已经大大优于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他们无需继续穿特殊服装,不再被迫居住于贫民窟中,他们可以自由定居,法律也不再禁止他们从事任何经营、生产或商业活动,犹太人可以雇佣非犹太人”[15]48。1855年,伦敦选举产生了第一位犹太市长;1858年,第一位犹太人被吸纳进议会;1884年,上议院有了第一位犹太议员;1870年,“大学测试法”(the University Test Act)的颁布使得犹太人能够就读牛津或剑桥大学。至19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均制定了全面解放犹太人的法规。西欧及中欧地区的公众普遍认为,像沙皇俄国那样未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太过落后[18]17-25。
至19世纪末,尽管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仍抱有种种矛盾心理,尽管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基督徒仍然会对否认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产生怀疑和偏见,尽管世俗的非犹太人仍会认为犹太人怪异,“启蒙运动的作用、科学革命、政治变革以及经验的教化影响,已经能够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改变了对欧洲犹太人的态度”[18]21。狄更斯正是在当时《物种起源》的出版,地理、天文和生物学的新发现的影响下,以及与犹太人的实际接触经验的教化作用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英国犹太民族的理解与认识。
1860年,狄更斯在将其伦敦的住房卖给一位犹太银行家的过程中,对犹太人的认识发生了更加客观具体的改变。从最初在给朋友的信中称买家是个“放债的犹太人(a Jew Money-Lender)”[26],到事后表示“我不得不承认,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买家表现都非常好,过去与我打过金钱交道的人当中,我不记得还有谁能够如此令人满意、如此考虑周全、如此可靠”[26],狄更斯对犹太人的认识从带有传统偏见的群体符号,变成了具体的“可靠、周全、令人满意”的个体。因此,当银行家妻子戴维斯夫人(Eliza Davis)写信指责其在费金形象的塑造上助长了社会对于希伯来民族的恶毒偏见后,狄更斯在《雾都孤儿》再版时将后十五个章节中的“犹太人”字眼全部进行了删除并致信回复:“我与我真正尊敬的民族之间除了友好并无其他,对于这个民族我无意冒犯。”[27]306结合小说中基督教济贫院叙事的描述,小说中费金的犹太性,与其说是作家对反犹主义的认同,不如说是狄更斯受英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偏见的影响,便捷地利用了英国文学传统中的刻板犹太形象;而费金形象被赋予的细微的复杂性与基本的人性,是英国社会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变革和进步使然,也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狄更斯在借助刻板形象的同时,反讽了基督教社会的自负与虚伪。
结 语
基于对14世纪至19世纪英国作家乔叟、莎士比亚及狄更斯所塑造的犹太人物形象分析,可以发现犹太人作为种族群体,在英国文学中的总体形象带有一脉相承的负面特征。这种负面刻板的形象源自犹太民族与基督教世界在宗教教义上的根本矛盾,受中世纪黑死病等危机的进一步影响,固化于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制定的一系列法律限制,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对犹太人长期制度性歧视和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偏见的结果。尽管在乔叟和莎士比亚所生活的年代,英国的犹太人处于被驱逐殆尽的状态,在狄更斯所生活的19世纪,犹太人已无着装、居住和从业等方面的法律限制,犹太人的境遇也已经在制度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600年间三位英国作家笔下不同的犹太文学形象,仍均处于故事矛盾冲突的唯一对立面,反映出传统的种族偏见已经植根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偏见并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性歧视的逐步取消而立即消失。
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无论是乔叟笔下的犹太社区群体,还是莎士比亚笔下放贷的夏洛克,抑或是狄更斯笔下的贼窝窝主费金,这些固化刻板的书写中也隐含有细微复杂的差异性。乔叟叙事中犹太人最终受到的残忍的、滥用的报复性惩罚,是对反犹情绪的一种客观性消解;莎士比亚叙事中安东尼奥及其他基督徒对犹太商人夏洛克的无故辱骂,一贯忍让的夏洛克为自己的种族所进行的辩护,是莎士比亚对犹太人弱势地位的一种矛盾的同情和对社会弊端的批评;而狄更斯笔下费金的一丝人性反映的是作者对维多利亚时期基督教世界的强烈反讽。乔叟、莎士比亚及狄更斯用他们的书写表现出了对人性的共同关注。
这种对人性的关注,是作家先于时代的自觉和思考,同时也反映出英国社会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的持续变革与进步。至19世纪末,尽管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仍然可能会对否认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犹太人怀有偏见和歧视,但“在很大程度上,宽容的需要、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身份、经济利益、或者仅仅是个人交往经历,这些考虑变得更加重要”[18]21。
当今世界,反犹主义也许不再是突出的问题,但其他形式的种族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日益抬头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2018年初借用前英国犹太教长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的警告——“始于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会止于犹太人”,告诫世人抵制仇外心理;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19年初明确强调,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反犹主义、反人类、仇恨和种族主义”[28]。在此背景下,对英国及整个欧洲历史上针对犹太种族的歧视和偏见、相关的变革,以及在文学中的呈现进行梳理和审视,对帮助我们认识过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