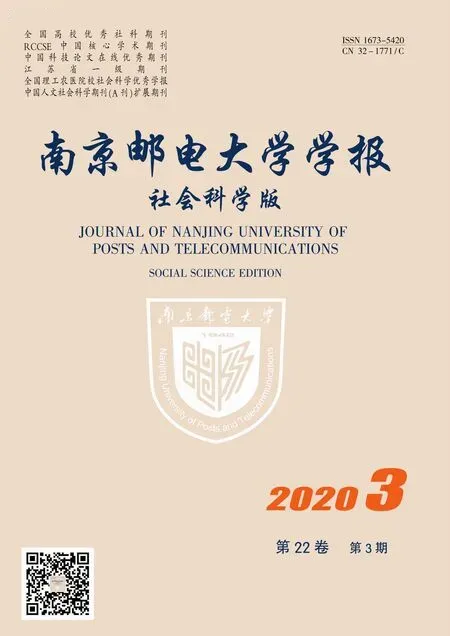映像之欺、异化规训和秩序超越
——对严歌苓《扶桑》人物主体建构的拉康式解读
2020-12-13唐军,徐敏
唐 军, 徐 敏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主要描述了华人女性扶桑和护华使者克里斯之间跨越种族的爱情故事,是一部以扶桑和大勇为代表的华人移民在文化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史诗性作品,曾荣登2002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小说。
以往的研究者聚焦于《扶桑》中的人物形象,探讨小说中颠覆西方想象的刻板华人形象,重塑华人的民族形象[1],解构美国的救世主形象[2],逆向书写华人英雄[3],展现女主人公的凄美[4],旨在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的阐释挖掘该小说的文化底蕴、人性内涵等。但鲜有研究探讨小说人物主体建构的历程,挖掘人物在他者影响下自我认知的偏离,以及在社会蒙蔽下失去自我意识的社会现象。
本研究基于拉康三界论,对《扶桑》中的人物进行深入解读,以期对小说人物的主体建构进行更为丰满的阐释,帮助读者正视自我,审视既存秩序的偏狭之处。拉康认为,主体由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三维结构构成。主体在想象界中,受“小他者”(父母、朋友、周围人等)的影响,形成自我认知,建构起被 “小他者”认可的理想化自我。在语言符号构成的象征世界中,主体建构由社会-文化这一“大他者”所主宰。主体在“大他者”的审视下,融入象征秩序,认同符号法则,同时渴望被“大他者”所认可,因而象征界中的主体不断异化,竭力完成社会性的自我认证。对处于“知觉与意识裂缝中”[5]149的实在界中的主体而言,他们处于原始的无序和无知中,不会产生匮乏和丧失感,能够忽视或排斥象征界的规则。小说《扶桑》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扶桑、克里斯和大勇分别在想象界中塑造了理想主体、在象征界中形成了异化主体,以及在实在界中打造了独立主体。他们的主体建构进程分别是华人女性守卫之旅、护华使者朝圣历程和华人男性颠覆之路的缩影。
一、华人女性的守卫之旅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扶桑是旧时代华人女性的代表人物。作为湖南茶农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扶桑惯于被忽视和被奴役。“小他者”即周围人对她的影响使扶桑误认为他人所认同的女性特质便是自我的内在属性。广东婆家人眼中的扶桑沉默寡言,“口慢脑筋慢”,“娶过去当条牲口待,她也不会大坑气”[6]41。在婆家人这里,扶桑认识到自己与牲口相似的愚笨痴憨的特质。为了讨婆家人的欢心,她任劳任怨、贤良淑德。唐人区华人男性眼中的扶桑,身上带着东方女性的奴性特质。扶桑那“任人宰割的温柔”和不知痛痒的痴傻使她注定 “是个天生的妓女,是个旧不掉的新娘”,“是每个人的老婆”[6]252。在中国男人那里,扶桑形成了对自我的虚假认知——柔弱顺从。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扶桑接纳所有的嫖客。她记不住任何嫖客的名字和面孔,所有华人因这份平等而感到“格外的体己”。她也因此成为美国唐人区“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一个风流绝代、一个绝代妓女”[6]3。而白人少年克里斯眼中的扶桑却是极具古典美、困囿于苦难牢笼的东方女奴。扶桑身上散发的颓废的美丽深深地吸引着他,扶桑 “泥土般真诚”和不加取舍的母性让他的“身心出现一种战栗的感动”,引起了他的倾慕。从白人少年那里,扶桑意识到自己的风情万种、真诚体贴。为了迎合克里斯在她身上寄托的幻想,满足男孩对她的迷恋,扶桑报之以真诚温暖的微笑,毫不吝啬地展示出自己的美丽,给予对方足够的母性关怀。
以扶桑为代表的旧时代华人女性,在想象界中对自我的建构遭遇 “小他者”的先行性诱导。“小他者”眼中的华人女性是柔顺依存、沉默被动的“女奴”。正因为“小他者”对华人女性的凝视和欲望投射扰乱了华人女性的自我认知,致使她们堕入对自我的误认之中,从而依循“小他者”喜爱的形象,塑造理想化自我。而当华人女性们面对东西方“大他者”的审视时,她们大多任由“大他者”摆布,在符号秩序(用语言符号所呈现的文化观念和规章制度)的规训中不断异化,在象征界的角色定位中“安身立命”。
中国封建礼教的桎梏、男权文化的压迫,使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和自我意志。在 “大他者”的奴役下,以扶桑为代表的华人女性们无法自我谋划。她们承认男性的优越,接受男性的权威,认同自己的附属性。她们不断加强所谓的“女性气质”,竭力塑造忠贞贤淑、逆来顺受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在小说中,扶桑被贩卖到美国,被迫从事皮肉生意,屈从男性的意志,迎合男性的喜好,彻彻底底地依附男性。
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审视之下,以扶桑为代表的穿着艳丽绸衫的唐人区女性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化身。透过扶桑,白人男子走进了具有魔力的东方世界,唐人区的华人男子甚至为了争夺扶桑而自相残杀。西方霸权文化灌输的等级和种族观念渗透到扶桑的认知和行为里,她在与同伴逛街遇到“规矩”的白人妇女时,会“慌张地挪着小脚,退进那家茶馆”,给马车里的白人妇女“腾出个干净的世界”[6]34。她默默忍受着白人社会的欺凌和胁迫,在潜意识里认同自己的存在是“对美国正派社会的污染”。后来在拯救会的白房子里,扶桑意识到唯有穿着红绸衣的她才是“原本”的她,才能被克里斯认出。就是在那时,扶桑察觉出起初克里斯对她的倾慕,源自于她身上所承载的古老国度的文化。彼时的扶桑已然完全接受异质文化对她的定位,她脱下“抹去一切魔一般的东方痕迹”的白麻布袍,心甘情愿地再次穿上那“邪恶肮脏”的红绸衫以满足他人的欲望,回归卑贱的身份。
以扶桑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象征界中逐步异化,她们的自我遭到阉割,自然天性受到压抑。在东西方“大他者”的驯服下,华人女性集体陷入沉默。她们戴上文化符号的面具,套上社会规范的枷锁,不断与原初自我分裂,逐步沦为象征界的囚徒。虽然象征界中的符号秩序能困住华人女性的肉身,却无法完全锁住她们的灵魂,更无法彻底压制住她们强韧的生命力。在重重压迫下,华人女性开始质疑象征世界的规则秩序,逐步恢复对问题的感知。
在小说中,扶桑真正地恢复自己的意志是那场在唐人区暴乱中发生的强奸,她“渐渐分不出偶然在自己身上的这件事和天天发生的那件事有什么区别,分不出出卖身体和轮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6]216。她开始审视自己的种种遭遇,开始察觉到实在界的存在。在实在界这一没有文明束缚、没有概念界定、没有真假对错的领域中,扶桑意识到自己以前的生活和自我都是从“小他者”和“大他者”的要求和期望中派生出来的,想要实现自己思想的独立,追求自身生命的充盈,必须从实在界中获取内驱力,让自己的内心拥有超出宿命的自由和独立,如此象征界的概念和定义才无法干涉她的思想。扶桑最终超脱了一切文明社会的教化,她身上的“神性”使苦难失去了原有的意味,变得高贵、圣洁。她在实在界中获得动力,在苦难中涅槃重生,在毁灭中释放自我,她以“跪着的姿态”宽恕了一切世俗的罪孽。她全身心地接纳苦难,享受苦难,“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6]216。她不觉得自己在出卖肉体,这是“肉体的相互沟通”,而这份交流则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而暴乱中的那场强奸,只不过是一场更为狂野的切磋,她对此没有恐惧,只是“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6]216。
面对象征界的畸形秩序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和精神毒化,以扶桑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沉默中保留残余的知觉,她们在审视自己所处的象征界时,察觉出符号秩序对事物真相的歪曲。虽然华人女性无法再度回归实在界,但她们以柔克刚,竭力摆脱符号秩序对其内心的侵扰,努力建构追求独立自主的主体。
扶桑的主体建构清晰地展现了华人女性守卫自由与独立之路的艰难曲折。初始时“小他者”的诱导将这些华人女性引入虚妄的想象界,使她们对真实自我产生认知偏差,并将自身塑造为他人欲望投射的对象。继而在象征界中,东西方文化压抑了华人女性的自然天性与原始欲望,符号秩序的规训不断剥夺她们选择的权利。但华人女性强大的感知力在重重压迫中逐渐恢复,她们开始质疑他者的误导和社会的规训,在符号触及不到的实在界中积攒精神内力,守卫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二、护华使者的朝圣历程
《扶桑》中的白人男性克里斯作为护华使者的先锋人物,来自缄默寡语的军人家族。军人的身份使克里斯家族(库凯家族)的男人们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家族的每位男性都有秘密的外族情人,“这是他们骄傲的需要,是征服和占领”[6]97。作为家族中的第九个孩子,克里斯未得到父亲太多的关注,自幼丧母的他有着鲜为人知的敏感脆弱。在家族的浸染下,12岁的克里斯走进了唐人区,不仅是为了体会异域文化,更是源于内心的征服东方的渴望。他的敏感多情使他在唐人区妓馆遇见扶桑时,为她的美丽而“无声地号啕”,“一脸泪水”。他的勇敢骄傲使他心甘情愿地投入骑士这个角色。在窥视到扶桑遭受的种种苦难后,克里斯一心想将她解救出来。而在扶桑病得奄奄一息时,克里斯带着拯救会的洋尼姑挽救了她的生命。当扶桑被大勇禁锢,克里斯依然没有忘记她,不惜与家族反叛,他甚至想杀了大勇,让扶桑不再被任何人所钳制和占有。
以克里斯为代表的护华使者在想象界中尚未形成对自我及外界事物的真正认知。他们当中有人对东方文明产生猎奇和征服心理,同时也因异族女子的风姿产生迷恋和怜惜之情。在家族成员等“小他者”的影响下,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想象中建构能够得到“小他者”认同的“伪自我”。在面对象征界的西方“大他者”时,他们更是难以挣脱“大他者”精心设计的幻象,从而迷失自我,不断异化。
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下,白人的优越性和殖民意识悄无声息地融进以克里斯为代表的护华使者的骨血。小说中的克里斯一厢情愿地认为受尽折磨和屈辱的扶桑渴望他的拯救。随着反华浪潮席卷整个美国社会,克里斯对华人的敌意也与日俱增。他在幽灵般的意识控制下不断异化,甚至祈望能有“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6]192,毁了那片“藏污纳垢”的唐人区。他加入了白人引发的那场暴乱,一方面是希望借助这场革命摧毁扶桑所有的不幸,将她从牢笼中救赎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获得白人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同。但在这场为“正义”所驱的革命中,势不可挡的愤怒和仇恨淹没了白人群体的理性,他们“渐渐陶醉在毁坏和残忍制造的壮观中”[6]198。克里斯受社会群体的驱使,“身不由己”地参与到了那场对扶桑的暴行中。
以克里斯为代表的护华使者,面对象征界对主体的控制,无法察觉完全被“大他者”支配的危险。西方社会的种族优越观念和反华浪潮,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皆如克里斯一样对华人移民虽同情却又不可名状地歧视、憎恶。这份恶意被聚集、被煽动,成为具有毁灭性的可怕力量。他们所建构的自我不断畸变,甚至在浑然不知中成为推波助澜的“纵火犯”。但是在尚未泯灭的良心的鞭策下,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与他人的行为。
在小说中,与扶桑的相识相爱、重逢别离,使克里斯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扶桑圣母般的宽容和对苦难的超然,让克里斯对生命、种族、唐人区都产生了新的认知。他正视自己曾经对扶桑的施恩姿态,直面自己犯下的罪恶,在“良心欠债和鞭打良心”中赎罪。克里斯感知到符号秩序中的虚伪、荒谬和愚蠢,他逐渐从实在界中清醒地认识到“小他者”和“大他者”对主体身心的管制和切割。尽管克里斯清楚地意识到象征界对跨种族、跨阶层爱情的歧视,但他最终仍无法完全逃离它的牵制。所以在面对已然超脱符号秩序的扶桑时,克里斯讨厌已经长大的自己,他甚至渴盼能“小到她能揣在她怀中”,逃脱社会秩序的制约和他者的凝视,回归到生命原始的状态中。但是克里斯与扶桑都没有与整个象征世界抗衡的力量,因而他们最终在象征界中别离。虽然他们的肉身无法相互陪伴,也无法双双回归实在界,但他们的灵魂却能够在实在界中肆无忌惮地跨越象征界的身份、地位的鸿沟,享受无限的自由。克里斯在对扶桑的爱与赎罪中,摆脱了白人社会对华人移民的看法,意识到种族歧视下华人移民的生存困境,也逐渐理解了使他困惑的“唐人区彼此戮杀又相依为命的关系”[6]224。他从实在界中获得内驱力,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中砥砺前行,成为中国学者,成为护华使者,“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6]263。
回顾克里斯的人生,可以发现护华使者踏上朝圣之路的历程颇为艰难。他们从不可言说的实在界中寻得内驱力,踏上了自我救赎确认价值的“朝圣”之旅。在西方迫害华人移民的主流文化中,他们逆势而上,为离散的华人移民发声,终其一生争取和维护华人移民的自主和自由。
三、华人男性的颠覆之路
小说中的大勇(阿泰/阿魁/阿丁)作为华人男性的核心人物,本是广东一户人家的少爷,自幼养尊处优。周围人对他的尊敬和偏爱,使他形成了“得罪天下气概”的自我认知。白人社会的恶意和敌视席卷着整个唐人区,寡言木讷的华人需要一个“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领头人,而外表强悍、身材雄壮的大勇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他腰带上一直挂着的俊美飞镖逐渐成为他“勇猛好战、杀人不眨眼的一个符号”[6]214。在唐人区华人的目光投射下,大勇形成了对自我的认知。在族人们的角色定位和期许中,他竭力建构亦正亦邪的自我形象。他“明里暗里的造孽”,欠下一堆血债,手里控制着一批批的禁运物品。同时,他作为唐人区华人群体的庇护者,与那里的中国人“彼此戮杀又相依为命”。当发现自己的同胞被剪了辫梢,他以牙还牙,在上百洋人的衣裳后背上划了刀口;当白人警察夜袭地下拍卖场,他一人抵挡警察;当老苦力被白人工友打得血肉模糊,他组织五千中国苦力全面罢工。唐人区的华人敬畏他,旧金山的白人则对他闻风丧胆。
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身上寄托着家人和族人的期望。在家人、族人等“小他者”的影响下,他们努力彰显着男子气概,极力确立着权威。华人男性在这样的映像投射中认识自我,在想象界中塑造理想主体,继而在符号秩序的畸形规制下构建出异化了的主体。
在中国父权文化的洗礼下,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坦然接受由象征界所赋予的威信和权势,他们将女性视为客体,看作自己的附属物。小说中的大勇之所以宠爱扶桑,是钟爱于她身上“牲畜般可贵的感知”[6]165。对大勇来说,扶桑最初只是个“珍奇牲畜”。他肆意物化扶桑,哄抬她的身价,主宰她的命运。大勇自视为中国女性的主导者。同时,美国的物质文明又主宰着他的价值观,他手上戴满的宝石戒指正是追逐金钱和权力意识的外化。在西方权财至上的文明秩序下,大勇自视为唐人区华人的主导者。当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到达美国时,他们发现,在19世纪的美国,强势的西方文化压制着东方文化,白人专横地侵压着中国人,排山倒海的歧视和肆无忌惮的敌意向聚集在唐人区的华人扑来。那时,在自视优越的白人眼中,这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血统低劣,语言笨拙,仪态粗俗。这群拖着辫子的中国男人“把人和畜的距离陡然缩短”[6]66。在重重的排斥和蔑视下,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并未被西方的符号秩序完全地规训。在小说中,为了更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异土上,抵抗西方“大他者”的欺压,大勇进一步异化自我,逐渐成为白人眼中奸诈乖张的亡命之徒。他“赌马舞弊,倒卖人口,杀人害命”[6]251,在触犯一系列美国法律之后,又利用法律的漏洞和乱世的巨变不断更名换姓,掩盖过往,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而在看清符号秩序的本质后,大勇生出了回归实在界的念头。
得知扶桑在白人残忍制造的暴乱中受尽屈辱时,无能感、挫败感折磨着大勇,他甚至想要结束扶桑的生命以维护她的尊严。他意识到自己与西方社会的“单打独斗”是徒劳的。这件事过后,大勇不再刻意地去维护骁勇善战、血气方刚的形象,他做起了“乏味的规矩人”,“全身素净”,“一颗首饰也不见”,“辫子没了油水”;他不再造孽,甚至登报嫁扶桑还她自由。唐人区的华人都在传“大勇脑筋有病了”,但其实他只是看清了想象界的虚幻和象征界的虚伪,不再渴望外界的认同。他抛下对外在物质和权力的追求,期望回归自由的实在界。小说的最后,大勇以死亡来摆脱象征界的奴役,倾覆象征界的秩序。大勇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对扶桑百般刁难的白人牛肉商,引来一片“众志成城的警察”。他本可以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带着扶桑离开戏院;他本可以在警察赶到之前逃之夭夭;他本可以在被逮住后,凭着身上的飞镖杀出重围。但这次大勇没有逃,也没有抵抗,而是从容赴死。他厌倦了九死一生、铤而走险的生活,用主动赴死表达对西方社会的抗议,以赢得民族的尊严,赢得白人和华人的钦佩;他是用自己的死亡还扶桑真正的自由,也与象征界决裂,重返实在界,追寻心灵的完整和生命的本质。
大勇的一生体现了华人男性颠覆想象界和象征界强加观念的艰难。华人男性在族人的影响下,产生自恋式的认同,构建出理想化的自我。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又被象征界“大他者”遮蔽,中国的父权文化赋予华人男性无上的地位,使他们纷纷成为恣意物化女性的男性;西方物质文化的价值观又引诱着他们不断追求钱与权。但是当面对异质文化的敌意凝视时,他们当中不乏大勇这般对象征世界中的西方秩序不妥协的人。在象征界中接二连三地惨遭否定与打击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逐渐醒悟,为了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竭力颠覆想象界的欺瞒和象征界的规训,不再期待他者对自我的完全接纳,渴望回归实在界。
结 语
小说人物扶桑、克里斯和大勇在19世纪复杂的世界大环境中,一直饱受想象界中“小他者”的映像之欺,沉迷对自我的误认与想象,建构出虚妄的理想主体;同时他们还一直惨遭象征界中“大他者”的凝视之殇,在符号规训中扭曲自我,因此构造出驯服的异化主体。当在象征秩序的压迫下变得伤痕累累后,他们透过知觉和意识的裂缝认识到象征界的不合理性,不再甘心囿于符号规则对身心自由的桎梏,而是努力挣脱主流文明畸形的教化和规训,从实在界中寻求力量,以期重建主体性,守护内心的丰盈与自由。
立足于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中的每个主体都遭受着想象界的欺骗、引诱和象征界的催眠、规训。如果不去认真审视象征世界的规则,我们无法知道事物平静的表面下藏着怎样汹涌的暗流,也会陷入自我建构的僵局中,与世浮沉,进而导致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不断为偏见和狭隘所吞噬。因而,为了建立人格独立的主体,我们需要保持反思问题的知觉,突破想象界和象征界的重围,超越符号秩序对主体意识和行为不合理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