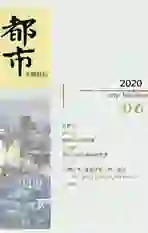“问题少年”是怎样被“炼”成的
2020-06-29王春林
王春林
虽然聚焦儿童成长问题的长篇小说《放养年代》(载《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3期)在马笑泉笔下的出现,多多少少看似有点突兀,但只要是对作家的小说创作历程稍有了解者,就会知道其来有自。事实上,早些年的创作中,马笑泉就曾经有过包括《红蛇男孩》《幼兽》《等待翠鸟》《他哥哥是黑社会》《我们到河里洗澡去》等在内的一个关注描写少儿成长危机的中短篇小说系列。也因此,从一种小说创作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说,由马笑泉写出如同《放养年代》这样一部关注思考“问题少年”的长篇小说,也就不过是或迟或早的事情。然而,一个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是,虽然活跃于《放养年代》中的核心人物,是以任冲为核心的一众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少年儿童,但这部长篇小说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简单地归入所谓儿童文学的范畴之中。正如同曾经的诺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那部旨在深入探讨人性恶的长篇小说《蝇王》,所集中关注描写的,都是一群六岁到十二岁的少年儿童,但却一向被看作是成人文学一样,马笑泉的这部《放养年代》,也只能够被放置在成人文学的范畴中来加以理解分析。
与戈尔丁的《蝇王》更多地关注思考人性恶的问题有所不同,同样是一部以一群少年儿童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放养年代》却带有某种不容忽视的成长小说的特点。关于“成长小说”,学者艾布拉姆斯曾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做出过这样的论述:“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尽管说等到《放养年代》结束的时候,身为小学四年级学生的主人公任冲,年龄也不过只有十一岁,距离通常所谓十八岁才真正成年尚有不短的时间,其成长的历程可以说还远远没有能够完成,但在我看来,这却并不妨碍我们把这部作品理解为成长小说。之所以要这么说,乃因为小说的叙事时间是从任冲呱呱坠地的时候开始的。从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成为十一岁的懵懂少年,十一年的时间,已然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成长时段。更进一步说,虽然《放养年代》并不完全合乎艾布拉姆斯给出的成长小说定义,只是写到了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的各种遭遇,同时也涉及了他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其缺失处在于没有能够写到他最后的长大成人。然而,尽管单纯从年龄的角度来看,任冲尚未长大成人,但从小说那帶有明显开放性的结尾处理方式来判断,主人公很显然对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已经有所体认和感受。到了小说结尾处,眼看着就要一败涂地的任冲,在老弟宋安(原名任安)所驯养的那条猛犬小毛的帮助下,终于反败为胜,扭转了整个战局。这个时候,“行近门洞的时候,任冲看到它的尾巴欢快地大幅度晃动起来,因为从偏门后闪出两个人来:宋安和许琪琪。任冲看到许琪琪弯下腰,仿佛是在摸小毛的头进行鼓励,而老弟则远远地望向自己这边。以为他会行过来的,任冲挺了挺胸脯。但宋安并没有像他期盼的那样行过来,而是和他对望了一会儿后,转身带着许琪琪和小毛行了进去。在那一瞬间,任冲看见门洞突然封闭,粗粝冷硬的围墙把他和宋安隔在了两个世界。”明明是同父同母的手足兄弟,二人感情一向要好的任冲与宋安,却因为父母婚姻的解体而被迫分别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一个尽情享受着来自母亲、姥姥以及姥爷的悉心呵护,另一个则被迫孤零零地与赌徒父亲相依为命。小说的结尾,毫无疑问首先是他们之间对比鲜明处境的形象体现。但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却在于,这个时候的任冲与宋安,其实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家庭,而是分别属于所谓“有志少年”与“问题少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宋安不仅一向表现得乖巧驯顺,而且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好孩子,或者可谓之曰“有志少年”。而任冲,不仅生性乖戾逆反,成绩糟糕,而且还总是热衷于各种暴力打斗,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坏孩子,或者说是“问题少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结尾处那个“粗粝冷硬的围墙把他和宋安隔在了两个世界”的细节处理,就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具体来说,它所象征隐喻的,就是身为一母同胞的任冲和宋安兄弟俩,被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硬生生地切割成了“问题少年”和“有志少年”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与此同时,我们也须注意到,结尾处两兄弟被那堵“粗粝冷硬的围墙”分隔开来的发现者,不是“有志少年”宋安,而是“问题少年”任冲。而且,从任冲的这种“发现”中,我们还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他对老弟一种莫名的羡慕与向往之情。在我看来,最后的发现者之所以是任冲,而不是宋安,关键原因在于,作家马笑泉是要借此而写出“问题少年”任冲对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的体认与感知。就这样,由以上分析可知,在艾布拉姆斯给出的关于“成长小说”的几个条件中,除了长大成人这一条之外,《放养年代》与另外几条可以说是完全相符。基于此,我们自然也就把马笑泉的这部长篇小说认定为“成长小说”。
然而,在充分肯定《放养年代》所具成长小说特质的同时,我们却也不能忽视其中某种自传性因素的存在。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因为主人公任冲与作家马笑泉自己的出生时间,均是1978年。尽管我对马笑泉的个人生平,尤其是幼年的经历一无所知,但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作家与小说主人公出生时间的一致,乃是一种无意间的巧合。虽然我们并不能凭此即简单地认定《放养年代》就是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但最起码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充分地调动了自我的生存经验,却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说到关注表现“问题少年”的成长小说,《放养年代》却又与早些年出现的杨争光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有所不同。如果说杨争光在深度剖析展示张冲人性世界构成的同时,更多地把关注点投向了教育体制对一个“问题少年”所具负面作用的思考,那么,马笑泉则更多地通过对任冲这样一个少年形象的聚焦,深入地思考探究“问题少年”到底是被怎样一种外在的社会条件“炼”成的。事实上,任冲那样一种不无乖戾的倔强与逆反个性,仿佛从他呱呱坠地的时候就开始了:“刚闯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任冲昼睡夜哭,似乎要把整座飞龙县城从梦中吵醒。他的哭声嘹亮、持久,倾注着婴儿全部的生命能量,简直不计代价、不顾后果,以至于宋巧云常常担心他突然背过气去。”尽管母亲宋巧云想了很多办法,但就是难以奏效,“仿佛是在跟人们作对,任冲哭得更加起劲。”果不其然,任冲那样一种特别好斗的勇狠天性,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还只是在一岁到一岁半,刚刚学会行路的任冲,在街上一看到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就会难以自控地冲上去打别人一下。“就这样,任冲结下了不少仇家。再过一年,这些小孩都能满地飞跑而且脚下生根了,见到他就想复仇。”关键还在于,任冲对此的反应总是特别兴奋:“一看到有人主动要跟自己打架,任冲顿时精神陡长,比那个前来挑衅的打得还猛些。一顿乱舞下来,往往是复仇的被结仇的打得哇哇大哭,鼻涕眼泪都迸了出来。”借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来说,这任冲好像天生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任冲虽然小小年纪,但却已经无师自通地获知了如何才能凭借蛮力加智慧或者说“胡萝卜加大棒”在同龄人中做领袖的奥秘:“就这样,任冲仗着这把先进武器,拉起了一支部队。而王军跟何春生为争当副司令,差点打了起来,任冲只有让他俩轮流来当,一人当一个礼拜的来。而杨真当上了军长,坐第四把交椅,倒也心满意足。最小的那个男孩也被封为排长。整支部队没有一个兵,个个都带长字,倒也皆大欢喜。”这一细节,除了对任冲少年领袖才能的凸显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不容忽视。一个是官本位思想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上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虽然只是一众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小孩子,就已经热衷于计较“官位”的大小,在乎带不带“长”字了。另一个则是军事化思维的深入人心。幼儿园的小孩子要当官,不去当别的,竟然一门心思地只是想要当司令或者军长什么的。如此情形,在充分说明一种英雄主义情结普遍存在的同时,却也明显暗示着某种暴力倾向的隐然存在。
事实上,任冲他们这一批少年人性世界中“恶”的最早表现,也正集中在暴力打斗与性意识的萌动这两个方面。首先,是暴力色彩十足的无端打斗。这一方面,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在盲目打斗中王军眼睛受伤。那一次,是任冲与对手周明他们一边三人,约定好晚饭后要在篮球场打一场弹弓战。眼看着周明他们已经认输败退,任冲和王军他们依然紧追不舍。没想到,“快要挨近楼房后墙时,王军一个箭步越过他,抢先拐入楼后的池塘边。还没有站稳脚步,黑暗中一丝金属的光亮直射过来,钻进他的左眼。”就这样,还仅仅只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王军的左眼就彻底“报销”了:“那颗子弹是截取了一小段电线内芯制成的。至于是谁制造并发射了这颗子弹,周明推给何春生,何春生推给周明,结果两家都赔了五百块钱,任冲家则赔了两百。”尽管叙述者并没有明确交代那颗子弹的制造者究竟是谁,但它出自这些小孩子之手,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既如此,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把它视作一种群体意义上“恶”的证明。眼睁睁看着王军的左眼被打瞎,他的母亲钱春花不由得发出了自己的“天问”:“你讲这些孩子何解这样狠喽?”实际上,早在王军左眼被打瞎之前,面对着任冲他们的争勇斗狠的暴力打斗,厂医郑小华就曾经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何解连小孩子打架都这样猛了?”是啊,究竟为什么呢?这也是我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性本恶”,那就是说如同任冲他们天生就携带着某种“恶”的因子。另一种解释,则是来自于周围人文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故事发生的年代,正是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尽管作家并没有在这方面做更进一步的描写,但一种顺乎逻辑的推理却是,那种“文革”期间的“斗争”思维,以“后遗症”的方式遗传表现在了任冲他们这一代少年身上。具体到任冲他们,我以为,虽然说以上两种可能性的因素都存在着,但相比较来说,恐怕还是后一种因素所占比例更大一些。
其次,则是性意识的过早萌动。具体到任冲,他性意识的萌动,与他对生命的来历发生浓烈兴趣紧密相关。紧接着,也就有了任冲和陈玉一起无意间目睹偷窥青工谢海龙与厂医郑小华之间性爱场面的出现。尽管说陈玉对此一无所知,但早已在赵虎那里接受了性启蒙的任冲,却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在做大人的事”。我们都知道,大凡小孩子,便都有一种模仿成人举止的好奇与冲动。任冲与陈玉也不例外。在意外地目睹偷窥了谢海龙与郑小华的举动之后,还只是幼儿园孩子的任冲和陈玉,便趁家里大人不在的时候悄悄地“偷试云雨情”了。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性意识的萌动,无论男女,乃是生命过程中一个必然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任冲和陈玉他们的行为诚无可厚非,并没有什么善恶可言。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任冲和陈玉,即使是周明、罗佳、孙爱红、何春生、杨真他们几位,其实也都有过过早地“偷试云雨情”也即文本中所谓“嬲麻屁”的经历。所谓“嬲麻屁”,也就是如同任冲和陈玉一样模仿成人性行为的一种举动。都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性意识就过早地萌动。如此一种多少有点违背成长规律的过早偷尝禁果的行径,被理解为人性中某种“恶”的体现,恐怕多多少少也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然而,生性调皮顽劣的任冲,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的偷窥行为,有一天竟然会不无巧合地应验到父亲任建国身上。那是一个星期天,无所事事的任冲偷偷地翻墙进入了幼儿园的院子。这一次,他又在无意间偷窥了一场男女间的床上好事。所料未及之处在于,女人是自己在幼儿园里的老师郭芳,而男人,则是自己的父亲任建国。这样一个不堪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任冲给打蒙了,使他的意识一时间陷入神思恍惚的状态:“恍惚间院子里的三面墙正在迅速收拢,向他挤压过来,任冲像只找不到出路的小兽,茫然站立着”。此后,马笑泉所描写展示的,便是任冲这一无意间偷窥行为所导致的一连串发酵型连锁反应。先是与街上的孙明明莫名其妙地打了一架后躲在张家奶奶那里不肯回家,紧接着,回家后却意外地得到了心怀愧疚的任建国一反常态的呵护:“对于任冲的失踪,任建国其实心里比宋巧云更急,生怕这小子受不住刺激,在外面乱窜,发生什么意外。”不只是任建国,接下来,任冲发现,郭芳老师也对自己格外地温柔亲切起来了。这温柔亲切的结果,竟然是把一向刺儿头的他出乎所料地任命为班长。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等宋巧云因为受到沈荷花的刺激而买回家二十只小鸡之后,任冲竟然狠下心来虐杀了无辜的小鸡:“他感觉到任冲的目光跳动了一下,眼神变得炽热而古怪。他不晓得这些小鸡惹得任冲喜爱到想虐杀的地步,只觉得背上没来由地凉气直蹿。然后他看到任冲一手扣紧鸡身,一手活生生地把鸡脖扭断,甩在地上。”就在老弟任安为此而大惊失色的同时,任冲却依然不动声色:“任冲脸上露出一种快意的表情,丝毫没有住手的迹象。”明明特别喜爱这些小鸡,可任冲为什么要下狠手虐杀它们呢?对此,我们恐怕只能够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因为在无意间目睹偷窥了父亲的偷情场面但却又需要瞞着母亲,任冲的内心世界一直处于某种极度的压抑状态之中。某种意义上,他的虐杀小鸡行径,正可以被看作是其精神世界在极度压抑后的一种猛然爆发。也因此,到后来母亲宋巧云因小鸡的被虐杀而痛打任冲时,他才会感到某种莫名的快意:“这一个星期,他隐瞒了任建国和郭芳的事,总觉得很对不起宋巧云。现在被宋巧云打,他心里倒好过了一些。似乎每一扫子抽下来,心里的愧疚就减轻了一分。所以尽管痛得流泪,任冲还是没喊哎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任冲的被痛揍,也正是他内心里郁积的精神苦闷被释放的一个过程。唯其如此,任冲才会在被打时做出那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反应。
关键的问题在于,虽然任冲可以强忍住不去主动检举父亲任建国的好色偷情行径,但不管怎么说,纸里都不可能包得住火。到最后,由于邻居沈荷花的告密揭发,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宋巧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沈荷花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正是为了求得一份内心的精神平衡。面对着因左眼被打瞎而陷入孤独乖戾状态的儿子王军,沈荷花内心的痛苦实在难以排遣。正是在如此一种境况下,宋巧云的出现让她顿时生出了告密的念头。这一意外信息的获知,对宋巧云一时间形成了极强烈的刺激。以至于起身告辞时,差一点被绊倒:“行出门的时候,她被门槛绊了一下,几乎摔倒。看着她像个木偶一样挪远,沈荷花心里突然涌出一阵隐秘的快感。”自己陷身于痛苦的状态中还不算,非得把其他不相干者也都拉入到痛苦的行列中,借此而达至某种微妙的精神平衡,方才彻底罢休。对于沈荷花如此一种充满恶意快感的告密行径,我想,我们恐怕只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这样的一种理解与把握。尽管说沈荷花的这一次告密,被任建国想方设法搪塞了过去,但却因此而引发了任冲对戴娜的强烈不满。到了学校放学时,陈玉建议任冲跟戴娜讲和:“任冲梗着脖子坚决不肯。陈玉问任冲何解突然就跟戴娜黑脸,任冲自己也搞不太清,反正就是不愿意跟戴娜一起玩了。最后陈玉叹了口气说:‘随你。”对于这样一个连任冲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的问题,我们所能给出的,也只能是精神分析方面的一种阐释。质言之,任冲之所以要莫名其妙地疏远戴娜,乃因为与父亲任建国发生暧昧关系的,正是戴娜的母亲郭芳。小小年纪的任冲,拿自己幼儿园的老师郭芳没有办法,只好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迁怒于郭芳的女儿戴娜了。分析至此,敏感的读者恐怕早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其实已经数次提及精神分析这一语词了。是的,正是精神分析。很大程度上,马笑泉《放养年代》这部长篇成长小说的艺术成功,乃得益于作家对一种精神分析表现方式的熟练操作和运用。
由于生性一贯贪玩且又顽劣好斗,所以,在由幼儿园进入小学后,任冲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一种结果。第一次考试结束后,任冲信心满怀地和陈玉一起去领通知书。原以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进入前十名,未料想,最后的成绩却是倒数第十名。如此一个不理想的成绩,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任冲自己,更是沉重地打击了宋巧云的自尊心:“任冲考了倒数第十名的事实,将她美好的憧憬击得粉碎。当任安报告哥哥回来时,她翻身而下,拿起早放在枕头边的竹扫子。看到宋巧云咬着牙齿、红着眼睛、头发凌乱地向自己行来,任冲整个人像是浸在冰水里。让他害怕的不是即将来临的打骂,而是宋巧云悲伤绝望的神情。”事实上,也正是在母亲宋巧云如此一种悲痛欲绝神情的强烈刺激下,任冲下定决心好好学习,一定要在下一个学期把自己的学习成绩赶上来:“这个学期,任冲的表现让老师们刮目相看。他不再捣蛋,而是把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始终追随着老师,瞎子也看得出这学生是在认真听讲。”这期间,尽管任建国与宋巧云夫妇也曾经因为向郭芳借钱一事而发生过冲突,但却又因为任建国的主动俯首低头而一度摆脱了危机。危机的摆脱,对任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任建国和宋巧云重归于好,压在任冲心头的那块石头也就消失无影,跳起舞来都轻快了许多,得到了杨洁心的表扬,获得了一个口头颁发的进步最快奖。”跳舞之外,更关键的是他这个学期的学习成绩竟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提高:“过了几天,任冲去领通知书,语文九十六,数学九十九,考了第四名。陈玉是第二名。头名让欧明夺了。按照惯例,前五名都能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陡然跻身于尖子学生之列,任冲全身每根骨头都轻了几钱,行起来头昂到天上去了。”与此同时,偏好喜欢钻研难题怪题的任冲,竟然也还取得了年级数学竞赛的第一名。
但就在曾经的“野孩子”任冲的学习成绩日渐向好的时候,由于父亲任建国又和厂医郑小华闹出了桃色事件,母亲宋巧云一怒之下再次携任安回到了娘家:“但宋巧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脸色惨白,一言不发,提了个皮箱,要带任冲和任安回娘家去住。如果她大哭大闹,任建国还不怕,但这个态度,着实让他胆寒。任建国很怕宋巧云一去不复返,但又不敢强行阻拦,便表示:崽是两个人的,要带也只能带一个回去。”因为任安年龄更小一些,所以,被迫留在任建国身边的,就只能是任冲了。在任冲这里,原以为爸爸妈妈还会像上次一样,闹别扭过一阵就好了。没想到,这一次,在外婆江萍态度坚决的支持下,母亲宋巧云竟然下定决心要和任建国彻底分手了:“任冲仰着头,瞪着江萍,却又不敢作声,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任安本想追随而出的,但见任冲遭遇到强力阻击,便还是缩在桌底下,直到宋巧云喊他出来吃饭。”从此之后,任冲也就陷入到了莫名的先是充满希望转而很快就失望的焦虑状态之中:“以后每天下午放学后,任冲都怀着焦虑和激动往家里奔。他渴望着还没进屋就看到门开着,从里面传出宋巧云和任安说话的声音。但每次门都是板着面孔等着他来打开。”尽管下定决心离婚的宋巧云曾经建议他离开爸爸,随同妈妈他们一起生活,但“看到他弓着背,眉头深锁,任冲觉得爸爸可怜。宋巧云所教的那番话,他实在是说不出口,只有重重地画着字,把纸都划破了。”虽然只是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学生,但任冲对父亲任建国的同情,却毫无疑问显示出了某种人道主义的意味。也正是在如此一种情形下,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此前实在不应该无端地虐待一只无辜的小老鼠:“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真不该那样对待小老鼠。那只小老鼠肯定是没有爸爸和妈妈管,单独溜出来,才会被人捉住的。他觉得自己跟那只小老鼠一样可怜。”从当初对小老鼠的戏弄与迫害,到后来对小老鼠一种强烈认同感的生成,这样一种心理变化,与宋巧云携带任安离家后任冲的孤独处境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到后来,在分居一年多后,任建国和宋巧云夫妇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孩子一人一个。这个时候的任冲“认为如果自己也跟着妈妈,外婆就会要他们到外面住的。而现在妈妈只带着任安,就可以在外婆家一直住下去。这让他越发有种被遗弃的感觉。在學校里,每当任安想来跟任冲套近乎的时候,任冲就会横他一眼,然后把背对着他,或者干脆行开”。无论如何,当任冲在校园里有意无意地规避着老弟任安的时候,他内在精神世界因父母离婚的被扭曲,就已经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了。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父母离婚这一残酷的事实,很快就影响到了任冲的学习状况:“回到机械厂,任冲就开始做家庭作业。他现在也不理会做得对不对,更不要说检查一遍了,只是飞快地赶完了事,字迹东倒西歪,如喝醉了酒一般。”紧接着,任冲遭遇到的,就是来自周围人群的一系列精神刺激。先是陈玉的妈妈陈红心:“整个下午,任冲都控制着自己,不去看陈玉。他想陈红心不准自己跟陈玉嗨了,陈玉是个好学生,自己已经不想变好了,那就干脆离她远远的,免得害了她,下定这个决心后,一种混合着弃绝和悲壮的情绪充斥着任冲身心。”这其中,一种破罐破摔心理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一种事实。紧接着,是面对着来自外婆江萍的斥骂,任冲逆反心理的不自觉生成:“任冲心想,开除就开除,却没有说出来,只是咬着嘴唇不作声。”“任冲心想:‘老弟是你的外孙,我才不是呢。我不要你管。”接下来,是面对着母亲宋巧云,尤其是当宋巧云突然叫他大名的时候:“宋巧云一向都是叫任冲小名的。听她这样叫,任冲的心像被薄而锋利的刀片飞快地划了一下,那种痛是猝不及防的。他勉强应了一声,就要回去。”到最后,竟然是他一直不管不顾地呵护着的爸爸任建国:“任建国的口气硬邦邦的,让任冲觉得委屈。他想到自己拒绝了妈妈那个诱人的建议,全是因为爸爸,而爸爸却一点儿都不晓得。任冲却不会去想,自己要是不说,任建国又怎么会晓得这件事?他从小的脾性就是对一个人感情越深,就越不愿意表露,觉得不太好意思。同时也认为,不说对方也晓得。”这样一来,父母离婚后的任冲,简直就是陷入到了某种“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中而难以自拔。似乎周围所有的人都成了自己的敌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与自己作对。在如此一种不正常心态的影响下,曾经一度的“三好学生”任冲,其学习成绩的每况愈下,也就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但千万请注意,在任建国与宋巧云他们夫妇俩离异后,破罐破摔的精神堕落者,其实并不只是小学生任冲,首先是身为父亲的任建国自己。任建国不仅不再好好上班,而且还整夜整夜地聚众赌博。更有甚者,毫无经商经验的他,竟然不管不顾地坚持要和两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一块做生意,以至于到最后,竟然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就这样,任建国自己既然已经是泥菩萨过河,那他当然也就无暇顾及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儿子任冲了。这样,也才有了左眼早已被打瞎的王军,对任冲那种可谓是惺惺相惜的同情。当任冲追问王军“你何解要帮我”的时候,王军给出的回答是:“因为你现在和我一样可怜。”面对着王军的这种说法,“怔了一怔,任冲想说:‘我哪里可怜了?但这话到了嗓子眼,就卡在那里出不来了。爸爸和妈妈离婚后自己的种种境况一一闪现,当时并不觉得怎样,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王军所说———可怜!呆站在王军面前,他久久说不出话来。”事实上,任冲之所以要和王军、陈勇成为结拜兄弟,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内心里倍感孤独的缘故。因为任建国无暇他顾,“任冲的一日三餐只能在食堂里打发,饭票菜票倒是从来没少过。任建国也因此自以为履行了抚养小孩的义务,心安理得地在外头游荡。”他根本就不知道任冲内心的苦楚。实际的情形是,面对着当下的孤独处境,遥想数年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情景,生性一贯刚强的任冲,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想着想着,眼里不知不觉就盈满泪水。泪珠溢出,沿着面庞流下来,他也不去擦。有的泪珠流到嘴角,沁进唇间,咸咸的,凉凉的。”在如此一种情况下,面对陈玉所一再强调的欧明“又斯文,又不做坏事”,任冲内心里的复杂滋味,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又斯文,又不做坏事,这句话像把刀一样插在他心头,让他又痛又恨。他想:‘我就不斯文,我就做坏事,看你们何解?这样想的时候,他面前不但站着陈玉、欧明、戴娜、赵秋云和钱亚男,还站着宋巧云、宋安、宋正德和江萍。他想着自己如何变坏,如何让他们吃惊,心头竟渐渐有些快意起来。”一方面,对于任冲上述破罐破摔的心理,我们固然也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难发现,到了这个时候,任冲的逆反心理已经发展到了某种极致的地步。不论是他的此前的偷铁行为,抑或还是此后的偷铝行为,都可以从这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处获得有效的解释。尽管内心里已经有了如此一种可谓是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事到临头的时候,在要不要去偷铝的问题上,任冲却还是产生了一番并非不必要的犹豫:“虽说如此,任冲对偷铝一事仍迟迟不做决定。在他看来,在机械厂偷铁,就好像在自己家里偷零食吃一样,虽然也叫偷,但又似乎算不得真偷,跑到外面去偷铝,那就真的是做贼了。任冲虽然甘心做一个差学生,但并不想当贼。”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任冲虽然不想做贼,然而近来任建国竟然连饭菜票都不能保证正常供应,弄得他有一餐没一餐的,时常饿得肚子阵阵作痛,像有只手在把胃揉來揉去。本来可以到宋正德家去吃的,但任冲宁可挨饿,也不愿让他们晓得任建国和自己过得这么差。那么剩下的唯一办法,就只有去偷铝了。”就这样,等到任冲与王军、陈勇他们一起合伙偷铝盗卖的时候,一个彻头彻尾的“问题少年”也就被最后“炼”成了。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作家也没有对任冲这一形象做简单化的艺术处理:“本来任建国不管他,宋巧云又几次托人传话要他过去,他大可以离开任建国。但任冲觉得要是爸爸很有钱而不管自己,就可以去跟妈妈,但爸爸现在过得很差,自己就绝不能离开他。看到他变得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还常常觉得心疼。在其他小孩面前,任冲还要掩饰自己的酸楚,显出一副很快活、很满足的样子。”虽然只是小小年纪,但任冲却既要顾及自己过度敏感的自尊心,又要怜惜早已先自己堕落的父亲,对于一个“问题少年”来说,能够具备如此一种人性层面上的丰富性,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无论如何,有一个重要细节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已然成为“问题少年”之后,任冲一次与戴娜模仿成人的“嬲麻屁”行为时,“心里不再仅仅是充盈着单纯的好奇和欢快,而是掺杂着一种隐秘的报复的快感”。首先,这报复,并不仅仅只是指他和戴娜之间的“嬲麻屁”行为,更是指他全部的堕落行径。其次,报复什么呢?肯定既有家庭,也有学校,或者更准确全面的表达,就是社会。因为,从根本上说,任冲最后堕落成为“问题少年”,正是以上种种合力发生作用的结果。也因此,任冲那样一种“报复的快感”中,其实明显隐含有对家庭、学校乃至社会所发出的强烈抗议。
事实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猛然意识到,马笑泉的这部《放养年代》,乃由两条互有交叉影响的线索结构而成。一条显在的线索,当然是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任冲个人的成长经历。另一条不易为人察觉的隐在线索,在我看来,就是对成人世界(其中自然也包括机械厂在1980年代末的日渐衰落过程)那样一种更多地将其置于背景状态下的描述与书写。更进一步说,如同任冲这样一位“问题少年”的最终生成,与这个成人世界的潜在影响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关联。这其中,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谢海龙与徐丰这两位任冲的“忘年交”的先后不幸弃世。先是谢海龙被宣判死刑后:“任冲则变得沉默起来,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谢海龙阴郁的没刮胡子的脸,贺薇苍白的赤裸的身体,不断地在他眼前交替闪动,有时还重叠在一起,反复刺激着他的神经,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残酷和不可理喻。”“面对这个世界,他开始真正有了恐惧感。”然后是徐丰意外被刺身亡后:“他甚至真切地看到了死亡的面容,那是巨大的冰冷、无边的黑暗,遂忍不住长久地战栗起来。”无论如何,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在任冲由一个曾经的“三好学生”堕落为“问题少年”的过程中,又或者说,在任冲那看起来只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谢海龙与徐丰的非正常死亡,的确对他产生了不容低估的重要影响。对于这一点,明眼人不可不察。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