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沈从文
2020-06-24汪兆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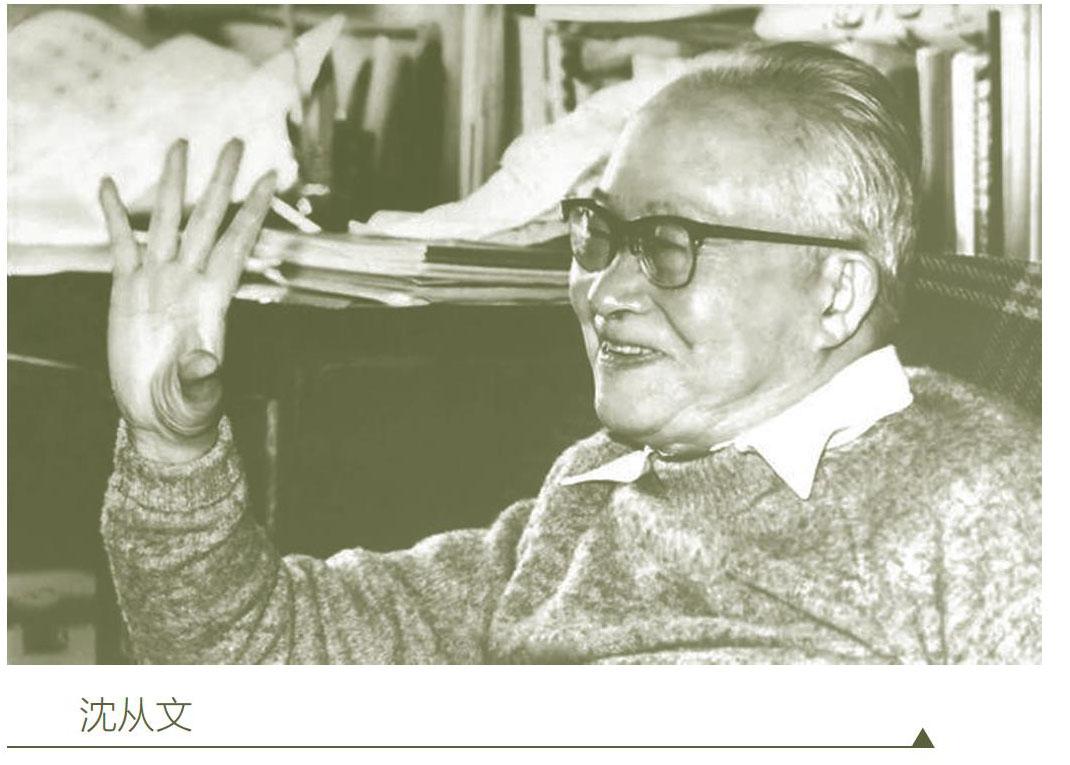
汪兆骞,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他与诸多文学名家相识相知,并给他们的作品“做过嫁衣”。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1980年代的文学,汪曾祺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在198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不仅因为继承1940年代的遗传关系而获得,还因其与80年代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关系而获得。古语说“斯文有传,学者有师”,汪曾祺的人生与文学羁旅,与他的恩师沈从文的教育、引导、护佑、扶植相关。从他们师徒的文学创作上看,有明显师承关系,他们的小说都避开当代主流文化,都取材于湘西山水或苏北民情风俗,以散文化的笔调表现出普通人的健康活力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动荡的时代、变动不居的历史相参照,表现出民间生活的真、善、美,及恒久的人性价值——正所谓“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
【师生情深】
识得汪曾祺的大名很早,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中文系上学时,因我的文学引路人严文井的推荐,读了很多沈从文的书,严先生又领我去小羊宜宾胡同三号,拜见过蜗居在前院一间东厢房的沈从文先生。后来我多次登门请教,听到过不少关于沈先生高徒汪曾祺的故事,还读了一些汪曾祺的早期作品,如《复仇》《鸡鸭各家》及上世纪60年代初的小说集《羊舍一夕》等。老实说,汪先生的作品并没有太打动我,倒是沈先生和夫人张兆和讲的关于汪曾祺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抗战时期,沈从文先生到昆明西南联大国文系教写作课,每天身着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去教室上课。沈先生讲课很认真,但口头表达远不如腕下书写那般行云流水、得心应手。他讲课时操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讲台上非常自制,声音又低,因此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唯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兴致。
沈从文更多的精力是用在给学生辅导写作、修改习作上。他教授的创作方法,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鼓励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汪曾祺等一干学生的优秀习作,沈先生经精心修润后,就以一个小说名家的身份,凭借他在文学界的声望,向熟人朋友推荐。为节省邮资,他还会剪去稿纸的留白,自费帮忙投寄出去。等学生的习作在报刊发表之后,沈从文便笑眯眯地将报刊和稿费交给汪曾祺他们,听他们兴奋地呼叫,老师也很高兴。
沈从文刚到西南联大,就受到傲岸的刘文典教授百般嘲讽,在讨论沈提升教授之事时,这位大学者勃然站起来反对曰:“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钱锺书、穆旦等也对沈从文多有非议。只有和学生汪曾祺等在一起,沈从文才感到轻松愉快。除了教书育人,他自己也经常在深夜伏案,忙着编撰自己的小说集《春灯集》《黑风集》及论文集《云南看云集》。
有天晚上,沈从文参加一场演讲会,深夜回家途中,忽见昏暗灯下有人倒卧街头,他忙去救助,孰料竟是喝得酩酊大醉的汪曾祺。沈从文便把他弄回家,熬酽茶灌醒,此事让汪曾祺不胜羞窘。还有一次,汪曾祺到沈从文家请教问题,老师见汪曾祺因牙龈上火,脸肿得老高,忙上街买回几个大橘子给学生吃,说此物治牙痛疗效甚好。
抗战胜利后,汪曾祺回到上海,此時的上海民生凋敝、遍地疮痍,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非常困难。汪曾祺在求职时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完,即将落魄街头,以至于他情绪低落,甚至想到了自杀。在北平的沈从文得知,十分生气,立刻写信教训弟子: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写完又怕严厉的语气伤了学生,因此特别让张兆和写信再去安慰,说你能写一手好文章,“将来必有大成就”。
接着沈从文又忙着致函好友李霖灿、李晨岚,请他们帮汪曾祺找工作,信中说:“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
1960年放寒假,春节前一个下雪的日子,我去看望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也在家,她刚从医院回来,说沈从文因病住院了。她告诉我,病中的沈从文见窗外大雪纷飞,惦记着身处逆境的汪曾祺,忙从笔记本上撕下12张纸,匆忙在小桌上写了六千多字的长信。告别张兆和,我又到一箭之遥的严文井家,将此事说给他听,他长久地保持了沉默。开学前,我又到沈从文那间小屋,得知沈从文出院回家后,我将写给汪曾祺的长信,重新用毛笔抄写在宣纸上,然后寄了出去。信中,沈从文鼓励学生不要放下笔,以自身及家庭的艰难经历,循循善诱,启发开导:“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汪曾祺的作品“至少还有两个读者……事实上还有(黄)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有了群众……”“只要有机会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趁年龄还来得及,有的是可学的东西。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时代大,个人小得很,惟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
1962年10月,沈从文在致程应镠的信中,批评了北京市文联的个别领导让汪曾祺“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空让他蹉跎岁月,然后又自己承担了责任,说“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值得深思的是,沈从文在信的开头,便开宗明义地说汪曾祺“人太老实了”,并对汪曾祺的文学才华,作了惊世骇俗的判断,“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先生这些信,是他人格的写照,他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湘西人的刚勇,他对北京文联个别人轻慢汪曾祺有不满,他对自己不得体言论影响了汪曾祺有自责,毫不虚与委蛇,有道义担当。特别是他目光如炬,对汪曾祺的文学价值有睿智准确的判断,这才有了1980年代汪曾祺横空出世的荣耀,也为文坛谱写了一曲师生情深的佳话。
【“我守住了‘京派的遗风流韵”】
我与汪曾祺神交久矣,而与他晤面相交,却是在1970年代末。我与军旅作家王愿坚去小羊宜宾看望沈从文先生,见屋里有位中年的“黑脸”客人,沈从文给我们相互介绍,便开始相识。王愿坚早就与我说过,他与别人合作写《闪闪的红星》时,汪曾祺也在当编剧,有时在一起开会,彼此不陌生。汪曾祺笑着对我说:“听先生说过你,有空到我家去玩。”
见汪先生待我热情,我心里有些忐忑,因为我曾向沈从文很委婉地表达过我对汪先生的微词。沈从文是被美学家朱光潜认定“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但他却一直被误解和封存,不得已离开了钟爱的文学,去博物馆致力于古代服饰和文化研究。尽管在新领域也获得极大成就,但离开文学之痛,一直在折磨着他。因此,他很理解高徒汪曾祺的遭遇与苦衷。
1980年代伊始,汪曾祺发表小说《受戒》,立刻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他。每次到沈从文崇文门新居去拜访,话题似乎总围绕着汪曾祺的新小说。在谈到《受戒》时,我说:这篇小说写小和尚明海与船家女英子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表现了“出世”与“入世”的航渡上,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向往,洋溢着像晓风露珠般的人性和人情的情趣与诗意,与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的诉苦和批判,走的不是一条路子。《受戒》《大淖记事》是选取中国文化中真善美的一面,以一种传统的民俗民情与源远流长的人格精神,映出恒定的人间之生活美、人性美。汪曾祺复出后的小说,一出手就真正回归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性。
沈从文先生一直微笑着耐心地听我“高谈阔论”。最后,他说:请注意《受戒》《大淖记事》的风格,不是汪曾祺独有的,它继承了废名的文学传统。我们的文学史,一直低估了废名和他的乡土文学。是废名把乡土诗化和理想化,将一种属于人类永恒的记忆和想象的诗性带入到文学乡土里。
沈先生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受戒》《大淖记事》不仅受废名的《桥》影响,还受他恩师沈从文《边城》等的影响。《桥》里的小林与细竹,边城》里的傩与翠翠,再看《受戒》里的明海与英子、《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与巧云,他们的恋情或单纯或忧伤,心中都有许多不如意。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
有论者说,汪曾祺小说乡土文本趋向于和谐和唯美,似可商榷。太过和谐唯美,导致优美诗化的同时,会泯灭文学的尖锐和深刻。其实,《受戒》《大淖记事》中,也蕴含着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还有人说,汪曾祺的小说比他师父的小说多了些儒雅气和文人境界,我认为此说有溢美之嫌。沈从文小说弥漫着文雅气、学院气和闲适气,是文坛公认的。他的小说在呈现湘西世界的悲凉的同时,还写出了湘民的野性和血性。汪曾祺的小说,从容澹定地叙述乡土市井风情,寄寓着一种与传统文化延续的悠长人生,透露出社会和历史信息。恬淡的人生、质朴的人性,构成了他小说的精神魂魄。师徒二人都本着文学家探幽烛微的勇气,行其所当行。
1990年代初,作为《当代》的负责人之一,我曾受邀到鲁迅文学院讲课并辅导学员写作。学员曾明了创作了中篇小说《风暴眼》交给我。没过几天,汪曾祺先生笑眯眯地来到我家,正是谈这篇小说。他说这是篇写荒漠中人物对自然进行抗争,充满神秘和诗境的好作品,说罢从大信封中抽出他为这篇小说写的评论,让我立即就看。看后,我对老爷子说,您比我看得深透。小说在《当代》发表之后,70多岁的老爷子又参加在鲁院举行的该作研讨会。会上老爷子高度评价了《风暴眼》,我委婉地指出小说对自然的神秘花费笔墨太多,人物略显单薄。
会后,老爷子顺路一定要去我家。喝了几杯小酒,他的谈兴正浓,指着书房的藏书说:“我家没几本书,但我都熟读了,你这一屋子书,读了几本?”劝我一定要认真读书,或会有大出息。但话题最终还是离不开他和沈从文。我把他的作品,如《受戒》归纳为从1930年代逐渐形成的,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具有“诚实、从容、宽厚”特色的“京派”小说。
微醺的汪老,谈锋正健,他如数家珍般,从废名、沈从文到萧乾、芦焚,再到杨振声、李健吾、林徽因,講“京派”小说的发展脉络。我都认真作了记录,后来我把这些内容写进了我的书里。老爷子最后拍着我的肩头,说了句极有分量的话:我守住了‘京派的遗风流韵!”
我想,文学流派,寻根溯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写什么、怎么写。我记得汪曾祺先生在《关于〈受戒〉》一文中,曾郑重地宣称:“我要写,就写美,写人性……”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都始终流淌在美和人性的河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