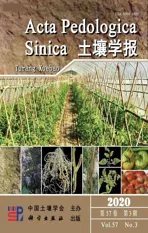生物质炭与秸秆施用对红壤有机碳组分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2020-06-23包建平袁根生董方圆李佳星梁辰飞徐秋芳陈俊辉
包建平,袁根生,董方圆,李佳星,梁辰飞,徐秋芳,秦 华,陈俊辉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浙江省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固碳减排重点实验室,浙江临安 311300)
农田土壤固碳减排是应对全球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促进土壤肥力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持和提升土壤固碳功能,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土壤固碳研究的新问题[1]。我国南方红壤区在粮食生产和固碳减排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红壤区中低产田比例高(占45%),红壤旱地养分贫瘠,生物功能退化,亟需建立瘠薄红壤地力快速提升的固碳培肥措施[2]。秸秆直接还田或制备成生物质炭再还田均是提升土壤有机碳库、维持养分循环及增加作物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之一[3-4]。秸秆易分解,通过秸秆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且其分解过程可能引起土壤氮磷养分的暂时固定,并对土壤有机质分解存在正激发效应,从而增加了土壤 CO2排放[5]。生物质炭是由生物质在完全或部分缺氧的情况下裂解产生的一类含碳量高达60%~85%的高度芳香化物质[4]。研究表明,生物质炭农田施用能影响土壤N2O、CH4等温室气体排放[6-7],提高土壤pH、水分和养分固持,对促进土壤碳库具有较大潜力[8]。陶朋闯等[9]研究发现生物质炭与氮肥配施可以提高旱地红壤中微生物量碳、氮及土壤氮素利用率。张影等[10]报道生物质炭与鸡粪或秸秆配施可以更均衡地提升土壤肥力。然而,生物质炭与传统有机物料的配施研究还比较少,联合施用影响土壤有机碳转化的互作效应还不清楚。
土壤有机碳含量是有机碳矿化分解和合成的最终结果,是影响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但其总量难以全面反映土壤质量的内在变化[11]。土壤有机碳可进一步分为活性和惰性有机碳,前者是衡量土壤有机碳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与土壤呼吸密切相关,而后者在提升土壤碳库和有机质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2]。研究表明,秸秆还田提高了土壤活性碳组分含量及微生物生物量[13]。生物质炭具有丰富的惰性碳,并含有少量易分解的活性有机碳[14],其施加于土壤后可改变土壤有机碳组分,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微生物组成及土壤生物化学过程[15]。一些研究表明,生物质炭添加不仅能显著提高贫瘠土壤的微生物丰度[16],对有机质含量较高的稻田土壤微生物量也有促进作用[17]。土壤酶参与土壤中各种生物化学反应,在营养物质循环和能量代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秸秆还田有助于提高脲酶、过氧化氢酶、蔗糖酶、纤维素酶等土壤酶活性[18-19]。生物质炭添加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已有报道,但还存在一些争议,主要与添加量、酶的种类、生物质炭性质等有关[20],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目前,国内外学者就秸秆还田或不同原料制备的生物质炭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土壤养分和作物产量等的应用效果展开了诸多研究[6-7,9-10]。然而,明确生物质炭的土壤改良潜力,特别是对旱作贫瘠红壤的固碳培肥潜力,需要充分了解其对土壤有机碳组分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以及生物质炭与其他有机物料的相互作用。为此,本项目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秸秆、生物质炭、生物质炭配施秸秆对土壤有机碳组分、土壤碳、氮、磷转化相关酶活性及微生物碳氮底物利用能力的影响,以期为生物质炭农田土壤固碳减排应用和地力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浙江农林大学试验基地(30°15′N,119°43′E),海拔 80 m。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15. 9℃,年降水量1 350~1 500 mm,年日照时数 1 774 h,无霜期236 d。试验地土壤类型属于粉砂岩母质上发育的红壤,较为贫瘠,本试验前闲置。试验地土壤基础化学性质为:pH 4.69,有机碳 4.55 g·kg-1,全氮0.45 g·kg-1,碱解氮 63.10 mg·kg-1,有效磷 1.58 mg·kg-1,速效钾 89.00 mg·kg-1。试验所用材料为玉米秸秆和生物质炭。玉米秸秆自然风干后切碎至1 cm 左右备用。玉米秸秆全碳35.26%,全氮0.92%,碳氮比 38.32。生物质炭在炭化炉 450~500℃厌氧环境下由风干玉米秸秆热解2 h 制备而成,过2 mm筛,备用。生物质炭基本理化性质为:pH 9.30,总碳 42.42%,全氮 1.02%,氢含量 1.98%,硫含量0.26%,碳氮比41.74。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对照(CK,不施用任何物料)、施用玉米秸秆(S)、施用生物质炭(B)、玉米秸秆和生物质炭配施(S+B)4 个处理。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处理 3 个重复,共 12 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6.6 m2。S、B 处理玉米秸秆和生物质炭分别施用10.2和 8.5 t·hm-2(折合 C 输入量均为 3.6 t·hm-2),S+B处理有机物用量为两者之和(折合 C 输入量为7.2 t·hm-2)。于 2017 年 4 月中旬将切碎的玉米秸秆和生物质炭均匀撒在土壤表面,然后用锄头均匀混入0~15 cm 土层。穴播法以30 cm 间距播入玉米种子。为避免肥料施用可能对秸秆和生物质炭效果产生干扰,试验期间不施用化肥或有机肥。
1.3 土壤采集和有机碳组分分析
土壤样品采集于2018 年1 月。在每个小区中按5 点法采集土壤样品,形成一个混合样。土壤过2 mm筛,混匀,分成3 份。一份自然风干,用于土壤基本性质测定;另一份放在 4℃保存,用于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碳源利用能力分析测定;剩余的一份冷冻干燥后保存至-70℃冰箱。土壤pH 采用 pH 计按土水比 1︰2.5 测定,土壤有机碳(SOC)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21]。采用硫酸水解法测定土壤易矿化碳组分I(LPI-C)(主要是来源于植物和微生物的淀粉和半纤维素类物质)、易矿化碳组分 II(LPII-C)(主要为纤维素类物质)和惰性有机碳(RP-C)(酸稳定的有机物,如木质素和单宁酸等)组分含量,具体参考Rovira 和Vallejo[11]报道。
1.4 土壤酶活性测定
土壤酶活性分析采用微孔板荧光法,其原理为利用底物与酶水解释放4-甲基伞形酮酰(4-MUB)进行荧光检测,通过荧光强度的变化反映酶活性[22]。选取的4 种胞外酶分别为:β-葡萄糖苷酶(3.2.1.21,4-MUB-β-D-葡萄糖苷)、纤维二糖水解酶(3.2.1.91,4-MUB-纤维二糖苷)、β-N-乙酰基氨基葡萄糖苷酶(3.2.1.30,4-MUB-β-D-乙酰基氨基葡萄糖苷)、酸性磷酸酶(3.1.3.2,4-MUB-磷酸酯)。括号中的文字分别表示酶学委员会编码和底物。用多功能酶标仪(Synergy™ H1,Biotek,美国)在荧光激发光365 nm和检测光波长450 nm 下测定反应液荧光值。酶活性以 nmol 产物·g-1土壤·h-1表示。
1.5 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测定
利用MicroResp 方法测定微生物基础呼吸和底物诱导呼吸[23]。该方法用原土进行培养,测定的底物诱导呼吸可以反映土壤的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与Biolog 微平板法相比,该方法克服了Biolog 微平板法依赖土壤悬浮液提取物和细胞后续生长状况条件制约,操作简便,反应灵敏。本文选用葡萄糖、苹果酸、天冬氨酸和丁香酸作为典型的碳源底物。碳源的最终添加浓度均为30 mg·mL-1。基础呼吸以无菌水代替底物测定。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8.0 软件以秸秆作为一个因子,以生物质炭作为另一个因子(Biochar),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检验秸秆和生物质炭施用间的差异及互作效应;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Duncan 法多重比较检验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显著性水平设为P= 0.05。相关性分析采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法进行双尾检验确定显著性。
2 结 果
2.1 土壤pH、有机碳及其组分含量变化
与对照相比,秸秆单施显著(P< 0.05)提高了易矿化碳组分I 含量,而对pH、总有机碳、易矿化碳组分II 和惰性碳含量无影响(表1)。生物质炭单施或与秸秆配施显著(P< 0.05)提高了土壤总有机碳和惰性碳组分含量,而对其余碳组分无影响。生物质炭与秸秆配施显著提高了土壤pH(P< 0.05)。双因素方差结果表明秸秆施用对土壤易矿化碳组分I 和惰性碳含量有显著影响(P< 0.05),生物质炭施用对土壤总有机碳和惰性碳组分含量有显著影响;生物质炭与秸秆配施对易矿化碳组分 I 和惰性碳含量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2.2 土壤酶活性变化
与对照相比,秸秆单施显著提高了 β-葡萄糖苷酶活性,而对纤维二糖水解酶、β-N-乙酰基氨基葡萄糖苷酶、磷酸酶活性无影响(表 2)。生物质炭单施或与秸秆配施对4 种酶活性均无影响。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秸秆施用对 β-葡萄糖苷酶和纤维二糖水解酶影响显著(P<0.05),但与生物质炭无互作效应。
2.3 土壤基础呼吸和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变化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生物质炭施用显著(P< 0.05)降低了土壤基础呼吸和微生物对葡萄糖利用速率,生物质炭与秸秆对基础呼吸速率有显著互作效应(表3)。单施秸秆显著(P< 0.05)提高了土壤基础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对葡萄糖、天冬氨酸和丁香酸利用速率,但对苹果酸利用速率无影响。生物质炭单施或与秸秆配施对4 种碳源底物利用速率无影响。
2.4 土壤基础呼吸与土壤碳组分、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和酶活性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土壤基础呼吸与易矿化碳组分 I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惰性碳组分含量显著负相关;土壤基础呼吸与土壤β-葡萄糖苷酶活性呈极显著(P< 0.001)正相关,而与其他酶活性无显著相关。此外,土壤基础呼吸与微生物葡萄糖和天冬氨酸利用速率呈极显著正相关(P< 0.001),与苹果酸和丁香酸利用速率无显著相关性(图1)。

表1 秸秆和生物质炭处理下土壤pH 和有机碳组分变化Table 1 Changes in soil pH and organic carbon fractionation as affected by straw returning and biochar amendment

表2 秸秆和生物质炭处理下土壤酶活性变化Table 2 Changes in soil enzyme activities as affected by straw returning and biochar amendment

表3 秸秆和生物质炭处理下土壤基础呼吸和碳源利用速率变化Table 3 Changes in soil basal respiration and microbial carbon sources utilization rate as affected by straw returning and biochar amendment
3 讨 论
3.1 秸秆和生物质炭施用对土壤有机碳组分的影响

图1 土壤基础呼吸与土壤碳组分、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和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Fig.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il basal respiration with soil carbon fractions,enzyme activities and microbial carbon utilization rate
本研究结果发现秸秆单施显著提高了易矿化碳组分I(LPI-C)含量,而对其他碳组分含量无影响(表1)。易矿化碳组分I 主要为一类来源于植物和微生物的淀粉和半纤维素物质[11]。易矿化碳组分含量的提高与秸秆本身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有密切关系。秸秆腐解过程一方面能释放较多的活性有机碳,一定程度提高土壤易矿化碳含量[24];另一方面能促进土壤微生物活性,促进作物根系的发育及增加根系分泌物,最终产生更多的活性有机碳。生物质炭施用显著提高了土壤总有机碳和惰性碳含量,而秸秆施用对两者无显著影响,这与王梦雅等[25]报道的结果较为一致。这是由于生物质炭含有丰富的芳香性碳组分,难分解,可长期促进土壤惰性碳含量[26]。与单施生物质炭相比,秸秆与生物质炭配施对土壤有机碳含量无显著影响,说明秸秆对土壤有机碳积累的贡献率较低。原因可能与秸秆易被微生物矿化分解,分解产物在较短时间内难以转化成稳定的碳有关。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秸秆还田可引起正激发效应,可能加速消耗土壤有机碳含量[5],有必要利用同位素标记技术作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发现生物质炭和秸秆配施具有显著的互作效应,降低了土壤易矿化碳组分含量,可能与生物质炭的易矿化组分、孔性结构和吸附能力有关。Lu 等[27]研究表明,生物质炭的多孔结构具有较高养分和可溶性碳吸附能力,导致土壤易分解有机碳含量较低。生物质炭也具有少量易分解碳组分,可促进土壤易矿化碳组分分解,即产生正激发效应[14]。此外,较多文献报道生物质炭施用提高了土壤pH,具有较好的酸化改良能力[28],这是因为与秸秆等物料相比,生物质炭具有较高的pH 和灰分含量,能中和土壤酸性。本文生物质炭单施对 pH 无影响,可能与生物质炭的施用量较低有关。因此,生物质炭与秸秆配施有助于提升土壤有机碳库和改善土壤酸化。
3.2 秸秆和生物质炭施用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主要来源于微生物,反映了土壤中各种生物化学过程的强度和方向,酶活性大小是土壤中物质代谢旺盛程度的重要指标[29]。本研究所检测的4 种酶与土壤碳、氮、磷循环密切相关。秸秆施用显著提高了β-葡萄糖苷酶和纤维二糖水解酶活性。与此相似,曹湛波等[30]通过田间试验发现玉米、黄豆、水稻等秸秆还田显著促进了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加了土壤微生物量以及β-葡萄糖苷酶和脱氢酶活性。β-葡萄糖苷酶和纤维二糖水解酶是纤维素分解酶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纤维素降解的关键酶,是影响还田秸秆分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秸秆还田后,土壤中微生物可利用的碳源物质,尤其是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类有机物的增加,可促使土壤微生物分泌更多的碳转化相关酶。范淼珍等[31]对祁阳旱地红壤长期施肥实验研究发现,单施粪肥和粪肥与化学肥料混施显著增加了β-葡萄糖苷酶、纤维二糖水解酶等活性。Elzobair 等[32]通过 1 年的田间试验发现木片生物质炭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β-葡萄糖苷酶、纤维二糖水解酶等酶活性无影响,而猪粪施用显著提高了酶活性。本研究发现生物质炭施用并未显著影响β-葡萄糖苷酶、纤维二糖水解酶、酸性磷酸酶及β-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推测原因可能是生物质炭本身难降解,易分解组分含量低,并不能作为长期促进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可利用底物,从而无法诱导土壤酶活性提高。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生物质炭的孔隙结构通过吸附底物或酶,可能会阻碍酶活反应[20]。Wang 等[33]通过微孔板荧光法发现低浓度(0.5%质量比)的生物质炭添加量促进了β-葡萄糖苷酶、α-葡萄糖苷酶和纤维二糖水解酶活性,而高浓度反而抑制了上述酶活性。Bailey 等[20]认为酶活性变异取决于生物质炭的孔隙结构和活性表面对酶和底物的吸附能力。因此,生物质炭施用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3.3 秸秆和生物质炭施用对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及基础呼吸的影响
土壤呼吸是陆地生态系统土气交换的重要途径,是土壤碳库输出的重要方式之一。土壤基础呼吸表征土壤有机碳分解状况,也是微生物活性的重要反映,与底物质量、微生物功能和酶活性密切相关[34]。王梦雅等[25]研究表明单施秸秆后土壤呼吸速率明显大于单施生物质炭处理,而生物质炭与秸秆配施的CO2排放低于单施秸秆,与本研究结果较为一致。酶活性和呼吸作用降低可使秸秆分解缓慢,两者强度与底物的可利用性有关。秸秆施用增加了土壤易矿化碳组分,为微生物活动提供了底物,促进了土壤活性碳库的矿化。Lu 等[27]发现生物质炭及其与氮肥配施降低了土壤呼吸,引起了负激发效应,其原因归结于生物质炭吸附并保护了土壤中的可溶性碳组分。本研究中土壤基础呼吸速率与易矿化碳组分(LPI-C)含量成极显著正相关,故印证了这一解释。如上所述,β-葡萄糖苷酶是降解纤维素β-1,4 糖苷为葡萄糖的关键酶,与土壤有机碳分解和土壤呼吸密切相关。本研究中土壤呼吸与β-葡萄糖苷酶显著正相关也支持了上述观点。Ameloot 等[35]认为,生物质炭在土壤中存在1~2 年后可以与土壤有机质及矿物形成稳定复合体,保护有机质被微生物和酶分解,从而降低土壤有机碳的矿化。由此推测,生物质炭与秸秆配施后土壤基础呼吸速率相对于单施秸秆处理低,也可能与生物质炭对易矿化有机质的保护作用有关。本研究发现土壤基础呼吸速率还与土壤微生物对葡萄糖和天冬氨酸的利用速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土壤基础呼吸除了与底物质量和酶活性有关外,还与微生物的底物利用速率有关。单施秸秆处理具有最高的葡萄糖、天冬氨酸和丁香酸利用速率,表明秸秆施用不仅促进了土壤微生物对易分解底物的利用速率,也对难分解外源底物利用有促进作用。这可能与秸秆易降解,其缓慢持续降解释放的可利用碳水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促进了微生物活性有关。与秸秆等相反,生物质炭对微生物底物利用速率无影响。Chen 等[36]利用 Biolog 微平板法测定土壤微生物的底物利用能力,发现小麦秸秆炭施用短期内提高微生物对酚酸类的利用速率。推测生物质炭对微生物碳源利用速率影响可能与生物质炭的类型及施用时间有关。
4 结 论
短期内单施秸秆提高了土壤活性有机碳库,促进了土壤基础呼吸速率,但对土壤总有机碳提升作用不明显;而生物质炭及其与秸秆配施能促进土壤总有机碳和惰性有机碳含量,降低土壤基础呼吸,相比秸秆直接还田更有助于土壤固碳减排。秸秆施用促进了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对碳源底物利用速率,而生物质炭对其无显著影响,这与秸秆和生物质炭本身的降解性和化学性质有密切关系。秸秆与生物质炭处理下土壤基础呼吸变化与土壤碳转化酶活性及微生物对碳水化合物的利用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