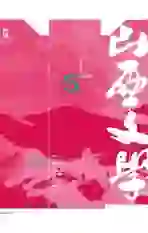记忆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2020-06-22吴佳骏
火
倘若不发生那场大火,小街的每个夜晚都是相同的——月光温柔地照亮铺着青石的路阶,屋顶上的残瓦蒙着一层夜露。风在左右两边的山崖上奔突,惊恐的猫躲在篱笆后面的草窝里哀鸣。伴着猫的哀鸣的,还有三条或五条狗的狂吠。它们的声音极具威慑力,能让在黑夜里醒着的一切胆战心惊。猫和狗,都是小街上的更夫。那些蜷缩在床上的人,只要听见更夫们的叫声,便知道今夜又将是一个平安夜,可以一觉睡到天明了。
然而,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就连人类都无法保护好人类,又怎能将人类对平安的期许寄托在那些弱小的动物们身上呢?待小街上的人悟透这个道理,已是在那场大火之后了。那是几天前的夜里。晚饭后,人们照例上床很早——对于一条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再也看不见有人聚集在院坝上仰望星空,谈论雨水和节气,聆听虫鸣和蛙声的寂寞的小街来说,不上床睡觉还能干什么?那夜一样有温柔的月光,一样有风在山崖上奔突,一样有猫的哀鸣和狗的狂吠。蜷缩在床上的人仍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们在梦里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打铁,有的磨刀,有的唱歌,有的放哨;还有的背着小孩在河边洗衣服,或叼着烟杆蹲在大树底下听报告;更有的在跟死去的亲人谈判,在哭喊着跟自己的疼痛和解……这些梦有旧梦,也有新梦。旧梦大多是黑色的、白色的和栗色的;新梦大多是粉色的、黄色的和蓝色的。他们就这样在色彩的包裹中沉睡着,而将梦之外的世界统统交给了值更的猫和狗去看护。那些猫和狗是十分忠于职守的。它们分别在上半夜和下半夜巡逻之后,也都疲倦地睡去了——它们已经用声音宣告了夜的平静和安全。但令猫和狗和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有间老房子失火了,一片火光冲天而起,照亮了整条小街。值更的猫和狗惊慌失措,拼命地狂吠,试图喊醒睡梦中的人们。可那些多彩的梦实在太缠人了,任凭猫狗们喊破了嗓子,也没能将他们从睡梦中催醒。眼看火势越燃越大,猫和狗都被吓慌了——它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灾难——它们料定再也拯救不了小街上的人,索性不再声嘶力竭地叫喊,纷纷逃命去了。后来,还是一个起床小解的孩子,看到外面通红的火光,才匆忙叫醒了熟睡中的大人们。他们拖着老迈的身躯,拼尽全力去扑火。遗憾他们太力不从心了,根本靠不拢边,只能远远地站定,露出恓惶和颓废的表情看着那间房子慢慢化为灰烬。幸运的是,那房子并未与街上其他的房子相连接,而是单独建造在靠河边的一块瘠地上,才未使火势继续扩散和蔓延,造成更大的悲剧。
天在大伙的议论和喟叹声中放亮了,小街上到处都落满了暗黑色的焦灰。从县城迟迟赶来的消防车停在废墟前,闪动的红蓝色警示灯让人心悸。消防车的后面,是一辆白色的警车。它那警报器发出的响声,比消防车的警报声还要嘹亮,还要刺耳。围观的人都屏住呼吸,空气也顿时凝固了,仿佛有一出好戏马上就要开场。随后,从警车上走下来两个警官。一番盘问之后,其中一个警官掏出手铐,将藏在人堆里的一个双目失明的花甲老人拷走了。那一刻,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夜的那场大火是那个盲人干的。
警车和消防车开走后,新的一轮议论爆发了。人们议论的焦点,自然从老房子转向了那个“盲人纵火犯”。据一个平时跟盲老人走得最近的另一个老人回忆,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发现了盲老人的异常——他特别怕见到火。就是平时煮饭和点烟时,他都会被火光吓得瑟瑟发抖。于是,人们大胆猜测,他在弱冠之年故意刺瞎自己的双目,大概也跟怕火有关。
事实上也没错,那个盲老人的怕火确凿是有缘由的。那时,他还只是个孩童。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然的一天,他那当厂长的父亲被几个魁梧的壮汉给绑走了。他哭着追出去,想把父亲拽回来。可没有人理睬他的咆哮。他看见壮汉们先是将他父亲的半边头发剃掉,又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着墨字且打了红叉的纸牌子。然后,再将他拖到戏台上,双膝跪下,不停地揍他,捶他,踢他。他觉得父亲是个好人,并没有犯错,想不通那些可恶的人为何要那般对待一个本分人。那天上午,他一直守在戏台下。他以为他们羞辱完父亲后就会放他回家。谁知,那天下午,那几个壮汉又将他那奄奄一息的父亲拖到野地里,扒光了他的衣裤,将其周身都抹上稀泥,点燃稻草像烤红薯般慢慢地烘烤。直至将稀泥烤干后,再一块一块从他父亲的身上揭下来。整个过程,他的父亲都在尖叫、呻吟。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死掉了。留给他的,除了悲痛和恐怖,还有一片血似的火光。从那以后,他便开始怕火,几乎夜夜都梦见他的父亲在火堆中惨叫。
听了那个老人的回忆,小街上的人突然对那个盲老人生出几分怜悯和宽恕。但他们实在想不通,一个因火而患上后遗症的人,又怎么会去纵火呢?而且,他又为啥要在踏上警车时抛下那句话:“等着吧,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条小街。”这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凳
每天的向晚时分,他都会坐在小街的那条石凳子上,等待黑夜的降临。石凳子的旁侧,生长着一棵皂荚树。那棵树已然很老了,树干的一大半边都失去了水分。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爬到树上去眺望远方。每次爬樹,他都能感觉到树的水分在流失。他将这个秘密告诉在树上筑巢的鸟儿,劝它们迁徙到小街后山的更加繁茂的树上去定居。可那些鸟儿根本不听他的话,仍旧年年都飞来繁衍子嗣——它们比他还离不开这棵树。
几十年过去,现在的他跟那棵皂荚树一样老了,他身体里的水分也已流失,像血液一样流失。他再也爬不上树,对远方也失去了兴趣。他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坐在皂荚树下的石凳子上,成为一个让时间打不败的“常胜将军”。
大概是他坐的日子太长了吧,以致小街上的人都称呼他为“树中的老人”。树是他的灵魂,他是树的肉身。只要他们靠在一起,时间仿佛就是静止的,光阴就会停止流转。他和树都是小街上的孤独者。孤独者唯有孤独可以依靠。这不是残忍,而是规律和宿命。不管是树是人还是别的什么,都无法逃脱这规律和宿命,就像孤独无法逃脱孤独的幽禁、围剿和追杀。
那条石凳子是见证了树和他在孤独中的相互依偎的——它是孤独的第三者。仿佛它的存在,本就是为了接待他和他的孤独。向晚的风吹着逐渐来临的夜色。他坐在石凳上,用拐棍不停地敲击皂荚树的躯干。他每次都是以敲击的方式来替代抚摸。他知道树不会再疼痛,故敲击得十分用力。可从内心来说,他又极其希望树能感知到疼痛。有感知就说明树是醒着的,还能吸收到水分、空气和阳光,还能感觉到他这个老伙计的存在。如此一来,他的敲击就变成了召唤和祈福。梆梆梆的敲击声擦着夕阳、云朵和晚风,也擦着记忆、年轮和哀悼。敲过一阵之后,他必然会对树展开滔滔不绝的诉说——在他的认识里,这棵皂荚树就是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病重的友人。他企图以回忆往事的方式,来帮助它重新长出绿叶。他从最最遥远的往事讲起——那时候,他还只是小街上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贫穷使他如一只燕子,只能在黄昏的边沿低低地、孤单地、迷惘地乱飞。他多次挣扎着想像其他鸟雀一样飞高飞远,但他的稚嫩的翅膀上总是粘满了煤灰和雾水,稍稍振翅,就会撕裂出血滴。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青春被染成红色,孤苦难耐的时候,他就爬到皂荚树上去,用眺望去抵达他在现实中无法抵达的远方。每次上树,他都会摘下一片树叶作为眺望远方的纪念。他房间的那个旧木抽屉里,藏满了大大小小的树叶。遇到阳光静好的天气,他会手拿那本当时唯一的,也是他最心爱的书跑去树底下反复地、忘我地阅读。他使用的书签就是他摘下的树叶。有时,他读得困倦了,浓浓的睡意征服了他,他就靠在树干上呼呼地打起鼾来。在睡梦中,他看见自己被一张巨大的树叶托着,在苍穹上漫无目的地飞翔。而那从书页里散落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方块字,印满了天空的肚皮。这一幕,被他那干活回家的父亲看到了。他的父亲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却是小街上著名的石匠。他喜欢看儿子捧着书睡着的样子,也心疼儿子被树荫遮蔽住的窘相。那之后不久,他的父亲便凿出一条石凳子,安放在了皂荚树的下面。从此,他也就开始坐在那条石凳子上读书和遐想,顺便聆听树上的鸟鸣,观察树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有一天下午,他竟然清晰地听到皂荚树在嘤嘤地哭泣,哭声跟他那本书中的女主人卖掉女儿时的哭声酷似。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从未听见树哭过,心里非常恐慌。他曾将这个发现讲给树上的鸟儿听,讲给刮过树梢的风听,讲给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听,可它们都没当回事,将他的诉说当作一个无知孩童的天真的谎言。他想给树一点安慰,就天天跑去坐在石凳子上陪着树。哪知道,他这一坐就坐了几十年,把自己从一个年轻小伙坐成了一个耄耋老人。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他的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姐姐离开了这个世界,连他的弟弟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他在送走一个一个亲人们的时候,他其实也在一天一天送走这棵树。一家人在树底下生活久了,家中的每个成员也都成了树的一部分,都是从树干上长出来的枝丫。因此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棵树的死亡。
他还在继续着他的回忆。他企图以回忆的方式来帮助一棵病重的树生长出绿叶。只是他也已经很老很老了,而他的回忆太多又太漫长,他没有把握能否支撑到将回忆全部讲完的那一刻。他和树都是孤独的。孤独者唯有孤独可以依靠。这不是残忍,而是规律和宿命。讲着讲着,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像幼年时一样坐在石凳子上睡着了。黑夜已经降临。在他那或许醒来或许再不醒来的梦中,他终于把自己挂在了树上,把孤独挂在了树上,把死亡挂在了树上,把永恒挂在了树上。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树中的老人”。
椅
那间逼仄的、阴暗的房屋坐落在小街戏台的旁侧。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随便站在屋中的任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节奏铿锵的锣鼓声和婉转多情的唱戏声。也就是说,住在屋中的人即使不出门,也能感知世态炎凉,体察生、旦、净、末、丑的悲辛。听罢了戏,将房屋的后窗打开,还可一边眺望对面黛色的远山,一边继续聆听窗下河沟里潺湲地流淌的水声。这种闲适的、有味的日子是令人怀念和憧憬的。只可惜,那座上演过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的戏台早就废弃了,窗下日夜不息地流淌的河水也早已干涸,如今唯剩下这间老屋子,还在挽留着遥远的记忆和易逝的光阴。
或许在许多人眼里,这间房原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整条小街上,像这样装满了回忆的老房子还有很多,但问题恰恰也就出在这里。当很多装满回忆的老房子都没人住了,关了门窗了,唯独这间老房子的门却一年四季都开着。开着也不全开,两扇木门只开一扇,另一扇关着。这致使仍旧住在小街上的人们都在猜测,它关一扇门到底何故呢?是想挡住些什么吗?想挡住白昼和长夜,日光和月光;还是想挡住时间和冷风,孤独和落寞?
没有人能够猜得透彻。越是猜不透彻,人们就越是觉得那间老屋子的神秘。因了这神秘,凡是从这间老屋子门前路过的人,都习惯性要扭头朝那半开着的门里瞅。瞅过之后,又都非常失望。因为那间屋里除了摆放着两张旧藤椅外,什么也没有。两张藤椅,其中一张的四条腿上缠满了红布条,另一张的四条腿上缠满了白布条。天光从屋顶上镶嵌的亮瓦照进来,落在两张安静的藤椅上,有一种古旧之美。可极少有人会对这种正在消逝的美生发出兴趣,大家都被繁琐的、庸俗的、不堪的日常生活裹挟得麻木了。只有小街上的几个小孩子还保持着人性原初的那份天真和好奇。当那些朝门里瞅过后的大人们全都败兴而去时,他们仍旧守在那扇半开着的屋门口,痴痴地凝望着那两张旧藤椅出神,像一群小天使殷切地期盼着圣母的降临。他们知道,那两张藤椅会带给他们好运。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开始围着那两张藤椅转了。这几个小孩都坐过那两张藤椅,轮流地坐,翻来覆去地坐。他们坐在藤椅上,好似中国那位叫溥仪的末代皇帝登基时坐在龙椅上,受到了最高级的礼遇。这将是他们终身难忘的大事。而赐予他们这种待遇的,则是那两张藤椅的主人,也是那间老屋子的主人——一个拄着拐棍,脊背伛偻,脸色苍白,眼神充满忧郁的老妇人。这个老妇人性情乖戾,长期一个人生活在这间屋子里。她的老伴儿在十年前就去世了。她生育的五个子女也都各自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平常她是基本不出来抛头露面的,要么躲在里屋靠窗的木床上睡觉,要么盘腿坐在木床旁边的蒲团上,对着桌上那尊已被檀香熏得面目模糊的观音像念经。她不是个佛教徒,也不在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吃素。但她一直坚持念经,很早就开始了。她说念经就是积德,可以让自己今后在面对死亡时获得安宁,不那么痛苦,并顺利找到一条通往天国的路。除非是在孩子们前来光顾的时候,这个老妇人才会从睡眠中醒过来,或者终止她的念经,手拿一串佛珠,拖着迟缓的步子走出来。那无疑是她最高興和幸福的时分——就连睡眠和诵经也无法给予她的一种祥和的感觉。见了孩子们,她照例先坐在一张藤椅上,然后再叫其中的一个孩子坐在另一张藤椅上,便开始了她的讲诉。半个小时过后,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糖果递给藤椅上坐着的孩子作为奖赏。然后,再换另一个孩子坐到藤椅上来,接着听她的讲诉。她讲诉的内容每次都是重复的——无非是一个女人的爱恨、波折、忧伤、失落、疼痛和衰老。这些深奥的内容孩子们全都听不懂,但他们仍然会耐着性子听她的唠叨,因为她奖赏的糖果实在是太甜了。这个老妇人就这么在孩子们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下午时光。
老妇人想,自己大概是可以在孩子们的倾听中终老的了。但突然的一天,那些孩子们不知是找到了别的乐趣,还是统统长大了,再也不愿到那间老屋子里去接受她的欺骗。老妇人变得不安起来。她再也睡不着觉,诵经的心思也淡了。她每天下午都坐在藤椅上等那几个孩子的到来。她的衣兜里时刻都装满了糖果,却再也没有奖励出去一颗。
也不知这样过了多久,三个月还是半年,有人发现老妇人终于找到了新的听众。它们比那些孩子们更尽职,更忠诚。不但下午去,就连上午它们也甘愿蹲在藤椅上聆听老妇人的讲诉。而且,它们还从不领取奖品。这批新的听众,有时是一只小狗,有时是一只小猫——它们在小街上流浪得太久了,没有家,没有归宿。它们都很感激这个老妇人收留了自己,给了它们这种卑贱的、遭人排挤的、受人歧视的小生命一把宽宽大大的交椅。有了它们后,这个老妇人的诵经声重又响了起来。这间逼仄的、阴暗的屋子总算是多了一缕若隐若现的生机。
石
他也许再也实现不了那个梦想了。他已经尽力了。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冬天,他都在为追逐这个梦想奔波着、劳苦着、焦虑着。他的脚上、肩上、头上都落满了太阳的芒刺和霜雪的颗粒。他的睡眠里、想象里、心灵里也都飘满了叹息的粉末和失望的灰烬。在他活过的几十年光景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默默地伫立在小街的一座垮塌的房屋前,发出一声揪心的浩叹。他搞不清楚,人活一辈子,想要实现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为何就那么的难呢?
许多许多的人都在嘲笑他——嘲笑他不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匠,却终年怀揣着一个建筑师的想法。但他不怕嘲笑,也从不将他人的嘲笑放在心上。谁说小人物就不该怀揣梦想?谁说一个石匠就不能建造一座宫殿?况且,他的梦想并不是真要建造一座像故宫那么庞大,那么豪华,那么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在他居住的小街上建造一个坚固的、隐蔽的、永不坍塌的城堡。倘若这个城堡真能建成,他就没有枉做一世的石匠,他就可以安心地待在城堡里守住这条小街,并与这个城堡一起成为小街最后的标志和记忆了。
看得出,他是一个好石匠。这条小街上的不少房屋都是他曾经参与建造的。他是一个老实的、有职业操守的手艺人。在替任何人家修造房屋的时候,他都是当作自己的房屋来修造的。他将自己的热情、真诚、信誉全都倾注在了一锤一錾上。只要见到经过自己的手敲打出来的石头给他人带去了家的温暖,他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巨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因此,他曾是小街上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各家各户都记挂着他的恩情。除建造房屋外,他还替人凿水缸、石磨、凳子和碾盘;也替人凿佛像和墓碑。他对这条小街充满了浓厚的感情。他也见证了这条小街的兴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滋生梦想。他每天都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来思考梦想的事。把每一块石头凿好,把每一家人的石工做好,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但时代说变就变了,记不得是从哪一年开始,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做石工活儿的邀请。谁家的水缸破了,都跑去商店里买塑料桶来替代。石磨和碾盘也没有人使用了,手工豆腐都改成了机器生产。一夜之间,他沉寂下来,小街上再也听不到他凿打石头的叮当声了。他从小街上走过,也极少有人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他昔日的辉煌和荣耀,受到的尊敬和爱戴,都随着他的生锈的锤子和錾子成为了时代的遗物。只偶尔在有月光的夜晚,他会一个人偷偷地将锤子和錾子拿出来在小街上敲来敲去,像一个过时的打更人。听到他敲打出的声音的人,没有一个不讨厌他,骂他打扰了小街的宁静和人们的清梦。脾气火暴的人,直接开门朝他泼水,扔石子;脾气柔和的人,背地里唆使狗去咬他,唆使鸡去啄他,唆使猫去挠他。他拖着凄清的影子走在狭长的街巷上,月亮照着他的身影,也照着他的落寞和孤寂。他没有理会人们的凌辱,默默地敲打着,踽踽地行走着。他原本就不是敲打出响声来给那些羞辱他的人听的,他是专门敲打给他曾经凿打出的那些石头听的。那些石头,就镶嵌在小街上的人家的地基里,墙壁上,院落中。他想念那些石头了,那些承载着他的体温、年岁和美好的石头。他相信那些石头也一定想念他了——是他将它们从山上劈凿出来,给人遮风挡雨,防贼防盗的。他使石头有了被人类高看一眼的价值。可现在不一样了,石头和他都受到了人们的冷落。小街上的人家几乎快搬空了。即使仍有愿意住在小街生活的人,也都将原来用石头垒砌的旧房子拆掉了,从城里运来红砖重新建了新房——用红砖建造的房子那可是比用石头建造的房子漂亮多了。就连石匠本人也都为那些新房着迷,也都想替自己建一座新的砖房。他那已经做了砌砖匠的儿子见他整天萎靡不振的样子,多次劝他也改行去做砌砖匠——那可是比他以前做石匠划算多了。他们父子之间为此而不断地争吵、赌气、埋怨。他也的确因此而反思过、动摇过、妥协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做一个守旧的人。他的儿子见他冥顽不化,抱残守缺,在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决绝地跟随一个建筑队去了远方,至今都没有回来看过他。
也正是从他儿子走后,他有了建造一个城堡的梦想。他想去将那些他曾经辛辛苦苦凿打出,如今却被人们抛弃了的石头聚拢起来,统统用于建造城堡。最近一年多时间,他一直在做着这件苦差事。他焚膏继晷地如同蚂蚁或蜗牛一样搬运着那些残碎的石头,以至于人们一见到他受刑的模样就发笑。但令他十分意外的是,不知是那些石头可怜他已年迈,且同情他的受辱,还是明白一个属于石头的时代已然过去,都从他的背上朝地下滚。他搬运一次,石头就滚落一次。为这事,他还特别去找过那些被他凿成佛像和墓碑的石头,他认为它们是见过生死的,一定会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然而,那些佛像前早就断了香火,那些墓碑也早已被荒草掩埋。他瘫坐在地上,流着眼泪悲哀地想——一个普通石匠的梦想是再也难以实现了。
瓦
许多年过去了,他仍收藏着那些记忆,梦一般的记忆。无论是在落日熔金的傍晚,还是在细雨飘窗的夕暮,只要他倚靠着那把黄杨木做的沉重的椅子坐下来,叼起那根跟了他大半生的长长的竹烟杆,不紧不慢地点燃烟锅里的烟叶的时候,那些遥远的、缤纷的记忆就会伴随烟草燃烧的红光和缭绕升腾的烟雾纷至沓来,一层一层又一圈一圈将他缠绕、包裹和覆盖。
长久以来,他都靠这些记忆活着,安度晚年。若非如此,他不知道还能有别的什么方法可告慰他作为一个烧瓦匠的一生。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光是在跟青瓦打交道,跟小街上的那个瓦窑打交道。烧瓦镀亮了他的前半生,也镀亮了他前半生的贫穷、苦寂和荒寒。他一直在回想他第一次烧瓦是什么时候,十岁或是十二岁?他被爷爷和父亲领去瓦窑烧瓦。那应该是盛夏时节,知了躲在瓦窑不远处的柏树、桉树和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等叫过那几天,它们就会死去。故知了的叫声既是赞歌,也是哀歌。就在这赞歌和哀歌的双重喧扰中,他看见赤臂裸身的爷爷和父亲,正汗流浃背地将一片片已被太阳晒干的泥瓦坯朝窑里放。那个窑子很大,不但能装下上千片的瓦坯,还能装下一个家族的梦想。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淡褐色的瓦坯看,竟意外发现那些瓦坯的颜色跟他爷爷和父亲肉身的颜色一个样——瓦坯来自于泥土,他的父辈也来自于泥土。这个发现让他悲伤,他觉得人活一辈子,就是一个不断地将泥土变成瓦的过程。他已经垂老的爷爷是这样,他正在垂老的父亲是这样,他的未来也必然会是这样。或许在他爷爷和父亲的眼中,他本来就是一片未烧的瓦。他们之所以带他来到窑前,其目的却是要将他这片瓦坯投放到窑内去进行焚烧、塑形,增加他人生的硬度。于是乎,就在那个夏天,那个知了唱着赞歌,也唱着哀歌的夏天,他第一次烧起了窑火,第一次见证了瓦坯如何蜕变成瓦的全过程。
许多年过去了,他仍收藏着那些记忆,梦一般的记忆。他清楚地记得每次瓦烧成后出窑时的情景。窑内熊熊燃烧的大火熄灭了,冷却了。一片又一片大小均等的青瓦被爷爷和父亲从窑里取出来,码放在旁边的草坪上。这时,他最喜欢用手指去弹弄那些瓦片,清脆的响声带着火焰的咆哮,可以穿透沉闷的、枯索的黄昏,或击退因长时间烧瓦而积聚在体内的困顿和疲乏。待出完窑,爷爷和父亲都累了,安坐在瓦堆上抽烟,彼此都不说一句话。夕阳照着他们清癯的面孔和古铜色的脊背,俨然照着两尊刚刚烧制出窑的地藏菩萨。第二天黎明,初升的朝阳甫一照亮大地,那些或挑着筐,或背着篓,或赶着马前来买瓦的人就陆续到达了。往往日落时分不到,满草坪的瓦就会被搬得一块不剩。整条小街没有哪户人家的屋顶上没有盖着他们烧出的青瓦,就连其他村镇的人家,也跑来买他们烧制的青瓦去盖房。那些坚硬的瓦替无数人家挡住了骄阳、风雨和霜寒;也替无数人家挡住了贫病、疼痛和忧伤。
他从来以为,他们一家三代都将成为用窑火焚烧日月到老的人,都将成为用窑火替他人送达幸福到老的人。但遗憾的是,时代终究改写了他们烧窑的历史,也到底修正了他日后收藏的记忆。不知是在他爷爷死去的第五年,还是在他父亲死去的第三年,他坚持焚烧的窑火永久地熄灭了。没有人再来买他烧制的青瓦。小街上大部分人家的屋顶都换成了宽大的、光滑的、美观的琉璃瓦。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靠记忆活着。他几乎天天晚上做梦,梦见熊熊的烈火焚烧了房梁,焚烧了大地,焚烧了他爷爷和父亲的遗像。梦醒之后,他将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境告诉给小街上曾使用过他们烧制的瓦的人家,劝他们继续使用自己烧的青瓦,且不会收取一分钱。他想以哀告的方式,驱逐纠缠着他的噩梦,并成全他把熄灭的窑火再点起来。然而,没有人可怜他,同情他。他骂他们全都是些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的家伙。其中只有两个年龄跟他一般大的人,明确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却最终又都被这两个人的后代阻止了。他深深地觉得,这条小街变了,这条小街上的人变了,甚至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了。但他心里又十分清楚,他阻挡不了、也改变不了这个时代变革的洪流。他只是一个过时的、年衰的、心中尚存几缕旧梦的烧瓦匠。
现在,他只能靠从前的记忆来安度晚年了。无论是细雨飘窗的夕暮,还是落日熔金的傍晚,他都习惯性在那张黄杨木做的沉重的椅子上坐下来,颤抖的手拿着一根長长的竹烟杆,一边吸烟一边梳理他收藏的那些记忆,梦一般的记忆。没有人去打扰他,也没有人去可怜他,同情他。谁也不知道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多少年。大家唯一知道的是,那把椅子是他祖上传给他爷爷,他爷爷又传给他父亲,他父亲又传给他的。那么,他又该传给谁呢?他的记忆吗?他和他的记忆都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他那烟锅里燃烧的烟草熄灭了。他拿烟杆的手垂了下来。
【作者简介】吴佳骏,青年作家,红岩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出版著作有《雀舌黄杨》《生灵书》《谁为失去故土的人安魂》《草堂之魂》等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