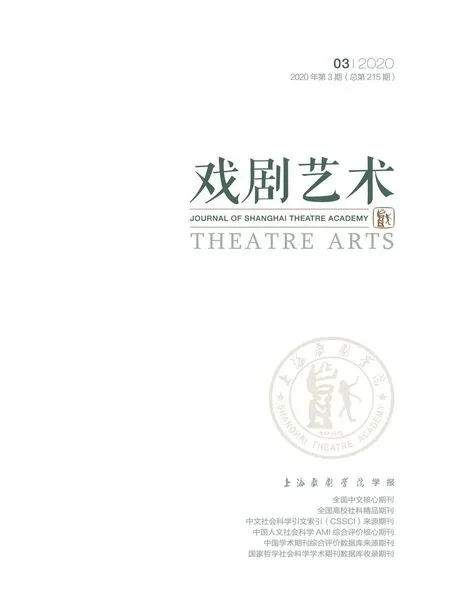再造“地方”:新的文化治理视域下上海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
2020-06-18杨子
杨 子
伴随“全球化”对城市地景的渗透,对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的探讨在多个学科领域与知识范畴内被广泛展开,诸如地方(place)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些人文地理学范畴的关键问题,成为其中的核心议题。
就表演场景而言,城市文化空间正逐步被批量生产的“迪斯尼”式的商业表演文化所占据。 以上海为例,由英国“Punchdrunk”剧团创作、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制作呈现的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于2016年登陆上海,引领中国大陆“浸入式”戏剧的文化风潮,自2016年11月11日预演到2019年12月13日,连续演出917场,观众人次逾30.3万,累计销售金额逾1.98亿元,总收入2.71亿,平均上座率超过95%,平均复购率超30%,创下1分钟最快售出216张、1小时最快售出1847张、夏季场6小时售罄12,600张的票房纪录,年度票房销售率一度高达100%。(1)“演界”公众号 :《“SMG Live”中国沉浸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9年12月15日。
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全球表演文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成功的市场占有率,也带来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浸没式剧场兴起、迪斯尼乐园和百老汇超级音乐剧批量生产填充城市剧场时,非地方性景观(全球景观)提高了存在的表象作用,“迪斯尼化”的表演场景在将历史、神话、现实和幻想进行超现实组合时,也进一步与所在地环境脱离。(2)(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如《妈妈咪呀》《猫》《狮子王》《剧院魅影》等超级音乐剧通过授权方式,在全球各大城市重制与原版几乎一模一样的演出,让全球戏剧市场充斥着同样的节目,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剧场经济的市场也向全球化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剧场保守主义和同质化的结果。(3)Jen Harvie, Theatre & the City(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70-71.全球城市的运行逻辑实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面对席卷而来的全球主义文化均质化的运行,我们的确看到传统意义的“地方”及地方性文化的消逝、文化特殊性的丧失等“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4)转引自陈全荣,刘渌璐 :《地方感研究文献评析》,《设计学研究》,2018年第1期。See Relph E.(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问题的发生,以及全球化背后新自由主义经济试图通过文化和资本重新定义和建构新的“地方”。
在诸多解决全球化“无地方性”的方法论域中,“地方感”的建构往往成为一条抵抗路径。在人文地理学家看来,作为特殊性的“地方(place)”是“适合所有事物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各得其所(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5)蒂姆·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 :《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63页。,也即“我心安处”,地方和地方感仍然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6)Maria Lewicka,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31, Iss.3,(2011):207-230.。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段义孚为主要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家对人地关系及地方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当某一个地点(locality)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人们停驻在那里,使得它成为感觉的价值中心,地方感的形成就得以可能。(7)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138.地方感是在人与地方相互作用下,由地方产生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8)转引自陈全荣、刘渌璐 :《地方感研究文献评析》。See Steele, F.(1981), The Sense of Place, Boston: CBI Publishing Company, Inc.,反映了人对于地方的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主张人们通过想象建构“共同体”国家,在段义孚看来,在地方感的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就是人们对一个“大地方”注入情感(9)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 p.18.,因而,从更大的层面出发,人们可通过地方感的建构,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作为地方性文化,戏曲高度凝聚了一个地方的语言、文化、历史、民俗、民族特质和风貌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发达造就了成熟的文化经营体制,为移民占总人口80%以上的市民阶层开拓了文化娱乐市场,这使得各种地方戏曲在上海都有生存空间。如淮剧、越剧、甬剧、扬剧、锡剧等诸多地方小戏进入上海后发展成为独立的戏曲剧种(10)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第18页。,戏曲演出场所林立,以戏曲、电影、话剧等文化形态为核心的文化娱乐产业发展盛极一时。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令上海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和远东第一大城市,近代上海的全球化发展肇始于此一时期。1990年,以开发浦东为契机,上海重新开始打造“国际大都市”的全球化征程。2016年,新的城市发展规划计划于2040年将上海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及文化大都市,发展模式由外延式增长向内生发展型转变。“全球城市”的形象如何塑造,“文化大都市”的定位如何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增强城市精神风貌的吸引力?在去地域性的全球城市发展中,以戏曲为代表的地方性文化如何在“无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11)(美)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7-302页。的、或曰地方性日益被消解的全球都市空间中重建地方感,本文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以上海戏曲演出主体为例,从新的国家文化治理政策、戏曲剧场的布局与空间实践、表演主体的艺术生产实践等角度,探讨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也即以都市戏曲为代表的地方性文化如何通过调整与再造“地方”,在全球表演场景中重建城市地方感,进而重绘城市文化地图。
一、新的政治文化风景再造“地方”
不可否认,文化带有政治性意涵,文化治理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特定时空条件下,基于国家的某种发展需求而建立发展目标,并以该目标形成国家发展计划而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进行干预,以达成原先所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12)廖世璋 :《国家治理下的文化政策:一个历史回顾》,《建筑与规划学报》,2002年第2期。,是“掌权者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和控制的一种策略,其本身就是具有工具性的特征”。(13)王啸、袁兰 :《文化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政策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政策分析》,参见2013年1月8日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108/c40537-20131372.html)。国家——地方权力通过特定的文化艺术象征物来树立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特定形象,利用文化艺术象征物来强调民族的共同性,促进内部稳定,从而使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14)(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第4页。地方戏曲在中国经济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市场后迎来新的挑战,面临在城市全球化治理逻辑中的文化定位及发展问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执政党对文化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中共十八大召开后,文艺工作被提升到改革开放以来“治国大业”的高度,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进一步强化,向政治进行“回归性”调整(15)王杰、石然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99-300页。,在此背景下,地方戏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重视与政策推动,被赋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并深刻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这一论述成为此后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之一。的象征符号之一,参与建构现代国家形象。随着“乡愁”这一指涉“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文学词汇第一次进入高级别政府工作会议报告(17)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强调在现代元素的建设中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系列文艺政策频繁发布预示着新的政治文化正式开启了对“地方”的再造工程,展开对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写。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执政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基本方针。(18)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重申“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详尽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强调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文艺的永恒价值是追求真善美。(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4-135页。2015年7月11日,国办52号文件《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公布,这是继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布以来,时隔六十多年后又一次就戏曲工作所做出的国家级别的总体部署和政策规定。2015年10月3日,对《讲话》的具体阐释及具体的文艺施政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简称《意见》)中正式发布,《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把文艺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落实中央支持文艺发展的文化政策,制定本地文艺发展具体措施,并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详尽指示,其中,“推进基层国有文艺院团排练演出场所建设”被列为“实施地方戏曲振兴计划”的具体方略之一。(20)《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0日,第2版。
新的政治文化风景中对“地方”的再造工程由各地政府实施进行。作为具有深厚戏曲文化土壤的城市,上海率先在全国将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推向深入,2011年既已集中优势资源成立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通过改变行政关系和院团名称及资金拨付方式,统一管辖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和评弹六大院团并全部实现全额拨款,完善各项演出专项扶持资金制度。在新的国家文化治理政策推动下,2015年5月,上海出台《关于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对18家市级国有院团按“一团一策”原则进行分类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着力解决各类院团共性问题的同时,分类化解个性化问题;对民营院团增加专项扶持资金,在场租补贴、创作孵化、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剧目展演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民营院团发展营造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长期战略部署下,2017年12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文创五十条”),明确提出上海要打造“亚洲演艺之都”,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对全市演艺设施进行优化布局,重点支持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等8个演艺集聚区建设,形成演艺产业集聚效应。2018年4月,上海进一步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提出“培育集聚更多优秀演艺市场主体,实施好‘上海首演’计划,力争实现年均演出4万场次的目标”。其后,“演艺大世界”(SHOW LIFE)工程启动,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计划建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核心引领区、亚洲演艺中心的核心示范区。
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戏曲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建国以来大有可为的发展期,自上而下体现国家意志的地方“再造”工程促进了上海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
二、“地方”的表征:上海市戏曲剧场分布与演出市场现状
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为诸多戏曲剧种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1930年代,戏曲市场的兴盛令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戏曲荟萃之地,班社林立,戏台密布。据不完全统计,彼时上海戏曲演出场所有一百多个,观众席位总数达10万个以上,一个演员有时一年要演出400多场。(21)沈洁 :《上海摩登时代的消费、市场与文化网络构建》,周武主编 :《上海学》(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1页。到1949年,上海市区共有12个戏曲剧种,96个正式剧团,四千余名艺人,如果加上酒楼或街头流动演出者,相关数字会更大。(22)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第23页。《上海通志》统计,1945年至1949年间上海剧场类型有7种,数量共有128座,戏曲演出场所占全市剧场总数的一半或以上,越剧、淮剧、沪剧、京剧、粤剧、扬剧、甬剧、锡剧、绍剧、滑稽戏等剧种都有相应的专属剧场。(23)贤骥清 :《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研究(1912-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3-74页。
建国70年,上海戏曲演出市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结构性变化,戏曲剧种此消彼长,目前有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滑稽戏、上海山歌剧、黄梅戏、豫剧等9个活态剧种(24)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报告》。,到2018年年底,上海市共有持证剧场152家,其中戏曲演出场馆有12家,占全市剧场总数的7.8%(表1)。

表1 上海市主要戏曲演出场馆(2019年)
上表所列12家剧场,专业戏曲演出场所9家,综合性演出场所3家,主要分布在徐汇区、黄浦区、浦东新区、宝山区和杨浦区,尤以黄浦区分布最多,这一区域是20世纪初上海演出空间密集分布区域,“演艺大世界”即是上海市政府以黄浦区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而打造。目前黄浦区区域内有专业剧场22家,展演空间37家(其中26家获“演艺新空间”授牌),汇聚戏剧(含歌剧、舞剧)、戏曲、音乐剧、音乐会等各个门类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人民广场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21个,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4个,形成国内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天蟾逸夫舞台、长江剧场、俞振飞昆曲厅、中国大戏院、上海大剧院皆位于该区域。
从建成时间看,建于1912年的天蟾逸夫舞台是上海历时最长、最具规模的戏剧演出场所,梨园素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现被上海京剧院定位为“以京剧演出为主的戏曲专用演出场所”。长江剧场建于1923年,原为卡尔登大戏院,是上海话剧演出主要场所之一,于2018年重新开放定位为创新型的戏曲实验小剧场。作为上世纪“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的中国大戏院建于1930年,在2018年5月重新开业后转型定位为综合性的演出场馆。其他演出场馆均为近年所建或重修。
从演出剧种看,京剧、昆剧、淮剧均有专属演出剧场。天蟾逸夫舞台和周信芳戏剧空间除满足上海京剧院京剧演出外,均向其他戏曲演出院团开放。梅派大舞台以京剧演出为主,为民营京剧演出公司所运营的梅派京剧传承基地。俞振飞昆曲厅为上海昆剧团辖下的“演艺新空间”,是兼具剧团排练及小型演出功能的多功能剧场。依弘剧场是全市首个以艺术名家命名的剧场,主要推出京剧音乐课本剧和史依弘名家工作室原创的京剧剧目及其他剧种的演出。红星美凯龙浦东金桥店浦兴“星”剧场为小型淮剧专属剧场,定期为社区举办淮音专场“月月演”活动。在建中的宛平剧院定位为满足各戏曲剧种剧目演出的大型专业化、现代化戏曲剧场和演出平台,与既有的戏曲剧场形成差异化运营。
从分布区域看,戏曲演出场馆聚集分布在黄浦区、徐汇区等浦西核心区域,折射出上海剧院“西盛东衰”的局面,2019年11月开业的浦东大戏院作为浦东首个区级戏曲演出中心,打破浦东无专业戏曲演出场馆的现实。
中国大戏院、上海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作为综合性剧院归入重要的戏曲演出场馆。作为1930年代“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中国大戏院重新开业后根据自身历史积淀和特点,定位为“世界名团名剧的中国首演地,打造创新戏曲的展示基地”,是以综合戏剧演出为主、引进创新戏曲演出的中型专业剧场,以“创新戏曲邀请展”品牌与周边剧场形成错位竞争。和在戏曲演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文化积淀的中国大戏院不同,作为综合性的现代化西式剧院,上海大剧院是以“演出场馆”介入戏曲的“创作生产”,从而兼具演出场馆和创作生产主体的双重身份。东方艺术中心于2008年创设品牌演出“东方名家名剧月”,是国内唯一在综合性剧院举办的以戏曲为核心、成规模定期举办的展演盛事,现已成为各大戏曲院团和戏曲名家汇集之地。
新的文化治理政策推动上海戏曲剧场的建设和重新布局,戏曲演出空间规模扩大,这些新老剧场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上海戏曲演出格局。不包括在建中的宛平剧院,专业戏曲剧场的观众座席加在一起共3398个,这对于上海这座拥有70个戏曲表演院团、戏曲年演出场次总量可达近7000场的戏曲重镇来说,依然有扩容的空间。(25)数据截止到2015年8月15日,包括上海市所有戏曲演出团体商业性演出、公益性演出以及民间班社在临时性演出场地的演出场次总和。参见《上海市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报告》。
新的政策之下上海戏曲演出市场如何?以2018年上海演出市场和上海市级国有戏曲院团演出市场为例进行比较,上海中心城区50家专业剧场共举办营业性演出7836场,其中剧院主办演出占比40.3%,日均演出21.5场;观众人次达547.7万;剧场实现演出收入9.7亿元,其中票房收入7.6亿元。从表2可知,上海市六大市级戏曲国有院团在2018年的演出总场次(975场)(26)2018年、2019年较2017年戏曲演出场次有所下降,一方面由于2018年3月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启动为期一年的大规模整体修缮而关闭,另一方面,2019年5月20日至6月2日上海承办第12届中国艺术节,市内剧场资源以满足第12届中国艺术节展演为主。占该年度全市专业剧场演出总场次(7836场)的12.4%。其他艺术门类中,话剧演出场次(2102场)占比26.8%,音乐会演出场次(1261场)占比16.1%,儿童剧演出场次(1257场)占比16%。上海市六大市级戏曲国有院团演出收入(5642.73万元)占2018年上海市演出总收入(9.7亿元)的5.8%,而占比最高的为演唱会(4.01亿元,53%),其次是音乐会(8735.37万元,11.6%)、音乐剧(7438.83万元,9.8%)。(27)数据来源:2017年至2019年《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考核材料》及上海市文旅局市场处。

不可否认,上海戏曲演出市场从2017年到2019年呈温和增长趋势,如果将全球表演场景与戏曲演出市场相比,仅仅一部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三年演出的总收入(2.71亿元),就远超六大市级戏曲国有院团三年演出收入之和(1.69亿元),可见,上海尽管具有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和相对集中的体制院团资源优势,但和音乐剧、音乐会、演唱会、沉浸式戏剧占据市场大份额的全球表演场景相比,戏曲演出市场份额依然处于低位。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一个有着特定发展目标的全球城市如何通过传统戏曲的生产实践获得文化意义,从而进行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和城市文化的再认同,这不仅关涉到剧场的空间实践,也同样取决于演出主体——戏曲院团的艺术生产实践。
三、剧场的空间实践:小剧场戏曲与大剧场戏曲
从空间生产理论视域来看,空间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被生产之物。(28)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 D. 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 ,1991), p.26.这一洞见将空间从静态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纯粹客体转向动态的社会生产实践过程,“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指明了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含括了生产与再生产……是指牵涉在空间里的人类行动与感知,包括生产、使用、控制和改造这个空间的行动。(29)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33.戏曲文化空间通过剧场中的表演实践获得最直观的型塑和再现,因而,探讨剧场的空间实践有助于理解如何通过它调整与再造“地方”,重写城市文化。
作为上海历时最长的戏剧演出场所,天蟾逸夫舞台见证了海派京剧的发展和繁荣,在中国京剧演出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在1989年划归上海京剧院所有后,天蟾逸夫舞台被定位为“以京剧演出为主、其他戏曲剧种演出为辅的戏曲专用演出场所”,采用“事业单位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年均演出达三百多场,其中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演出占三分之一,来自全国其他省区的外地剧团演出占三分之一,来自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下辖的其他5家院团的演出占三分之一,以传统戏曲演出建构上海地标性的戏曲文化空间。
2018年10月,与天蟾逸夫舞台同属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拥有近百年历史的长江剧场重新开业,一定程度改变了上海的戏曲演出空间格局。长江剧场原名卡尔登(CARLTON)大戏院,1923年2月建成,初期以放映外国电影为主,1935年后,黄佐临、费穆、朱端钧等话剧名导演的《秋海棠》《浮生六记》《雷雨》等佳作在此上演,奠定其“中国话剧大本营”的美誉。戏曲其后在此登场,“孤岛时期”,周信芳带领的移风社在此演出京剧长达4年之久。1951年12月,卡尔登大戏院更名为长江剧场,一度作为华东实验越剧团的演出基地。在1985年划归上海市演出公司管辖后,长江剧场成为上海话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但于1990年代因建筑陈旧而关停。在“文创五十条”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规划下,长江剧场于2016年底启动装修改造工程,2018年10月重新开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定位为“先锋性、实验性、创新性小剧场,以戏曲为主,兼顾戏剧类演出和教育展示活动”。重新开业的长江剧场将传统戏曲与新兴的“黑匣子”剧场模式相结合,包括“红匣子”(230座)和“黑匣子”(100座)两个小剧场,这是继2015年5月328个座位的周信芳戏剧空间开台后,上海的又一家专业戏曲演出剧场。在此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对外公演的戏曲专业剧场主要是拥有928个座位的天蟾逸夫舞台。
区别于面向中型制作的传统戏曲剧场天蟾逸夫舞台,长江剧场聚焦创新性、实验性小剧场创作,被指定为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主场剧场。上海小剧场戏曲节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主办,以“戏曲·呼吸”为主旨,寓意在吸入传统精华的同时,呼出创新理念,为传统戏曲寻找出路,为年轻戏曲创演人才搭建平台。自2015年创办以来,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已上演44台在题材改编、主题思想、观演模式、艺术表达等方面具有探索性的小剧场戏曲作品:既有根据残本排演的古老剧种,也有改编自中外小说极富创意的跨界作品;既有旧戏新编,解构经典之作,也有诸多在观演模式和表达形式上大胆创新的新创作品,涌现出不少口碑之作(如梨园戏《朱买臣》《御碑亭》、黄梅戏《天仙配》、昆剧《夫的人》《伤逝》《椅子》、京剧《草芥》、越剧《洞君娶妻》《再生·缘》、京淮合演《新乌盆记》等,当然也存在诸多在艺术表达方面尚需打磨的作品)。其中,上海市级国有戏曲院团入选剧目在历届小剧场戏曲节中占重要位置,一定程度引领小剧场戏曲的发展方向。在入驻长江剧场前,小剧场戏曲节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周信芳戏剧空间辗转上演,直至2018年,才有了契合自身气质的专属剧场,其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性、探索性和实验性,与从老牌“中国话剧大本营”转型为“百变戏曲匣子”的长江剧场的宗旨定位相契合。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以“小而精”的体量以及多题材、多风格、多形式、多剧种的实验性、创新性展演与市场对接,吸引戏曲新观众走进剧场。自2015年举办以来,小剧场戏曲节呈现出“三青”特点:青年创作人才、青年演员、青年观众。年轻观众占观演人群70%左右,超过八成观众在35岁以下,其中50%的观众是第一次进剧场观看戏曲演出,且多数观众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可谓青年人的戏曲节。
以小剧场戏曲节为演出主体,长江剧场“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概念,更多的是心灵空间的开拓和释放,是创作者与观者共同创造的无限能量”。(30)沈昳丽 :《向世界展示中国戏曲的丰富可能性——以〈伤逝〉〈椅子〉为例》,《光明日报》,2020年3月1日,舞台艺术版。
如果说长江剧场呈现的“小剧场戏曲”在其“小”的空间属性中强调“既传承经典,也面向未来”的实验创新属性,那么上海大剧院的“大剧场戏曲”则是以西式现代化剧场介入戏曲原创,另辟蹊径弘扬京昆传统国粹的剧场空间实践。
作为国内最早建成的现代化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在重塑城市文化,建构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中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定位确保大剧院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作为行政权力在表演艺术场所的表达,上海大剧院是城市治理策略和规划蓝图在文化治理意义上的具体呈现。(31)杨子 :《大剧院的“政治叙事”及对城市文化的塑型》,《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剧场节目体系的全球化定位确定了大剧院“世界主义”范式的艺术和审美追求,“歌剧、芭蕾和交响乐”三大艺术形式的节目成为大剧院建立以来最主要的艺术呈现。直至2010年,上海大剧院的节目选择体系开始有意识地推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演出,坚持“不仅要上演海外进口的节目,也要给国产文艺精品提供舞台”的定位,本土制作、民族艺术进入历年演出季的剧目安排。2009年至2010年演出季中的“上海京昆群英会”,由上海大剧院、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昆剧团合作,开启了大剧院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系列。
在弘扬京昆传统国粹的剧场实践中,上海大剧院并不满足于仅提供演出场所的功能,而是介入原创制作,开启“场团合一”的剧院功能建设。2007年,在新增“原创性”为“国际性”“艺术性”“经典性”之外的品牌定位后,上海大剧院与院团展开合作,以平均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打造“上海大剧院版”原创作品,其中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戏曲原创作品。2014年,上海大剧院与上海京剧院联合制作新编京剧《金缕曲》,探问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变迁和嬗变轨迹。2015年,上海大剧院与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联合出品昆曲《春江花月夜》,将昆曲艺术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相结合,在上海大剧院进行首轮三场演出,近五千张票悉数售罄,引爆戏曲界“张军现象”。2018年,上海大剧院与上海昆剧团、上海京剧院联合出品京昆合演《铁冠图》,由沪苏两地京昆大师、名家联袂出演,将消失于舞台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的骨子老戏复现于舞台,被视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在戏曲界的独特表现”(32)傅谨 :《改革开放与戏曲的再出发》,《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在海派戏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2019年,上海大剧院首次尝试独立出品,联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集结青年主创,将清代沈复的自传体笔记小说打造为同名昆剧《浮生六记》,再现江南文化古典美学,开票当天4小时内售出一半门票,旋即全场告罄,创下舞台戏曲新创剧目的票房奇迹。《浮生六记》的创制模式昭示了上海大剧院以剧场介入戏曲原创制作,从联合出品到独立出品的进阶,以及向制作机构与剧院主体重合的“场团合一”运营模式的转化,这一转化的意义在于,由剧场主导舞台艺术生产,将戏曲剧目生产与上海大剧院强势的市场营销相结合,利用大剧院观众精英化、年轻化的优势,打通创作与市场隔层,激活观众观剧需求,从而扩大戏曲的受众面和传播效力。
“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33)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 D. 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 ,1991), p.22.,空间是行为发生的载体。人的行为建构空间,对空间实践的研究将剧场空间从一个背景性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实体范畴,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剧场空间实践的基础上必然生产出新的空间。无论是传统戏曲与当代实验创新戏剧形态发生碰撞升华的“小剧场戏曲”,还是以剧场主导艺术生产,将传统戏曲摆脱“一桌二椅”进入“大剧院”全球化语境的“大剧场戏曲”,长江剧场和上海大剧院都各自以不同的剧场实践路径,聚焦以年轻观众为核心的新观众群体,构建异于传统戏曲空间所营造的“地方”氛围,重写被全球资本和权力所规划的上海文化地理空间,完成“地方”再造和城市文化再认同。
四、戏曲院团的艺术生产实践
针对上海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的“一团一策”工作机制是国家与地方合力之下,上海文化管理部门进行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该机制在遵循艺术生产规律的基础上,为国有文艺院团打开各具特色的发展和创作之路。进一步说,“一团一策”是国有院团个性化发展的深层制度机理,其背后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协调的文艺发展观,也是对国有文艺院团自上而下的大一统和保护性运作模式的反思和调整。(34)吴筱燕 :《都市情未尽,曲中意犹新——“一团一策”助力上海越剧院再探荣光》,《上海艺术评论》,2018年第5期。这一工作机制赋予国有戏曲院团在生产实践中一定的能动性,培育院团面对市场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培育和构建具有海派特色的戏曲文化生态链。
随着政府对戏曲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有院团“自给率”(演出收入占经费收入总数之比)也在逐渐降低,政府资助份额越大,“自给率”下降幅度就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院团自身能力、活力、发展力在衰退,从2017年到2019年,除了上海滑稽剧团有限公司保持平稳状态之外,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五大国有戏曲院团的演出收入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充足的财政拨款确保国有戏曲院团在规避全球表演市场挑战的同时拥有充裕的创作生产空间。继承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对传统经典剧目的整理、复排是国有院团剧目生产建设的重点,确保传统经典艺术的赓续和发扬。如上海昆剧团全本《临川四梦》、四本《长生殿》《狮吼记》《十五贯》、上海京剧院《七侠五义》、上海滑稽剧团《乌鸦与麻雀》、上海越剧院《凄凉辽宫月》等,在复排中传承经典旨趣,展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其次,在新编和改编剧目中打磨精品,提高新创剧目向保留剧目转化的效益。新时期以来上海打造的一批戏曲精品力作如京剧《曹操与杨修》、淮剧《金龙与蜉蝣》等,在思想性、艺术性、探索性等方面都被誉为中国戏曲的里程碑之作,成为经典保留剧目。进入21世纪,国有戏曲院团新创佳作不断,诸多优秀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如京剧《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昆剧《班昭》等均斩获文华大奖。新政之下的上海戏曲舞台依然保持强劲的创作活力,新作涌现,如上海昆剧团《红楼别梦》《浣纱记传奇》、上海淮剧团《武训先生》《纸间留仙》、上海京剧院《新龙门客栈》、新版《大唐贵妃》、上海滑稽剧团《皇帝勿急急太监》等。一批以中华创世神话为主题的新创剧目出现在舞台上,如淮剧《息壤悲歌》《神话中国》、越剧《素女与魃》、昆剧小戏《神农尝草》等,以戏曲为媒介挖掘与阐发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编和改编剧目中,出现一批小剧场实验戏曲作品,结合戏曲传统和当代审美,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如上海越剧院小剧场作品《洞君娶妻》、上海昆剧团小剧场昆剧《长安雪》《椅子》、上海淮剧团《画的画》、上海京剧院小剧场京剧《草芥》《青丝恨2018》等,这些颇具探索性、实验性的小剧场作品立足传统,在形式与内容上进行升级转化,进而扩容海派戏曲的表演格局与艺术体系。
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政策倾斜与资源挹注的重点。现实题材作品或展开对“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英雄楷模事迹的弘扬,或聚焦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如越剧《燃灯者》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的英雄事迹,彰显上海干部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良好形象和职业操守;沪剧《敦煌女儿》通过演绎“上海女儿”樊锦诗穷其一生致力于敦煌研究的传奇人生,谱写知识分子的平凡与伟大;淮剧《浦东人家》以浦东开发为大背景,以小家庭与大社会的发展变迁透视普通市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起伏,用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表达回应时代话题和社会问题。当然,体制机制开创出国有院团前所未有的创作生产空间,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以弘扬主旋律、讴歌正能量的红色题材开拓新的戏曲文艺生态,推动剧种表演体系的创造,如上海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浴火黎明》《北平无战事》、上海沪剧院沪剧《一号机密》等。其中,《浴火黎明》通过革命者对“革命”从迷失到回归的转变来刻画斗争的艰难和人性的深度,走出并超越红色题材戏剧作品对正面人物塑造的“高大全”模式,因其创新的人物塑造和深刻的人性挖掘被誉为“红色题材戏剧创作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的重大突破”。(35)傅谨 :《2017年度戏曲的多元景观》,《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
上海国有戏曲院团共有11家,虽只占上海戏曲院团总数的15.7%,却是上海戏曲舞台艺术发展和创作的主力军,也是继承和弘扬海派文化艺术的重要实践基地。在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逻辑下,国有院团的艺术生产实践集中展示了上海戏曲文化多样性发展和多元化的创作理念,在继承海派传统戏曲艺术体系的基础上,为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开拓实践道路,以其丰富的精神内蕴形成戏曲院团发展的上海经验和上海模式,在全球表演场景中重构“上海”地方特质,从而建构上海城市文化主体性。
市场机制打开体制外的创作空间,活化戏曲创制机制,助推民营戏曲院团提高市场活跃度,增强市场意识,进而根据自身资源优势、艺术特点和市场情况打造个性化运营模式。作为致力于昆曲的开拓与实验的民营院团,张军昆曲艺术中心自2009年成立以来,对当代戏曲如何传播、振兴和发展,戏曲审美风范如何彰显和重建,走出一条可行路径:自觉适应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演出场所与传播平台,创作出与当代社会、当代审美相适应的“当代戏曲”。其独创“水磨新调”新昆曲——将正宗昆曲水磨腔与时尚摇滚乐、说唱乐“无缝对接”,举办“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市场火爆;当代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弃传统一桌二椅式舞台进入城市大剧院,探索传统戏曲在新的“城市剧院”语境下的传播和现代表现形式;独角戏《我,哈姆雷特》用昆曲演绎莎士比亚故事,“一人多面”的演绎、中英双语切换、先锋前卫的理念为昆曲的全球表演场景开拓诸多可能性;实景园林版《牡丹亭》抛开现代剧场镜框式舞台,以上海朱家角课植园为特定演出场景,将牡丹亭还于园林,以实景、实情营造古韵氛围,完成戏曲艺术虚实结合的美学统一。自2010年6月世博会首演以来,十年时间里,实景园林版《牡丹亭》已在课植园定时演出226场,全球观众累计5.5万人次,并于2019年5月作为第14届“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开幕演出,在莫斯科州立大学药剂师花园带领当地观众穿越600年时光,领略中国传统戏曲之美。十年间,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生产实践并未因其“跨越文化”而失去“地方性意义”,恰恰相反,它试图超越传统戏曲内生性发展的封闭结构,突破“地方”边界,对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将“实验昆曲”的地方性意义放置在与全球文化互动的动态社会关系体系中,在对“地方性”的全球想象中重新定义和建构新的“地方”,从而生产“全球地方感”。
结语:重建地方感,重绘城市文化地图
以地方为基础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实践,是重构地方与区域世界的另类视野和策略。(36)蒂姆·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 :《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第137页。以上海为范例的全球化城市在地方性日益被消解的全球都市空间中再造“地方”,在压倒性的全球表演场景中重建当代本土表演情境,从而构建城市文化主体性。
如果将戏曲艺术视为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上海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表现了新的文化治理政策下,戏曲演出主体围绕再造“地方”所展现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地方”不仅是概念,也涉及实践,地方的特质特性和文化意义,以及地方概念的建构本身,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维系。(37)王志弘 :《领域化与网络化的多重张力——‘地方’概念的理论性探讨》,《城市与设计学报》,2015年第[7]23期。上海的“地方”再造由强大的国家意志所主导,在剧场空间实践、院团艺术生产实践和全球表演场景的博弈互动中被再生产与再认知:新的文化治理政策推动戏曲剧场的重新布局,实验创新性的“小剧场戏曲”与剧场介入原创的“大剧场戏曲”,以不同的剧场实践生产新观众群体,完成“地方”再造;国家意志与市场谋利原则结合形成的文化生产逻辑下,处于不同场域的表演院团以戏曲为媒介,通过艺术生产实践传达特定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在城市文化地理版图中再造不同的“地方”,生产多元各异的“地方感”。
文化治理场域是文化政治的权力战场,其统辖下的“地方”再造是为了改变地方,或者说是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想象,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环境正义及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新的政治文化风景中的“地方”再造帮助我们重构城市戏曲文化空间,在全球表演场景中重建城市地方感,因为“地方的重构可以揭露被深埋的记忆,召唤可期的未来”。(38)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