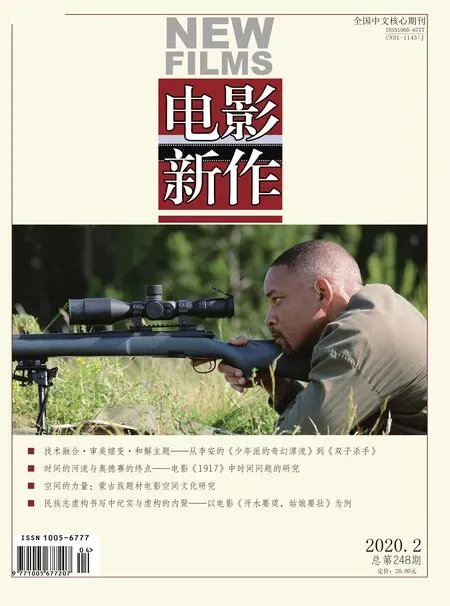中国文化视角下的科幻世界观
——电影《流浪地球》的故事与情感
2020-06-13徐梦娜
徐梦娜
相对于好莱坞常见的建造飞船逃离地球的移民策略,电影《流浪地球》中为地球装上发动机与人类一同逃离的“流浪地球”计划可以说是空前的设想,也将中国文化中的“故土”情怀展现在世界面前。在中国文化视角的预设下,《流浪地球》中近距离观察木星的窒息感,地球飞出太阳系的景象,历经种种灾难后被冰封的地面模样,构造出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影片的一些场景设计有着好莱坞科幻片的影子,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地标、中国元素,以及中国人被放置到科幻故事的核心位置,在地域上的拉近,远比隔着太平洋观望地球危机带给中国观众更大的心理冲击。而基于原著中的“木星危机”所搭造出的全球性救援的故事框架,体现了人类需要共同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精神内核,在叙事上也突破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套路。电影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之间的情感做了更立体、更具观看性的改编,刘培强与刘启父子之间的情感纽带成为故事主线。
在家国情怀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宏大主题下,人物的情感与抉择是更为打动观众的核心,个体情感也为故事发展提供了合理性。饶曙光也指出“《流浪地球》的人设关系及其情感表达,最大层面与观众尤其是本土观众建立起了内在的情感张力并且形成了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了‘共同体美学’。”而影片对人类命运、个体抉择、人类情感与人工智能的对弈等方面的表现与思考,也使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独特视角:中国文化预设下的科幻世界观
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它将观众带到未来世界中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灾难面前,而故事中的一切都构建在虚拟的科学预想之上。剧作家拉约什·埃格里指出:“每一出优秀的戏剧必须有一个经过合理规划的前提”,与发生在现实世界的故事不同,科幻电影“所要构筑的是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想象世界,在构筑不同的地球物理环境的同时,还要创建独立的基于道德、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框架预设与前提逻辑。”这就是科幻电影的世界观。

图1.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流浪地球》中的两个主要前提预设,一是带着地球去“流浪”,二是全球性救援,都是不同于以往好莱坞科幻片的科学预想,带给观众空前的故事体验。原著为电影提供了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前提逻辑:“流浪地球”计划的开启是由于太阳氦闪即将发生,太阳将爆炸变成一颗红巨星,它周围的行星都将被吞噬,包括地球;逃亡计划被分为看起来非常具体且经过严密科学计算的五个步骤,即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I(加速)、流浪时代II(减速)、新太阳时代,电影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第二步中遇到的木星危机之时,而木星危机的理论根据是“洛希极限”。将人类与地球置于未来巨大危难中的预设是许多好莱坞科幻片都做过的尝试,然而我们更常看到的是人类建造飞船逃离地球,或是寻找另一个适合生存的星球,也就是移民思路,却从未有过带着地球一起逃离的情节,而这个独具一格的设想也是一些美国观众所不能理解的地方,“美国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恰好就是中国文化最具独特性的部分,而这份独特性就是《流浪地球》所表现的文化内核。”
实际上,“流浪地球”计划的本身并不是在完全科学理智的决定下产生的,它很明显是基于人类对地球家园的依赖,它饱含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怀,也正是在这个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构建出的故事,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和心理冲击,并通过宏大的故事将中国文化中的“故土”情怀展现在世界面前。与建造飞船逃出地球相比,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的计划本身充斥着无数的危险与未知,原著也对地球和地球上的人们所经历的难以想象的灾难和考验进行了描绘:火山爆发、岩浆淹没地下城;巨浪和海啸之后,大片陆地被冰雪封冻;穿过小行星带时的陨石雨等。并且,计划历经2500年,持续100代人,如此漫长而宏伟的“流浪”,要靠每一代人的信念和努力才能坚持下去。人类在漫长的流浪中将和地球一起见证前所未有的灾难,也随时可能被末日吞没,这个看似浪漫的计划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同时也需要极强的毅力,科学和技术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硬件条件,但真正能支撑人类执行下去的是人类的情感,人类情感在故事中演奏者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与原著不同的是,电影根据“洛希极限”的科学理论,围绕“木星危机”展开整个故事,构建出全球性救援的框架预设,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原著中仅是寥寥几笔带过。地球上的发动机坏掉一半以上,人类展开全球性的救援,主角刘启所在的救援队只是冰山一角,而在最后“点燃木星”的计划执行中,也是靠着调转救援车方向来到赤道发动机的许多个救援队的队员们一同努力才完成的。在危难面前的全球性救援的情节设计体现了独特的精神内核——人类需要共同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实际上,这个独特的视角是由电影故事情境的自身特点决定的。《流浪地球》中的人类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宇宙危机,不可能依靠某个超级英雄来拯救世界,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4000多个发动机坏了,全球各个救援队同时展开不计代价的救援,如果在这样的情境中,出现一个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那么它的真实性和震撼力就会大打折扣,故事的说服力会被极大程度的削弱。国外的一些评论也指出这一点:“‘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相对好莱坞科幻片常见的英雄式的主角人物拯救世界而言,这样的情节设置更具中国科幻片的独特视角,也是其与众不同的精神与文化内核。
二、视听设计:中国元素与国际化视野
独特的故事预设呈现出的视觉体验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窒息感和心理冲击,如地球临近木星,可以近距离观察木星的景象;地球发动机带着地球飞离太阳系的场景;“流浪地球”计划开始后历经各种灾难后被冰封的地面。故事情境和世界观的设定也是电影视觉化呈现的基础,而前者也正是通过而视觉细节来表现的。“为了实现畅想,《流浪地球》单道具就做了1万件,置景展开面积达10万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影片后期的特效制作有3000多人参与其中,整个制作过程有7000人参与,在中国科幻片的创作规模中堪称‘史诗’级别。”由此可见创作团队在视觉化表现上所做出的努力。
无论电影的故事背景是什么,它都需要通过视觉化的呈现来传达给观众,观众并不是去阅读你所设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是通过影片中的各种细节来提取信息的。《流浪地球》几乎没有以往的中国科幻片可以用来借鉴,在空间站场景的视觉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好莱坞科幻片的影子:刘培强在太空站的生活空间与电影《月球》中的场景相似;休眠仓的设计及休眠的方法则很像《太空旅客》中的情景;刘培强和马卡洛夫一同前往驾驶室的过程又与《地心引力》在太空中行走的内容如出一辙。地球上的场景则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面上的世界是一个历经极端考验的场地:地面上零下80度的低温和被冰雪覆盖的世界;在厚厚冰雪上驾驶的特殊救援车辆;刘启带着朵朵从地下城升到地面需要穿着的隔热服。这些有着灾难片既视感的细节一部分来自刘慈欣原著的描绘,而视觉还原更多还是参考了好莱坞的灾难片,如《后天》中纽约被冻住的模样。但是,这次被冻住的地标建筑是上海东方明珠,这对中国观众来说也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体验,远比隔着太平洋的观望来得逼真和强烈。地下城中的场景则加入了更多中国元素,如北京地下城的模样,城中心的小吃,和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

图2.电影《星际穿越》剧照
另一方面,不论是故事场景的选择还是人物关系的设定,《流浪地球》都体现出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合作精神:设置联合政府来代替某个超级大国主导人类命运;太空站中与刘培强一同前往驾驶室的是俄罗斯的友人;地球发动机的救援是全球性的;“点燃木星”的最后救援集中地在赤道转向发动机所在的苏门答腊;完成拯救地球的任务是各个国家救援队的队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在语言选择上则体现了独特的考量,既体现出本土化特点,又有站在未来视角上的思考和国际化视野。由于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人,发生的场景主要在中国,所以中文对话贯穿始终是非常自然的,中国观众也很是过瘾的在科幻片中听足了母语。而电影中刘培强与马卡洛夫的对话是各自说自己国家的语言,朵朵对着世界广播的时候也是说的母语中文,但他们之间都能无障碍地进行交流。由此可见,电影所展现出来的未来世界的语言交流情况是以广泛运用的同声传译为基础的,人们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就能与其他国家的人进行流畅的对话,这比用某一个通用语言来进行国际交流似乎更加符合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三、情感表达:推动叙事的情感纽带
《流浪地球》的独特设想和视觉设计构建了一个精彩的科幻世界,而故事中的人物和情感则是它能够成功抓住观众的内在原因。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电影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符合故事情节、更具观看性的改编,将原著中并没有用太多笔墨描绘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立体、真实,将本是轻描淡写的情感关系发展为故事主线——刘培强和刘启父子之间由冲突走向和解的过程是故事的重要纽带,而电影前半部分则充满少年刘启的成长主旋律。
在《流浪地球》的原著中,由于生活在地球末日临近时,生存的渴望和压力大过一切,刘培强和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情感和家庭责任很淡,小说中对人物之间的情感也没有深入的描写。并且,原著中的刘启更多是起到“流浪地球”计划的见证者和叙述人的作用,而原著的重心也放在对“流浪地球”计划本身的讲述上。但是改编成电影剧本后,刘启和其他角色的形象是立体、丰满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也更加深刻。
好莱坞硬科幻电影的代表《星际穿越》,也是以情感内核为叙事主线。“库珀和墨菲之间深厚的父女之情,成为影片贯穿始终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他们经历矛盾、冲突,到最后的和解,父女间的情感线是故事发展每一阶段的纽带,并且父女之间的默契也成为拯救人类的密码。即使观众看不懂电影中的一些太空探索内容,比如黑洞、纬度,但也会被电影中的情感所打动和征服。在《流浪地球》中,同样的纽带体现在刘启和父亲刘培强之间,而故事的发展也是他们之间由冲突走向和解的过程。刘启对刘培强的误解与矛盾一开始没有明确表现,但通过刘启几次拒绝与空间站中的刘培强通话的细节,可以看出他对父亲有着不满。而这也引起观众的疑问:小时候的刘启和刘培强之间有着浓浓的父子情,刘启对前往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刘培强很是不舍,期盼父亲早日回到地球。可为何十七年后刘启对父亲的态度如此恶劣?是因为对父亲离开的埋怨,还是青少年时期的叛逆?这个答案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才揭示:刘培强为了儿子能够有进入地下城生活的机会,放弃重病的妻子,让刘启的外公韩子昂带着刘启进入地下城,自己则前往太空站执行任务,正是这一决定造成了儿子对他的埋怨与误解。
随着危机的深入,刘启也从被动加入到救援队,到成为拯救地球的主力,他在危难中迅速成长。故事开始于刘培强即将返回地球时,此时的刘启从地下城来到地面,恰好巨大的灾难来临,全球性的救援开始。他和妹妹朵朵以及外公韩子昂驾驶的车辆机缘巧合地被救援队征用,韩子昂在运送火石的过程中遇难,兄妹俩从安逸的地下城生活的假象中,突然被拉扯到残酷的现实灾难里,他们亲眼目睹亲人的离世,杭州城的毁灭。在救援队即将解散之时,刘启决定征用救援队,共同支援赤道上的发动机。这一刻,不谙世事的少年刘启好像瞬间成长了,而成长的主题也变成故事前半段的主旋律。这个过程也使刘启逐渐认识到责任,让他与父亲的角色逐步靠近,也是使他最终在内心情感上与父亲达到和解和认同的重要内容。

图3.电影《地心引力》剧照
发动机的救援成功后,地球并未从危机中脱险,仍将与木星相撞,救援队倾尽全力却迎来绝望,在强大的宇宙力量面前人类的任何努力都显得如此渺小。在所有希望熄灭的最后一刻,刘启仰望木星,回忆起儿时与父亲的对话。这里体现出在他内心深处是思念父亲,盼望团聚的,只是他的叛逆和误解使他压抑了这种真实又自然的情感,选择用逃避和拒绝面对父亲。在我们感受刘启的内心情感时,回忆中的一句话却又恰好成为拯救地球的最后方案,这是情感线推进叙事的有力一笔。
最后,刘培强为了助地球上的人类完成点燃木星的最后五千公里,放弃了与空间站上的人类一起生存的机会。当听到父亲在广播里说出自己的计划时,刘启控制不住的歇斯底里,此刻他知道再也无法和父亲相见了,这中间隔着17年的分别与期盼,支撑自己的期待瞬间化为乌有,坚强与叛逆的外壳一刹那崩塌,所有的不舍都变成拼命阻止父亲的大喊声,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释放出来,矛盾与误解在这一刻消散无踪,父子之间一直以来的冲突变为和解。而看到儿子在救援中的表现与成长,刘培强感到欣慰,认为他已经成为和自己一样有担当、有责任,并且有能力的男人。刘启此刻也理解了父亲当初的决定,并认识和接纳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父子在这场危机中逐渐走向互相理解、认同,并达成和解。“故事外部的形态是拯救了地球和孩子,而内部则指涉的是人物内心的传承。”刘培强的牺牲也意味着他的精神在儿子身上被传承下去。
四、人类抉择:情感与理智的对弈
科幻电影不仅给观众带来不同日常的体验,同时也常常包含对生活、人性、抉择等方面的思考。影片用不露痕迹的方式刻画了极端未来世界中人物个体的抉择和命运,以此展开对情感、责任、人性等多方面、多维度的深入探讨。“这部电影试图以未来视角,在全球层面上探究人类在极限状况下的抉择。”刘培强为了让儿子刘启获得进入地下城的资格,前往空间站执行任务,并放弃重病的妻子;刘培强请求联邦政府支援地球救援队时,有着双重身份的联邦政府负责人的回答很耐人寻味;“点燃木星”的计划通过广播传出后,全球不同国家救援车中的救援队员们开始了不同的权衡与抉择。而电影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培强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莫斯的合作与对抗,前者代表人类的情感与感性,后者代表人工智能的科学与理性。随着故事的发展,危机的深入,刘培强与莫斯从工作中默契的合作伙伴,逐渐走向决裂,这个过程其实是人类情感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对弈。在抉择面前是选择理性的科学计算结果,还是相信人类的情感、信念,为渺茫的希望奋力一搏,影片给出的结局虽然包含了绝境中的无奈,但也彰显了人类的勇敢和自信。
莫斯是一个没有具体视觉形象的角色,只有声音出现在电影中。它初次出现时像是刘培强的助理,在刘培强中校的指令下完成操作,帮助他与家人进行通话,两人之间的关系像亲密的合作伙伴。但是,木星危机爆发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频频出现。
第一次对抗:刘培强与莫斯的第一次对抗是在太空站即将进入休眠状态时,这时的刘培强已经进入休眠舱,却发现不对劲,意识到太空站的“叛逃”,于是他拼尽全力破坏休眠系统,企图从休眠仓中逃出。
第二次对抗:被唤醒的俄罗斯人马卡洛夫与刘培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在知道联合政府放弃地球转而采用新的“种子计划”后,随刘培强一同走出休眠舱,前往驾驶室,企图制止“叛逃”行为。在两个宇航员前往驾驶室的过程中,莫斯消失了一段时间,没有听从刘培强的指令给予帮助。而当他们在艰难中接近驾驶室准备登陆时,消失的莫斯突然出现,并将马卡洛夫击伤,马卡洛夫在最后一刻推了刘培强一把,使他能够顺利进入驾驶室。这是莫斯对刘培强行动的一次强烈反抗,刘培强愤怒地控告莫斯“这是谋杀”。
第三次对抗:影片的最后,刘培强决定驾驶空间站去撞击木星,助地球上的人们完成最后5千公里的火焰冲击时,莫斯认为他疯了,马上取消他的控制权,并说“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种奢求”,这是他们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对抗。失去控制权的刘培强摔碎酒瓶,破坏控制室,夺取控制权,分离休眠舱,驾驶太空站撞击木星。在这场对弈中,刘培强以自我牺牲成功拯救地球,以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彻底反抗告终。
刘培强与莫斯之间这场激烈的对抗反映出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矛盾。对于莫斯来说,他的一切决定只要遵循科学计算就可以;而对于人类,他们并不能仅仅以科学理论作为唯一的执行依据,他们的思考与抉择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也是打动观众的重要内容,是电影的情感内核。
结语
电影《流浪地球》的上映是中国科幻片史上的重要一笔,“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浪漫而大胆的情节设定带来不同以往的故事角度和观影体验,电影中极端环境下的未来世界也在以中国元素为主导的基础上,具备前瞻性的国际化视野;在模仿好莱坞一些细节设计的基础上,也对突破其叙事套路和情节设定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为世界科幻电影带来独特的视角和理念;在严密科学逻辑的硬科幻外壳下,它有着细腻感性的情感内核,以人物情感推动故事主线发展,并延伸出对人类情感方方面面的关注与思考。
【注释】
1 饶曙光.《流浪地球》与“共同体美学”[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2-20(008).
2 [美]拉约什·埃格里,高远译.编剧的艺术[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64.
3 陈成、申林.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框架预设与前提逻辑——以《星际穿越》《阿凡达》《超时空接触》为例交叉对比[J].电影评介,2016(09):47-50.
4 郭帆、孙承健、吕伟毅夏立夫.《流浪地球》:蕴含家园和希望的“创世神话”——郭帆访谈[J].电影艺术,2019(02).
5 钟声.《流浪地球》折射源自现实的未来感[N].人民日报,2019.2.14.
6 冯芸清、陈汉辞. 票房攀升背后是文化产业升级[J].宁波经济,2019(03).
7 王杨.《星际穿越》:宏大叙事架构下的冲突与和解[J].电影评介,2015(04).
8 王蒙蒙. 太空科幻电影叙事研究(硕士论文)[D].海南:海南师范大.2016.
9 郭帆、孙承健、吕伟毅、夏立夫.《流浪地球》:蕴含家园和希望的“创世神话”——郭帆访谈[J].电影艺术,2019(02).
10张颐武.现实照进《流浪地球》了吗?[N].环球时报,201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