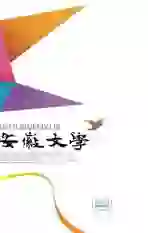月光如此皎洁
2020-06-12李新文
李新文
一
“呼”的一下,月光把一座大山给包围了。这样的速度快得无药可救,连时间也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又将一幢木物和一个人的影子急速推出。刹那间,有了光与影相互照应的效果。
木物站在山腰上,恍若时间里的侧影。
等到靠近,你才看清是个凉亭——一座实打实的木物:四根柱子撑着一敞茅草顶儿,坚定地立着,仿佛站在坚强的意志里。大概木柱受不了月光沐照,干脆把壮实、挺拔的姿态展示出来,算是一种回应。左看右看,这模样与庄稼人的身子骨相差无几,用手敲几下,即刻发出“咚咚咚”的大响,激起一串岁月的余音。亭子里,设有靠背、坐板,可以坐,也可以躺。四周静悄悄的,似能看清月光挥洒的速度以及晚风掠过山野的痕迹。月光一照,人的气息也从亭子里漫出来,水一样流动。如此这般,一座亭子有了说不出的深邃。听说,早年上山砍柴的,挑谷子的,打土车的,以及婚丧嫁娶的人,从山脚爬到山腰,或从山的反面翻过来,总要在这里歇一下,喘口气儿。一线线的风,不请自来。“哧溜”,钻进人的身体,舒服得不行。
每有月光的夜晚,那个叫徐大柄的老头儿会如期而来,在亭子里坐一坐,抽几口旱烟或咳嗽几声。不知不觉,袅袅的烟雾加深了夜色。
此刻,他望了望木亭,骤然觉得日子不像在山里走动,而是落到亭子里。一只只木柱上,现出不少时间的纹路和风雨爬过的痕迹。不一会儿,日常生活的镜头随之铺展开来:日出、种作、上山、喘气、歇息,而后下山……如此循环往复,是不是将人间的日子画成一个圆呢?就在这样想着时,不料,木亭也望了他一眼,发现老头儿比先前更老了。额上的皱纹一根根弯曲着,像书法里的铁线小篆。或许,刻在上面的,还有更深的东西吧。
月光不愧是奇异的光。轻轻一照,能让许多记忆复活。尤其,过往的时光从他脑海里哗啦而出——那年他刚八岁,也是这样的月夜,他趴在爹的肩头一步步上山。其时,满月儿把山野照得分外明亮——黑黢黢的山,重重叠叠的树木,还有一线线奔跑的风和天上挂着的星斗,全一目了然。那时,爹坐在亭子里吸着烟,吸一口,吐一口白烟。接着,慢慢地、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这亭子是祖上造的,要换草,要轮番刷油,遇到热天或下雨,还得备下茶水和吃的,好方便路人……爹说得很慢很慢,像翻捡一段家谱,或讲述一个传奇。那期间,他把每根听觉神经舒张着,认认真真地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记在心里,记得很牢。只是,爹说这话时,两眼发出奇怪的光,有着难以琢磨的坚执和兴奋,就像满山的月光亮得不可思议。哎,太快了,一晃几十年了……回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老头儿叹口气,望了木亭一眼,起身往回走。谁知脚儿一动,“哗啦”,月光破碎一块。再一动,粘了一脚。
山脚是大屋场,叫徐家凉亭,清一色的瓦屋与大山、亭子咫尺相望。这格局,静谧、偏幽,并夹带着几分原始。
打小,我经常往这里跑。与其说是我表伯徐大柄吸引我,倒不如说被山上的木亭所吸引。每次前来,总要朝山上的亭子望几眼。不知怎么,粗壮的木柱、伞一样的棚顶和一根根齐整的茅草,进入视线内,有着画儿般的美好。那样子,疑是悠闲的野鹤,把自个儿的闲适和大山的静谧一并展示出来。可看久了,又像久经岁月的老人,将人世间的起承转合通通交融,融为难以解读的哲学。
大山,木亭。木亭,大山。彼此间,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起先,我弄不清表伯为何老往亭子里跑,是否有什么力量拉着?等后来问了几个老班辈,才知是祖训使然。我一头雾水。心想,难不成世上真有这样的训示?
印象中,表伯就是个农民。平日里,无非干着耕田、耙地、种菜、砍柴、烧炭什么活儿。一双满是茧子的手,成为日子的显现与表征。尤其往人堆里一站,肤色、衣着、貌相和口音等等,跟别人没什么不同。但与我姑表叔徐光大一比,差别大了。平素,徐光大喜欢打猎,铳杆一抬,砰,一只野兔栽了;又一抬,砰,一只山鸡闭上眼睛。倏然,一抹兴奋的笑在他嘴角边荡漾,继而水一样往下滴、滴,拉成一个个快活的线条。我疑心这样的线条,成了他生命的经纬。可每次,表伯见他撬着血淋淋的东西从山上下来,忍不住嘟囔:作孽。我不懂大人的心思,便去问徐光大。你猜怎么着?他嘴巴一翘,连珠炮似的甩出一串:嘿嘿,老子打的是野兽,关他鸟事,总比成天待在亭子里磨阳寿强……这种答案,让我惊讶得两眼发直。忽然觉得人与人之间大不相同,好比每个瓦屋里掩藏着各自的心事。
一天早上,我在表伯家里翻看他们的家谱,不经意间,发现他的祖宗叫徐昆山。只不过,积满岁月的面盘上,流淌着静静的笑。那笑,了无波澜,却看得出一个个日子从容行走的姿态。这才明白,他们是从江西迁过来的,宛若一次生命的旅行。随后,这梅溪沿岸的大山里便有了一栋住场和山上的亭子,另外,还从山脚到山顶铺出一条飘带似的石板路。不难看出,瓦屋、亭子和石板路,无异于三个生命支点,又像一个家族的精神坐标。
那天早晨,我傻乎乎地问造这么大的家业,是不是给子孙留点念想或在家谱上写点什么?表伯听了哈哈大笑,却啥也不说。等翻到祖训这一页,才知我的莽撞——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欲求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欲求家之盛者,必先固其善德。是故造木亭一,泽披乡梓,肇自昆山公始,相守于亭,不可废离……”哪怕就这几句,也让我大为惊诧——一瞬间,一代代人轮番看守的样子在我眼前浮现开来,一如站在坚强的意志里,书写着生命的册页。稍不留神,那些个体生命与木亭绾在一起,成为岁月的走向。由此,不难想见,表伯每向山上攀爬一次,何尝不是踩着先人的脚步在移动,如同一种气味贴着另一种气味移动。
二
自然,他要做的功课不外乎攀爬、守望、换草、刷桐油……把一个个日子打理得极有动感。很多次,我看见他提着老大的茶壶和盛有食物的篾篓向上行走,让人觉得像某种抵达,似在靠近一个家族的灵魂。此时的亭子,恰如一只白鹤打量周边的事物,又好似他们的祖宗在注视一个家族的动向。
站在亭中一望,蜿蜒曲折的古梅溪,状若星点的村落以及连绵不断的峰峦,一股脑儿落入视线,要多辽阔有多辽阔,像在告诉你,人世间的近与远、实与虚、得与失,已知与未知、个体生命与岁月长河等等,不过是岁月时空里的符号。现在,亭子上的茅草换新了,齐整整地排列着,能瞧见那分细致和一丝不苟的心情。阳光一照,新鲜的草木气息弥漫开来,进入木亭的内心,有了老而弥坚的气象。柱子和横档也是重新刷过的,浓郁的桐油气味与阳光的分子摻和着,不停跳动、旋转,成为不可知的场。恍惚看见,老头儿捏着毛刷的手在来来回回地动,不紧不慢地动,连他的魂儿也融在里面,成为一种存在。
这山太大,一眼望不到边,俨如横在时间里的一道坎。不错,那些匆匆而来的行人爬到山腰,累得汗水直冒,忍不住喊一嗓子:娘呃,奈不何啊!喊声一落,眼前的金星子乱冒,只好挪到亭子里坐下,敞开嘴巴喘气儿,让跳得过快的心律慢慢归于平稳。老人打着抿笑说,莫急、莫急,喝口茶再走不迟。婆娘汉子听了满脸高兴,随即用瓷花把盅筛了茶,慢慢喝,一口一口地喝,清亮的茶水流进肚里,通体爽快,仿佛又活了过来。娃儿们却没这等斯文,仰头一阵猛灌,不料一个喷嚏,震得空气东倒西歪,还把附近做梦的野鸡惊得咯咯飞起。老人见了就笑,说,慢点,慢点,又不去赶考。料想,这等光景让亭子见了,也在暗暗发笑吧。
木亭敞开着,接纳风,接纳雨,接纳阳光、月光和一个个日子的到来。
吃食只有雨天才有。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不片刻,雾也来了,活像放牧一群白羊。人在山里走,哪怕腿脚再快,也跑不过雨。雨,尽着性子在下。横着的,竖着的,斜着的,全是雨的线条,并与云雾沆瀣一气,没个消停。这时候,你只能躲,或许躲只是过程,那就躲吧,就算把肚子等饿了,也不用担心没吃的——亭子坐板下的小木柜会提醒你那儿备有食物,即便一根麻花、两块发饼也能填补一下空着的肚皮。那时节,我便得了这种待遇,不单单躲过突如其来的风雨,还没让肚子空着。这时候,你望一下木亭,木亭也望一下你。不知不觉间,人与亭子融为气息相通的整体。
时间一长,方圆数十里的人,谁都晓得这山上有座凉亭,也知道那守亭的人叫柄爹。每天,他忙完活儿后待在亭子里。要不,抽几口旱烟或歇息一下;要不,拿起抹布在柱子和坐板上抹,一块接一块地抹,似要擦出日子的亮色。另外,还把抛在石板路上的烟头、甘蔗屑儿什么的拢在一起点燃。一刹间,飘出的蓝烟儿,将他的思绪牵得很远,似能抵达无数的岁月。
老头儿满脸是笑,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这笑,有如大山的宽怀。白天里,一个个村民扑闪而来,家伙什一放,在亭子里喝茶,聊些山外的七七八八,恍惚把時间的节奏放得很慢。兴起时,传出一串爽朗的笑。笑声,在阳光里扩散,连一旁的柴草也想笑了。想想,这样的木亭何尝不是心灵的驿站?至少让你收获一些轻松愉快。即使到现在,也不多见。去年春天,我去南方一座名山溜达,沿着石阶往上爬,仰头看见一个亭子,好不兴奋。等满头大汗靠近时,一块牌子挡住去路,上面赫然写着:“照相方可入内!”那样的字迹,无疑给你一个警示——得先拍张照片,方可坐上一阵,对身体有所交代。
三
出乎意料,老人终于发了次脾气,发得够恶。记得那天中午,表伯喝了几杯谷烧后,一路晃到山腰。眼睛一瞟,感觉不对,很不对。定定神,分明瞧见亭子的木柱上有刀刻的痕迹,是一排字儿。并且,每道刻痕咬得极深,像是把全身的劲儿都铆上。往常,他最忌讳在上面涂涂画画,何况用刀刻呢。这下,心里的火上来了,想堵也堵不住了。于是,乘着酒兴大骂:杀千刀的,杀千刀的,下回碰到定要剁你的脑壳。这会儿,就算他不开口,我也猜得到是谁干的。但骂归骂,一闪身跑到山下找来刨子、刷子和桐油。一时间,刨子的呱唧声在阳光里跳跃,成为一种舞蹈。不一会,刻痕渐次消失,状若痛感哗然退潮。紧接着,刷桐油。刷一下,现出一道光,又一下,凸显出一股活力。
日子在时间里行走,老头儿和他的亭子一天天变老。可谁也没看清时光走动的痕迹,而时光却在老人头上撒下一层白霜,并把他看守亭子的身影定格成一种姿势。那么,在守啥呢?时光?岁月?好像都不是。我下意识地想,也许是一种承诺吧。倒听说,承诺像一条溪水,能把许多生命连结起来,不知可有依据?我又想,说不定这样的溪岸会开出迷人的繁花,将生命的空间装点得生机郁勃。长大后一翻《金刚经》,发现其中写有“千金一诺,至大至刚”的话儿。照这么看,人世间的承诺应该是从人的心底里发出来的,比花儿还美,比月光还洁净,比天空更广阔的人间大义。先前,我问表伯啥叫大义?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等把书读熟就明白了。现在想来,还真是这个理,否则,《道德经》也不会出现“大道废,有仁义”的句子。由此看来,表伯的举动也不失为一种义,大义。况且,他抱定祖辈沿袭下来的“承诺”,日复一日看着、守着,用他的目光和脚步穿越一个个春夏秋冬和花开花落。想想,这种穿越与传承,需要多大的定力,抑或化入心魂的家园情结。若是反过来看,山上的亭子又何尝不在看守着一代代人的生命呢。漫长的时间里,一个个人降生了,在土地上晃荡一番后,一转眼又消失了。不禁要问,人、亭子与时光之间存在多少隐秘?
此时此刻,我也在时间里晃荡,并遭遇着一架大山、一座木亭和一个老人。可惜,我没长一双透视眼,压根看不清一个老人的内心有多强大。但隐隐感到,表伯心里也隐伏着一道坎——不是担心时间会从身边溜走,而是怕没人接他的班。还真没错,你想,一个家族从遥远的时空一路守来,穿过那么长的岁月,怎能说断就断?据我所知,表伯从十六岁起一直守到现在,跟坚守某种使命那样,差不多把一生的光阴耗在里面,确实有点累了。于是,自然让儿子接着守。可这小子没守三天,死活不干,说,干这等小事没出息,要守就守大的。还说什么月光太亮太邪,能把人的魂魄照出来……这样一来,让老头儿无比紧张,有些害怕。的确,这山太大,是整个梅溪流域最大的一架山,我曾用一整天的时间满山乱跑,也没跑到十分之一。山上的月色更加明亮,猛地一照,许多白天看不见的东西会拱出来,在石板路上飘飘忽忽,飘飘忽忽,像许多先人的灵魂在晃动,甚至能看见自己的魂魄。
第二年春上,表哥果真一身戎装去了边疆。送走儿子,表伯踏着一地夕阳走向木亭,甚觉空落。这空落是从没来由的,并以一点为圆心迅速扩大,占据着他的胸腔。夕阳也不含糊,贴着他的脊背照着,照得如一张薄纸。那天傍晚,我看见他在石板路上走,走得极慢极慢,如一只蠕动的虫子。一眨眼,又发现他的身体在晃,像随时被风吹倒。话也越来越少,只抽烟,闷闷地抽,如抽一段空洞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束手无策,唯愿上帝出现,好解救一下内心孤独的人。抬头望天,却啥也没有。可上天又似乎安排好了一切——那天傍晚,突然“轰”的一响,山腰上那经了数百年风雨的凉亭,那牵系着无数目光和脚步的物象,在一阵大风里倒塌了,倒在数丈深的山坳下和众多惊诧的目光里,俨然一段幽深的岁月訇然崩塌,让人无法接受。一同倒下的,还有心力交瘁的徐大柄。其时,他望了凉亭最后一眼,身子一歪,跌在地上,像跌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可谁也不曾料到,闻讯赶来的徐光大一手扒开众人,大喊:怎么啦?怎么啦?随即铳杆一撂,掐人中、灌姜汤、捶背、拍胸口……一连串的动作比打铳还来得细致。一时间,我猜不透他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倒是表伯醒来后,一种不祥的预感骤然升起,压迫着每根神经。
几天后,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山道上,一群人捧着表哥的骨灰和一块刻着光荣烈士字样的匾额,在一片哀乐声里走进村庄,成为谁都始料不及的场景。落日的余晖洒在老人身上,一片苍黄。
听说,夕阳只能照亮一个具体场景,月光却能抵达一切的一切。也许是真的吧。譬如,这大山里的月色,将凉亭、石板路和一个家族的心魂融为一种生命场。其间的玄妙,谁能说清?
月儿又一次降临人间,衬得一座大山更加苍茫辽阔。老人拽着蹒跚的脚步往山上挪,挪一步,与月光靠近一步。这是中秋的满月。如水的月光,洒在遗址上埋着儿子骨灰的墓碑以及墓碑的字迹上,清晰如画。字是老人亲手刻上去的,刻一下,涌一串泪,似乎连他的魂魄一道刻了进去。这时候,他用满是皱纹的手抚摸着一个个字迹,就像抚摸儿子或一座木亭的肢体。偶尔一声咳嗽,让月光愈发洁白起来。此刻,你的感觉里,仿佛满世界除了皎洁,还是皎洁。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