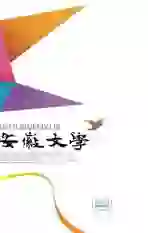残书
2020-06-12程永刚
程永刚
一
我和贾振邦学习篆刻的时候,是在我情绪低落的一个冬天。那个冬天贼冷贼冷的,常常下雪,这場雪还没有清理干净,另一场又铺满了大街小巷。街道上的积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把路弄得高低不平,走起来一跐一滑。
那个冬天,和我相依为命的老爹去世了。我的母亲去世得早,是老爹一手拉扯大了我。老爹的去世,让我大学四年中时时刻刻盼望的骨肉团聚还报跪乳之恩的愿望烟消云散。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干不下去,每天浑浑噩噩,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德行。
贾振邦说:“跟我学篆刻吧。”
学就学呗,无所谓。我那时在县图书馆工作,反正也得经常去他那个旧书店修补残书。其实我心里明白,学习修补残书也好,学习篆刻也好,都是摆摆样子。特别是学篆刻,无外乎是在石头上一刀一刀地消磨时光。
贾振邦经营的旧书店,坐落在县城的十字街上。小街不长,开了七八家收购兼出售的旧物店,有经营旧铜钱旧珠串旧手镯旧古玩玉器的,有经营旧钟表旧收音机旧电话机的,有经营旧书旧报纸旧杂志旧图册旧书画的,还有一家花店也混在其中。一进小街,就见墙上还刷了一条字迹斑驳的“扫黄打非”的标语,小街尽头是一家号称内蒙古纯羊肉的炭火烧烤店和一家有十几张床铺叫大河洗浴中心的澡堂子。
那个冬天,我不止一次地骑着自行车在这条溜滑的街道上摔倒,又满身冰雪地爬起来走进贾振邦的旧书店,把装着需要修补残书的口袋扔到一边,用冻得僵硬的手掏出新刻的印章递给他说:
“看看,有点儿进步没有?”
贾振邦先不忙着看,端来一大缸子热茶放在我手里:“忙啥?先暖和暖和。”
虽然我刻字的积极性不高,可是一旦刻出来了,还是想让他给鉴定鉴定,我捧着热茶催他:“你先给我看看啊。”
他嘿嘿地笑了:“养孩子也不等毛干。”
他看得很慢,还常常找来印泥印出来看。这时候,我最怕忽然有人进来打扰,一有人打扰,我总怀疑他的鉴定会打几分折扣。而且最怕来的人是左邻右舍拉家常的老板们,他们对本地的历史文化格外钟爱,凑在一起唠上辽帝春捺钵就没完没了。
我的家乡阿拉嘎县,地处松花江边,蒙汉杂居。阿拉嘎在蒙语里是手掌的意思。县志上说,这里是历史上辽帝春捺钵所在地。何谓辽帝春捺钵?就是辽朝皇帝在春天捕鱼猎雁的地方。我在大学学习东北史的时候,专攻东北史的老教授曾详细讲过这段历史。我虽学过,但和小街上的老板们比却甘拜下风。他们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几乎都称得上半个辽金史专家。尽管周围的市县一直争论不休,说辽帝春捺钵在他们那里,也毫不影响小街上的老板们以此为荣。
可是那天我担心来拉家常的左邻右舍却都没来。贾振邦拿着那枚印章看来看去说:“可是大有长进了。”
其实我和贾振邦认识的时间并不长,是我开始修补残书时认识的。贾振邦三十多岁,长得黑黑瘦瘦的,嘿嘿一笑,便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他和我打过几回交道后,觉得很谈得来,慢慢地就成了好朋友。
“别给我灌迷魂汤,哪里长进了?”
他用手指着说:“以前刻得太方正了,显得不够大气。”
“这次大气了吗?”
“不光大气了,还有劲道了,有了点儿苍凉的意思。”
我疑惑地问:“这玩意儿还能看出苍凉?”
“看得出。”
“真的?我不信。”
他放在眼前,又细看了看说:“方便了给我刻一枚,我挺喜欢你这样风格的。你就给我刻‘残书斋吧。”
“你不是有吗?”
“我刻的那几个都不满意,磨下去了。”
残书斋是他开的这个旧书店的店名。如此重任交给我,看起来我在他眼里确实是大有长进,不由得咧嘴笑了。
他看我笑了,拿过一块墨绿色的印章石递给我:“可不能让我等得太久了。”
“总得让我再修炼修炼啊。”
“别修炼成了,就不给我刻了。”
“咱可不是那号忘恩负义之人。”
“是不是想忽悠一顿烧烤啊?烧烤店可是新进了蒙古羊肉。”
“那是必须的,撸完了串儿,再去泡一下洗浴中心。”
他拉着长声说:“长本事喽,刻一枚章子,还要勒索一顿大脖子烧烤。”
我们来到烧烤店点了羊肉串、羊腰子、烤羊蹄,这都是我的最爱。他又要了一瓶本地小高粱酒。肉串在红红的炭火上,被烤得滋啦啦地淌着油,香气直往鼻孔里钻,稍不留意,我就撸光了一大把签子。
刚要和贾振邦举起小高粱酒,就听耳边有人吃吃地笑着说:“又把我们给撇开了呀?”
我抬头一看,是贾振邦的妹妹贾小凤,领着贾振邦的儿子贾庆庆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
我工作的图书馆大楼后院有两间平房,一间是我的工作室,另一间是我的宿舍。老爹病重时,我把家里的房子卖了给老爹治病,从此便住在了单位。工作室里奢侈地摆着一张旧乒乓球案子,是我修补残书的工作台。我对这样的工作环境还是十分满意的。主要是清静,从后窗朝外望去,还能看见不远处的松花江。
贾振邦一般不到我的工作室里来,常常是我把修补不上的残书给他送去,由他的妹妹贾小凤把修补好的送回来,修一册五角钱。贾小凤高考落榜后,就帮她哥哥看店儿带庆庆。
“你和我哥学篆刻呢?”贾小凤把一本本修好的书摆在我的案子上。
我说是。
她捂着嘴笑了。
我问她笑什么?
她说:“我看你是三分钟热情。”
“怎么见得?”
“你的心思不在这上边。”
我老老实实地说:“就是闲的。”
她拍了拍修了几次的残书又吃吃地笑了:“能盖这么好的大楼却买不起书,真是吃得起饺子打不起酱油。”
我也笑了,佩服她牙尖嘴厉。
贾小凤长得很好看,瓜子脸大眼睛,特别是皮肤白白净净。不知为什么她哥哥那么黑,她却那么白。
她又说:“图书馆弄到江边这么远,谁来?还不是养了一帮闲人。”
我说:“领导说盖大楼建三馆是上边硬性要求的。”
“哪三馆?”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你是学历史的,这三馆都和你刮拉不着,看起来当年你就不该回来,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阵发酸。她哪里知道我那时的处境,虽然我念书时也是志向远大且品学兼优,深得教授们的喜爱。但毕业时身无分文,家里的老爹又体弱多病,就算我去了省里要我的那几家和我专业有关的单位,别说买房子,就是租房子也租不起,依旧不能和老爹团聚,不回来咋办?老爹一死,事业无成,我完全被一茬茬毕业生边缘化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记了。
但我嘴上还是说:“不回来怎么能认识你?”
她的脸有些红了:“不过,搞装裱也一样有出息。去年省里大赛,我哥还得了个一等奖呢,好几个公司都要他,他不去。”
說实话,我应聘回到家乡图书馆工作,基本上是个闲人,再加上情绪低落,一天天无所事事。好心的馆长大姐看我郁郁寡欢的样子,还真动了脑筋安排我这个图书修缮工作。还说我眼下难以胜任修补残书,可以花点儿钱出去修,我只负责缺边少沿儿的文字就行。因此,我才认识了贾振邦。
我说:“我也没说不好好学习装裱啊,现在不是正学着吗?”
贾小凤又吃吃地笑了:“以你的聪明,半路出家搞装裱也一样成名成家啊。”
我也笑了:“说不定马粪蛋子发烧,或许我以后还能成为一代装帧大师呢。”
贾小凤这一次没有笑,而是两眼看着我认真地说:“这也说不定。我还打算去考工艺美术学院装裱系呢,没准咱俩以后就成了同行。”
她临走时扔给我一本书,说是她哥捎给我的。
这可是一本真正的残书,序言和后记都没了,尽管我看书从来不看序言、后记。也没有作者的姓名,目录只剩下半页。封面是修补上去的,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书名《辽帝春捺钵》。一看就是贾振邦的手迹,清秀有力。
我把这本书翻了翻说:“你哥怎么想起来送我这样一本残书?”
贾小凤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他新收上来的。”
三
贾振邦平时并不是总待在店里,有好几次我在街上碰着他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收购旧书刊。他见了我就像没见着,仰脸朝天地蹬过去,直到我在后边张三儿似的追上他。
“以后看我在街上收破烂,别和我打招呼。”
“为什么?”
“你交了一个收破烂的朋友,让别人看见给你掉价不说,也影响我做买卖。”
我悻悻地说:“小样儿,多大的生意呀?看把你嘚瑟的。”
他挨了我的训,反而呲着牙嘿嘿地笑了。我知道,这一刻他一定很开心。也许人和人之间的尊重,是最值得珍贵的东西吧。
他曾经和我说,想去一趟北京的潘家园,他听说那里的旧书市场很大,特想去淘。他还想去一趟琉璃厂,看一看高手的装裱。其实去一趟北京并不难,不知他为啥一直没去。
贾振邦除了平时走街串巷收购旧书刊,把收购来的旧书刊修补好摆在书店出售外,还修补古旧书籍字画。开始我还不知道他的本事,直到他把我送去的一堆破烂残书修补得整整齐齐,才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我曾经问过他:“这一手好活,是在哪儿学的?”
他说:“我爹就是个装裱匠。还没等我把他手艺学完,他就死了。”
我又问:“书店为什么不叫店,叫斋呢?”
他说:“店名也是我爹起的,我也不知道为啥。”
“你愿意干这行?”
“我爹说这些旧物也有生命呢。修复一件旧物就像救活一条生命,它反过来还能养活你。”
“可也是,有的残书都该去化纸浆了,你又把它们救活了,说不定到了一些人手里还大有作为呢,你是个功臣啊。”
“又开始忽悠我。”
说实话,我很欣赏贾振邦修补残书的认真甚至一丝不苟,连折叠的页码都舒展得平平整整。以至于我们给他微薄的酬金,连我也有点儿替他不平。有时他看我潦草填补的文字问:“这个字对吗?”
我说:“反正是抄的,大概对吧。”
他便找来原作一字一字地校对后,再打字修补。我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修补残书的辛苦,后来养成爱惜图书的习惯,大约与这些有关吧。
贾振邦不但修补残书字画,他还爱好书法篆刻,店里摆了些文房四宝印章印泥。我每次去都见他伏在案子上,忙得头不抬眼不睁,不是修补残书就是刻字写字。
“哈哈,好用功啊。”我每次去都这样夸奖他。
让我感到纳闷的是,他虽然爱好书法,却不见他的任何一幅作品挂在墙上,也不知写完了都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左邻右舍们凑过来谈古论今,他也任随他们谈,自己忙自己的。对于别人津津乐道的辽帝春捺钵,我也一次都没听他参加议论过。
“要说辽帝春捺钵在哪儿?没啥可争论头,铁定就在咱们这疙瘩……”隔壁的老于头儿每次见了我都这么说。他儿子媳妇在海参崴开东北餐馆,他和孙子住在这里,开了一个旧家具店,店里塞满了破旧的桌椅,正中的玻璃柜里,却恭恭敬敬地摆着一对儿旧马蹬,说是辽金的。
贾振邦偷着和我说:“那是老于头儿的镇店之宝。”
“……辽朝君臣都是契丹人,马背为家,四季捺钵……”老于头儿每次来手里还要捧着一个沏着浓浓茶水的大搪瓷缸子,说着说着就喝上一口。小街上的老板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春夏秋冬,都要捧着一个沏满茶水的大搪瓷缸。
贾振邦也有一个这样的大搪瓷缸子,我去了他就塞到我的手里。常常是我听完老于头儿讲述了一段儿之后,也喝完了大茶缸子里的茶水,还不等去添,贾振邦就及时地从案子旁抬起头来,举着大铜壶走过来给我们茶缸里注满了滚开的开水,对老于头儿说:
“你老爷子算是找到知音了,人家是历史系的大学生。”
老于头儿笑了。如果有别人,也跟着笑了。店里一片欢乐。
我在小街上晃荡的日子里,深深地感到小街上的人淳朴厚道,大事小事都相互照应,谁有了急事离开,随便喊一声都有人帮着看店,并且毫不走样。逢年过节礼尚往来,小街上更是热闹。有快乐的事,不管是谁的,大家一起乐。
四
贾振邦平时少言寡语,性格属于内向的那种。在别人面前他高兴了只是嘿嘿一笑,不高兴了也不见他发什么脾气,顶多是不吱声,只有和我在一起话才多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兄妹俩父母早亡,妹妹小他七八岁,是他一手带大的。听说他死去的老婆很漂亮,以前在医院里当护士,俩人感情很深。如今他儿子都上小学了,他还一直是独身。
那天我和他吃完烧烤,泡在洗浴中心的热水池子里。我看他闭着眼睛在热水里泡得挺舒坦的样子说:“你也该找一个了。”
他依旧闭着眼睛哼哼呀呀地说:“整天沿街收破烂,没个人样,谁跟我。”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有个人的眼睛总在你身上瞄来瞄去的。”
他睁开眼睛嘿嘿一笑:“有啥瞄的?黑得像驴屌。”
我说:“笑啥笑,人家看中的就是你这个黑劲儿,成天黏在你的店里。老于头儿早就告诉我了,花店的何茹姐上赶着你,你就是端着。何茹姐又漂亮又挣钱,你还有啥可端着的?虽然离了婚,又不怪她,也没有孩子牵扯。”
“庆庆还小,我不想让他早早地有后妈。”
“不是有小凤带着吗?”
“小凤也不小了,还能总指望着她。”
快过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把年底清理出来的最后一批残书送去,刚进了书店,花店的何茹姐笑盈盈地端着一个大花瓷碗走进来,大花瓷碗里装着冒尖的黏豆包,好像刚出锅还冒着热气:“我淘了米,蒸了两大锅。”
小凤接过来说:“你一个人还淘米?”
淘米是东北人的习俗,记得我小时候要过年了,家里就把成袋子的大黄米淘了,磨成黄米面用大盆发酵,再烀一大锅芸豆,用豆杵子杵得烂烂的,攥成香喷喷的豆馅,用黄米面包好,蒸了一锅又一锅的黏豆包摆在帘子上,送到外边冻得像冻梨蛋子,装到缸里能吃一个正月。那时候的年,可真有年味儿啊。
何茹姐说:“我就得意这一口,外面卖的总不如自己蒸的好吃。”
小凤瞟了哥哥一眼说:“八成还有人得意这一口,你不如一次都拿来,天天送也不嫌麻烦。”
何茹姐伸手打了小凤一巴掌说:“死丫头。”
那晚贾振邦就留我吃黏豆包,小凤又添了两个菜,把何茹姐也拉来了。我们端起酒杯,刚喝了一口酒,小凤看何茹姐心满意足的样子,撇着嘴说:“真不吃亏,谁家娶了你这个媳妇儿,保證得发家致富。”
我说:“此话怎讲?”
小凤笑得端不住酒杯说:“给人家送来一碗黏豆包,就来吃回扣。”
何茹姐瞅瞅我,又瞅瞅小凤,也笑着说:“你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把家虎似的,谁娶了你谁享福。”她这一笑,小凤抬眼看了看我,脸倒是腾地一下红了。
五
那个春节前我修补完了所有该修补的旧书,没事时就天天泡在旧书店。贾振邦看我游游逛逛的样子就提醒我:“我的那个章子你还没动手呢。”
那些天贾振邦趁家家户户搞卫生,天天出去淘宝。特别是一栋教师楼竣工,老师们欢天喜地要喜迁新居,搬到新楼去过年。他们抛弃了一些旧书,要头清眼亮焕然一新轻装上楼,这就成了贾振邦伺机而动的黄金时间。我去的时候他常常不在,我就伏在他的案子上,开始给他刻“残书斋”。
这天中午,我已经刻完了“残书”两个字,还差一个“斋”字没有刻出来的时候,贾振邦来电话了。他哼哼唧唧地在电话里让我带点儿吃的速去支援。我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一直跑到松花江大桥上,见他脸色蜡黄地坐在三轮车旁,一见了我就伸出手:“拿来。”
我递给他两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他一口咬了半个。我看了一眼三轮车,上面的书摞得像个山:“你也太贪了。”
他在冷风中咕嘟咕嘟地喝着矿泉水不说话。我趴在大桥栏杆上,看着封冻的松花江又说:“拼命三郎。”
他噎得打着嗝说:“不会吧?”
回到店里,小凤也回来了。小凤心疼地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他说:“你去了,谁看店?”
我明白,贾振邦不让妹妹去,他怕人家笑话。
一直到腊月二十八,贾振邦才偃旗息鼓,估计是那里也被他淘完了。那天他坐在收购回来的旧书堆里,一本本整理着,嘴里啧啧地赞叹:“还是人家老师文明,有的还包着书皮。”
他的话音还没落,只听一声门响,走进一个七十岁左右穿的鼓鼓囊囊冻得哆哆嗦嗦的老头儿,胡子都挂了冰,一进屋就吵吵,没头没脑地说:“我是打农村来的,上百里地呢,还能叫我白跑?”
老头儿怀里抱着一个陈旧的黄油布捆,一层层打开,是一幅破旧的宗谱:“我叫孩子们来谁也不来,都说修不了了,我不信就没有能人了,修啥样算啥样呗,老祖宗的东西可得传下去。”
贾振邦把那缸子热气腾腾的茶水端给老头儿,又把他让到椅子上坐下说:“别着急,慢慢说。”
老头儿叹了口气说:“能不急吗?来到年下了,过年还要上供哪。”
贾振邦问:“你家年年供祖宗?”
老头儿说:“年年供。一年不供,都觉得心里慌慌地没底儿。昨个不小心又折了一道口子,实在是挂不了了。我走了好几家店铺都摇头说修不了。”
我凑上去看,也难怪了,这真够得上是出土文物级水平。我数了一下,宗谱上已经有十八代之多,岁月久远,折出了一道道口子,好像碰一碰就能碰掉一块纸片儿下来。
贾振邦在这幅宗谱前看了良久,不说能修,也不说不能修。老头儿眼里已明显地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老人家祖上是山东人吧?”
“祖太爷那辈闯关东来的,从老家抄了这宗谱,一辈辈传下来,有死的就添上。”
贾振邦两眼依旧盯着这幅宗谱说:“我可不如你了,祖上出来的时候说,出来闯荡几年就回去,没带宗谱,可再也没回去,把子孙都撂这儿了。”
老头儿听了,顿时长吁短叹:“祖宗辛苦着呢,能不想着回去吗?来了,就回不去了。”
贾振邦不但把活儿收了,还满口答应老头儿耽误不了过年上供。看他果断的样子,我还真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么破旧的宗谱他能修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过来想看个究竟。贾振邦不但留老头儿吃了饭,还把床铺倒给他睡,自己开了夜工。我去的时候,他正用熨斗熨着用明黄绫子装裱成轴的宗谱,残破的地方已经修补好,几乎看不出来。那么破烂的一幅挂图,竟变得完整无缺金碧辉煌。老头儿都看傻眼了,临走问多少钱?
贾振邦摆了摆手说,算了吧。
老头儿眼睛瞪得像牛:“你又供吃供喝,熬了一宿搭工搭料,咋能算了呢?”
他嘿嘿一笑:“都是山东人,就当是山东的汉子给祖上尽孝了。”
操,这小子,别看是个卖旧书的,仗义。
看着老头儿走远了,他又说:“这年头,有的人连活人都不敬了,还敬死人。他上百里地来,难得啊。”
六
年三十晚上,小街上家家红灯高照。小凤把何茹姐叫了过来,也把老于头儿和孙子小顺子叫过来了。老于头儿一见了我就愤愤不平地说:“县上开了个辽帝春捺钵研讨会,也没说找我们,我看那些专家也未必就比我们强。”
那个研讨会我知道,是我们馆里搞的。我们馆长大姐是一个深谙领导意图的人,她请来一些辽金史专家,搞了个阿拉嘎县辽帝春捺钵研讨会,让我也参加了。不知道老于头儿是怎么知道的。
我故作不知地说:“他们可也真是的,怎么把您给落下了。”
小顺子已经初三了,也哼了一声说:“他们真是有眼无珠,竟敢把我爷这个真正的专家给落下了,不像話。”
老于头儿说:“不找我拉倒,这可不能怪我保守,我还有新发现没说呢。”
庆庆眨巴眨巴眼睛说:“于爷爷是个大专家。”
小凤点着他脑门说:“你是个小专家。”
我们都笑了。
老于头儿说:“他们忘了还找我搞过调研呢。要说辽帝在松花江边搞春捺钵,那时把松花江叫鸭子河,举办头鱼宴头鹅宴……”
何茹姐问:“什么是头鱼宴头鹅宴?”
老于头儿说:“皇上打的头一条鱼和头一只大鹅举办的宴会……”
老于头儿的精神头可真足,半夜吃完了发纸饺子,又领着庆庆和小顺子去放鞭炮,小凤和何茹姐也出去凑热闹。饭桌上就剩下我和贾振邦,他嘿嘿地笑着说:“一年就这么一回,让他们闹去,咱们喝。”
小凤跑进来说:“要放花了,还不出去看。”
贾振邦拉起我说:“咱们看看去吧,这新的一年马上就来了。”
门前的小街上,家家门口聚了一堆人,鞭炮礼花燃亮了一条街。
那晚我到底是喝高了。天还没亮我起来撒尿,贾振邦没在床上,从门缝透出一缕灯光,我推门一看,他趴在案子上睡着了,面前摊着一堆正在修补的残书。
这一幕,让每天吊儿郎当的我顿觉羞愧。
七
新的一年,我还真有些走运。在贾振邦那里过完了年回到单位后,我重振旗鼓,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辽帝春捺钵的论文在《历史》杂志上发表了,没想到竟然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说我提出的辽帝春捺钵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在松花江沿岸多地举行的观点,是历史研究的新发现。于是我一鼓作气,又带着论文参加了省史志办的招聘,没想到竟一举中榜。
临走时,贾振邦在酒店为我举办了一个欢送酒会,把左邻右舍都请来了。只是小凤没来,我知道她为啥没来,心里挺难受。
我到省城以后,贾振邦来办事常常来看我。我们在小酒馆里谈天说地,还是老习惯,哪一次都是他抢着去结账。有一次他嘿嘿地笑着说:“小凤有对象了,是她同学,一起办公司。她对象人挺憨厚的,一说话脸就红。”
我走那年,小凤考上了沈阳工艺美术学院装帧设计系,几年后她毕业留在了沈阳,和同学办了家装帧设计公司。
“何茹姐呢?别不小心给人家弄出大肚子再打主意。”我说。
“尽瞎扯。”
“我可没瞎扯,有一回我住在你那里,半夜你就不见了,天亮时才从花店出来,我看得真真的。”
他脸红了。
我又说:“你还晾着人家?”
他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人家不要我这条黑驴屌喽,嫁给了一个官员,连花店都兑出去了。”
“那都怪你自己端着,整天穷忙,把正事儿耽误了。”
“没啥忙的。”
“你不是闲着的人,我知道。”
“忙也是瞎忙。不过,庆庆学习倒是挺好的,我没白操心。”
我说:“当年我不成器的时候,如果不认识你可就惨了。说起来,我写的那篇论文能有些新意,也靠着你给我的那本残书做指导才启发我完成的。”
“哪一本?”
“《辽帝春捺钵》啊,你那位功臣至今还供在我书架上呢。”
他又嘿嘿地笑了:“你还欠我一笔旧账,可别忘了。”
“哪一笔?”
“我托你刻的那枚印章。”
我说:“忘不了啊,不就是那枚印章吗?等刻完就给你了。”
八
十年过去了,头几天贾振邦来电话,说庆庆考上大学邀我回去喝酒。
小街和小街上的人似乎什么都没变,墙上那条扫黄打非的标语还依稀可见。老于头儿依旧精神矍铄,孙子已经大学毕业去南方工作了,儿子媳妇接他去海参崴他不去。见了我张口就说,辽帝春捺钵遗址我又有新发现了。旧钟表店的王二哥远远看见了我,抢上前就把我抱住了,憋得我半天没喘上气儿。古玩店的张三叔在酒桌上和我碰了一杯又一杯。
客人散去,我和贾振邦余兴未尽,回到店里又对饮起来。
他说:“我过几天送庆庆去北京上学,这回一定得去一趟潘家园的旧书市,还要去一趟琉璃厂。”
“闭上眼睛,把手伸出来。”我说。
“又搞什么猫腻?”
“让你伸你就伸。”
他乖乖地闭上眼睛伸出了手,我把那枚印章放到他手上,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说:“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这么一枚残章,有啥可显摆的?”
我说:“别管残不残,让我接着刻是不可能了,试了几次都不敢动刀,那点儿功早就废了。”
他又拿在眼前看了看:“你还别说,这上面计划刻的三个字只刻了‘残书两个字,留下的这个空白,还真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
我捋杆便爬:“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没刻完,怎么就给你拿来了呢。”
这一晚我又喝高了。半夜我又起来撒尿,摸不着墙上电灯开关,蒙头转向地竟走到了书店里。那摆着的书架,像一堵堵墙围起来的堡垒更让我发懵。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门,推开,才发现外面是门前的小街。我努力辨认着,旧家具店、旧古玩店……一瞬时,家家门前红灯高照,鞭炮礼花燃亮了一条街。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