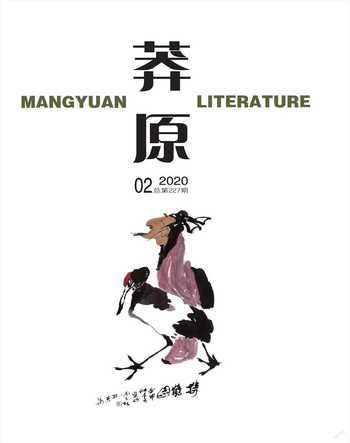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召唤革命
2020-06-09李勇
李勇
一
一个老妇人病了,住在台北的某家医院,看护她的是早逝的“丈夫”的弟弟。小叔子对“嫂嫂”的病和她病后的表现感到奇怪——这病没有前兆,“嫂嫂”也似乎没对康复抱有太多兴趣,她只是沉默着,而病也日复一日地重了。后来她干脆拒绝进食,直到阖上双眼,沉默而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弟弟整理遗物时,看到她的一封信,进而知悉了她离奇病逝的原因,以及那背后藏着的惊人秘密。
这是 《山路》 讲述的故事。故事中的弟弟叫李国木,他早逝的哥哥叫李国坤,“嫂嫂”名叫蔡千惠。那封信,是蔡千惠写给她曾经的未婚夫黄贞柏的。千惠在少女时代,因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哥哥的好友李国坤。李国坤和她的哥哥,以及她的未婚夫黄贞柏等,都是20世纪5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反抗国民党专制的青年,他们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台湾,向往并努力追求一个美好的世界,蔡千惠对此虽懵懂,却也耳濡目染,直到事情败露,李国坤、黄贞柏和哥哥均被捕,有的被杀 (李国坤),有的被判无期 (黄贞柏),而哥哥却在父母帮助下自首,沦为一个“卑鄙的背叛者”。目睹這一切的千惠,背负着羞耻,以李国坤“在外结过婚的女子”的名义,来到山区国坤贫困无助的家,用大半生的辛劳偿还家族的罪愆。
《山路》 讲述的故事,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忏悔。不过,这个关于“忏悔”的故事,却足以让人震惊。震惊之处在于两点:忏悔的强度以及它的复杂性。
首先看强度。千惠为了偿还家族的罪愆,付出的是她的青春和整个生命。根据信中所写,李国坤之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千惠病逝是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说,蔡千惠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以付出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和岁月的方式去赎罪。在现实生活中,一段时间的自苦,甚至瞬间的自裁,都是容易的,而半生的苦役 (照顾一个失去长子、非老即幼、背负着社会歧视和排斥的至为贫困的家庭,为老人送终,抚养弟弟成人、供养其读书成材),确实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正是千惠忏悔的强度。
然而,千惠的忏悔,除了因为自己家族的罪愆 (哥哥的背叛),还有稍显“暧昧”的因素,即对于她信中所称的“国坤大哥”的李国坤,少女千惠一直是怀有一份包含了爱慕的敬重的。从信中可见,这份爱慕和敬重,一直持续了她的一生,当然也让她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一生付之于她的忏悔行动。这是千惠的忏悔之复杂性的第一点。然而,仅仅是爱慕和敬重,并不足以解释她最后的赴死。按照小说的介绍,老年的千惠是以对治疗极为消极的态度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这放弃其实很奇怪,因为当年的未婚夫黄贞柏的被假释,无论怎样对她都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以一生的苦役为家族赎罪的她,按理说是可以坦然面对当年的受害者黄贞柏的——也就是说,她没有必要如此决绝地赴死。但她却这么做了。显然,这里另有隐情。
这隐情,或者说真正压垮千惠的,是她所感受到的另一重罪愆。这罪愆,来自于她对三十年来 (尤其是信中所说的最近这“七八年间”)自己所过的生活的反省。在信中,她这样痛切地对黄贞柏说:
在您不在的三十年中,人们兀自嫁娶、宴乐,把其他在荒远的孤岛上煎熬的人们,完全遗忘了。这样地想着,才忽然发现随着国木的立业与成家,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早在十七年前,我们已搬离了台车道边那间土角厝。七年前,我们迁到台北。而我,受到国木一家敬谨的孝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贞柏桑:这样的一想,我竟也有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了的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
在这里,蔡千惠把自己指认为一个“堕落了的自己”。而正是这个“堕落了的自己”,成为了她新的罪愆,并将她压垮。仔细体味这里蔡千惠所指认的她的“堕落”,其实就是对于革命和革命者的遗忘。然而,这种遗忘真的是有罪的吗?
二
为理解小说中蔡千惠的心理和行为,需要介绍一下故事的背景,也就是当时台湾的历史和现实。
“历史”指的是1950-1952年的国民党白色恐怖。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展开的对共产党和左翼进步人士的大肆捕杀。这正是小说中千惠所见证、黄贞柏和李国坤所经历的过往。但国民党的这种高压统治,在当时所激起的是青年人对于理想和反抗的进一步渴望与追求,而当时他们大多数所皈依的,正是共产党和左翼。李国坤、黄贞柏便是身在其中的青年。而他们非死即囚的命运,也是当时那一代左翼的共同命运。蔡千惠作为当时左翼的边缘人,见证了那一代青年如火的青春与牺牲,并深受感染。所以在他们仆倒后,她很自然地便成了一个革命的遗腹子——尽管她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革命的理想主义之光照耀了千惠,正如小说以最动人的笔墨所描写的她跟随黄贞柏走过的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我们挑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您讲了很多话:讲您和国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讲您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
在这种革命理想主义之光的照耀下,当时懵懂的千惠,毅然做出了行动——以忏悔和赎罪的方式,继承革命遗志。
也就是说,千惠是背负着历史之重,尔后才一步步地步入了台湾的“现实”。而从1950年代白色恐怖到1983年,沿着少女千惠一路走来的轨迹,我们看到,围绕着她发生了很多事:她扶老携幼担负起那个家庭的重担,代替李国坤给老父亲送终,抚育李国木一步步成材,直到他开始自立,并通过努力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在台北买下房子,娶妻生子,还接来老去的嫂嫂,一起安居乐业。革命的故事就这样一步步转变为了一个“由乡进城”的家庭奋斗故事,而这个小家庭“由乡进城”的奋斗故事,其实也正是台湾三十年现代化转型史的缩影。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李国木及其家庭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时值20世纪80年代,在台北拥有体面工作、美满家庭的李国木,显然是这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的受益者。而作为这个家庭一分子的蔡千惠,当然也是受益者。换句话说,她应该感到幸福才对啊……然而,对于这一切,她感到的却是羞耻:
就这几天,我突然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遗忘了。
这羞耻,就像千惠自己说的,是因为她在这“幸福”的时代里遗忘了自己的革命“初心”。然而,最难解的问题出现了:革命难道不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吗?李国木一家乃至于当时的整个台湾,难道不是已经实现 (或基本实现)了这种安定富裕了吗?——这方面相信并不用过多解释,因为台湾在战后大约二十年里通过借助美援、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加工替代工业,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经济发展速度和民众富裕程度一跃而成为发达地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如果真是这样,那蔡千惠的“羞耻”难道不是有些自寻烦恼、矫情做作吗?
三
作为小说人物的蔡千惠,她的“羞耻”,显然是作者加诸的。所以,要理解这“羞耻”,首先要了解陈映真。
陈映真 (1937-2016)是战后台湾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从1959年开始以作家身份踏入台湾知识界,批判和反抗国民党专制(戒严时代),批判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解严时代) 等,毕生致力于反抗一切形式的专制和强权,谋求民族统一,以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
对于陈映真的名字,今天的大陆知识界已不再那么陌生,而相对于大家的理解,上述描述恐怕是非常概念化的。而大陆知识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陈映真的隔膜和误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概念化”的理解所致。在这个理解中,“左翼”“民族主义者”都是附在他身上的标签。而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语境中,这些标签所带来的影响,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这种负面的理解和标签,很大程度上又和我们这里讨论的“蔡千惠难题”有关。
蔡千惠在一个富裕的时代却“自寻烦恼”般地失落和羞耻。革命的目标既然是安宁和幸福,那么在当时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的台湾,蔡千惠的“羞耻”,其依据和合理何在?
蔡千惠的失落和羞耻,当然是陈映真自己的。而1983年的陈映真,其失落和羞耻,与他当时正遭遇的精神危机有关。陈映真在大学时代便因读鲁迅等人的作品而思想左倾,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左翼已经被杀伐殆尽,国民黨高压体制使得他和他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们只能从读禁书 (左翼书籍)中缓解内心的压抑和痛苦,但后来聚读禁书事件败露,他和他的伙伴们被捕。1968年底,陈映真作为主犯被判刑十年,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但陈映真出狱后所遭遇的,却是远比七年监禁更为痛苦的精神危机。
这危机,就来自于当时已经富裕的台湾社会对于革命历史和革命者们的遗忘。如果台湾当时的富裕和繁荣,是真正的富裕和繁荣的话,那么遗忘带来的,恐怕不过只是一点点失落罢了,但陈映真发现了那富裕和繁荣的虚假。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种“虚相”,而真正的“实相”,是发展背后的巨大危机。
陈映真出狱后直到去世,写下了海量的文字,这其中相当大的比例,便是致力于揭露这种危机。在他看来,危机在于两方面:第一,台湾的发展并不是一种自主性的健康、良性的发展,而是一种依赖于外力的“依附性发展”,这外力,即美国的扶持和援助,而美国自战后便开始的对于台湾的援助,背后的动机,则是一方面扶植国民党作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远东防线,另一方面又将台湾纳入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之成为自己发展的附庸,而作为“附庸”的繁荣和增长,只是暂时性的,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真正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自主权的丧失。第二,即便是当时台湾社会所展现的繁荣和富裕,其背后也隐藏着并不难于发现的贫困和不公,比如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受到损害的农村和农民(还有山地民族、城市底层等),陈映真的小说 《忠孝公园》《归乡》 便描写过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受害,不过真正揭露这种受害的,是20世纪70年代影响甚巨的台湾“乡土文学”,而其中的代表作家黄春明、王拓、王祯和等,无一不是受到陈映真的影响才走上了那样一条揭露台湾社会发展不公的“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的。
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革命者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地去追求的,是贫困和不公的消除的话,那么他们的目标在富裕的台湾并没有实现。甚至,在那种虚假的繁荣和富裕背后,隐藏着让台湾陷入更固化和永久的不公平不自由、被压迫被奴役的巨大危机。然而,富裕时代的来临,使得一切都被掩盖了。而且,个人发家、小家庭致富的理想和文化,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发现真相、直面真相的愿望和能力,他们甚至也遗忘了曾为他们的幸福而奋斗和牺牲的人们——那些身死或被囚的革命者。
但陈映真没有忘。坐牢本可以让他选择遗忘,但坐牢时,他却因缘际会地遇见了20世纪50年代被囚的那些黄贞柏一样的革命者们。这是他青年时代读禁书时便朝思暮想的那群人,和他们的相遇——按照陈映真在其名篇 《后街》中所写——既给了他挺过牢狱之灾的力量,也让他更坚定了追随这群革命者的信仰的志向。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出狱后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沧海桑田般变化了的故乡——“后革命”或者说“告别革命”的台湾。身处这样的台湾,他怎么会不失落甚而悲愤?
四
所以,《山路》 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作品。
这种痛苦,在陈映真面对改革开放的大陆的时候,变得更甚。因为青年时代的陈映真深受鲁迅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一方面痛恨国民党专制,另一方面则把全部的理想和热爱都献给了对岸的红色中国大陆。
孤独和失落,正是陈映真自20世纪80年代末来到大陆直到去世这些年里的真实遭际。这些遭际,在大陆文坛已成为很多人都不陌生的逸闻趣事。很多年来,人们谈起这些逸闻趣事,带着对他的不解、不屑甚至讥嘲。不过,大概从最近十来年开始,情形却越来越发生着逆转。陈映真的那种传统左翼 (“统左”)立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他的文字和实践中,蕴含着解开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很多时代性难题的线索。比如他一直致力于批判和思考的美国霸权问题、消费主义文化问题、分离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亚洲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等等。这些课题,都是陈映真立足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整个近现代史所发掘和思考的课题。对于大陆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陈映真面对台湾时所见证、忧虑和思考过的问题,所以陈映真的思想蕴含着对我们的巨大启示。
陈映真的启示,可以展开为方方面面。但从精神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陈映真,其最大的价值,也是他相较于其他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在于他对于共产主义初心的坚持——他从大学时代寻找到这个理想,一直矢志不渝地坚持了一生。左翼理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变革和革命的浪潮,但这些浪潮后来大多受挫,甚至归于寂灭,幸存者也面临着艰辛。而在这个历史挫折中,太多人都沮丧了、虚无了,甚至转向了,而陈映真则是少数挣扎着站立起来,守护并呐喊着的知识分子之一。
《山路》 便是他挣扎着站立和守护的明证。蔡千惠的信里,一再提到那“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那是千惠的初心,也是陈映真的初心。20世纪80年代之后,陈映真走过那段“山路”继续跋涉,当年的战友和同伴几多凋零,有的离他而去,有的反戈相向,他依然倔强前行。当然,陈映真之受人敬重,还有方方面面,以我并不全面的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理想的坚持并不止于精神和言语上,而是扎扎实实地付诸于社会实践的——就像他早年以实际行动反抗国民党专制一样,在出狱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他创办 《人间》杂志、参与创办“中国统一联盟”、与台独派论战……以惊人的能量和战斗力,不断斗争着。
可能我在这里的描述,总是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一种生硬的概念化的境地,而真正的陈映真——那个远比我的描述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陈映真——在他的文字里,在他八十年的生命里。
五
《将军族》 是陈映真早期的代表作,小说叙述了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一个爱情故事:作者根据主人公的相貌特征为其取名曰“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三角脸”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年已四十,来到台湾退伍后,孑然一身,只能到“康乐队”里吹吹小喇叭;“小瘦丫头”是台湾花莲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生活所迫,家里把她卖到青楼当妓女,她坚决“卖笑不卖身”,并逃跑出来,到康乐队里跳跳舞或“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唯一美丽的地方——鼻子,瘦板板地站在台上”演女小丑。这两个人,一个无家可归,一个有家难回,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使两个人迸出了爱的火花。“小瘦丫头”的遭遇使“三角脸”这个曾经一向“狂嫖滥赌的独身汉” “油然地生了一种老迈的心情”,他真正地关心起这个身形瘦小、无依无靠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小瘦丫头”;有家难回的“小瘦丫头”对这位“外省人”也产生了好感。于是, “三角脸”做出了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在一个夜晚,悄悄把自己的三万元退伍金留在“小瘦丫头”的枕边,悄悄离去。而“小瘦丫头”并没因他的帮助而脱离苦海,反而被嫖客弄瞎了一只眼。但想见“三角脸”的信念让她活了下来,并于五年后重逢。只是,“小瘦丫头”怕自己身子不干净愧对“三角脸”,“三角脸”说“我这副皮囊比你还要恶臭不堪”。于是两个人为了纯洁地结合在一起,决意放弃生命,一起自尽于甘蔗林。
从题材上看,这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并辅以现代派的技巧,把一个来自大陆的国民党退伍兵与台湾本土姑娘之间按常理不可能发生的感情,写得真实感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底层民众,“给予举凡丧失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从立意上看,作品不仅讴歌了人间真情,且包含着对人生、對社会的思索,借此严肃地探讨了迁居台湾的大陆人与台湾省本土人之间的关系,传达了希望在台湾的“分离或有相分离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的心声。从现实意义来看,《将军族》 之所以拨动海峡两岸许多人的心弦,就在于它契合了希望统一的共同愿望。正如作者所言,“一个分离和对峙的民族,是残缺和悲伤的民族”,“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团结”。这个无比真诚的统一情结,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分别为“大陆人”和台湾“本省人”,通过这两个小人物真诚关心和相爱,表现了作者消弭两岸隔膜的愿望。两个人物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台湾和大陆不可分离,寄托了作者“一个中国”的理想。
《将军族》 在创作上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技巧,通过象征、暗示、时空交错等手法,使故事情节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动、现实与回忆交叉切入,具有明显的跳跃性。无论是“外省人”“三角脸”在台湾的“沧桑传奇”,还是本省人“小瘦丫头”的不幸经历,要么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动而展现给读者,要么通过人物对话来呈现,既避免了叙述人不必要的交代,又在今昔联系中增强了人物情感的浓度和历史的沧桑感。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