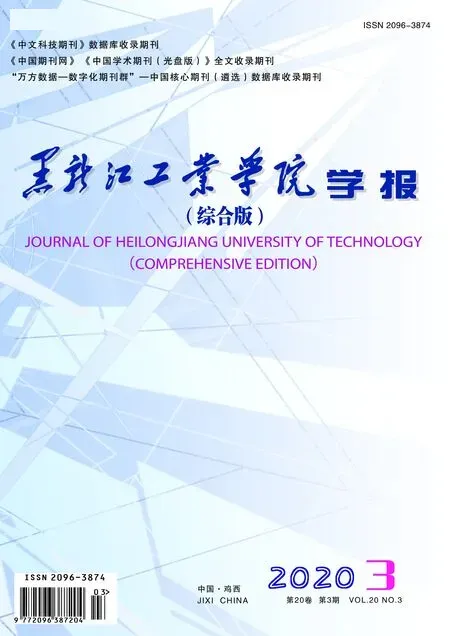常用词“带”与“携”的“携带”义发展及更替
2020-06-02崔蓝月
崔蓝月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1]中指出,常用词“主要是指那些自古以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经常会用到的、跟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词”。“带”作为现代汉语常用词,其发展历程值得关注。同时,汪维辉提及“携/带”存在变化更替关系,为我们考察“携带”义词汇的演变做出了启发。关于这一问题,谢玥、刘红妮(2015)[2]对“带”对“携”的替换过程有所考察,但对于“携”和“带”的“携带”义发展路径考察不足,对于“携带”义与“牵引”义“佩带”义未能进行很好地区分,此外对于元代文献考察不足,认为“带”对“携”的替换时期为元代。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带”与“携”的“携带”义发展路径进行了讨论,并对“带”与“携”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对“带”替换“携”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携”与“带”的“携带”义发展路径
1.“携”的“携带”义发展路径
“携”的本义是“提”,《说文解字》:“携,提也。”在先秦时期,“携”已经从其本义“提”发展出引申义“牵引”:
(1)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礼记·曲礼上第一》)
郑玄的注中注明“提携,谓牵将行”。而“携”从“提”发展为“牵引”主要是因为用手提着的对象必定跟施事方之间有伴随的关系。
(2)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诗经·板》)
郑玄的注中说“如取如携,言必从也。”用“携”来表示“跟从”,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携”的“提”本义当中包含的施事方与受事方之间的伴随关系。蒋绍愚《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3]中指出,“一个词经常处于某种这种表示语法意义的语境中,这个词原有的词义淡化,逐步吸收了语境的语法意义,形成一个新的意义”,这就是“语境吸收”。在“携”的使用过程中,其所在语境当中存在的施事方与受事方之间的伴随关系被吸纳进“携”,和其“提”的手部动作结合,同时,其“提”的本义中表示“位移方向为向上”的语义淡化甚至消失,由此发展出了“牵引”义。早期,“携”的“牵引”义使用还是有较大局限的,多强调手部这一动作接触点,且受事对象较为局限,多为妇女、老幼等群体,符合需要牵引这一客观需求:
(3)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诗经·北风》)
(4)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战国策·齐策四》)
而在后期发展中,“携”搭配有生名词出现的语境发展到一些时间跨度比较大、位移距离比较长的情境,如:
(5)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羈旅入京师。(班固 《汉书·翟方进传》)
(6)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范晔 《后汉书·赵憙传》)
对于这样的语境,很难说“携”是指保持牵引这一动作,但因为对象依旧局限在弱势群体,因此其“牵引”义还不能说完全消失,只是开始弱化。同时,两汉时期“携”也开始出现与无生名词搭配的情况,不过较为少见,且基本局限为“剑”这一特定对象,依然是其“提”本义。
(7)仇牧闻君死,趋而至,遇万于门,携剑而叱之。(刘向 《新序·义勇》)
(8)樊、酈、曹、灌,携剑推锋。(班固 《汉书·燕剌王刘旦传》)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携”已经从“牵引”发展出明确的“携带”义了,其搭配对象明显可看出并非需要或者可以用手牵引的对象。
(9)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干宝 《搜神记》卷三)
(10)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讬,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刘义庆 《世说新语·德行》)
在例(9)中,郭璞不会直接用手牵婢女而去。例(10)中,“王欲舍所携人”的“携”显然不是“牵引”,而是指位移过程中有伴随关系的行为,也就是已经与“牵引”义明确区分开的“携带”义。
“携”可与无生名词搭配的“携带”义也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11)当有老公从东方来,携豚一头、酒一壶。(陈寿 《三国志·魏志·管辂传》)
(12)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刘义庆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袁宏《名士传》)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携”的“携带”义是按照“提”—“牵引”—“携带”发展而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携”才出现完全脱离“提”或“牵引”义的可与无生名词及有生名词搭配的“携带”义。
2.“带”的“携带”义发展路径
“带”在先秦时期则基本作为名词使用,含义为用以束衣的腰带,《说文解字》:“带,绅也。”
(13)容兮遂兮,垂带悸兮。(《诗经·芄兰》)
(14)若父则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带。(《仪礼·士相见礼》)
偶有作为动词“佩带”使用,不过并不多见,如:
(15)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礼记·月令》)
当“带”作为“佩带”义动词使用时,对象均为需要被固定在腰部佩带的用具或装饰物,其“佩带”义是因为其“腰带”本义具有“束缚”义引申而来。王念孙在《广雅疏证》[4]中已经有所揭示:“带者……著于衣如物之繫也。是束之义也。”“带”的“佩带”义在汉代已经固定下来并成为常见用法:
(16)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周礼·考工记·玉人》)
汉代郑玄注:……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带之。
同样是表达“佩带”义,《周礼》原文用“服”,而到了汉代的注释中,已经用“带”了。
另外,也是两汉时期,“带”开始出现“携带”义,不过仅见两例。
(17)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
(18)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班固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带”的“携带”义用法较为多见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19)献帝纪曰:“辅……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璎。(范晔 《后汉书·董卓列传》)
(20)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刘义庆 《世说新语·德行》)
(21)诸天神地神山神皆来侍卫带是经者,一切灾害不敢干犯,是为菩萨已得神通。(《佛说菩萨内戒经》刘宋三藏求那跋摩 译)
但总的来说用例还是较少,且依然未见与有生名词搭配的情况。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带”是按照“衣带”—“佩带”—“携带”发展出了“携带”义,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止,表“携带”义的“带”只与无生名词搭配。在这一时期,“携带”义语义场词汇中,“携”的用例要远远超过“带”。

表1 魏晋南北朝“携”与“带”表“携带”义情况①
二、“带”与“携”的竞争及替换
1.唐至元:“带”与“携”的竞争期
这一时期是“携”与“带”的竞争期,“携”在初期仍处于“携带”义词汇的主导词地位,例:
(22)巨川为韩建副使。朱令公军次于华,用张濬计,先取韩建,其幕客张策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诣辕门请降。(孙光宪 《北梦琐言》卷十五)
(23)帝意令岛继长沙故事。敕曰:“……今既却携卷轴,潜至京城。遇朕微行,闻卿高咏。……”(何光远 《鉴诫录·贾忤旨》)
(24)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陈鸿祖 《东城老父传》)
(25)庚申岁,客辇下,会菖蒲节,余偕一时好事者邀子固,各携所藏,买舟湖上,相与评赏。(周密 《齐东野语·子固类元章》)
(26)内四僧偶別门徒,至中途忘携雨具,还取之,至江干则渡舟解维矣。(周密 《癸辛杂识·湖翻》)
另外,这一时期“携”后常有省略宾语,而在前文中指出受事对象的情况。
(27)丰干乃名为拾得,携至国清寺。(释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
(28)姓沈氏,年七岁父携入白重院。(释道原 《景德传灯录》卷八)
(29)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拣退银绢甚多,逼令携归。(周密 《齐东野语·淳绍岁币》)
这说明“携”的“携带”义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其发展过程中,受事宾语有生名词与无生名词的比例逐渐失衡,有生名词的比例小于无生名词。而在这一时期,虽然“带”在占比情况上要远低于“携”,但是从受事宾语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带”的使用情况最为均衡。首先,“带”的受事宾语中有生名词与无生名词比例相差非常小,并且,有生名词中人与其他生物均有。
(30)九月十日,闻王旻带所纳叛军来,襄人疑其反覆不常。(周密 《齐东野语·端平襄州本末》)
(31)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至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癸辛杂识·白蜡》)
(32)皇甫殿直道:“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过去,带一管锁,走出门去,拽上门,把锁锁了。(《简帖和尚》)
(33)当日歇了一夜,至次早,安住径往开封府告包相公。相公随即差人捉刘添祥并晚婆婆来,就带合同,一并赴官。(《合同文字记》)
同时,“带”还可以接抽象名词做宾语,说明“带”的用法发展得更为均衡:
(34)李霸遇问道:“你曾带得来么?”贵人道:“带得来。”李部署问:“是甚的?”郭大郎言:“是十八般武艺。”(《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表2 唐至元“携”与“带”表“携带”义情况②
2.明清:“带”对“携”的替换期
这一时期,“携带”义词汇的主导词已经可以确定为“带”,只有《牡丹亭》中“携”占比稍高,这也许与《牡丹亭》相对而言较为文雅的语言风格有一定关系。
(35)管他人话鬼话,带了些黃钱,挂在这太湖石上,点起香来。(汤显祖 《牡丹亭》第三十五出《回生》)
(36)王冕道:“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吴敬梓 《儒林外史》第一回)
(37)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第三回)
而“携”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不再作为“携带”义词汇的主导词,多用于“携手”“牵引”义:
(38)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宽夹道。(曹雪芹 《红楼梦》第三回)
(39)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吴敬梓 《儒林外史》第一回)

表3 明清“携”与“带”表“携带”义情况③
三、其他包含“携”“带”的表“携带”义的双音节词
1.携带
大约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表“携带”义的双音节词“携带”:
(40)一日,太尉要到郑州上冢,携带了家小同行。(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
(41)每次回家,狄希陈必定白煮十数个鸡蛋,携带一大瓶浓酾的烧酒。(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六十一回)
但“携带”一词初期并不单指使受事方与施事方发生附着伴随性位移,而还有“提拔某人”“使……与一同做某事”的用法,且两种用法比例较为均衡:
(42)又把吴主管携带做了驿丞,来保做了郓王府校尉。(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第三十回)
(43)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携带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寻常小可。(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
(44)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萨,在这里洗澡哩,也携带我和尚洗洗何如?”(吴承恩 《西游记》第七十二回)
(45)石勇道:“江湖中只闻得哥哥大名,……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是必携带。”(施耐庵 《水浒传》第三十四回)
到了清代,这两种语义也依然都有所沿用:
(46)前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带下凡,如今尘缘已满。(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
(47)你若中了才女,你父母面上荣耀,……倘能携带若花、婉如也能得中,那更好了。(李汝珍 《镜花缘》第五十回)
但表示使受事方与施事方发生附着伴随性位移语义的“携带”在用例上已经远超过“提拔某人”“使……与一同做某事”的用法。
“携”与“带”在发展出“携带”义后均有使受事方与施事方共同发生位移的语义,并且施事方处于主导地位,可抽象出施事方处于较高地位、使受事方追随自己或引领受事方前进的语义,因此可演变出受事方因施事方而得以提高地位或有机会共同参与某事的语义。但因为“提携”一词同样有此语义,且“提”“携”均指位移方向向上的动作,更符合语用要求,因此在“提拔”语义场内“携带”被“提携”取代,其“提拔”义逐渐弱化消失,最后只保留了“携带”义。
2.将带/带将
“将带”一词在唐代已有使用,并且一直持续到明代。
(48)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司马迁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正义:将,谓将带群众也。(张守节 《史记正义》)
《史记》引文中用的是“将”,而《史记正义》中做注解时用“将带”来解释“将”,说明这时已经有“将带”接有生名词表示“携带”义了,并在之后用例颇多:
(49)数中有掌印柴夫人,理会得些个风云气候,看见旺气在郑州界上,遂将带房奁,望旺气而来。(《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50)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崔待诏生死冤家》)
(51)知远令郭威将带黄金玉带等自随。(《新编五代史平话》)
(52)朱温未听得万事俱休,才听得后,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却不叵耐这黄巢欺负咱每忒甚!”时下间,便带将他的老小、部所属军,不辞黄巢。(《新编五代史平话》)
3.拖带/带挈(挈带)
与“携带”类似,“拖带”也同时具有“提携、提拔”与“携带”两种意思。当“拖带”表示“携带”义的时候,对象为人,而且往往是受事方对施事方有所请求,我们不能说其“携带”义是可以与“提携”义完全区分开来的。
(53)(末)惭愧,拖带一道行。(净)你命快,撞着我一道行。(《张协状元》)
(54)(末、净)我每等来,它做得官时,我两口也得它拖带。(单纯表“提携”义而无“携带”义)(《张协状元》)
(55)俺是高丽人,汉儿田地里不惯行。你把似拖带俺做伴当去,不好那?(《原本老乞大》)
与此情况相似的还有“带挈”(挈带)。
(56)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十五贯巧言成戏祸》)
(57)行瑜度不能免祸,乃挈带家小,突围走遁。(《新编五代史平话》)
四、结论
表“携带”义词汇的主导词“携”与“带”在先秦两汉时期各自向“携带”义发展。其各自所接受事宾语也有一定演变,“携”后无生名词做受事宾语比例的增加与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比例的失衡,以及“带”所体现的有生名词与无生名词在其受事宾语比例中的渐趋平衡有利于“带”成为“携带”义词汇的绝对主导词。另外,“带”的“携带”义由其“束缚”义发展而来,受事方与施事方结合更为紧密,更符合“使受事方与施事方发生附着伴随性”位移这一语义要求中对于受事方与施事方紧密关系的强调要求,而“携”由“提”到“牵引”义再发展出“携带”义,对于双方关系的强调要弱于“带”,这也最终影响了“带”取代“携”成为“携带”义词汇主导词。
总的来看,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携”与“带”各自由其本义向“携带”义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携”的“携带”义出现于两汉,要早于“带”的“携带”义出现,“携”是早期“携带”义词汇主导词。而唐宋元时期应当可以看做是“携带”义词汇的同义竞争时期,在这一竞争过程中“携”的搭配中无生名词与有生名词比例逐渐失衡影响到了下一阶段“带”对“携”的替换。到了明清时期,“带”成为发展趋势始终向上的“携带”义主导词,“携”则最终被“带”取代,用例远少于“带”。另外,在各个时期曾出现不同的双音节词来表示“携带”义,最后“携带”成为了其中的主导,而其它双音节词的“携带”义用法逐渐消失。
注释
①本文所有表格中均以“a”代指有生名词、“b”代指无生名词、“c”代指抽象义名词。
②表格中统计语料包括:王梵志诗,敦煌曲子词,包括《冥报记》《游仙窟》《宣室志》《蒋子文传》《北里志》《鉴诫录》《次柳氏旧闻》《柳毅传》《东阳夜怪录》《博异记》《长恨传》《东城老父传》《非烟传》《红线传》《霍小玉传》《集异记》《离魂记》《李娃传》《柳氏传》在内的文言小说,包括《伍子胥变文》《捉季布传文》《孔子项讬相问书》《董永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秋胡小说》《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在内的敦煌变文,《北梦琐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刘知远诸宫调》,《景德传灯录》,《齐东野语》,《虚堂和尚语录》,《癸辛杂识》,《伊川击壤集》,《老学庵笔记》,包括《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合同文字记》《快嘴李翠莲记》《洛阳三怪记》《阴鸷积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刎颈鸳鸯会》《杨温拦路虎传》在内的《清平山堂话本》小说,包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在内的《古今小说》,包括《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陈可常端阳仙化》《崔待诏生死冤家》《范鳅儿双镜重圆》《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在内的《警世通言》,《董解元西厢记》,《张协状元》,《原本老乞大》,包括《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汉高皇濯足气英布》《张千替杀妻》在内的元杂剧,包括《汉宫秋》《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包待制陈州籴米》《杀狗劝夫》《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薛仁贵荣归故里》《裴少俊墙头马上》在内的元曲,《新编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
③表格中语料分别为包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滕大尹鬼断家私》《杨八老越国奇逢》在内的《古今小说》,包括《金海陵纵欲亡身》《十五贯巧言成戏祸》在内的《醒世恒言》《金瓶梅词话》《老乞大谚解》《牡丹亭》《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