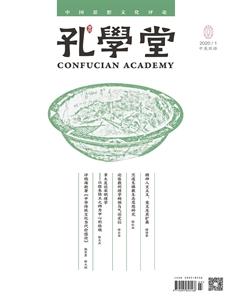贵州自觉的历程:从地理空间自觉到人文价值自觉
2020-06-01周之翔
周之翔
摘要:从明代地理空间意识的建构与自觉,到清代黔人修黔志的身份意识自觉,到清末民初黔人建黔学会的文化意识自觉,到当代提出“多彩贵州”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和近些年提出“贵州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自觉,基于反思与觉醒的贵州意识历经六百余年,完成了一轮深刻的自我认识,为黔学学科建构提供了方法论:要运用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和分析、解释工具,从贵州人文精神入手,回溯贵州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以服务于面向未来的贵州人,并致力于培养拥有未来的新贵州人。
关键词:黔学 贵州意识 贵州人文精神 学科建构 自觉
置于长时段的贵州发展史来考察贵州人文精神的提出,绝不可等闲视之,它其实是历经千年积淀与淬炼的贵州精神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斷运动和人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自然结果,是贵州人文价值自觉的标志。这为黔学的学科建构指明了精神价值基座和思想文化内核,奠定了黔学学科建构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
我们知道,要探讨黔学和黔学的学科建构,首先要追溯贵州的思想文化历程,更要追溯这个思想历程中基于自我认识与觉醒的贵州意识的部分。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文化与文明都是基于人类的自我觉醒,从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到部落、部落联盟、方国与国家意识的自觉与形成,由此才逐步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史与人类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历史。可以说,反思与自觉是国家文明与各类地域性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关键要素,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从1852年贵州学政翁同书提出“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而创生“黔学”之名,到20世纪80年代贵州学者再度提出“黔学”概念,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贵州各类学术机构纷纷成立以“黔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可以说“黔学”本身已是一个具有160余年历史纵深的概念。但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黔学”的内涵并未达成可信服的共识,而黔学的学科建设也方法未明。因而,从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探索贵州意识自觉的发生、发展与演进的历史,对于深刻理解和认识黔学的问题意识所在、黔学的历史定位以及黔学的内涵、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是十分必要的。
反思贵州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史,也就是追溯对于贵州的发现与认识的历史,既有基于他者的唤醒,也有基于黔人的自我反思与自觉。而与认识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对贵州的认识也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对所谓“黔”的地理空间的认识开始的。
一、“黔”地理空间意识的自觉 [见英文版第25页,下同]
正如学者所指出,“黔”作为地域名称,直到明代贵州建省(1413)以前,都只是一个动态的地域称谓。从战国时期楚国的属地“黔中”,到唐朝时期的黔中道,“黔”所指的地域范围或广或狭,都不能覆盖今天作为行政区划的贵州省境。今天贵州省境的一些地域,在明代以前,也是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并且有鬼方、夜郎、且兰、牂牁、犍为等名。这说明,黔地在明代建省以前数千年,没有作为一个具有某种统一特性的地理空间而为人们所认识。而是经过数千年各方势力之间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的长期互动,到明王朝时期,人们才意识到黔地无论作为行政区划还是作为文化、经济与族群的承载地,本身已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尽管战国时期已经有“黔”之地域命名,尽管这个命名本身也是一种基于文化观察的文化现象而有其思想史的意义,但作为独立的地域空间意识的自觉,“黔”直到明朝才开始实现。直到清朝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后,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以及湘黔边境各卫划归贵州,这一过程才最终完成。
黔地地理空间意识自觉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其自觉的过程本身就在塑造着这个地域空间里的文化、思想与学术。首先,黔地的地域空间范围与界限的确立,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它最根本的依据是黔地地域本身的地理肌理。换句话说,在黔地地域空间里,人们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亦即天人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特性,为明、清王朝划分行政区划,实现有效政治管理奠定了基础。同样,明、清王朝将黔地独立出来,设置贵州行省,正是意识到了黔地作为地理空间的独立性,而加以了尊重与肯定。其次,黔地地域空间范围的确立,使基于长期的天人互动而形成的各族群的生存与生活智慧,能以整体面貌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为黔地地域性文化提供了新的生长与发展空间。
作为黔地地理空间意识自觉的文化标志,当属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的完成。作为“最有范型意义的志书”,《黔记》在黔地地理意识自觉之后,以完备的志书体例,全面总结了贵州的地方性知识,实际上是较早的一次对“黔学”的研究与总结。诚如同时代的贵州人邱禾实所总结的地理、人物与文献的关系——“地之重人也以山川,而人之重地也以文献”,郭子章的《黔记》,同时代的人已认为其意义在于使世人对贵州的认识“番然改观”,即将使国人重新认识贵州,确立对贵州的印象,并由此而推进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孔子“欲居九夷”和阳明为官贵州龙场驿的思想史意义。
二、黔人身份意识的自觉 [26]
有了贵州,也就有了贵州人,但其是否认同、接受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贵州生活着49个民族,其中有18个世居民族。而对于地域身份意识的自觉与认同,又是地域文化中地域意识产生与壮大的必要条件。若无黔人身份意识的自觉,构建黔学核心的“黔人”的主体意识即无法形成,黔学就始终只是一种异域之学,一种关于他者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而不是关于黔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成长的知识体系与价值系统。
追溯黔人身份意识自觉的历史,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汉族移民和因各种原因客居贵州的汉族士人对黔人身份的认同。邱禾实指出明代士人对自己黔人身份多有不认同的现象,他说:“宇内往往少黔,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固无恠然。乃士生其间,或亦谬自陋,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由于黔地经济落后,汉夷杂居,而且夷人居多,所以汉族官员不愿意来黔地为官,来当官的也急着走,这本不奇怪;怪的是出生在贵州,户籍也在黔地的汉族士人,也不愿以贵州作为自己的籍贯,而以先世的籍贯为籍贯,将作为贵州人视为一种侮辱。邱禾实对此“居常每叹之”。可见,直至明代晚期,像邱禾实一样,认同自己贵州人身份的汉族士人并不多,他们更愿意认同自己祖先的地域身份。
而对于世居少数民族来说,有明一代,更无以黔地地域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意识。王阳明的感受可以说明已归属明王朝管辖的世居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他才来贵州龙场驿时,感觉自己像来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唐尧虞舜时期。龙场周边土著百姓不仅没有贵州人的身份认同,也没有明朝子民的身份认同。此外,在明代到清朝前期,贵州地区还存在大量的不归属中原王朝,也不受土司管辖的“生界”,其中的各土著民族各依其生存智慧生活于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中,中原王朝不知有他们,他们更不知有中原王朝,甚至连附近的土司也不知其详,也就更谈不上黔人的身份认同了。
不难看出,黔人身份意识的自觉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明代邱禾实、陈尚象等人已明确认为“余黔人”,并认为明代贵州已“观文成化”,“民鼓舞于恬熙,士涵泳于诗书,亦既彬彬质有其文矣”。他们算是汉族士人中,较早具有黔人身份认同意识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有明一代,即使认同自己黔人身份的汉族士人,其认同仍是基于中原文化认同,而非基于对黔地文化的认同。甚至其思想依据还是孔子“欲居九夷”与阳明为官龙场驿,以离开无道之中原而避隐的隐士意识。
大体上,直到有清一代,汉族士人才基本认同自己的黔人身份,而且这种身份认同已包含对黔地文化的认同。如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莫友芝、郑珍、黎庶昌等,他们极其重视乡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积极参与到黔志的修撰工作中来,表现出明显的贵州气质。曾国藩评价黎庶昌的文风,指出:“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莫友芝、郑珍合修的《遵义府志》,以黔人修黔志,运用汉学治经之法治史,突破前人志书义例,增加“金石”“农桑”“坑冶”等门目,不仅大大增加了黔地地方性知识的门类与体量,更表现出基于发展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本土关怀。黎庶昌积极收集、网罗黔地故事,先后收集了《牂牁故事》《全黔国故颂》等数十万字的资料。至于世居少数民族的黔人身份认同,虽有较早的改土归流后彝族学者安吉士、安淦辛父子主动修撰《贵州新志》,体现出鲜明的贵州认同,但大多数少数民族例如苗族等的黔人身份认同,似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才基于国家认同而认同了自己的黔人身份。
总之,黔人身份认同从思想文化来看,既有基于中原学术贵州地方化的认同,也有基于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碰撞、交融、渗透之后的认同,这使得“黔人”概念本身成为黔学的重要内容,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三、黔学、黔学会与黔地的文化自觉 [28]
身份認同显然既基于自然地理空间的认同,又有其思想学术为内核的人文基础,只是此种人文环境或隐或显,不像地理环境一样易于识别与觉察,所以,何时形成了黔地之学是一回事,而何时意识到、认识到黔地有学则是另一回事。
明代郭子章已提出“黔之学”,他说:“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榷鲁,未有学也。黔之学自元始,元有顺元路儒学,有蔺州儒学。”显然,郭子章所提出的“黔之学”,并非指黔地的思想学术,而是指黔地由中原王朝主持开展的儒学教育和教育体系的建设。当然,这种由官方开展的儒学教育及其体制的建设对“黔学”来说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首先,黔地的儒学及其教育体系的建构本身是黔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次,官方建制化的儒学教育,相当于在中原文化与黔地本土文化之间开通了一条学术“官道”,必然大大拓展中原文化与黔地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中原思想学术及其理论体系,无论作为外来的、陌生的异质的文化,还是作为思想学术的镜子和思想方法上的他山之石,都将年深日久地不断唤醒黔地本土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事实上,就中原文化在黔地的扎根、生长与开花结果来说,于明代中期已蔚然可观,上文所引陈尚象等言贵州已“观文成化,民鼓舞于恬熙,士涵泳于诗书,亦既彬彬质有其文矣”,并非夸大之语。
与郭子章不同,清代咸丰年间江苏籍学政翁同书提出的“黔学”概念,则确然是指黔地的思想学术了。他说:“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公始,文成尝主讲文明书院矣,即今贵山书院是也。”进而指出阳明在贵州:“悟反身之学,揭良知之理,用是风厉学者,而黔俗丕变。”在这里,翁同书基于中原文化的视角,回望了贵州的思想学术,指出阳明龙场悟道和文明书院讲学是贵州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学术史之肇端。稍后,黔籍学者莫友芝更深入地考察了贵州的思想学术史,指出明代黔籍学者易天爵是贵州建省以后的“文教鼻祖”,他是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著有《易经直指》《群经直指》等。而阳明的黔籍首传弟子陈文学与汤伯元则是传承阳明良知之学,开创“黔学”的本土学者。莫友芝的考察,不仅追溯了贵州儒学思想史的肇端(陈文学与汤伯元),更考察了儒学经学史的开创者(易天爵),同时还将二者落实到了黔籍学者身上,显然表明了他对本土学者的思想学术与籍贯的特别关注,无疑代表了贵州学者对本土思想学术的自觉。
如果说黔学与黔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自觉是基于“中学”和“中学”视域下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那么,光绪二十三年(1897)经贵州学政严修提出,由黔籍学者雷廷珍等创立的“黔学会”,强调经世致用和强国富民,则是基于国家近代化历程中,“中学”与“西学”碰撞视域下的地域文化的反思与审视。这既是对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变法维新、富国强民运动的支持,也是在此背景下,基于国家和贵州的近代化而对贵州思想文化与教育的重新认识。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人、教育家任可澄出任黔学会会长,在贵州推广宣传新科学、新思想,敞开怀抱拥抱西学,是对这一思想风潮的继续推动。可见,“黔学”再次出现在贵州的历史上,恰恰是对过去以“中学”为内核的黔学的反思,黔学的内涵也转变为以推动贵州近代化为问题意识、以推进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改造贵州固有思想与学术为目标的现代学术。
传统黔学的近现代转型正如传统“中学”的转型,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黔地的文化自觉,只有经过反思式的自觉,才能走出基于地缘与血缘等的自然因素而建构起来的思想学术传统,进而在以理性规则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中获得新生与发展,当然,这需假以时日。
四、多彩贵州与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 [29]
然而,无论是根于中原文化视角的翁同书、莫友芝的“黔学”,还是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严修与任可澄的“黔学会”所代表的黔地的文化自觉,仍然是笼罩于“华夷之辨”范式下的地域文化认知,世居贵州的17个非汉族族群的文化不是被漠视,排除在“黔学”之外,就是被视为“黔学”的异质部分,所谓“鸟言卉服”,是需要“丕变”的夷俗。新中国成立后,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基本原则,黔地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各世居少数民族的古籍以及口传文献得到整理和发掘,他们灿烂的历史文化终于抖落被各种文化偏见所蒙上的尘埃,成为照亮黔地未来的璀璨明珠。这为构建新的“黔学”界定了合理的视域和清晰的内容边界,也为如何准确概括、表述这一丰富、多元的地域学术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以“夜郎文化”“高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来指称民族平等视域下的贵州文化,都不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显然,其困难是巨大的,有待于更深刻的贵州意识的自觉。
2005年是贵州意识自觉的重大时间节点,贵州省委宣传部提出“多彩贵州”的概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表征。它表明随着贵州意识的不断自觉,贵州丰富的思想文化的特性得到了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概括与表达,它也象征着贵州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所谓贵州文化主体意识,是指贵州摆脱各种文化比附与模仿,对自身作为地域文化的特性可以准确言说和轻松驾驭。这使黔地各民族及其文化彼此之间获得新的相处模式,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通过各自尽情绽放、争奇斗艳而呈现出一个美丽多彩的共同的贵州文化;同时也使贵州和全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相处能更平等、互动能力更强。
“多彩贵州”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仅从贵州意识的自觉历程来看,“多彩贵州”的提出,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跳出华夷之辨和以教化为主的中原学术中心主义视角,跳出近代以来弥漫思想学术界的科学主义视角,是对作为整体的黔地文化与思想学术的全面肯定。由此,一直隐没在思想史视野的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与习俗,以及文字典籍与活态的口头经典,都得以以主体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奉献给世界。而作为贵州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流布贵州的中原思想学术包括儒学、佛教与道教文化,在多彩贵州的语境中,也更能彰显出鲜明的黔地特色,获得贵州式的言说方式。以孔学堂为代表的当代中原儒学传播与研究中心,和尽情展露贵州民族风情的“多彩贵州风”,在爽爽贵阳并行而不悖,相得益彰。
从黔地的思想历程来看,“多彩贵州”的提出,探及了贵州文化多元一体、万彩同春的特性,对黔地地理空间多元、族群多元、思想文化多元而又具有统一的深层结构的本質特征做了很好的总结和表述,同时又体现出了基于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谦逊、包容的文化品格。
五、贵州人文精神与价值自觉 [30]
众所周知,广义的文化包括四个层次:第一是物态文化层,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如各族群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和房屋、庙宇等建筑物,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第二是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如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第三是行为文化层,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第四是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将之与贵州意识自觉的历程进行对照,不难发现:明代黔地地理空间意识的自觉正是对贵州物态文化的认识,明清时期黔人身份意识的觉醒和黔学会所代表的文化自觉可以说是对贵州制度文化的认识,而“多彩贵州”的提出所代表的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则可以说是对贵州行为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作为省域文化的形象符号,“多彩贵州”无疑是十分准确、形象的,但还是仅停留在贵州文化的行为表征层次上,还没有触及贵州文化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心态文化层。
探索贵州文化的心态文化层亦即价值层面的任务,是在“多彩贵州”提出十年后随着贵州人文精神的提出而开启的。2016年1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同志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弘扬贵州人文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首次提出了“贵州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内涵。随着陈敏尔同志讲话的公开,旋即在全省展开了贵州人文精神的热烈讨论,并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吴根友指出:贵州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两个中国哲学命题为核心,并对其做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时代性与区域性阐释,表明贵州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了巧妙的历史“接合点”。与省外学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思考“贵州人精神”不同,本土学者麻勇斌研究员则更重视贵州人文精神的原生性与本土性,他指出:贵州人文精神,是贵州各民族适应生存环境条件和历史变迁的哲学思想、智慧知识和经验理念,不断接纳新的优秀文明基质叠累而成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迄今为止最为凝练和精准的关于贵州人文精神的概括。
显然,不管对贵州人文精神及其内涵如何认识与理解,贵州人文精神的提出本身已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这已触及贵州文化的最深层次——心态文化,可以说是贵州人文价值自觉的标志性事件。至此,我们可以认为,贵州人文精神的提出,标志着贵州意识完成了一轮基本的自觉,人们对贵州文化的认识已行进到了最深层的精神价值领域。从这个角度看,贵州在以“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为内涵的人文精神中,“天人合一”表征着贵州高原上天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塑造贵州多元地理空间与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内在动因,也是这种多元性、多样性的共同本质所在。“知行合一”表征着黔地人人关系,即指人们之间、不同族群之间依照共同的道德良知相处,而各自展现自身文化习俗的多姿多彩风貌;也指各族人们各依其善良本性与自己相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
总之,贵州人文精神直指对贵州地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价值的思考与揭示,成为一把打开贵州地域性知识系统与精神世界宝库大门的钥匙。这为黔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精神价值指向:黔学是以发掘和弘扬贵州人文精神而服务于贵州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地域性学科。进而也为黔学学科建构提供了方法论:要运用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和分析、解释工具,从贵州人文精神入手,回溯贵州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以服务于面向未来的贵州人,并致力于培养拥有未来的新贵州人。
(责任编辑:杨翌琳 责任校对:罗丽娟)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孔学堂的其它文章
- Xu Qi: The Imprint of Thought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Cultural Issues
- Qian Hai: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Serving Heaven and Emulating the Ancients: Western Han Confucians’Movement to Reform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Governance
- Early Modern Guangdong Academies and Their Academic Ethos: A Case Study of Zhu Ciqi’s Early Education Experience
- Nationalism and Spirit of Freedom: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Carsun Chang’s New Confucian Thought
- Ming–Qing Ritual-Based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hu Xi’s Doctrineof Ritual: The Dimension of Outer Kingliness in Neo-Confuc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