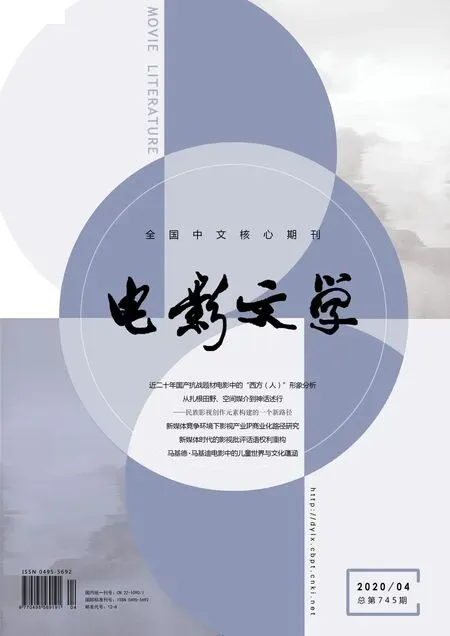“南京大屠杀”系列电影的新世纪演变与局限
2020-05-27黄娟
黄 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1937年12月5日,日军从三面包围南京,发起猛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六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奸淫、纵火、抢劫,无恶不作,惨绝人寰。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1985年,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南京人民在日军的屠杀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先后在多处大屠杀遗址设立丛葬地纪念碑。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无论是纪念馆、纪念碑,还是国家公祭日,都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与此同时,这样的立场与诉求也需要在精神、文化领域得到体现,尤其是在非常有影响力的影视业。新时期以来,国内确实出现了一系列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主要有《屠城血证》(1987)、《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南京1937》(1995)、《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黄石的孩子》(2008)、《拉贝日记》(2009)、《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九部。那么,这九部影片完成为“南京大屠杀”立碑的任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这九部影片的变迁史进行综合分析。这九部影片,以进入新世纪为界限,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由高到低:影片镜头的残暴指标直线下降
作为以残暴著称的历史事件,表现这一特点的镜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然而,这些电影作品以进入新世纪为界限,前后的区别非常明显。根据笔者对这几部影片中日军血腥、残忍、暴力镜头的统计,其时长和占比列表如下:

项目片名 总时长(含片头尾)正面血腥、残忍、暴力镜头侧面血腥、残忍、暴力镜头占比(含正侧面)《屠城血证》(1987)86分钟7分45秒32秒9.63%《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91分钟19分44秒21.68%《南京1937》(1995)117分钟17分58秒15.36%《五月八月》(2002)88分钟35秒2分37秒3.64%《栖霞寺1937》(2004)98分钟1分49秒1分2.87%《黄石的孩子》(2008)125分钟1分22秒1.09%《拉贝日记》(2009)134分钟3分35秒2.67%《南京!南京!》(2009)132分钟4分48秒3.64%《金陵十三钗》(2011)145分钟3分48秒2.62%
(列表说明:这里的侧面血腥、残忍、暴力镜头主要指采用声画分离的方式,用外围事物占据画面,用声音传达暴力的方式。凡是出现流血、尸堆画面的,即使并未拍摄兽行过程,也归为正面。单一击毙而未有显著流血画面的短暂镜头忽略不计。表内数据的误差控制在秒的单位范围内。)
由上述统计可知,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中对日军血腥、残忍、暴力行为的表现时长和时长占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另外,数据中未能体现的残暴指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虽然残暴指数很难用数据统计,但是却很容易被观众从感官上辨别。比如新世纪以前的三部影片,它们对日军残暴行为的表现各有侧重,《屠城血证》的特点是血腥,影片给人一种血淋淋的感觉;《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的特点是残忍,剖腹杀婴、热锅杀婴、奸杀老幼等极端残忍的行为都出现在这一部影片中;《南京1937》的特点是暴力,在表现日军施暴时的动作性很强。但是,不管侧重点有何不同,这三部影片在表现日军的残暴指数方面都是相当高的。与表现时长相适应,残暴指数也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显著降低。新世纪拍摄的几部影片中,《五月八月》是从儿童的角度展现南京大屠杀,《栖霞寺1937》是从佛教的角度展现南京大屠杀,所以这两部影片主要采用了侧面表现日军残暴的方式,正面的镜头很少,残暴指数很低。还有《黄石的孩子》,主要表现西方人士对战后幸存儿童的关爱,涉及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比较少,所以表现日军残暴行为的时长很短,残暴指数也很低。残暴指数略高的是《拉贝日记》《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这三部。但是,也远远低于20世纪的三部影片。也就是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中对日军血腥、残忍、暴力行为的表现时长、时长占比、残暴指数等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现出直线下降的显著现象。
二、由正面到侧面:影片题材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影片镜头的残暴指标直线下降,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新世纪前后,“南京大屠杀”系列影片对题材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20世纪拍摄的三部影片都是直接以“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作为表现对象的,虽然也分别选择了若干中心人物或家庭作为受害对象的代表,但都只是作为点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带动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面的理解。也就是说,主旨都是为了正面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其中,《黑太阳·南京大屠杀》没有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散点最多,且加入大量的纪实录像,有一种很写实的惨烈风格。《屠城血证》以医生展涛护送照片为中心事件,但基本上起一个线索作用,串联起社会各色人等在国难之际的多重面相和遭遇,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南京1937》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个日本妻子理惠子的角色,故事性最强,对中心人物的复杂心理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刻画,但人物仍然让位于事件,表达的重心是事件带给人物的惨痛遭遇。所以,这三部影片都是直接或间接扣住南京城命名,聚焦事件的意图不言自明。与这三部直接聚焦“南京大屠杀”正面表现这个事件的影片不同,进入新世纪以后拍摄的六部影片对题材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转换视角,反衬“南京大屠杀”。代表作品是《五月八月》《南京!南京!》。《五月八月》从两个女孩五月、八月的视角看“南京大屠杀”,孩子们天真、可爱、年幼无知,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饱尝人间冷暖、艰辛,反衬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无情。显然,这种转换视角后的侧面烘托的方式避免了对事件的正面表现。《南京!南京!》虽然有多个视角,但“由于陆剑雄的过早被枪杀和安全区里的人物(拉贝、唐先生、姜淑云以及其他几位国际救援者)视点的分散,有意无意间使得角川这一线索成为贯穿影片始终也是最为清晰的主线”。也就是说,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事实上成为主视角。于是,角川目睹惨象的内心触动、不堪忍受精神折磨而选择自杀的心路历程成为表现“南京大屠杀”暴虐无道的主力,这显然也是一种反衬的方式。而且,由于受制于角川这个视角,不得不花大量的笔墨来展现日军的日常生活和仪式,所以进一步稀释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正面表现。
二是背景化“南京大屠杀”,聚焦历史人物或历史原型基础上的虚构人物的表现。代表作品是《栖霞寺1937》《黄石的孩子》《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其中,《黄石的孩子》仅仅把“南京大屠杀”当成故事的起点,简短地交代了基本情况后就致力于叙述英国人乔治·何克如何克服困难,改变并保护、关爱父母被屠杀后移居黄石的孩子们的故事。《拉贝日记》虽然不像《黄石的孩子》那样把“南京大屠杀”处理为遥远的时代背景,但也仍然是把“南京大屠杀”背景化的,以德国人拉贝为首的国际人士始终是影片表现的核心。所以,对于拉贝在这场灾难中的心理、情感、取舍等花了大量的笔墨,观众看到的是以拉贝为首的国际人士的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把“南京大屠杀”处理为遥远的时代背景,还是近距离的舞台背景,这两部合拍片都有共同的旨归:传递西方价值观念。所以,“讲述南京大屠杀,实则是讲述西方自我,‘被看’的中国人及其民族灾难构成西方世界自我认知、评估的重要一极,这不仅映照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且彰显了理性、健康的国家形象。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对他国弱族的无私救助,隐藏着东/西方国家、民族命运的对比与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并未成为这些合拍片真正关注和思考的对象。至于国产片,《栖霞寺1937》聚焦以寂然法师为首的佛教僧人,主要叙述了他们在国难之时由分歧到统一,为保护难民所做出的牺牲与努力。《金陵十三钗》聚焦闯入教堂的十几个秦淮河妓女和一个伪神父,主要叙述了伪神父由自私自利、漠不关心到主动维护女学生,妓女们由借地避难、明哲保身到挺身而出、代替女学生赴虎狼之会的故事。和《拉贝日记》一样,这两部影片也毫无疑问以写人为主,“南京大屠杀”只是人物形象与精神得以凸显的舞台。所以,《栖霞寺1937》里有很多基于刻画佛教僧人需要的寺庙日常,《金陵十三钗》里有很多基于刻画秦淮河妓女和伪神父需要的言行,比如玉墨挪动腰臀的极富魅惑力的走姿特写,固然是勾引伪神父的需要,也分明是职业习惯和身份使然。一部影片主要的意图表达必然挤占最多的时间,也必然导致无法全面、深入地去反映“南京大屠杀”。因此,与其说这两部影片在讲述“南京大屠杀”,还不如说它们展现了各色人等在国难救赎中的勇气、智慧、力量与人性的良善,至于事件本身的反人类特征,则是无从反思的。
三、由政治主导到政治、经济合力:影片制作环境日趋复杂
福柯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影视作品讲述历史时,确实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讲述的层面和角度。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新世纪前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系列影片对比鲜明,直接原因是编导对题材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而处理的方式受制于个人的拍摄思路,个人又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于是,时代的需要自然会在拍摄理念上打下烙印。也就是说,时代影响思想,思想决定取舍。时代对拍摄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影响;二是经济上的影响。当然,除此之外,编导的个人风格也必然影响影片的处理方式,但是,凡是需要公映的影片,都无法回避时代的需求。个人风格的体现往往是在这个范围之下的有限施展。
20世纪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三部影片中的第一部就完全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在日本妄图篡改历史、拒不承认错误的时代背景下拍摄的。“1982年6月,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将其中记述的对别国的侵略一概称为‘进入’,并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减。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虽然中国就此问题向日方正式提出多次交涉,但是,“1986年5月,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7月7日,日本文部省无视日本国内和中、朝、韩等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最后批准了经过多次修改的《新编日本史》”。这就是著名的教科书事件。所以,1987年上映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接下来1995年上映的两部,也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局面和抗战胜利50周年的需要拍摄的,正如《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的导演牟敦芾所说:“日本全国各地民间已组织了‘南京大屠杀’宣传委员会,欧、美、中国香港也正组成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准备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举办活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活动,更是深入日本民间的一个教育机会,所以我要赶紧拍这片子。”因此,配合政治上的宣传需要,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真实面貌的拍摄目的决定了上述三部影片即使讲故事的风格不同,也必然直接聚焦“南京大屠杀”,正面表现这个事件。
然而,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对原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永三郎就日本教科书提出的第三次诉讼做出判决,判定了文部省要求删改“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行为是“违法”的。之后,日本的右翼学者和日本的进步团体之间就篡改历史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博弈,最后,真正采用涉及历史问题的教科书的学校极少,采用率不到1%。但是,这并不代表复杂的中日关系从此走向平和。相反地,由于右翼暗流的煽动,“在政府方面,进入21世纪后的最初几年里,日本的对华政策趋向的确也发生了愈加明显的变化,越来越表现出远去甚至对立的情形——不能心平气和地与中国交流……”在这种情形下,拍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目标上无须强调血证了,方式上也需要顾及敏感的中日关系。所以,2002年为纪念南京大屠杀65周年而上映的《五月八月》和2004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上映的《栖霞寺1937》都采用了尽量回避暴力镜头的侧面表现的方式,同时,主要内容也采用了转换角度或将南京大屠杀背景化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编导的拍摄目的决定的。正如《五月八月》的编剧徐小明和监制徐李凤明夫妇所说的:“在拍片的时候,我们起用的几十个小演员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影片拍完后,他们都记住了这段历史,我们最初的目的达到了。”《栖霞寺1937》的出品人是传真法师,他也谈到了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我1987年在栖霞寺出家后,听得最多的就是寂然法师反抗日本侵略者、保护难民的故事。后来我长大了,也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于是渐渐就有了拍电影的想法。”可见,无论是向孩子们普及历史知识,还是传播佛家的真实故事,都注定了这两部电影会采用非正面表现的方式。然而,也只有契合了时代的需求,才能让编导的拍摄目的成为现实而正常上映。所以,时代始终是拍摄目的无法回避的决定因素。
虽然新世纪初还主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诉求也开始在电影产业方面展现强大的驱动力。而且,随着外资的引进,政治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渗透)进一步复杂化。所以,中外资本在电影产业的合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为逐利而设置卖点,二是输入外资方文化。即使是涉及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也不例外。所以,《黄石的孩子》和《拉贝日记》这两部中外合拍片必然以外国人为英雄主义的主角,让历史事件退居背景,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并增加毫无必要的恋爱戏。在这两部影片里,中国人的形象被弱化、符号化。然而,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以《黄石的孩子》为例,其开头字幕部分就提示根据乔治·何克的真实故事改编,“但是读一读那些来自现实生活的经历和观察笔记,何克离开英国,游历了欧洲,见识了美国,评判了日本,最后选择了中国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中间,他自身作为被拯救者也对西方人有着强大吸引力。在他笔下,那些有名有姓的中国妇女、农民、难民、青少年……都栩栩如生。‘今天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事实确是如此:人民确实是无比英勇的。这种英勇精神存在于平凡之中,是我或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也是我望尘莫及的。’那些他帮助过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也反过来成为拯救者,感召并影响到何克的思考及行动”。显然,改编是在以合乎市场和政治目的的需要而非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拉贝日记》稍好一些,但为了凸显拉贝的英雄形象,增加影片的卖点,也进行了相应的虚构。这并不是说历史题材的电影就绝对不允许虚构,而是必须谨慎,必须符合艺术的真实。然而,在偏离艺术真实的改编道路上,本国资本主宰的影片也同样未能免俗。《南京!南京!》中的角川正雄自杀赎罪的形象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而《金陵十三钗》在“南京大屠杀”的悲惨语境下刻意表现美色并设置床戏就更让人无语了。无论是合拍片基于文化输出的选择性无视,还是本国片基于迎合西方口味的自我卖弄,都是政治与经济合力运营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历史题材的电影面临日趋复杂的制作环境。
四、现状与追求:拍摄“南京大屠杀”系列影片的意义
上述三个方面其实是彼此影响的因果关系,时代的更迭带来制作环境的改变,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中外意识形态和经济诉求的合力作用使得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系列影片必然越来越远离对历史事件的严肃审视,题材处理的角度也许会有不断的创新,但都难以重返正面表现历史事件的态度,残暴指标当然会降低,虽然这个指标与影片的质量无关,但肯定与对历史事件的正面关注程度有关。总之,新世纪以前的三部影片不为人物立传,只为还原历史事件用心的态度才是为“南京大屠杀”立碑的正确态度。新世纪以后的六部影片虽然也表现了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但一味地张扬人物其实是越来越远离正视历史事件的态度,也就无法真正地还原历史真相。同时,不管是正面地还是背景式地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与暴虐,都缺乏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的反思以及反法西斯、反战的诉求。也就是说,新世纪以后的六部影片有两个很明显的局限:一是以人物为中心,偏离了、淡化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现;二是没有处理好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人物无法成为揭示主题的有力支撑。当然,所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都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或证明这一历史事件的作用。这也是日本拒绝上映此类题材影片的原因。所以,拍摄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无疑是有意义的,但目前的影片还没有完成为“南京大屠杀”立碑的任务。
所谓为“南京大屠杀”立碑,指的是影片的艺术效果足以让全世界人民永远铭记并反思,让全世界人民感同身受并发自肺腑地抗拒日军之恶,永远维护正义与和平。正如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为“纳粹屠犹”立碑,震撼了全世界一样,人们在一系列荒谬事实中深刻领悟并永远记住了德国纳粹反人类的罪行,记住了那个历史倒退的黑暗时期,感同身受并发自肺腑地抗拒纳粹之恶,呼唤正义与和平。所以,拍摄“南京大屠杀”系列影片的意义,不能止步于简单地传播或证明,而应该以“为‘南京大屠杀’立碑”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既是历史的责任,也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当然是学习《辛德勒的名单》。事实上,拍摄“南京大屠杀”系列影片的编导并不缺乏学习《辛德勒的名单》的姿态。《栖霞寺1937》和《拉贝日记》都曾被称作“中国的《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南京!》也被人认为是有意学习《辛德勒的名单》,这说明大家都知道目标在哪里,但就是达不到那样的水平。除了日趋复杂的市场化的制作环境掣肘太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真正读懂《辛德勒的名单》的艺术密码。《辛德勒的名单》确实塑造了辛德勒这个鲜活的人物,但这个人物并不是影片的中心,他只是透视“纳粹屠犹”这一历史事实的角度,或者说是一根线索,导演的目的不是为了讲他的故事,而是为了还原、折射、批判、反思那段荒谬的“纳粹屠犹”的历史。这个角度的巧妙之处在于“辛德勒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所以他成了进入奥斯维辛这个暗黑世界和展示人性的明亮与阴暗的最佳入口,整部电影实际上是他弃暗投明的过程,人性的苏醒在斯皮尔伯格精准的节奏之下被表现得荡气回肠”。而且,这种人性的复苏并不是突兀的,而是在犹太人史登的促成之下逐渐发生的,十分真实(与一般的好莱坞英雄主义影片截然不同)。辛德勒的人性复苏是对“纳粹屠犹”之恶的最深刻的鞭挞,对善的最深情的呼唤。所以,他的故事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增加了可观性,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强化主题。除了辛德勒之外,纳粹军官阿蒙也是一个重要的附证。他既是一个施害者,也是一个受害者。他残酷无情,滥杀犹太人,枪毙女工程师的行为等同于枪毙真理;他爱上了犹太女人却违背本性,变态地自我压制。这个人物形象强烈地揭示了德国纳粹反人类的本质。因此,这个影片的重要人物并不是影片的中心,他们只是抵达影片中心的途径。角度的巧妙、细节的真实、人物的鲜活都是这部影片成功的法宝。
然而,反观国内的抗战影片,新世纪之前的作品欠缺深化主题的有利角度,往往流于暴力与血腥的展现,趋于同质化而表达力太弱;新世纪之后的作品虽避开了对暴力与血腥的大面积展现,但往往上演的是英雄人物拯救难民的戏码,历史事件成为衬托英雄人物高大形象的背景。也就是说,与《辛德勒的名单》相比,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历史灾难题材,《辛德勒的名单》有令人震撼的、恢宏的史诗气质,而中国的抗战电影却千篇一律或离题万里。虽然《南京!南京!》尝试了新的切入角度,可惜并不成功,相反地,角川视角的选择造成了立场混乱,结果是离初衷更远。这个角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写角川这片黑暗中的微光,而且由于这片微光的限知视角,连黑暗都被淡化了,所以既没有说服力,还背叛了主题。相反地,辛德勒站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扬弃和阿蒙既代表黑暗又被黑暗吞没的人物塑造则既真实,又强化了主题。所以,尝试新角度的同时,永远不要忘了终极的诉求。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南京大屠杀”系列电影在日趋复杂的时代环境下讲了许多人物的故事,但却远离了对历史事件的正面揭示,张扬了些许人性的良善,但却无从还原和反思历史,更无从感动全世界人民,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如果未来的此类影片不明确反法西斯、反战的诉求,真正立足于反思“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那么为“南京大屠杀”立碑的任务就永远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