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众听到阿甘那句话
2020-05-14刘月新
刘月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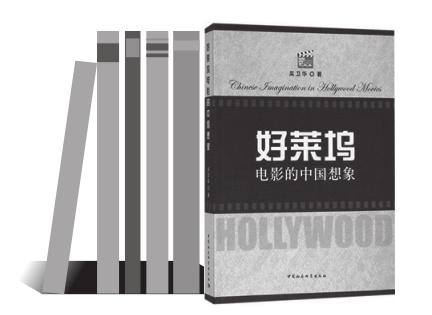
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立场,利用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全球信息传播载体和文化娱乐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虚拟统治权”(马丁·雅克语),塑造和播撒他国野蛮、愚昧落后的形象,妖魔化具有不同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作为“非我族类”的中国自然是“在劫难逃”。如果不对美国媒体、好莱坞电影等建构的中国形象及隐含的意识形态偏见进行澄清和批判,将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与巩固自身的正面形象。基于这种认识,吴卫华的专著《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对历史以来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形象状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考辨、梳理和阐释,彰显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
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范式,之所以被广泛运用于电影批评,是因为相对于其他艺术类型而言,电影更适合于承担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运用意识形态批评来分析好莱坞电影具有其他批评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它通过对电影符号和叙事方式的解析,洞穿其潜在的意识形态蕴含,达到警醒受众的目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与最初法国一批电影理论家的批评实践有很大的关联,让—路易·科莫里的《技巧与意识形态:电影、透视、景深》、让—路易·科莫里和让·纳尔波尼的《电影·意识形态·批评》以及让-路易·博德里的《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等,堪称意识形态批评的典范之作。
一度时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在西方形式主义的影响下,重视文本内在的審美分析,淡化社会政治指向,鄙夷意识形态分析,使批评失落了现实批判精神和文化使命担当。《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却属意将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上升到一种批判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约翰·费克斯的大众文化理论、新历史主义、性别理论、种族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熔为一炉、融会贯通,建立了一个自成一体、立体多元的叙述框架,从不同层次、侧面和角度对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进行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以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与文化偏见。在宏观把握方面,作者梳理了历史以来好莱坞中国形象的流变,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流行桥段和话语范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沉潜与剖析。作者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在早期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中,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中国女性是西方男人征服的对象,中国男人不是猥琐的无能者便是狡诈的阴谋家。“红色”中国建立以后,好莱坞更是泄愤似地诅咒新生政权,以一种道德使命感和优越感丑化中国,把中国视为一个“黑暗”国度。上世纪80年代以降,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好莱坞的中国故事在赓续陈腐的“中国观”和种族主义话语外,还增添了所谓的中国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入侵”、“中国制造”低劣、中国偷渡与间谍活动频仍等议程设置。某些影片甚至将中国与国际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好莱坞电影充斥着美国至上意识或“冷战”思维惯性,试图通过对“他者”的任意贬损,以达到推行美国价值观的目的。某些华人导演、演员也甘愿拜倒在好莱坞文化资本的强权之下,有意识迎合西方受众的“期待视野”,这不仅是丧失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客观上也参与了东方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过程。作者认为,华裔艺人的这种“自我东方化”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意识形态批评必须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电影文本的叙事策略、镜头语言、场面调度、人物对话等要素的剖析来揭示潜在的意识形态话语。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叙事大致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意识形态倾向鲜明突出的创作,这类作品常常肆无忌惮地去丑化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现实,受众在接受过程中一般会有所警惕。另一类则是在叙事中以“不经意”的方式植入矮化中国形象的桥段或话语,其因为隐蔽性特点,很容易被观众忽略不计或不以为然。《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对这两种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都有鞭辟入里、令人信服的阐述,将意识形态批判贯穿于电影叙事的细节分析之中,尤其是对后一种叙事类型的阐发更见功力。作者善于于细微之处见乾坤,将受众容易忽略的细节置于特定的时代与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下,揭橥其隐含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作者对《阿甘正传》的文本分析。阿甘作为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曾到中国访问,回国后即接受了电视访谈节目关于中国印象的专访,阿甘只说了简单的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很穷,另一句是中国人不信教。貌似是对中国的客观介绍,其实背后隐含着好莱坞的中国“原型”偏见——中国人在物质上一穷二白,精神上一片荒芜。众所周知,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一个人信仰缺失便与动物没有了区别。《阿甘正传》是好莱坞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一部经典电影,其实彼时的中国社会面貌已然与70年代初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好莱坞的叙事语境中,中国被定格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历史交汇点上,即便在时移世易的当下,凡是能重睹《阿甘正传》的每一个角落,仍将回荡的是中国贫穷、中国人没有信仰的陈词滥调和讥嘲。“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福柯语),诚然,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首先要关注电影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影片中故事所发生的年代。专著作者在分析好莱坞的中国叙事时,发现了其一个固化的叙事策略,这便是电影常常将过去时的中国镜像与现在时的美国镜像并置,省略了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将中国形象定位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通过造成一种空间对比的效果,来强化受众的中国原始落后的刻板印象。这种叙事策略的分析就是意识形态批评所擅长的症候阅读,它将文本中的沉默、省略和空白之处作为理解文本潜在话语的入口,发掘创作者想说而没有说的意图,暴露文本的意识形态真相。在电影作品的阐释上,作者还采用了文本内外互证的方法,将外部资料的引用与文本内在的艺术分析融会贯通,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强化了观点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作者的研究也不乏历史和辩证的眼光,始终将中国形象生成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来进行探讨,肯定了某些影片对中国亲善友好的叙事,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银幕上的偏见和歧视,本质上暴露出的是好莱坞的狭隘与时代的局限性。梳理好莱坞中国形象的变迁史,正视好莱坞扭曲的中国形象,其实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作者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一个严峻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一如落后就要挨打,失语必定挨骂,回应好莱坞的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挑战,向世界展陈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就必须要讲好中国故事,争夺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正在这个意义上说,《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一书,体现了鲜明的主体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具有某种不可小觑的当下意义。
(作者系三峡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