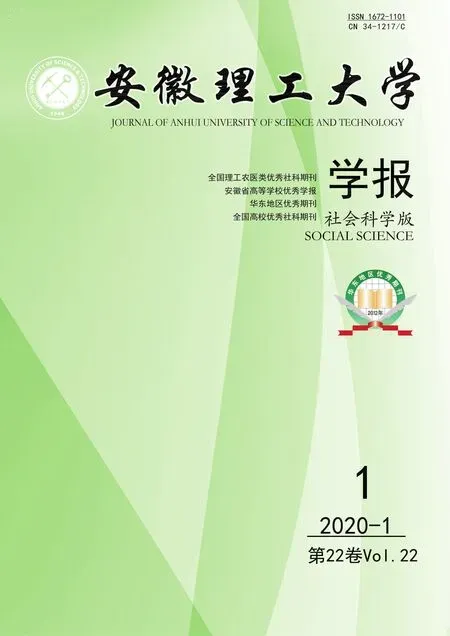朱《说文假借义证》假借研究
2020-05-12史萍
史 萍
(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朱珔(1769-1850),字玉存,号兰坡,清末安徽泾县黄田村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元年(1821)直上书房,升右春房右赞善。后辞官归田,潜心著书,孜孜不倦。其一生著作颇丰,于小学、经学、诗词多有创作,与姚鼐、李兆洛为儒林三大宿望。著有《文选集释》二十四卷、《说文假借义证》二十八卷、《小万卷斋文集》二十四卷、《诗集》三十二卷、《续稿》 十二卷、《经文广异》十二卷、《诂经文钞》七十卷等。
《说文假借义证》是朱珔晚年所撰,共14篇28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此书将谋付梓时,朱珔不幸病故。适值清末时期,由于战乱,此书稿本被毁坏,残缺不全。光绪十九年(1893),其后代摘取《经文广异》及其他说添补《说文假借义证》缺佚,交付族曾孙朱麟成授梓刊出,为癸巳本。之后,因其本偶有他说添入,殊失其真,又有族曾孙朱荫成请其原本,重为厘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依原貌重新刊出,为乙亥本。
现易见版本:一为《说文解字文献研究集成》(古代卷)第七卷。此版选自续修四库全书本,即清光绪二十一年嘉树山房刻本;二为清光绪二十五年约古阁重刊本,中国图书刊传会影印。后由安徽古籍管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组织,余国庆、黄德宽点校出版《说文假借义证》,收入《安徽古籍丛书》,1997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附校勘记。本文则以余国庆、黄德宽点校版本为研究对象。
一、《说文假借义证》体例
《说文假借义证》(下简称义证)按许慎《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排列次序。《说文》十四篇,每篇各分上下。《义证》则以此分为二十八卷,每卷均有目录注明所选《说文》之字。《说文》收字9 353个,《义证》择其要说明先秦两汉魏晋等时期古籍中假借之字,全书六十万字,共出《说文》字头3 524个。每字之下先列小篆字体,或举古文、籀文等重文字体,注明《说文》解释,再举文献典籍及有关传笺注疏对该字的假借情况,用诸多术语对字与字之间关系进行阐释分析,少则一对,多则几十对。每对之间用“o”隔开。其基本的术语为“是某为某之假借”。
如卷一对“一”字的说解如下:“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文为弌。《仪礼》屡见壹字,注皆云古文壹作一,是壹为一之假借。壹为部首,训嫥一也。《礼运》‘欲以一以穷之’,《正义》谓专一。《管子·心术篇》‘执一而不失’,注:‘一谓精专’。则一又壹之假借。《史记·秦始皇本纪》琅琊台石刻颂云:‘普天之下,抟心揖志’。《索隐》引《左传》‘如琴瑟之抟一’,是‘揖’为‘一’之假借,亦‘壹’之假借也。”[1]12
二、《说文假借义证》假借术语
《义证》一书为假借而作,但由于本书的凡例和序文佚失,无法窥探朱氏对假借的理论论述,然从其对《说文》3 524个字的假借分析中可见其假借理论。文中主要结合朱之垿对《义证》的体例归纳和书中大量的例证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朱氏所用假借术语的内涵,为分析朱氏的假借观作基础。
(一)假借
假借,许慎在《说文·叙》中说:“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2]314由于许慎对“六书”的说解过于简略,故学者对“假借”的理解莫衷一是。《经典释文·条例》引郑玄语:“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3]203可知早在汉代,学者对于假借的理解就有两种,一是许慎“本无其字”的“六书”之假借,一是郑玄“仓卒无其字”的“以音类比”之假借。宋元明时期,对假借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探讨。如徐锴认为假借是“一字数用”,第一次对假借作进一步分类;郑樵把假借分为“有义之假借”和“无义之假借”两类。此时的假借已不是许慎时期的笼统定义,而是有了更为精密的分析和分类。
随着“六书”研究的深入,清代学者对假借的研究主要围绕“假借与通假”“假借与引申”两个问题进行。如戴震主张“四体二用”说,赞同者如段玉裁、朱骏声,将假借定为“用字说”,影响极大。王筠、孔广居认为假借与字形有密切关系,不仅仅是语音上的相同或相通。从总体上看,清人对假借的研究实现了从文字向语言的跨越,注意到了音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假借作为“六书”之一,从汉代到清代,“造字说”“用字说”纷争不断,莫衷一是。但对于假借重要性的认识,学者观点是一致的。如汉代郑樵:“六书明则六经如指掌,假借明则六书如指掌。”[4]503清代朱骏声:“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5]4朱氏在《义证·卷一》中也说:“不识假借,不可以读经也。”[1]23认为假借是明经通道、阐释经典的重要手段。但与前人不同的是,朱氏对假借的分类更加细致繁复。如朱之垿所作条例说:“假借之例不一如同一语。”《义证》对于“假借”用语,通常是在各字下注有“是某为之某之假借”的术语。如卷一“一”下云:“《仪礼》屡见壹字,注皆云古文壹作一,是壹为一之假借。”[1]12朱氏从语言事实出发,除假借之外,还有“通借”“省借”“转借”“异体假借”“形近假借”“不定谁借”“互借”“通用”“两借、连借”等术语。
(二)通借
朱之垿《凡例》说:“每字各有所释‘本义’,固可通借,或他书别释一义,而所释之字即可借或所释之字与本义合,亦可通借。”[6]383可知通借是指同义、近义字之间的通用互借。如卷一“元”下云:“《春秋繁露·重政篇》元犹原也。刘熙《释名》原,元也,是原为元之通借。……《文选·东都赋》注引《春秋元命苞》,元年者何,元宜为一。《公羊·隐元年》传注变一为元。是元为一可为通借。”[1]12“原”与“元”互训,古书可通用;“元”与“一”异文同义,也可通用。故朱氏称为“通借”。通借侧重探讨在文字本义上的相通与印证,符合本义和引申义,可看作通借,但也有单纯借音而意义上毫无联系的。如卷二“兹”下云:“《左传·僖公五年》‘公孙兹如牟’,《公羊》作‘慈’;又《僖八年经》:‘宋襄公兹父’,《公羊》作‘慈父’,是‘慈’为‘兹’之通借。故《汉书·西域传》:‘龟兹国,兹亦音慈。’”[1]52“兹”和“慈”意义毫无联系,《说文》:“兹,草木多矣”。《说文》:“慈,爱也。从心兹声。”朱氏引异文与注音材料,说明二字音同通用而非义通。
(三)省借
朱之垿《凡例》说:“凡各字偏旁皆从其声,可省借。”[6]383可知省借是不论形符,把声符作为同声符形声字的假借。如卷一“瑁”下云:“瑁,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今《考工记·玉人》作冒。《书大传》亦云;‘天子执冒。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则冒为瑁之省借,而本因以得之。’”[1]26还如,卷一“旁”,“旁盖为膀之省借。”“祥”,“羊为祥之省借。”“祀”,“巳为祀之省借”等。冒与瑁,旁与膀,羊与祥,巳与祀,即就古书用字而言,则是古今字,即是后世文字的分化现象,或称为“区别文。”朱氏则称之为“省借”。
朱氏的“省借”,实就汉字形体而言,是一种省形用声的文字现象。早在宋代的王观国《学林》中就有:“盧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爐,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7]84王氏汉字“字母说”的分析与朱氏类似,揭示的是汉字早期的一种文字使用现象,对于认识形声字的产生有借鉴作用。胡秉虔在《说文官见·省文假借》中也对此现象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称为“省文假借”。胡氏说:“《尚书》:‘懋迁有无化居。’‘化’当即‘货’字。‘货’从贝化声,故亦省作‘化’。《史记·弟子传》:‘与时货赀’,《索隐》云:‘《家语》货作化。’是其证也。……此皆省文假借也。”[8]295王筠《说文释例》也认为:“夫转注、假借在形、事、意、声四者之中,而可专属之声者,假借固无不以声借也。有去形存声者,石鼓文‘其鱼隹可’,即‘维何’也。是谓省借。”[9]8胡氏、王氏与朱氏所论都是单纯用声符来记录语词的一种文字现象。省借的声符是古字,加形符的多是后起的分化字。
(四)转借
朱之垿《凡例》说:“此书作此字,彼书作彼字,彼字又作他字,可转借。”[6]383可知转借即为一字多借的展转假借。甲字借用作乙字,乙字再借用作丙字。乙字丙字均是甲字的借字,只丙字因乙字而借,故称为“转借”。如卷二“兹”下云:“兹,草木多益。《义证》云:《尔雅·释诂》‘兹,此也。’《书·大诰》:‘卜陈惟若兹。’《汉书·翟方进传》作‘若此’,是兹为此之假借。《释诂》又云:‘咨,此也。’则以咨为兹之转借矣。”[1]52“此”借为“兹”,又借为“咨”,为展转假借。朱氏书中所指“转借”,多为经传异文,旨在阐明一字展转借用他字的现象,揭示了假借字内部的复杂现象,有利于我们分析研究一字多借的文字现象。一字多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未必都是转借。
(五)异体假借

(六)形近假借

(七)不定谁借
朱之垿《凡例》说:“书中人名、地名各本异字甚多,而或义无可证,则注不定谁为假借。”[6]383可知不定谁借是指不能确定何为本字、何为借字,大多存在于人名、地名中,仅有标音的作用。“人名不定谁借”如卷一“瑶”下云:“若《晋语》‘荀瑶’,《墨子》作‘荀摇’,《淮南·修务训》作‘荀繇’,此人名不定谁借。摇、繇亦通,《明堂位》注:今之步摇。《释文》:摇,本又作繇業。”[1]30“地名不定谁借”如卷七“羑”下云:“ 《殷本纪》‘纣囚西伯羑里’,《书大传》作‘牖里’,蔡邕《独断》同是,牖为羑之通借,盖传闻异辞,不定谁为正字。”[1]215
“不定谁借”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提出的“托名标识字”相似,朱骏声认为事物的命名字无法确定何为正字,何为借字。陆宗达说:“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是可以通过语源来“贯其声音,求其条例”[10] 89。早期名物字的字形是有本字可考的,但到了后期,名物字重音不重形,多用同音或音近字记录,故而不知何为本字何为借字了。朱氏客观实事,对此存而不论,称其为“不定谁借”。
(八)互借
朱之垿《凡例》说:“此字作彼字,彼字又作此字可互借。”[6]383可知互借是指两字之间可以互为借用。如卷十“静”下云:“《尧典》:‘静言庸远’,《汉书·王尊传》《论衡·恢国篇》并作‘靖言’,《诗·小明》‘靖共尔位’,《韩诗外传》作‘静恭’,《春秋繁露·祭义篇》作‘静共’,是二字可以互借。”[1]279“静言”同“靖言”,“静”与“靖”互借。
(九)通用
通用即是通假术语。由于凡例的缺佚,在《义证》中未能得见朱氏对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的理论区别,但散见于各字之下的“通用”和“某为某假借”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如卷一“瑕”下云:“《文选·甘泉赋》:‘吸青云之流瑕兮。’注:‘霞与瑕古字通’。……又《江赋》:‘壁立赮驳。’注:‘如赮之驳也。赮古霞字,当即瑕之或体。”[1]28可见,书中“通用”与古今字和异体字有交叉。
(十)两借、连借
朱之垿《凡例》说:“各书中某字借此字,彼字亦借此字,可两借。某字连借二字,可连借。某字已借此字,又借彼字,而借彼字与借此字义同,亦可两借。此处两字与彼处两字或音通或义同亦可连借。”[6]383可知“两借、连借”是为一字多借现象。书中“两借、连借”用例较少。如卷二十八“阪”下云:“《尔雅·释地》作:‘陂者曰阪。’《诗·东鄰》:‘阪有漆。’《毛传》同,土部‘坡’字云:‘陂也’,是坡与陂义本通,故可两借。”[1]780“陂”与“坡”为异体字,与“阪”为同义字,三字音近义同。朱氏的“两借、连借”理论继承了段玉裁的假借观。但朱氏云“音通义同”可为“两借、连借”,与“通借”混淆,也说明了朱氏假借理论的逻辑不清,概念交叉。
三、《说文假借义证》假借观
从以上《义证》中术语内涵的探析,可以看出朱氏的假借理论研究大量参考了清代及清代之前众多学者对假借的研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朱氏疏通文献,从具体语言文字本身出发分析假借现象,探究假借规律,建立了自己的假借观。
(一)确立“以义正字”的假借原则
假借问题的研究,至清代达到最高水平。其主要代表观点有:“引申假借说”“一字本义之外的意义为假借”“义无所因、特借其声”。朱氏突破了以往学者以声音为假借的主要判定依据,以意义为依据,把“以义正字”的假借观贯穿全书。如卷一“壮”下云:“《射义》:‘幼壮孝弟’,注:‘壮或为将’,将为壮之假借。《诗·北山》:‘鲜我方将’,将,壮也。义亦通。”[1]33卷四“逆”下云:“《禹贡》:‘逆河’;《汉书·沟洫志》作‘迎河’,此义通,亦假借也。”[1]105卷二十三“聖”下云:“《左氏·文十七年》:‘葬我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古今人表》:‘卫聲公’。《索隐》作:‘聖公’。案:《风俗通》曰‘聖者,聲也’。言闻聲知清,是义本通。故可相假借。”[1]671朱氏认为如果在文献中使用“借字”时语义未通,改为“本字”后,就能够语义通顺,则是假借。“义通”“义合”“义证”“字异而义同”是确定假借最重要的标准。能够“义证”的就是“正字”,不必通音。
(二)假借是用字之法,必有本字
清人对假借的认识有三种观点:“造字说”“借字说”“兼体用说”[11] 101-102。朱氏将假借认为是“用字之法。”他主要是从《说文解字》收字、《经典释文》等文献例证或大量的异文材料中探讨假借的标准,来确定其本字。认为假借是以有本字作为“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的标准,讨论的多是用字假借。朱氏承认“本无其字”假借的存在,如语气词等虚词。如卷二十七“载”下云:“载,又借为语辞,《诗》:‘春日载阳’。笺云:‘载之言则也’。‘则’语辞,载、则音亦同”[1]772。 “载”本义为动词“乘车”,又借为语气词。同时,朱氏又为这类词寻找本字,如卷九“兮”下云:“《诗·伐檀》:‘河水清且涟漪’。《汉石经》”作‘兮’,‘大学断断兮’。《正义》云:古文《尚书》‘兮’为‘猗’,猗乃兮之假借。”[1]261“猗”早在《尚书·秦誓》“断断猗,无他伎”中就是语气词。可见,朱氏认为并非所有的虚词都没有正字,他将无法寻到正字的词认为是“假借为语辞”,将能寻到正字的以“某为某之假借”术语为其寻本字,认定假借是用字现象,有“本字”、有“借字”。
(三)归纳“非必假借”,明确假借范围
朱之垿《凡例》说:“书中虽云某又作某,而与本字义实难通,或为各本之异,则注‘非必假借’。或两字难分部而实为一字,亦不在假借之别。”[6]384可知,朱氏把形体相似的讹误字,传本不同、传写各异的异文用字,异体字等认为是“非必假借”,匡定了假借的内涵与外延。如卷二十一“雩”下云:“《尔雅·释天》:‘螮蝀谓之雩’。郭注:‘江东呼雩音芌’,是异名耳,非必借字也。”[1]650异名异义是不同区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属于方言词汇,不是假借。卷十五“伐”下云:“《洪范·五行传》:‘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郑注:‘伐宜为代’,蓋字形相涉而异,非必假借。”[1]457形体相似出现的错讹字是在传抄过程中导致的,不是假借。卷十七“页”下云:“若《公羊·成二年经》:‘曹公子手’。《释文》:‘手,本作午’。则传写各异,非必假借也。”传本不同,不是假借。此外,朱氏还指出了“此为义通,非必假借”“误混一字,非必假借”“方言之异,非必假借”“本一字,非假借”等“非必假借”现象,匡定假借的范围。
(四)“引申假借”观
引申和假借的关系问题一直是 “假借”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许慎定义假借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所举例字“令”“长”是词义引申而非假借。众多学者都对词义引申和假借现象进行思考和研究,有不同的见解。汉代郑樵提出“无义之假借”,戴侗强调文字假借不应该包括词义引申。清代朱骏声承袭戴侗的观点,认为本字与借字之间意义无联系,应该把词义引申和假借区分。

总之,朱氏的假借观综合了清代各家之长,从训诂用字角度,将众多无假借关系的用字都冠以“借”字,将其认定为假借,内容庞杂。朱氏对假借的研究展示了不同字记录词的使用语境,为我们阅读文献提供参考,尤其是异文资料的总结归纳,互相参照,可以从多角度了解文献中的用字情况,对阅读文献古籍也有帮助。但是朱氏的假借研究也存在不足和缺陷,诸如假借定义过宽,混淆不同语言文字现象;分类繁琐,界定不明确;术语缺少严密性,与其他术语有交叉现象等,为研究《义证》制造了困难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