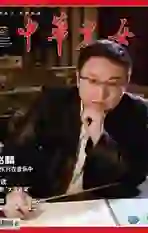叶星生 雪域文化守望者
2020-05-11陈晰
陈晰

叶星生有着众多的头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西藏博物馆名誉馆长……这些都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相关,那就是西藏。
11岁进藏,29岁时在全国美展获奖;因创新布画《赛牦牛》获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二等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81年至85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绘制的大型壁画《扎西得勒图》等7幅大型壁画,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悬挂至今三十多年。他用收藏的方式保护西藏文化,并为之倾尽所有。痴迷收藏近半个世纪,他却在1999年将36年所收获的2300件、价值8000万的收藏全部捐出,让世人震惊。有人称他为“高原怪杰”,有人说他是西藏文化的守护神。冯骥才对他的解读是:“……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把整个民族的文化使命放在自己背上。用身体做围栏,保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他是民族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从成都到拉萨
2020新年将至时,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北四环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叶星生的工作室。他正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有电视台记者正架好设备等待;有创业团队希望将他的藏品进行扫描之后录入APP,正在为他用平板电脑演示……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不计其数。他的大脑就在不同的来访者、不同的主题之间切换着频道。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叶星生仍然礼貌而耐心。“我需要一分钟时间准备一下。”
他点起一支烟,望向远方,仿佛瞬间屏蔽了外界的声音,沉入到了回憶中。
“我出生在四川,父亲是18军战士修路进藏,从小父母就不在我身边,我跟随爷爷奶奶住在成都青龙巷3号……”他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幼年的叶星生有些沉默寡言,随祖父一家住在成都青龙巷的四合院里。当时四川有名的画家冯灌父住在正厢房。叶星生常常帮助冯先生做家务活:扫地、倒痰盂……冯先生就成了他的美术启蒙老师。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他来说,画画成了童年生活最好的心灵慰藉,当时他才7岁。
“我的画被邻居老太太挂在窗子上,然后表扬我,我心里面好高兴。那个荣誉感啊,我现在都记得。”叶星生微笑着回忆。现在,他的工作室里还挂着一幅国画作品《情系山茶花》,那是他9岁时画的,然后寄给了远在西藏的父母,被他们一直悉心保存下来。
13岁时,叶星生和弟弟被父母接到了西藏。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成为拉萨中学的第一个汉族学生,开始学着抓糌粑,喝酥油茶,吃生肉,学藏语……他是学校里的“珍稀动物”,常有藏族孩子在教室的窗外偷偷“参观”他。班长次旺俊美将他的名字翻译成藏语,叫“罗玛萨吉”。后来,西藏老百姓又赐给他一个藏文名字“嘉措”,意为“大海”。
西藏的艺术对叶星生的心灵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精美的唐卡、绚丽的壁画……“感觉和自己之前学的画完全是两个世界。”丰富多彩的西藏艺术一下子征服了他。“原本我想呆一年就回成都的,来了以后,根本就不想回去了。”有幸的是结识了原十世班禅的画师、“勉萨画派”的第六代传人西洛为师。跟随老人学习唐卡,西藏的文化、艺术就这样在他幼小的心中生根发芽。西洛老师成为叶星生艺术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引导者,将他带入西藏艺术的神秘殿堂。
带着“酥油糌粑味”的艺术
因为画得一手好画,叶星生13岁就被吸收到西藏日报社副刊部,边学习边画画。拉萨中学毕业后,分配到拉萨城关区从事基层美术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住进一位以放牧为生的翻身农奴波查色家,在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与他同吃同住了近两年。他住的“柳霞”大杂院里有100多户人家。叶星生用藏话和他们对话,用文字进行调研,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真正和藏族人民打成一片。他在大昭寺门前以铁板、木板创办了“西藏第一画廊”,以社会主义教材为蓝本,以彩墨的形式创作绘制各类美术作品32幅,分三期在大昭寺门前展出。“后来因观众太多造成交通堵塞,而被迫停办。”叶星生笑呵呵地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条件艰苦,叶星生住的是没有取暖设备的铁皮土砖房。就在这间冬天室内在0度以下、比室外还冷的铁皮小屋里,叶星生完成了他的成名之作《赛牦牛》。此画取材于西藏庆丰收的传统节庆,“望果节”中的赛牦牛场景,充满生气与活力。
此画最大的特色是在艺术上创新,在继承藏族绘画基础上融入了汉地水墨国画的艺术手法,用墨汁在纯棉布上顺着经纬线纹理晕染开来,形成牦牛的机理。但又比宣纸上的笔墨更显生动厚重。而对牦牛的饰品、装饰,他运用了唐卡绘画手法,让艳丽的矿物颜料和牦牛的水墨效果形成对比,加上天上飞翔的云雀、地上奔跑的藏獒和八位朝气蓬勃、姿态各异的藏族骑手,完成后取名为《赛牦牛》。由于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在所有参展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西藏美展一等奖、全国美展二等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开创了美术展览中一个新的艺术形式“西藏布画”。
1981年,因布画《赛牦牛》的成功,叶星生被西藏人民政府抽调到北京,担任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组组长,并担任《扎西德勒图》等七幅大型壁画的创作任务。 1981年至1985年用了五年时间反复设计、修改了19稿。终于在他34岁那年完成了这幅长18米,宽4.5米的壁画,包括71个人物、49个动物、100多种节日用品和吉祥图案的《扎西德勒图》。被视为“西藏壁画创作新的里程碑”,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幅在人民大会堂中从未更换过的壁画,悬挂至今三十多年。
此后,叶星生陆续创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2009年,他的作品《极地》和《山神》分别被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收藏。同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中获得“时代功勋·感动中国60人”。
2015年,他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设计的纪念邮票及首日封在全国发行。
2016年,他为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创作了三组七幅大型丙烯壁画:《布达拉宫祥云图》、《雪域圣境图》和《春华秋实·新年吉祥》。
叶星生说,因为从小就在西藏传统艺术的熏陶下、在藏族恩师西洛老人的教导下成长,自己的作品始终带着“酥油糌粑味”。他的艺术创作历程,就是在学习、传承西藏传统绘画基础上进行发展并不断创新的历程,而被李苦禅大师称为“布宫彩笔、藏派丹青”。
衣带渐宽终不悔
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叶星生却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这一切源于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为了抢救和保护西藏的珍贵文物,他甚至到了“倾家荡产”、“走火入魔”的地步。
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似是从天而降。13岁那年,他在山南昌珠寺临摹壁画。一天,一位仙风道骨的僧人见他很饥饿,就送了一罐酥油人参果给他。果子吃完,却发现老僧人不见了。叶星生拿起这件被寺庙供奉过的绿釉陶罐细细把玩,越看越喜爱。这罐子便成了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
第二次难忘的收藏是叶星生与波查色老人分别时,叶星生从部队弄了一袋面粉、一桶青油送给“阿爸”。老人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一件墨竹工艺官窑烧制的薄胎古花瓶,他说这是他帮人所得,送他作纪念。这件花瓶一直陪伴着叶星生。现珍藏于西藏博物馆,成为汉藏友谊的象征。
叶星生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扎西德勒图》而享誉国内外,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便开始花钱收购他喜爱的西藏民间文物。他跑遍西藏农牧区去寻找、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宝物,甚至马棚羊圈都不放过。拉萨的八廓街更是他淘宝的重要阵地。西藏人都知道八廓街有一位“款爷”,买东西大方。很多人捧着宝贝到家里找他,有人戏称八廓街搬到了叶星生家。这位款爷也经常“开白条”。西藏的老百姓都相信“嘉措从来不会不还钱”。每到发工资的日子或者收到稿费时,钱在手里还没捂热,就还了欠条。“每当在大街小巷、在荒野发现一个心爱的艺术品时,我就像找到了希望,找到了爱情”,不惜重金收购。
收藏带给叶星生的不只是得到的喜悦,也有错过的揪心。一次,叶星生在八廓街看中一块藏经板,砍价砍不下来,佯装要走。走了不远回头看时,经板已被一个外国人托在手上,人家掏出美金,当场就拿走了宝贝。叶星生急得数日失眠,连续三天在八廓街转悠,寻找那个外国人的身影。最后还是与这块经板失之交臂,那失魂落魄的感觉他至今都记得。他感慨道:“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经常把我折磨个半死。”
为了收藏,叶星生几乎卖掉一切可以卖的东西:甚至将母亲给他结婚的订婚盒都换成钱买了藏品,当年他在拉萨的家,地板裂了几十道口子,就用透明胶带粘上。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常常噼啪作响,“看的时候我总是坐在桌子后面,以防它突然爆炸”。
1990年,叶星生受邀参加“中国首届民间美术博览会”,他带去的藏品引起巨大的轰动,而获全国唯一的个人收藏奖。无数精美绝伦的唐卡、精雕细琢的佛像、神秘莫测的法器、难得一见的远古生活用品……“好多藏品都是历代罕见的珍品、孤品、绝品,可谓是西藏之魂。说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都不为过。”但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疲惫不堪,1985年终于回到成都住进了医院。身体虚弱的日子,他萌生了退意。这时,海外企业在成都创办“西南日月城”聘他当艺术总监,给房给车,待遇不菲。他也打算安定下来,结婚生子过普通人的生活。
1995年,叶星生拿出部分藏品举办告别展览。“正在撤展的时候,一位藏族老阿妈拄着拐杖带着他的小孙女进来了,围着展品转悠,并不时用颤抖的手去抚摩那些坛坛罐罐,对小孙女念‘这是我爷爷小时候用过的,这是我奶奶穿过的……老人还想通过这些器皿、衣物来寻觅爺爷奶奶的影子,也希望小孙女不要忘记。”那一刻,叶星生的眼眶湿润了。“如果我的行为能让藏族人民受益,为他们撑腰打气,那是上天赐予我的福分与使命。于是我辞退了成都的优厚待遇,又重新返回西藏这片哺育我成长的土地,因为我与西藏血脉相连。”
两次骨肉分离
叶星生一生没有结婚,但他并不孤独。他常常称自己的藏品为“我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的孩子”。“几十件藏品算‘把玩,几百件藏品办展览,但拥有成千上万件藏品,我便成了库房管理员,请库房保管员也不放心,常常昼夜难眠……”叶老说,“更重要的是,我真正感受到藏族人民才是这笔藏品真正的主人,是他们在历史岁月中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是发现保护了下来。而最后还应该回归它的主人——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
于是在他收藏的高峰期,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这笔珍贵财富捐给西藏人民,他给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信中写道:“经受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逐渐清晰了多少年来萦绕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将我视若生命的民间艺术珍藏,全部回报西藏这块抚育我成长的土地,报恩于厚爱于我的西藏人民。”
1999年1月,捐赠仪式在西藏博物馆正式举行,得到西藏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经西藏文物局鉴定,叶星生捐赠的藏品共计2300件,其中一级文物22件、二级文物 43件、三级文物100件。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于他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展示了一位汉族同志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努力增进藏汉民族团结的崇高风范。他的高尚行为和他对西藏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载入西藏文化发展的史册。”
捐献了自己全部身家的叶星生,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没家、没画,陪了我30多年的宝贝也没了,真正的家徒四壁。整个人有如孤魂野鬼,一个月没出门,烟缸里烟灰堆积如山,心中空空落落。”
为逃避痛苦,叶星生带上跟随多年的弟子,再去一次淘宝之地——拉萨八廓街,拿上5000元钱,准备大吃一顿,彻底告别八廓街的收藏。然而,两个半小时过后,他手里又大包小包地提满了 “破铜烂铁”,助手提醒他,吃饭不想去了,关键得“留点回去打车的钱”。
就这样,叶星生的小屋墙上又重新挂起唐卡,屋里又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佛龛、陶罐……
第二次的捐赠故事要从1991年说起。一天晚上,一个康巴汉子背着一个口袋来找叶星生。里面的宝贝露出来后,叶星生眼睛一亮。收藏了20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唐卡!“唐卡的内容是色拉寺护殿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带翅的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其工艺为藏族传统的堆绣工艺,以用五彩绵缎拼接、缝制,其臂纹撄珞是用了1300余粒古老珍珠串连而成。将堆绣和珍珠这两种藏族传统工艺结合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十分难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6万5千元成交,这相当于他当时7年的工资。
这幅唐卡曾被北京的一个老板看中,要以65万元外加一套价值300万的别墅来换。叶星生也心动了,签了转让意向书,收了2万定金。但当天他心神不宁,晚上噩梦连连,预感这是不详之兆。最后终于反悔,退了定金,还赔了对方5000元的违约金。

1996年,“叶星生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展览在拉萨举办,这幅珍贵的“马头明王珍珠堆绣唐卡”也是进门的重要展品。就在展览开幕的第二天,来了一批肩披袈裟的喇嘛,他们进入展厅后直奔这幅唐卡,膜拜、敬香、献哈达。原来这是拉萨色拉寺丢失了10年之久的镇寺之宝。于是叶星生将其从捐赠的2300件清单中划掉,而要将其归还寺庙。
2003年10月,唐卡的捐赠活动在拉萨色拉寺吉扎仓广场举行,七大寺院的480位高僧举行隆重的迎请仪式,五彩经幡飘扬,鼓乐法号声声,色拉寺等七大寺院联合“祝颂”并授予他“色拉寺大乘州·群则”法位和金印,这是西藏历史上获此殊荣的首位汉族艺术家。
在19 9 9年叶星生2300件藏品捐赠17年之久,在区党委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叶星生民间珍藏捐赠馆”于2016年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建立。此馆在内容上分为民俗文化、宗教艺术两大部分和远古文明、生产生活、餐饮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等6个民俗系列,及唐卡佛像、木雕经板、法器饰件、嚓嚓陶艺、石刻艺术等共600多件。同时叶星生怀着对这批藏品及对藏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写了十条“收藏感言”穿插于各个单元,以引导观众对藏族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艺术创新永不止步
“我本是画家。”叶老说,以收藏知名的他,更愿意强调自己的画家身份。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今天的他仍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新人”,炽热自由的心灵仍在创新探索,拥抱艺术。
西藏民间艺术给了叶星生深厚的滋养,也使他在艺术上受益无穷。从1979年创新布画《赛牦牛》开始,他始终在吸收藏汉艺术的养料,来进行创造。他曾在文章中写到:“人不应该在固定的形式中憋死自己的创造,而应当在创造中找到更多更好的形式。”他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拓绘”。以藏族人民所创造的玛尼石刻艺术为主题,将古老的玛尼石刻及珍贵的的木雕经文、图纹拓印在皮纸或宣纸上,再结合内容需要,以唐卡的构图、国画的手法在拓片空白处呈现出祥云、山水、花草、飞禽,用以对拓片内容进行罩染延伸,最后题款盖章,让绘画与拓片相辅相生,让藏、汉文化融为一体。叶老告诉记者,这些拓绘作品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果,而是“与古人的对话合作”的结晶,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长路漫漫,他将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求索。
2018年9月,由西藏自治区文联、文化厅举办的叶星生“传承与创新——雪域星生拓绘经典”艺术展在西藏自治区群艺馆开幕。共展出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拓绘作品50余件。一场关于藏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坚守与情怀,对话与交流的话题,成为西藏美术界的又一热点。
西藏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及300多位专家学者和画界同仁出席开幕式。叶星生动情地说:“感谢西藏各级组织及西藏人民的关怀与支持,是西藏这片高天厚土和藏族人民所创造的民间艺术滋养了我,我如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西藏和藏族人民给予的,我感激不尽,并将为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如果当年没有到西藏。我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番模样。”采访最后,叶老说。
他给记者的名片上,有一张他自己设计的简笔头像,再仔细看,那头像的头发、耳朵、脖子巧妙组成四个缩写字:“雪域星生”。他说:“我与西藏血脉相连,汉族母亲生下了我,但藏族人民养育了我。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思想,我的全部均受益于西藏民间艺术和我的收藏。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钱财,我的全部也抛洒于西藏的一草一木,大山大河,而永不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