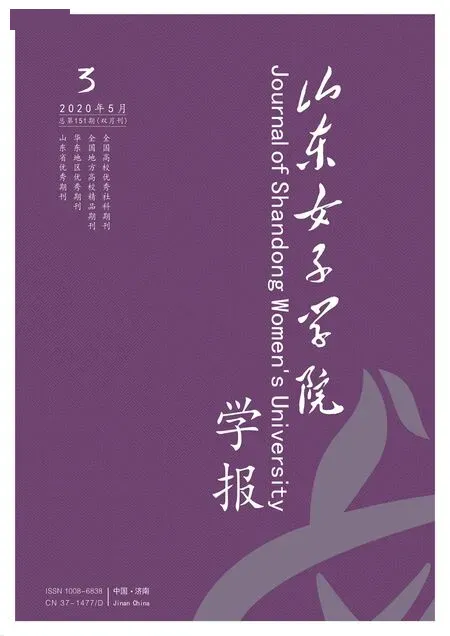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展望①
2020-05-08李勇
李 勇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民权运动催生“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在此背景下得以产生。女性主义法学家从男性偏见的假设出发,得出了女性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即“法律的性别为男”[1]。“女性主义法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国家权力和法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父权制在法律中的体现。第二,在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中应当(或不应当)反映女人和男人的差异。”[2]我国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始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此后,学者开始译介并系统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方法、以“女性与法律”为核心议题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如今,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从产生到发展的迈进。然而,处境的边缘化,加之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存在与否争议的持续存在,使得少有学者对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1)目前,有关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发展的文章有两篇。参见马姝:《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1期;夏吟兰,周应江:《性别与法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2013年6月4日《光明日报》。。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文献的收集整理,勾勒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新阶段的期望。
一、从译介到著述: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兴起(1995—2012年)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转折点,此次盛会不仅使我们得以窥见西方女性的独特风采,亦为我国女性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分析工具。正如马姝所言:“此次大会让各领域的学者注意到‘社会性别’这一西方女性学中的理论工具之于我国女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社会性别与法学的结合开启了我国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3]
(一)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译介热潮的到来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引入,促使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开始性别“意识觉醒”[4],他们好奇于西方女性主义法律理论家的理论构建和推理逻辑,进而思考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之于中国的意义。然而,女性主义法律理论大厦的构建并非一夜能成。他们旋即转向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希冀依此寻找展开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智识来源。
一些密切关注性别与法律的学者(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学者)(2)例如,《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的译者熊湘怡,现为新华社记者、编辑,“女生网”的首席顾问;《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译者曲广娣,现为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员;《不信任与不和谐》的译者王笑红,任职于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开始着手翻译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文献。但是,相较之部门法学和主流法学理论研究在法学研究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作为外来之物的女性主义法学则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时下,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的译本总体较少,且既有译本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女性主义法学著述的移译。截至2012年,与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译文主要包含两种。一是直接涉及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的文献(3)参见[美]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熊湘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凯瑟琳·巴特勒:《女性主义的法律方法》,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美]尼科拉·雷茜:《女权主义者的法律理论》,吴玉章译,载《环球法律评论》1992年第3期;[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有性别吗?》,郭义贵译,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等等。。此类文献的翻译旨在介绍作为一种新兴法学流派或法学思潮的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其中多是运用社会性别来分析女性之于现行法律中的处境问题,并得出“法律的性别为男”的女性主义法学基本观点。二是对与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具体议题有关的著述的翻译。在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但国内对此方面文献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性骚扰[5]、堕胎[6]、女权诉讼[7]、女性法学教育和职业处境[8]以及色情[9]几方面。
除翻译外,国内学人亦开始基于自身视角分析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并探索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的中国借鉴问题。有别于女性主义法学初期译者所处领域的多样性,女性主义法学的评述工作则主要由法律学者完成。其中“包括将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置于西方新兴法学流派中作以简要评述,还包括对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产生的内在动力、思想渊源,女权主义的法律方法以及主要研究问题等,所作的专门评述”[3]。具体而言,将女性主义法学作为新兴法学流派进行评述的有吕世伦主编的《现代西方法学流派》,朱景文主编的《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明辉、姜小蕾主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程》,等等。此类文献将女性主义法学作为一种西方新兴法学流派作了详细的评述。我国目前没有评述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的专著,但法学界老前辈沈宗灵[10]、吕世伦、范继梅[11]等,已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撰写了女性主义法学的开创性评述文章,稍靠后的学者也开始更全面和深入地评介西方女性主义法学。
(二)以“法律与性别”为核心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兴起
随着译介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已实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自塑的转变。2002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设立了我国首个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4)此外,还有2008年成立的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该研究所开设了研究生公选课程“性别、心理与法律”(现已撤销);2009年复旦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成立的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研究子议题包括“社会性别与法律”;2006年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成立的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2005年陈苇设立的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1995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等等。,并撰写了该研究所的首部教材[12]。此时的法学研究者掀起了一小股在中国视域下探讨“法律与性别”的热潮,进而涌现出不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开拓者。他们或是从自身出发,体味到作为女人的艰难;或是游学诸国后,意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示下两性现实中的不平等;抑或是试图在西方新兴法学思潮的影响中,寻见中国法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法学浓厚的激进色彩,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较温和。此阶段,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存在两个突破口,即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进行总体性的性别分析,以及基于性别视角对女性面临的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家庭暴力、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性骚扰等具体议题的探讨。
从总体层面讲,周安平和孙文恺等学者开始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来探讨法律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从博士论文《性别平等的法律建构》,到文章《社会性别的法律构建及其批判》《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之批判》《社会性别与法学研究》,再到专著《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周安平教授率先扛起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自主研究的大旗。孙文凯教授亦开始关注“法律与性别”研究议题,并贡献出了《法律的性别分析》《女性主义的法律观及其局限性》《法律与女性社会性别角色之理论问题研究》等极具价值的著述。此外,还有《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法律》《社会性别与法律》等研究法律与性别议题的著作。还应注意的是,李明舜教授的论文《妇女法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完善中的妇女法和发展中的妇女法》,以及著作《妇女法研究》等,试图构建的则是一种“妇女法学”。
此外,不少女性法律学者开始基于社会性别视角,以反对就业性别歧视、反家庭暴力、反性骚扰、婚姻家庭等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展开学术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头十年中,以郭慧敏、魏敏、刘明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难题。她们试图从涉及有关女性劳动权益保障(5)参见郭慧敏:《女性劳动权益研究:来自陕西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魏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劳动法律制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魏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劳动法律制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明辉:《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险权利研究》,中国劳动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就业性别歧视(6)参见魏敏:《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社会性别解读》,载《江西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刘明辉:《地方反就业性别歧视立法的优势》,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中的歧视问题》,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等。、女性退休年龄(7)参见刘明辉:《推动男女同龄退休的保障和出路》,载《朝阳法律评论》2009年第2期;《走出退休年龄的误区》,载《中国社会保障》2010年第3期;《对退休年龄改革方案的性别检视》,载《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5期;《中国退休年龄制度中的悖论》,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劳动立法和执法中的性别盲视(8)参见刘明辉:《论在劳动社会保险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性别盲点》,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载林嘉主编:《社会法评论》(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以及家政工人(9)参见郭慧敏:《家政女工的身份与团结权政治——一个家政工会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刘明辉:《家政工获得劳动保障权利的障碍及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等。等问题出发,改善中国女性在职场中的处境。自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以来,婚姻家庭是谈及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性权利保障历久弥新的话题,众多女性法律学者加入到了此议题的研究行列中。薛宁兰强调通过保障女性的婚姻财产(10)参见薛宁兰:《中国夫妻财产制的社会性别分析——以离婚夫妻财产分割为侧重》,载《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S2期;《中国夫妻财产制的社会性别分析》,载2010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离婚财产权实现中的性别平等》,载2010年3月23日《中国妇女报》;等等。和确立婚姻无效制度(11)参见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如何构建中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2001年2月27日《中国妇女报》;等等。来改善中国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处境;夏吟兰亦从女性婚姻财产(12)参见夏吟兰:《对中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家务劳动的价值》,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在国际人权框架下审视中国离婚财产分割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等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关系及离婚女性权益保障(13)参见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6期;《离婚妇女权益保障比较法研究》,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5期;《离婚衡平机制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论离婚妇女权益的保障》,载《中国妇运》2004年第11期;等等。等议题出发,探讨了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权益保障问题。
家庭暴力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陈敏研究员专注研究反家庭暴力,历时17年,她终于撬开了司法制度的缝隙,并在其他女性法律人士的推动下,使《反家庭暴力法》最终于2015年获得通过[13]。此外,她还是我国首位系统研究“受虐妇女综合征”的法律专家,并在《呐喊: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等著述中展现了对家庭暴力和干预措施等问题的深刻认识及独到见解。就性骚扰而言,自麦金农的性骚扰理论引入中国以来,性骚扰便逐渐成为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此阶段有关此议题的论文有近1000篇,加之薛宁兰、唐灿等学者的引领,我国有关性骚扰的研究已日趋成熟。曲广娣则在中国语境下率先提出色情问题[14],并指出色情并非言词而已,而是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压迫。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立法的文献[15]。也有著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女性各方面的权利保障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探讨(14)参见李明舜:《妇女权利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薛宁兰:《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王菊芬:《妇女权利保障与妇女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袁秀锦:《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总之,以法律与性别为核心的理论研究的兴起,女性劳动权、婚姻家庭权、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等具体议题研究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兴起。
二、从演进到反思: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2012—2019年)
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冲击及中国妇女运动的推动,女权意识正在中国迅速发展。2012年是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不平凡的一年:2月,最大胆的女性团体“麦子家”在广州发起“占领男厕所”运动;4月,中山大学研究生郑楚然向世界500强企业的CEO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解决招聘时歧视女性的问题;8月,北京部分女性剃光头发,抗议国内大学中的招生性别歧视现象……故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主义元年”[19]93-93。女权行动者的努力,一方面促使学者关注对女性的歧视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提供了新议题。于此情形下,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开始了自主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新阶段。
(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逐步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相较上阶段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机构、专业领域和法律学者,此阶段的研究则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女性主义法学领域,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就研究主体而言,部门法研究者开始投身到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中来。他们所处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学科专业上说,除以前参与女性法学研究的法学理论、民商法、刑法专业的研究者之外,近年来,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等专业领域,也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和从事女性法学研究”[17]。从地域上看,上阶段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集中在十余所高校,此阶段的研究者则分属全国近六十所高校。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有关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在研究议题上也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许多新兴议题开始出现。例如,独身女性生育权(15)参见汤擎:《单身女姓生育权与代际平等——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2款的非合理性》,载《法学》2002年第12期;刘志刚:《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合法性——兼与汤擎同志商榷》,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曹玉娟、张文霞:《独身女性无伴侣生育的社会困境——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问题探究》,载《科学与社会》2014年第3期;等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代孕问题(16)参见吕群蓉:《“母亲”之法律再构建——以代孕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6期;张融:《女性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代孕规则检讨》,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等等。、地方立法性别评估(17)参见薛宁兰:《以良法保善治 以平等促发展——构建新时代的法律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周应江、李明舜、蒋永萍:《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张再生、曲瑶:《公共政策性别评估机制构建路径研究》,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等。、家务劳动的货币价值(18)参见赵婧:《家务劳动价值的法律承认与保护》,载《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5期;陈颖:《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实践反思与制度调试》,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21期;赫英淇、张先昌:《从案例看我国〈婚姻法〉对性别平等的保障——以家务劳动问题为着眼点》,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等。、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19)参见林建军:《从性别和家庭视角看“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杨菊华:《“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及应对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荣振华:《妇女法律权益对二孩政策影响之检视与制度回应》,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等等。等。总之,“近十年的女性法学研究涵盖了政治、劳动、人身、财产和婚姻家庭权利等各方面,几乎延伸到了所有部门法领域,研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17]。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此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亦有了新突破。一方面,女性主义法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学的研究视角。于此视角下,研究者开始运用包括提出女性问题、实际推论、性别意识觉醒、社会性别分析在内的女性主义法学的特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特别是对有关女性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已成为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常见方法。另一方面,研究者专业领域的广泛性也为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带来了其他学科的视角,法学相关交叉学科的方法亦被引入女性主义法学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开始展开对女性主义法学理论流派的精细化研究。邱昭继教授较早关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其在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领军者辛西娅·格兰特·鲍曼教授的帮助和指引下开始了此议题的研究。近两年中,他不仅发表了《女性主义法学的马克思主义之维》一文[18],亦在其任执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第2卷)中设置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专题(20)该专题刊有三篇文章:[美]辛西娅·格兰特·鲍曼:《在21世纪复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邱昭继、李勇译;[美]黛博拉·L.罗德:《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林芳译;邱昭继:《通过法律实现妇女解放——基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学的分析》。参见李其瑞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2018年卷总第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且正着手出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文集》。当然,除对自由女性主义法学、激进女性主义法学、文化女性主义法学等传统女性主义法学流派的研究外,有关后现代女性主义法学[19]、生态女性主义法学[20]、家族女性主义法学[21]的研究亦开始出现。
(二)国内外研究平台的搭建助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
随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开始逐步突破各自为政的状态,以寻求构建一种研究的新平台。就教学平台的设置而言,如,苏州大学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中设置了“性别与法律”方向;厦门大学获批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博士点,下设“性别与法学”研究方向;西北政法大学为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在西方法理学课程下开设了美国女性主义法学专题。从国内学术会议层面上讲,2018年5月,中国法学会首次以“法律和性别”为主题,举办了“法律与女性发展圆桌论坛”;2019年9月,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在第一届“法律与女性发展圆桌论坛”的基础上,举办了“新时代妇女与法律的发展、挑战与应对研讨会”。在新近成立的研究中心方面,例如,2019年4月,南通大学、南通市妇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南通性别平等研究所[22];2015年,山东女子学院成立了“性别与法律”校级科研团队[23]。还应当关注的是,《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等妇女/性别学期刊,均设置了与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栏目(见表1)。

表1 2012至2019年(截至2019年10月1日)国内主要女性杂志刊载女性主义法学文章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中国妇运》等女性杂志官网和中国知网数据整理而成。
此外,我国也有学者试图展开同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家之间的对话。2013年4月,鲍曼教授受邱昭继教授之邀到西北政法大学作了关于美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学术报告,本次学术交流中“双方的良好合作使她萌生了在中国某地邀请美国与亚洲学者举办女性主义法学理论会议的想法。因此,“美国和亚洲国家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研讨会——跨太平洋的对话”最终于2015年5月在上海召开”[16]前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和康奈尔法学院共同资助,来自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十位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此乃中美沟通协作共同促进女性主义法学发展的成功例子。得益于“美国和亚洲国家女性主义法学理论研讨会”的召开,历时三年的斟酌打磨后,《女性主义法学:美国和亚洲跨太平洋对话》一书得以出版,该书收录了五位中国学者的文章(21)具体包括,陈昭如:《麦金农的宰制理论》;於兴中:《女性主义法学在中国:现状与前景》;杨晓畅:《家庭劳动分工、妇女地位与女性主体性》;邱昭继:《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与妇女解放》;杜仪方:《中国生育立法制度与实践之演变》。参见[美]辛西娅·格兰特·鲍曼、於兴中主编:《女性主义法学:美国和亚洲跨越太平洋对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时至今日,沟通和交流正在推进,在各国致力于女性解放的法律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有可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新突破。
(三)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不足
发现问题乃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女权主义法学研究发展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当下研究者之间呈现出的各自为政的状态,进而指出要整合、统一并迈向作为独立法学学科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这无疑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重大进步。社会性别理论指引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已有二十余年,当下,学者开始基于不同视角反思这段学术史。审视结果固然会因为所在学科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他们基本形成了共识,即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在法学研究和法学学科设置中被双重边缘化。具体而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存在法学认识论层面研究不足、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边缘化、研究者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立场以及研究队伍小且学科背景单一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掣肘着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发展[3]。
事实上,自沈宗灵发表第一篇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的论文以来,不少学者也发表了有关女性主义法学的著述,但这些著术偏重于对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的评介。尽管我国婚姻法学者对许多女性主义法学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此种研究侧重于对法律制度的评价和建议,较少涉及女性主义法学理论问题。社会学界亦有不少学者研究女权主义,但他们的研究对法律问题的关注不够。这便导致了国内女性主义法学远不及分析法学、法社会学、自然法学甚或是法经济学的影响力[24]。就概念的使用而言,“女权主义法学”“女性法学”“妇女权益保障法学”“妇女法学”等概念虽然已被使用,但研究者并未对这些概念及其社会背景、学理基础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梳理,更没有形成通行的系统化理论和知识体系[25]。
从学科设置的角度上讲,正是系统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缺位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因此,“未来中国女性法学研究应继续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学科专业间的理论交换与整合”[17]。与此同时,也需要促使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学科聚焦中国女性问题、加强对中国性别平等经验的总结、明晰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并通过加强人才培养来壮大女性法学的研究队伍,以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学科的设置奠定基础。在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队伍上,於兴中教授身处旁观者之位尖锐地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女性主义意识持续增长,法律女性主义或曰女性主义法学却进步甚微。很少有法学学者有兴趣参与到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中来。几乎没有人被称为女性主义法学家”[16]93-94。於兴中教授的判断固然可能因视角不同而存在偏差,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队伍弱小却是事实。
可见,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的关注点虽有差异,但历经二十余年的研究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女性主义法学在法学研究中处境的边缘化以及既有学科设置对女性主义法学的排斥,进而提出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新发展的期望。
三、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发展
1949年以来,我国在否认歧视和压迫女性之法律的基础上颁布了坚持两性平等的新法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了较完善的保护女性权益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法律体系。然而,法律的完善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繁荣。即便1995年以后我国开始引介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著述,并逐步形成学术自觉,但中国并未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或学科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法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梳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历史,旨在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新发展。就可能的路径而言,大体可包含如下三方面:
(一)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和女权行动者之间应形成平等的沟通和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法学之间存在辩证的螺旋发展关系[26]。在美国,女性为改变与女性权利有关的法律而发起了女权运动。女权运动不仅促进了女性的意识觉醒,也为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素材,包含凯瑟琳·麦金农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法学家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反观我国,清末伊始,中国女性便踏上了漫长且艰难的解放之路。辛亥革命至今,我国至少有过六次女权运动(22)郭箴一先生将中国妇女运动划分为辛亥革命以前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运动、北伐时期的妇女运动。参见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妇女运动,参见单炜鸿:《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此外,还包括以“女权五杰”为代表所展开的新时代女权运动。。然而,当女权运动风起云涌时,中国女性主义法学仍了无起色,缘由之一在于女权行动派和研究者间存在的某种博弈。特别是今天,研究者多讳言“女权”,亦为“明哲保身”而与女权行动者保持距离。特别是在“中华田园女权”被极度丑化,“女权婊”“女权癌”“女权纳粹”等污名化语词不胫而走的今天,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更是闭口不言。事实上,实现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和女权行动者之间的“破冰”或许能为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打开新的突破口。
具体可从如下三方面展开。一是,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可采用座谈和访谈等方式,认真听取女权行动者的意见,以发现研究的突破口和新问题,或直接参与到女权主义实践活动中;抑或是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发声,以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指引中国女权运动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二是,中国女权行动者应主动调整心态,破除同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之间的隔阂,树立与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合作的观念。同时,女权行动者应认真阅读与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理论著述,并学习掌握“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争取在中国女性主义法律理论的指引下,有针对性、有策略地开展活动。三是,官方和社会各界应为女权行动者和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提供沟通和互动的平台。平台的构建可由妇联牵头,各合作高校联合开展。例如,全国和各地方妇联对此两类主体设定专门的座谈机制、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定期邀请女权行动者中的杰出者作报告、妇联和高校联合召开包含此两类主体的学术会议等。
(二)国家法治应实现从专注“丈夫之仁”到兼顾“妇人之仁”的转型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大多被贴上了贬化的标签,有关女性的文化亦如此。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许多积极方面,其中之一即是对关系的强调,这又集中体现在“妇人之仁”概念中。然而,此种强调关系的“妇人之仁”历来被贬损和压抑,进而成为了懦弱的代名词。相反,从王朝的更替,到平民百姓的生活起居,中国历史无一不是由“丈夫之仁”写成。作为被历来忽视的仁爱类型,“妇人之仁”关注的是生命的成长,而非权力和领土的扩张;其以情绪、爱和热情为注解,并珍视养育、教诲和规劝。然而,“几乎所有文明的官方历史都是服从和支配的历史,权力与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的历史,疆域分合的历史”[16]98-99,都与“妇人之仁”相去甚远。事实上,“妇人之仁”在历史上受到贬损应归因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崇拜。
西方女权主义者在两波女权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开始挑战男权至上的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波伏娃和弗里丹等女性先驱率先道出了女性的奥秘,并揭开了男性崇拜的面纱。反观我国,虽然有过几次妇女运动,但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多是男性。在男性把持和官方主导下的妇女运动即便关注女性权利问题,亦不免带有浓厚的家长主义色彩。如今,此种状况已在发生改变。挑战男权统治固然是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大步,但问题的关键并非迫使男性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强调“丈夫之仁”和“妇人之仁”的融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男女平等”,强调男女的相似性,以实现法律的同等对待[27]。但无论如何回避,女性皆不同于男性。关系女性主义法学采纳“道德相对论”[28],试图构建的正是“妇人之仁”意义上的美好社会生活图景,即注重爱与关怀,推崇仁慈、怜悯、同情心[29],并强调热爱和平、反对暴力。
自学者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伊始,此种陌生的资本主义理论便备受质疑。如何将西方女性主义法学引进并改造,以融入中国文化,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面临的棘手难题。“妇人之仁”兴许能担此重任。当下,不仅要实现对被贬化甚或污名化的“妇人之仁”的“拨乱反正”,更要加以褒奖并使之复兴,以平衡国家法治整体中的性别差异。无疑,国之强盛不能没有男性之阳刚抑或必要的“暴力”,但民之幸福亦不可缺少“妇人之仁”倡导的关爱、自然与和谐。于此,若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法学,要同等重视“丈夫之仁”和“妇人之仁”,以使国家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从关注权力、抗争转移到对生命的滋养以及人性的成长;从制度安排转移到对才智的陪护上来。融合“妇人之仁”的中国女性主义法学或许能够清除男性主宰法治的弊端,从而赋予女性的道德声音以同等的分量,亦可能扩大法学研究的内容范畴,进而形成一种聚焦边缘群体并有审美旨趣的法学理论。
(三)凝聚共识是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发展的前提
当下,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问题在于,就基本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及研究立场等方面,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当下,各自为政、互不了解甚或立场对立,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的现状。这导致的后果是学术交流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达成共识是展开平等对话和争鸣的前提。但因女性主义法学在我国不受重视,加之研究者各自为政的状态,导致了凝聚学术共识备加困难。凝聚共识尽管艰难,但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也要负重前行,首当其冲的便是明确概念。虽然本文采用的是“女性主义法学”一说,但研究者使用的概念可谓五花八门,包括“女权主义法学”[30]“妇女法学”[31]“女性法学”[17]“妇女权益保障法学”[32]“女性法哲学”[33]等。各概念所用语词虽有不同,但实质内容却并无太大差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可与中国法学会合作举办研讨会,邀请持不同主张的代表性学者共同商讨,以求达成概念共识。各大女性期刊杂志有关女性主义法学栏目的编辑亦可召开内部联席会议,商讨并推动实现论文发表中的术语统一。此外,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还应树立凝聚共识的学术自觉。
若言及明确概念是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前提,那么科学设定研究范畴则是使其成为独立法学学科的关键。就研究范畴的分类而言,本文认同马姝的做法,即将研究范畴划分为认识论层面的研究和法律事实层面的研究两部分[3]。一方面,应当强化我国女性主义法学认识论层面的研究。相较之法律事实层面已有的经验,如何在认识论层面作出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贡献,是研究者面临的时代拷问。我们何以关注西方文化女性主义主张的关怀和同情,却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妇人之仁”?何以相信激进女性主义扬言的女权颠覆,而置“和谐”“中庸”等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于不顾?事实上,确立中国版本的女性主义法学无疑要回到中国。另一方面,需要整合法律事实层面的研究。相较于认识论层面研究的匮乏,具体实践层面的研究已有了较多的成果。时下,要推动中国女权主义法学研究迈向发展新阶段,则需要整合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并按照学科门类或问题划分,确立事实层面的研究范畴。
凝聚共识还需从教育层面着手,各相关高校可设立与女性主义法学有关的课程,并编写女性主义法学的统编教材。具有博士或者硕士点的高校可在法学理论等专业下设置“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方向,统一培养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后备力量。此外,“扩大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消除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知识隔膜,运用跨学科的思路和方法”[17]亦是凝聚共识的重要方面。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应主动担负起凝聚学术共识和形成学术共同体的重任,以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法学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并实现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从边缘到中心的迈进。
四、结语
自中国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法学以来,被冠之以“女性主义”之名的法学理论研究无奈被置于不被接受甚或是被贬损的尴尬境地。有鉴于此,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者面临之最棘手的难题是——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女性主义法学?此待决问题的存在致使女性主义法学研究走进了“死胡同”,不少研究者曾在学术生涯的某个阶段涉足过女性主义法学,但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退离女性主义法学的研究阵地。
事实上,导致女性主义法学处境边缘化的原因大体包含三方面:一是受本质主义的影响,将西方女性主义法学视作某种具有本质属性的理论,一切与之不相符的内容均不属于女性主义法学。简言之,无论语境和内容如何,但凡提到女性主义法学便会被贴上西化的标签。二是女性主义法学概念的异化,潜移默化中,原本中性的女性主义法学被带有价值判断的“女性主义法学”所取代。三是女性主义法学概念下之“名”与“实”的混淆。由于作为舶来品的女性主义法学被异化,与之同受贬损的则是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内容,即名称的贬化导致了内容的贬化。
就此而言,有关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梳理具有重要意义,其表明无论名称如何,中国存在女性主义法学议题的探讨和研究,故女性主义法学概念的“祛魅”尤为重要。当我们为附着“激进”“后现代”和各种被污名化的女性主义法学概念正名时,不难发现,即便我国女性主义法学在理论层面稍有欠缺,但在反就业性别歧视、反家暴、反性骚扰等议题上已形成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而这些恰恰属于女性主义法学实践层面的研究。因此,历史和现实已证明中国存在女性主义法学,这构成了推动迈向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新阶段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