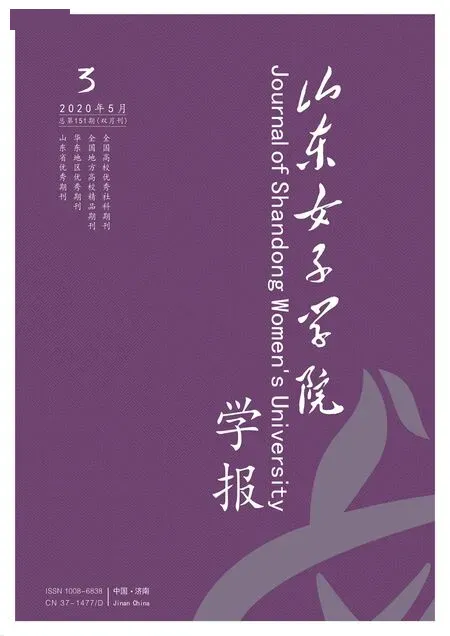“匹妇”有责:女性在抗战中的角色与作用
——以湘桂抗战为例
2020-02-26庞少哲
庞少哲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开端,此后,中国军民开始抵抗日军侵略。这场抗日战争使得“战争不属于女性”这句话几乎沦为空谈,这一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促使社会各阶层联合起来,当中就包括各女性阶层,如上层精英女性、女学生、普通家庭妇女,甚至歌女、妓女等底层女性。学界对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不胜枚举,对抗战时期的女性研究亦有不少,但大多是以个人传记类的形式叙述女英雄事迹,或是从宏观角度对女性群体的抗战动员、团体组织、政治参与、婚姻问题等进行讨论,对某些战役中女性的作用似乎缺少一定的研究(1)例如,丁卫平的《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丹柯的《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出版社,2015年),游海华、叶潘虹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区域的妇女动员与救亡》(《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3期),宋弘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朱旭旭的《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历史作用》(《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乌尼日、张艳的《闺闱救国与人同——中国妇女与抗日战争》(《广西党史》,2006年第11期),夏蓉的《“省新运妇委会”与战时广东妇女界的抗日救亡工作》(《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林庭芳的《邓颖超与国统区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1期),等等,皆是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李黎明的《近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运动研究综述》(《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及徐明涛、谭刚的《近八十年来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民国研究》,2018年第2期)两篇文章中,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关于抗战妇女史研究作的详细梳理,但都是以1937—1945年为上下限,对1931—1937年间的妇女史研究有所忽略。。在民族危难时期,她们用特殊的方式参与着反侵略斗争,甚至将反侵略使命融入日常生活中,她们在后方抑或在前线的工作都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尤其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湖南和广西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前线和主战场,在湘桂抗战中,许多女性个人、群体纷纷起来,支援这场民族战争(2)关于湘桂两省的妇女抗战研究,例如,刘惜时的《简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妇女界的活动及贡献》(《红色记忆-雨花党史丛书》第1辑,2015年),莫俊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湖南妇女》(《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唐剑彦、郭双林的《“强种强国”:抗战动员与广西新女性形象的构建》(《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颜小华、胡桂园的《民国新女性郭德洁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1期),秦雅萌的《“木兰从军”故事的现代讲述——以抗战时期的上海、桂林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陈一新的《抗战时期广西推进妇女武装文化教育概况与启示》(《抗战文化研究》第4辑,2010年),詹永媛、李继东的《论抗战时期广西妇女运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等等,均涉及相关内容。。这不仅展示出女性非凡的行动力,而且还为实现民族解放,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
因此,本文以湘桂抗战为例,包括长衡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重要战役,探析女性在战争的特殊时期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抗战作出的贡献,主要从上层精英女性的组织抗战、女学生“投笔从戎”的前线抗战与动员、普通家庭妇女的有力支持、底层女性的协助抗日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探讨在这战争的非常时期,各阶层女性群体是如何产生关联的,以期丰富人们对中国抗战史的认识,并促进妇女史的研究。
一、上层精英女性的组织抗战
民国时期上层精英女性的活动对社会是有一定影响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促使社会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于传统压迫中解放女性的呼声愈发高涨。湘桂地区原本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影响较大的女性逐渐挣脱原有束缚,走上街头,甚至寻求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参政权、参军权。到了抗战时期,这些当初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女性,例如,湖南地区的王家祯、张素我、洪希厚、曾宝荪,以及广西地区的郭德洁等,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精英人士。
1937年9月,曾作为湖南省体育代表、以国术指导兼运动员身份出席全国第六届体育运动会并斩获女子射箭项目第一名的国术馆教授王家祯女士,退役后招募100多名进步女青年[2]14-15,成立女子大刀队,专门训练杀敌技能。受训一个月后,这些女青年直接开赴前线,挺入战火纷飞的最前沿,奋勇杀敌。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为了配合战区抗战宣传慰劳工作,该国术馆增添了抗战宣传队、伤兵慰劳队、防空训练班、抗战图书阅览室、抗战话剧队等,这些与王家祯不无关系。
1934年蒋介石开始提倡新生活运动,至1937年全面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已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夫人洪希厚为主任,而实际为其女张素我代理。张素我较为开朗,能接纳妇女界各方面人士的活动。在她的积极努力下,从1937年11月下旬至1938年5月18日,在妇女运动中领导工作的干部就达三百人[3],她们的工作中心是改善妇女生活与组织各界妇女的联合以支持抗战,工作范围包括伤兵救助、难民救济、战地慰劳、募集物资、救济流亡学生以及组训等。她们的带动使得湖南省妇女团体在服务伤兵和救济难民运动中成为贡献最突出者。而洪希厚作为实际的主任,也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在她的号召下,“各地女同胞,奋起捐募不相让,政府只要百万件,我们要捐百万双”[4]。还有长沙艺芳女校的创办人、曾国藩之曾孙曾宝荪自1942年11月下旬由香港脱险返抵衡阳后不久即返回老家“富厚堂”,并一直居住至抗战胜利。在老家居住期间,她慷慨招待各路抗日游击队,“专请了两个工人,探听各路游击队的动向,如若在我们的境内——荷塘乡下半乡——我们就差遣人挑肉、米、菜、酒去劳军”[5],或是提供各部召开协商会议的场所等,以支援抗战。再有,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之妻张默君女士,为纪念丈夫殉难两周年,特将平日储存的五千元全部捐出,其中四千元为前线将士作寒衣,一千元则赈济长沙大火的女人和孩子[6]。这些社会上层的女性群体,组织妇女联合抗日、带头劝捐、慰劳军队的工作,既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又促进了后方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而广西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地情地貌,原本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广西女性接受外来新思想的阻力亦相对小些。例如,抗战期间,广西第一夫人、李宗仁之妻郭德洁就全身心致力于抗战救国。在1939年7月,郭德洁便开始担任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为《广西妇女》杂志社社长、国家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理事、广西妇女抗敌后援会常务理事,以及第五战区妇女委员会主任,身兼多个要职。在抗战期间,她对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尤为关注。在她的领导下,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要从倡导妇女积极参战、训练妇女、提高其谋生能力、改变旧风俗等方面领导妇女运动,切实以唤起妇女思想觉悟、促进妇女进步、支持全国抗战为出发点。为积极推动妇女解放,郭德洁具体提出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内容,共八项,其中,就有社会服务一项(3)另外七项内容为妇女职业、参政运动、女子教育、儿童教育及母性保护、妇女生产事业、新生活运动及政府倡导的各种社会运动、健全及发展妇女团体组织。,内容包括慰劳、救护、劝募、扶助难民抗属(抗日军人家属)等[7]。此外,她还主持发动桂林各界妇女卖花筹款慰劳将士,并带头认制纸花一千朵[8]。
其实早在大革命时期,郭德洁就先后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和广西女子北伐军宣传队队长[9],跟随李宗仁部队出征。据李宗仁回忆:“时余妻郭德洁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10]238她甚至还专程为女兵作报告,以鼓励后者。抗战爆发后,她在第五战区视察时,就对女兵演讲:“我们第五路军第一届学生军中的女生,她们在前方做许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个人也到过前方,关于学生军及其他战地服务队救护工作团的工作情形知道不少。在工作的效率上讲,女子服务的作用,有时比男子为大”,并分析了目前抗战工作中女生要注意的各个事项[11]。作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到桂林考察妇女救亡运动时,也“曾来对女生大队训话”[12]。1938年,当广西女学生军北上抵达武汉时,同为广西人的时任中央长江妇委委员邓颖超在蛇山抱冰堂前就对她们作了“关于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战争”的报告,指明中国妇女唯有积极参加抗战,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才有妇女的彻底解放[13]。她们对广西女学生军的演讲与训话,有效地激励了后者在前线的工作,并成为后者了解上级抗战工作指示的重要来源,也为后者在普通家庭妇女、底层女性等其他社会阶层中传达上级抗战思想提供了支撑。
除了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上层女性之外,地方官太太也尽一己之力,为组织民众抗日发挥着作用。例如,为改善民众生活、协助民众生产、增强抗战力量,藤县“陈副县长夫人,亦参加工作”[14],并组织民众成立生产合作组织,从事各种生产;蒙山县的县长太太在义卖活动中“挨各家商店征募什物”,所得款项后被用于救济“重庆的被炸难胞”[15]。
综上,这些社会地位颇高的上层精英女性在面对救亡图存的国家危难之际,或组织志同道合的女青年赴前线奋勇杀敌,或是在后方加油打气。简言之,她们更多的是凭借着自身的社会地位发挥着组织者与号召者的作用,也可以说,她们是女性抗战的直接领导者,而女学生军的“投笔从戎”则更巩固了她们在女界抗战的组织与领导地位。
二、女学生“投笔从戎”的前线抗战与动员
国难当头,校园象牙塔里的青年无法静心只读圣贤书,所谓“日寇不除,何能安心读书?”[16]283这些投笔从戎的女兵,在寻得读书受教育权后,亦渴望像男性一样参军上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作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湖南分会(简称“妇慰会湘分会”)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谢冰莹(4)谢冰莹(1906年9月5日—2000年1月5日),原名谢鸣岗,字凤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铎山镇(今属冷水江市),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在她年幼时,虽然家族的塾馆不收女生,但由于其家中资财富足,塾馆先生碍于其外祖的面子及谢冰莹对求学的执着,破例收下这位弟子习读四书五经。之后谢冰莹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校(又名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未毕业即投笔从戎。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经过短期训练,便开往北伐前线与敌人恶战。1927年又先后入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习。1931年毕业后,谢冰莹赴日本留学,不久因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等种种原因被日方遣返。1935年她再次赴日,七七事变后回国加入抗日队伍中。,为救祖国危亡愤而从日本返国,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自任团长开往前线。例如,同年9月14日,她带领十六人奔赴前线[17]10,于长沙乘火车赴武汉转上海前线战地服务。大批长沙市民纷纷前往车站送行,不少女学生临时苦苦要求加入服务团,场面颇为感人[2]15-16。谢冰莹带领着这些女学生们在“流弹到处乱飞”[17]80的战场上救助大批伤员,并做宣传鼓动工作。她把战地当成自己的家,“战士们的鲜血,是世间最雄壮最美丽的鲜花”[17]223,还写下抗战日记,记录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战地生活的一点一滴。她的出现,吸引了全省大量进步女性报名入团,其中包含大量女学生。该团在谢冰莹的领导下,在长沙统一训练,主要学习医疗护理、女工剪裁和战地实践技能,做到了成熟一批,便送去外地一批。至1938年2月,为战地前线共计送去一千多名妇女,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抗日最前线为伤病员包扎护理,为人民军队缝衣补鞋,并且在战地开展赠送书刊、教唱爱国歌曲等精细化的服务,为鼓舞士气、救援伤病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除谢冰莹外,同样率领湖南战地妇女服务团前往前线的还有刘慕棠,其从军校武汉分校六期女生队毕业后,于1937年10月4日率第三批服务团六十余人[2]19,紧随谢冰莹步伐,赶赴上海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广西地区的女学生投笔从戎现象就更司空见惯了。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所说:“青年为革命之先锋队,国家之新生命,在此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斗争中,尤端赖于青年之策动以为其主力。”[19]因此,除了男学生军以外,早在北伐战争中,为配合军队作战,在郭德洁的领导下,有女学生百余人组成“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10]238。由于在校时已接受过军训,较易于组织,她们行军的“服装、生活,都和其他部队的男战士一样,耐劳、勇敢,也和其他部队的男战士一样。总之,她们的一切,都不会落人之后……有时,杂在正规部队中和敌人作战,她们因为比较沉默和镇定的缘故,对于一切战略的运用,还胜男人一筹,常使男人遭受重大的挫折”[20]。这些女学生军,“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抛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她们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10]238-239此后,广西战场上也不乏女兵的身影,尤其是在抵抗日军侵略的战场上。七七事变后,广西桂林组建第二届学生军,全称“广西学生军大队”,其中,下设男生中队与女生中队,中队长由大队长和队副兼任,另设中队副三人[21]。经过一个多月的短暂训练,于1937年12月中旬,学生军即北上抗日。当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广西由于接近战场,地位愈显重要,为适应环境,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扩大学生军团队伍,“增强我省抗战力量,以对付敌人计……召致所有向来救国有心,而请缨无路之热血青年学子,参加入团”[19]。因宣传与号召有力,许多青年学生在抗日热情的驱使下,毅然投军,虽原计划招考一千二百人,但报名的人数达一万八千人,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精选了五千余人集中训练[22],其中有“娇生惯养的女同学,不顾爹娘的鞭骂与哭泣,英勇地、坚决地走上她认为应走的途径”[23]。当白崇禧认为女子更宜任后方之宣传救护锄奸等工作、男子更宜军旅之事时,女学生军毫不退缩,请愿参加前线工作,认为“行军算不了一件难题”[24]。除了在广西境内之外,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省份的抗战前线,亦不乏广西女学生军的战斗背影[25]408,她们保卫国家的决心与毅力不让须眉,甚至被称为“铁的女性”[26]。当然,在战地后勤和救护工作中,女学生同样表现出色,她们积极参与救护工作,例如梧州女中学生就组织战时服务团六十余人出发桂南前线工作,分赴石龙、柳州、迁江、宾阳各处医院服务[27],“为伤兵敷药裹伤写信缝补送茶添饭,以至于慰问伤状、报告战况、宣传抗战意义等,她们的工作是那样的勤恳,她们的精神是那样的奋发,她们的工作是那样的紧张”[28]。女生参与救护,不但有利于鼓舞伤兵、提高士气,且因多数女生事前都接受过一定的战地救护训练,工作亦较为细心,对伤兵的照顾较为周到,能使伤兵很快出院归队,提高部队战斗力。
这些女学生们不但自己参军,还拥护政府的征兵政策,动员民众参军。她们主要从慰问军属、宣传入伍的意义着手。例如,桂南战役爆发后,女学生军积极慰问军属,以提高官兵士气。“那天慰问团来了五个人,全是军人装束的,是什么学生军。五个人中有两个是女的,她们手上挂了一团纸制作的小红旗,到了桂英的家,说是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的。她们说,当兵去打日本鬼,保卫国家,这是最光荣的。政府很关心他们家里人的生活,派了她们来慰问一下,送来了一些火柴、肥皂、毛巾等日用品,还在桂英家的门口贴了一张光荣牌。”[29]此外,当女学生军在行军途中宣传抗日救国时,就有一老太婆深受感染,大喊“我也要叫我的侄儿去当兵了,要把日本鬼赶快杀光”[30]。正因这些女学生军的努力,不少民众打消了原本的顾虑,认识到被征入伍的意义,对政府的征兵政策由反抗、迟疑转为拥护,由害怕当兵转为积极踊跃应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解决了兵源缺乏的问题。
在筹集物资上,这些女学生身体力行地为抗战物资的筹集献出一份力。例如,1937年10月,湖南省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全体师生于4、5、6三日,每日节食一餐,以所省之费慰劳前方将士[2]19;1939年10月,全国各地掀起慰劳湘北将士热潮时,周南女中捐出44元并义卖捐款157元,明宪女中捐出92元[2]127。非在校的女学生军则大多是在集训期间,利用训练空闲,组织义卖队,走上街头开展义卖活动。由于她们每到一处,都“通过帮助群众做家务劳动,很快和当地妇女打成一片,亲如姐妹”[31],这就为发动妇女群众打下良好的基础。于是,女兵们得以利用群众中的“姊妹会”形式来发动和组织妇女募捐。如苍梧县广平圩的女兵就筹得桂钞80多元,布鞋140多双,献给前方战士[32]375。
并且,这些女学生军在联系当地妇女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对外抵抗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动员民众参军、筹集物资之外,她们还积极动员广大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参与抗日救亡。首先,她们积极组建抗日救亡团体,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在广西岑溪县县城里便“组织了妇女抗敌后援会,会员竟达三百多人”[33];在桂西南地区,女学生军“组织和恢复了十三个妇女会,会员共三百多,成立了三十六个成人班和妇女干训班,人数八百多,姐妹会八个,其他临时性的组织实无法统计,但在我们的缝补队里,除了青年力壮的外,更有花花白发的老太婆”[34]。其次,女学生积极引导和训练妇女组建游击队,或直接对日作战,或参与战地后勤,以种种方式支援前线。“抗战形势日益加紧,加以主观上的努力,在流行各乡的姐妹会读书会良好的影响下,武装的妇女游击队以新的姿态出现了。”[35]68由于广西女学生军“在行动方面,尤其是女生的武装精神,常会使各地虚挂照牌的抗援会及妇女团体,受了对照刺激,而实干起来”[36],当她们北上途经湖南时,当地妇女“成群结伴拥到我们的宿营地,争着看女兵……人们在振奋地谈论着:‘你看!广西连学生都动员上前线了,还有那么多女学生呢!只要全国民众奋起抗战,中国就不会亡!’”[25]411每到一地,女学生军还试图组织战区妇女,发挥她们在抗战中的作用。“敌人的炮声促使战区妇女的觉醒,我们要很好地引导她们,鼓励战区妇女积极支援部队作战,为打败日本鬼子贡献妇女的力量”[25]421。因“女学生军到达一个工作地区,就……拜干妈,结姐妹,一套联络感情的方式,使妇女们在妇女会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她们不但积极起来参加了各种救国工作,像玉林、陆川、北流各县都组织了妇女游击队了”[37],而且当地妇女也“因为契儿女在军中,契妈(5)契妈,即干妈。渐渐注意了国事,渐渐参加了民众救国团体”[38]。包括游击队的策源地陆川县西稔乡,以及米冲、山口、陆城等地的妇女游击队,均是在女学生的策动和帮助下组织的。当妇女游击队组建后,为了加强训练和教育,女学生军便负责该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对她们讲解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妇女解放的道理,并教她们学文化,学宣传技术,如唱抗日歌曲、演话剧等”[39]。再次,女学生动员当地妇女参加破路,以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阻止日军的前线步伐,迟滞日军对前线的增援。“在上思,女同学领导民众破路,感动了当地的妇女,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来参加,妇女破路队也就在邕钦线上活跃着。”[40]
3) 根据铁钻工对其回转机构旋转功率的需求,选择液压泵驱动系统,设计相应的减速器并选择配套电动机,提出了液压系统的设计基本方法。
不难看出,这些年轻气盛的女学生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愿挺身而出参军保家卫国,积极响应上层女性的组织与号召,她们在行动上诠释了何为可柔亦可刚。她们的柔和细致可以为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增添一份筹码,包括以建立妇女救亡团体、妇女游击队、妇女破路队的形式,联合普通家庭妇女支持抗战,组织与训练妓女、歌女等底层女性支援抗战,并向她们灌输上层领导的抗战思想,宣传抗战理念。据统计,女学生军工作一年多以来,组训的妇女训练班有38个共2416人,妇女会有63个共4047人,妇女游击队有7个共332人,妓女(旅业姐妹)训练班或歌女救亡队有13个共763人[41]。这些抗战团体大部分是在桂南会战前组织和成立的,这就为切实保证各阶层女性联合抗战、共同参与救亡活动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这些女学生军在战场上勇敢、刚强,不输男性,她们的出现,有力地推进了这场全民族的抗战。
三、普通家庭妇女的支持抗战
战争是人制造的,对战争影响最大的是人,受战争伤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别是普通人。当普通家庭中的男性都上战场奋勇杀敌后,留守家庭的重任便落在妇女身上。普通妇女在抗战时期为生存而作出的努力,是值得重视的。这当中,有送儿上战场的女杰,有居家做坚定后盾的慈母,还有化身为白衣天使救助伤者的普通家庭女信徒。
1943年常德会战时期,衡阳女杰周咏南携子一同参军的故事被立为楷模。其子黄天在《我的母亲率我从军抗日》中说:“我的母亲,名叫周咏南,湖南省祁东县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6年。她是黄埔军校16期的毕业生,我也是16期毕业的,我们母子二人,在抗战初期,同时报考了黄埔军校,为同期同学,以后又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42]98当时她39岁,早已超过报考年龄,但她的“日寇不灭,难以家为”感动了军校并破例录取之。在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对其母子二人进行了嘉奖:“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42]100。《救国日报》亦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了报道。后此事感召大批长沙妇女参军报国,军队建立了专门的女兵连,对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女兵统一训练,周咏南任上尉连长。在常德会战期间,她率军参加津市(6)津市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下游,为省辖市(地级市代管),隶属于常德市。保卫战,进行白刃战时,虽腿负重伤,仍指挥女兵抗击敌军。在其英勇指挥下,击毙日军数百人,为阵地战提供了有力支撑,最终使常德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
然而大多数普通家庭妇女并不能如周咏南一般随子从军参战,而是留守家中待夫凯旋或待儿归来,扛起武器的她们更多是从自卫的角度出发。例如,1943年11月下旬,湖南澧县三沫乡的两民妇智杀5名日军。日军侵入该乡时,有两名日兵进入该民妇宅,两妇于日军卸装时趁机将其击毙。次日,又有3名日军进入该宅,两妇各执菜刀,将其砍死[2]238。这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及保卫家园的目的,而被迫与日军发生的正面冲突。当然,亦有家庭妇女如前所述,接受女学生军的帮助,组建游击队,直接抵抗侵略。对于当时的陆川妇女游击队,有人评价道:“广大的妇女能够武装起来,这在广西是破天荒的,她们实在是一群妇女解放先锋队”[43]。1939年12月,上思妇女成立自卫队,她们“与男子同样地受着游击战术训练,而且同样地负起重大的任务,她们日夜轮流着当哨兵,在山谷野麓中监视着敌人的到来,假使是鬼子来了的时候,她们便毫无畏惧地拿起枪杆与敌人作殊死战”[44]。除了自卫队以外,上思妇女还组织了洗补队、运输队、慰劳队、锄奸团,成为一套近乎完整的抗日团体。再如,横山女游击队中全副武装雄赳赳的女健儿,被当作是妇女解放的先锋队,是新妇女的模范,她们“跑出深闺厨房,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保卫祖国”,成为乌石妇女等其他地区女性学习的榜样[45]。这些妇女的抗战,不但有效地动员了民众参与支援军队作战,而且鼓舞了中国民众的士气。甚至连日军军官高木都对此惊呼,谓广西宾阳附近战斗着“支那娘子军”[46]。
除了扛起武器自卫的部分妇女之外,还有留守家中的普通家庭母亲,她们心系前线,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47]200的口号号召下,开展捐赠,以一己之力支援抗战。最令人感动的是,有一次,一个小孩扶着一位盲眼的老婆婆上台捐献,她用枯槁的双手颤颤巍巍地将多年储存的“棺材本”——二十枚银元,小心地从一块一块破布中剥露出来,把它投进献金箱去[47]201。在号召全民参与抗战的热潮下,因男子大多被征为壮丁或被政府征工从事其他服务工作,参加生产组织的民众主要以妇女为主,而妇女对抗战的贡献,也逐渐由个别人参与变为一种普遍现象,上至八十岁的老太婆,下至七八岁的女童,无法直接加入抗战阵营时,便在田间、家中忙碌,间接帮助抗战。1938年9月,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总会成立之后,就有上林妇女“以赤诚的心,密密的线缝成了两千双的布鞋,捐献给前线将士,更有上林某村,全村妇女用自己血汗积成的钱,捐献了五十余元给将士做寒衣”[48]。再如,北流妇女“发动了做鞋运动,后来竟做了七百双布鞋送给前方英勇的战士们”[49];1939年的三八节,广西玉林有妇女“义卖和募捐,一共得了一千多块钱”[50];陆川妇女成立“消费合作社”,这是“由热心的妇女合股经营,做鞋、衣车成绩也不错”[35]71。除了捐钱、做鞋、衣车之外,还有捐出田产、慰劳伤兵的普通家庭妇女。1942年11月,湖南武冈紫阳乡的王黄翠女士捐田产600亩,交县府兴办各种公益事业[2]211;湖南南县、石门、沅江、湘阴、益阳、浏阳等地的妇女团体也在慰劳伤兵、募捐物资上为抗战献出一份力[51]。
此外,相比于拿起武器自卫、捐献财物,还有一些信教的家庭妇女依托宗教团体组织,积极对社会展开救助。由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柏德贞(Charlotte Bacon)创立的桂林道生医院、由美国雅礼协会在长沙创办的湘雅医院等,在抗战时期,其女医生、女护士在治病救人上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抗日战争的号角吹响,驻华的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浪潮中,在1937至1941年间,增派两广地区的修女从28人变为38人[52]362,当日军暂停轰炸时,她们便行走街道慰问民众,分发药品,救助伤员[52]369。这些外籍修女的救助活动,无不影响着本土女性学而趋之。当位于“两广交界的梧州市外围到处都遭到惨烈的轰炸”[53]时,隶属于美国浸信会的梧州思达医院全体外籍医生拒绝撤退,积极参与救助,与中国人共抗日军[54]。之后,他们积极筹备药品物资,其中的理力善牧师(Rex Ray)甚至冒险偷越日军封锁线南下香港以进购药物,而其中的同行者就包括两名中国女信徒[55]。并且,在女学生军的号召和发动下,不单是基督宗教女信徒参与抗战救援,还有女佛教徒亦加入其中。梧州市珠投岭的佛寺西竺园的女佛教徒就在园内走廊设立“抗日阵亡烈士灵位”,每天念经祈祷,并积极为抗战献金;还有富民佛堂的女教徒,连同一百多名家庭主妇教友,参与捐款和衣物、浴巾等慰劳品,送给前方战士[16]302-303。这些宗教界的女信徒,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在湘桂的外国人,虽分属不同的团体组织,有着不同的信仰,但共同的反法西斯和抗日要求,促使她们联合了起来。
这些家庭妇女不顾一切困难,冲破旧礼教的重围,将家庭琐事暂放一边,将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放在首位,将“保家”与“卫国”合二为一。她们参与抗战的形式,或是直面敌军、勇敢地携子参军抗日,或是在女学生军的鼓励带动下成立自卫游击队保卫家乡,或是坚定不移做士兵们坚强的后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私地支援着前线与后方的抗战工作。她们这种勇气与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她们的贡献是伟大的,可以说,“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成功”[56]。
四、底层女性的协助抗日
“商女不知亡国恨”一语在亡国灭种之际,逐渐过时。歌女、妓女等底层女性在女学生的积极感召下,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下,亦意识到自身应竭力为国效力。歌女、妓女加入抗日救亡队伍,是抗战时期战场上出现的新现象,有效地激励了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借着女学生军的训练与帮助,她们成立救亡团体,慰劳将士、拯救伤兵,以更好地服务于抗战。例如,容县有“花界姊妹训练班”的妓女团体;玉林有“旅业姊妹训练班”;而梧州的歌女则先是称作“歌女救亡工作队”,后由于社会上对歌女、妓女带有一定的歧视,不得不将名称有所改动,把“歌女”“妓女”等字眼隐匿起来,改称“梧州鸳江乡东一村妇女战时救亡工作队”,以更便于展开抗日救亡宣传。“由队长花寄尘,率领全体歌女救亡工作队三十七人,及音乐技师数人,前往某地慰问受伤将士,并唱各种救亡歌曲,为受伤将士娱乐。”[57]所谓“各尽所能”,歌女们的歌唱,能使受了伤的战士获得心理的一丝慰藉[58]。此外,还有平乐县歌女亦有所行动,她们组织战时服务团,奔赴前线协助抗敌。“该县百余名歌女自动组织战时服务团,愿意担任战时后方服务工作,且呈请省党部核准,省党部昨日特令该服务团改组为战时工作队隶属于八步妇女抗敌后援会管理,该歌妓有此爱国热忱,实堪赞扬。”[59]还有北流县的妓女,1939年8月8日在女学生军的协助下,将高贤街处的妓女组织成妓女训练班,为抗日救亡效力[60]。湖南汉寿地区的妓女在经过训练后,有一百余人加入到当地各机关团体中[61],又为抗日尽己之力。这些歌女、妓女团结起来,抛却原先灯红酒绿、风花雪月的娱乐性生活,充分展现了其进步的一面。她们愿接受代表先进的女学生们的训练,组建抗日救亡团体,就表现了她们拥有强烈爱国心的一面。
其次,她们积极参与到抗战的捐献运动中。例如,1944年2月,影星胡蝶、紫罗兰先是在桂林,后又抵长沙,举行音乐会,筹募基金[2]248,以援助前线抗战。在梧州,“歌女救亡工作队”在队长冷静(艺名)的带领下,积极参加募捐,许多歌女、妓女到献金台献出金、银和现钞[32]378;副队长盼文君甚至“愿意把她每日所从歌喉上得来的钱,除了她本己一人的生活外,余下的通通积起来捐给国家,作为救国基金”[33]。在桂东南地区,“‘六、十六’玉林各界根绝仇货的大请愿,玉林全体歌女参加,而且捐出自己的‘卖笑钱’,给赴桂请愿的代表作路费!‘七七’举行的献金运动,她们每日都轮派到献金台去负责歌唱,白天在街头担负义卖,她们虽然碰到嘲笑,凌辱,但是并不沮丧,相反,她们更坚决地站起来了!献金队、寒衣募捐队……她们募捐的成绩由几百元达到几千元,总共有八千元以上,她们自己的私蓄、金饰贵重物品都捧了出来……香港珠江日报的记者在玉林的时候,也因为她们的赤诚工作而捐出四十多块钱来”[62]。她们的无私奉献,也感动了在场的其他人。
再次,她们在窃取情报上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在缉私中,一些歌女和妓女自觉将所获得的有关情报报告给军队。在参加了女学生军组织的学习班之后,梧州“歌女救亡工作队”的歌女们学习了有关抗战形势、抗战知识,增进了她们对抗战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觉悟。一次学习结束后,其中的歌女冷静向学生军报告称“有一批鸦片烟走私”,学生军立马“取了枪支,约了几个民团,一起在船上把那批鸦片缉获了”[16]301。这虽不如国家间谍般能够窃取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但在维护社会稳定、安定和平上亦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些妓女、歌女们,通过女学生军的训练,知晓了她们对国家应有的责任。她们原本是一个被社会所损害、被人们所贱视的群体,是压在社会底层的“弱者”。但当知晓了亡国灭种之机身为国民一分子应有的责任后,她们毅然将所遭受的各种苦难经历、满腹的委屈和满腔无奈的心情,化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并学会了用救亡歌曲代替原本的靡靡之音,歌唱“流亡三部曲”,也对嫖客宣传抗日救国。而当战争胜利后,因经历了抗战的洗礼,其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她们当中有的人毅然逃离妓院,另谋出路,这种弃恶从善的行为又对社会健康起到一定的作用。
五、结语
没有国就没有家,反之亦然。长期以来,饱受封建压迫、无权参与国家大事的旧社会妇女,一旦被发动起来,她们火热的激情和积极的行动,往往不输男性。在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上到精英女性,下到歌女、妓女等底层女性,团结一致对外抵抗侵略,用各自独特的方式保家卫国,谱写众志成城的新篇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女性扮演着组织者、号召者与领导者的角色,培养并带领一批批妇女组成军队抵挡侵略的同时,更是积极影响女学生、传达她们的抗战思想;投笔从戎的女学生军则是她们的追随者,在战斗中,这些女学生军的奔赴前线战斗、协助其他妇女参与抗战、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起社会募捐等行为,无不是在执行上层女性的抗战理念,成为连接上层女性与普通女性、歌女、妓女的关键环节,是真正团结各界女性共同参与抗战的实际执行者,是推动全民抗战不可忽视的一份力量;普通家庭妇女则采用各自的方式为抗日作出贡献,她们当中,或是出于单纯的自卫意识而扛起武器,或是经女学生军的宣传、帮助而组建抗日团体,亦有送儿上战场的女杰,居家做坚定后盾的慈母,还有化身为白衣天使救助伤者的普通家庭女信徒;而歌女、妓女等底层女性则是在女学生军的训练下有所觉悟,积极成立团体协助抗战,并慷慨捐献。这些女性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她们的行为实际上体现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女性,归根结底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她们一方面要忍受丈夫、儿子随时可能战死沙场的忐忑不安,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保卫家园的重任,甚至是防范日军的侵犯与蹂躏。因而女性天然更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当国难当头、直面敌军之时,原本柔弱的女性亦毫不退缩,勇敢、刚强不输男性,她们联合起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捍卫着家国的每一寸土地,为早日赶走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