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居住的金沙江(组诗)
2020-05-01普驰达岭北京彝族
普驰达岭(北京·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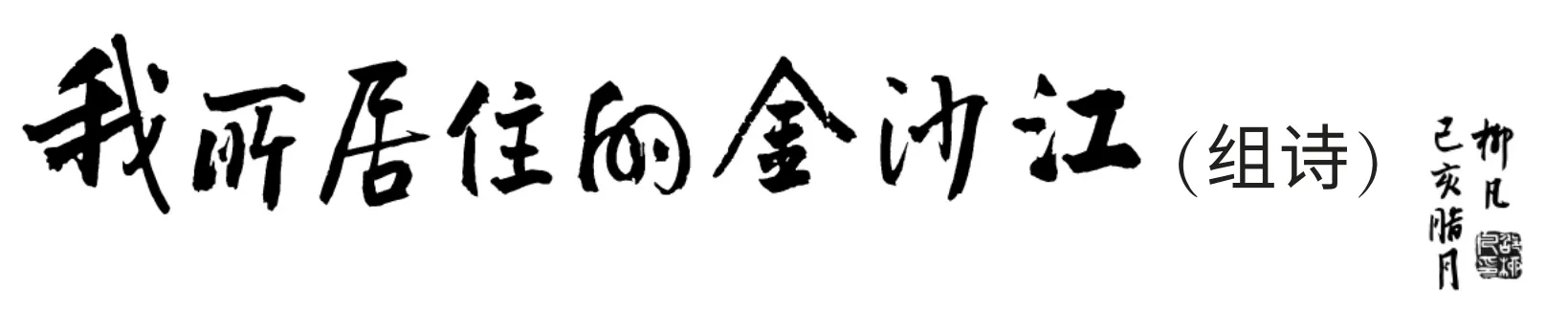
(一)
在金沙江两岸 火把一样的七月深居在盛夏
沿着一座山并走向另一座山
抬头碰触的大山并没高过彝人的额头
无数支火把经过的路口 一把把黄伞
依旧可以如数回到大凉山的腹地
你看到或没有看到的 索玛的眼睛
都将成为今生你无法躲闪的熊熊火焰
(二)
在神川金沙江 沾满夜露的星光
从山谷倾泻下来 在那红晕迷离的夜晚
我只能向深秋投去沉默的目光
蹲守在瓦板房下 任凭火焰的词语
把彝历年吐得老长
(三)
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金沙江畔
在千年的火塘万年的火光面前
阿嫚惯常的坐姿始终低低地走
从右而左的幅度高过远山低过屋檐
手中旋转的酒碗 在毫无修饰的母语面前
锅庄石上涂满的诗行已在火塘边隐约中活显
(四)
与金沙江隔岸而坐 从一抹招魂的叶片出发
季节的想象 已高出花的色彩
比春天还要沉默的秋水 如花在空气中绽放
我要把秋天一样的脸庞 埋入水中
让石头一样的语言回到水面
让水滴一样的炊烟远远地升入天际归空
(五)
在金沙江的上游 阿而酋长的一本彝文经书
坐在罗婺旧寨 在更低的高处
仰望易笼坝子更高的低处
顺势而下的水漫过千山之下的万壑
醒着的只有易笼坝子那片沉睡的土地
以及同罗婺旧寨的遗骸和远走他乡的移民
(六)
记忆中 易笼坝子的稻香
都顺着爷爷的影子疯长
彝人威武的过山号如风过林啸
时立低处万物景迁 去时的路
是一定弯曲到洛尼山顶的 如今
来时的路已汪洋成蓝蓝的水
明朗朗的湖光 紧贴着罗婺寂寞的骨头
往日狂野的掌鸠河 早已化为喘不过气的水
(七)
已经久风霜的金沙江上 那些我停留过的地名
透明的忧伤与荞花一起躺在坡头
凤氏土司的风云像寂寥在半空的星辰
半没在掌鸠河的岸上 嵌入彝文的镌子岩
在半淹的石壁上站着 那张被风雨残损的脸
就像穿过厚厚的春雨还生生枯卧的老树
无论天黑还是地北 复苏的叶片
只待罗婺的毕神最后一次向石头招魂
(八)
就在我们祖先居住的金沙江南岸
牂牁苍茫在南天的细雨还在辽远的耳畔
被雨点放大的夜郎淋湿过多少入主中原的帝王
坐井观天的半张脸 在可乐供奉的祖灵面前
南高原延绵不绝的部族谱系 像一帘幽梦
不知会有几千重抵达过帝王自大如天的头颅
(九)
越过群山 顺着金沙江的流向
雪芒擦拭过的大地 就在你我的身后
远山的光阴厚重炫目 尘土飞扬的旅途
浮现在岁末的正午 最硬的刀锋横在路上
带霜的光芒刺穿万重千山 坐拥岁月的尽头
又一把被人生的光阴打磨得锃亮的剑峰
高耸在时光来去 记忆回响叮当的档口
(十)
翻转的流云穿过金沙江两岸 在南高原
一些隐秘的词汇开始步入山谷
落在山顶的雪花如神 渐次推开厚厚的颂辞
在风寒之夜 有些山神筑云而居
一些语言飘过来 念念有词的祭祀
已经在指路经上铺开 彝人迁徙的背影清晰灵显
(十一)
酒中舍曲 鹰翅如风
拍打着金沙江南岸 午夜的愁肠
站成并流的澜沧江 荡气的怒江
剑刃孤独世声清静 酒酣梦已沉
酒杯捏碎的时光似缤纷落英
孤影剑行的长歌如飞舟浪迹
马背上的行囊 何日在长河骑行高远
(十二)
细柳拂风 娴淡只需一朵花开的时间
阳光过往 雅韵只待一盏茶香的光影
矗立在回归祖界的路口 请允许
我亮出一路虔诚与膜拜 三场红雪的辗转中
被雪芒嚼白的南高原 在奔流的金沙江面前
早已泪湿忠贞雾锁廊桥 从无声的静夜
我听到了风的祝福 在无月的迁徙中
我读懂了一个族群千年指路的祭辞
(十三)
怀揣洛尼山顶的积雪 在金沙江临风而望
用水的脐带 穿连绵延不绝的乌蒙山脉
绕山的游云 一次次在神启的经诵中走远
在雪线之下 阳光山脉悬在记忆的高空
时间被雪握暖 毕神的经诵走在岸上
开在水中的花 总被占卜遗忘
点不燃的归途 依旧藏在指路经念念有词灵舞的额头
(十四)
临风喝下夜的黑 让荡漾在心头的暖
回到攥满故乡的手心 歌谣漫过的夜空
黑色的云朵始终流浪在夜的尽头
一滴北方的春雨 迟迟落不到手心
不变的是我故乡的金沙江 春的容颜依旧在手上波澜
踏青的脚印落在水里 火塘的亮光依旧挂在墙上
(十五)
在石板铺就的屋檐下独坐 遗留在金沙江的往事
那些细碎如沙的过往 如刀锋横过指间
风中纵横 月下磨刀 光影划过水声
月光网住的屋檐 漂白了原野
躺倒在石板上的阳光 陈香了岁月
东山采蒿西坡牧羊 屋檐下的春秋
风当吹时吹 雨当下时下 雪当落时落
(十六)
顺着金沙江流而下 一些眼神停靠在雾中
冬日的雪光照亮了大地 一缕风穿过一片山穿过一片云
城市中的村落和尘埃中的田野 被一一穿过
雪落无声中 只有那些单薄的声音
从天空离散 然后在水声里重逢
一场雪的辗转 同样可以
让从天而下的雪芒 将祖灵居住过的山脉嚼白
(十七)
站在金沙江的垭口 闻得到苦荞的香
却难以擦拭搁浅在汗水中的苦
听得清煮熟的《查姆》 而走不进那张多年失散的脸
江流划过记忆的歌 可以像风走遍天涯
沉吟中的南高原 远离的字眼还熟睡在原地
难以割舍的那一句乡愁 被移植到了心口
而远走他乡的脚印 至今居住在我的头颅
(十八)
在我所居住的金沙江 留白的意境
就像空谷中的幽兰 花开千年的骨骼
枝干流沙的生命 古铜色的面孔自然而然
根植着彝人内在的诗脉 被红黄黑色彩燎原的心情
在我既定的远方 亦然无处不在地驻扎在彝人的骨头之上
(十九)
手牧苍茫间 素纸青灯夜阑珊
梦枕金沙江 我从雨声中醒来
泪水打湿的梦境是波澜的故乡
山高水长处 天空已横陈在我的仰望里
(二十)
伸出去的手握不住自己
放出去的目光难于抵达故乡
只是时间悬在高处 南高原依然在眼前
只是母语挂在舌尖 金沙江依旧在心里
(二十一)
在无尽的想象面前 深居在金沙江的深处
彝人的血脉早已深植为南高原的石头
白天如高原广袤 静夜似江山坐镇
无论人在何方 要把金沙江流的源头藏在心尖
无论身处何地 要把乌蒙山的祖源置在圣山祭奠
(二十二)
停靠在被时间打磨的锻刀之上
先祖最先落脚的坡头依旧比我幸福
疆域辽阔 万物茂繁 牧草丰美
而老去的酒杯紧贴着胸口我相信
这一张张的脸 总有那么一天
会沾满火焰 那一柱青烟就是划过云天的归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