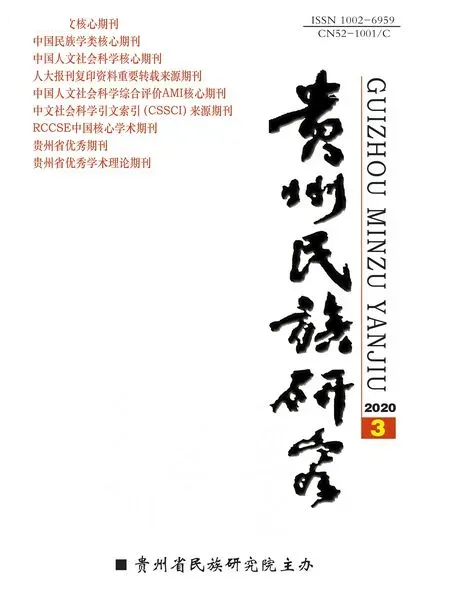西安坊上回族居住空间与言语社区的分化
2020-04-28董洪杰周敏莉
董洪杰 周敏莉
(1.西安文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2.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广州 510800)
一、研究缘起
西安坊上世代居住着老西安回族,是陕西省境内面积最大、保持最完整的历史街区。长久以来,在教坊制度影响下,坊上回族“围寺而居”“依坊而商”,在居住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上自成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宗教社区,也构建起以坊上话为主导的语言共同体。近年来,西安城市改造不断加快,坊上的社会经济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传统围寺而居的模式发生了分化。美国人类学家Gillette Mari(2000年)的坊上调查表明,当时的多数回族居住在平房区,为解决人口增长、社区总体面积不变的问题,已有回族开始将平房原地改造为楼房,“平房”和“楼房”居民生活方式存在差异,楼房居民有离心倾向。不过,Gillette 并未从语言变异的角度展开论述。韩卓(2014年)的后续调查表明,十几年前开始的平房改造已成规模。如今,76%的坊上回族选择在原地加盖楼层,形成2-5层不等的自建房群,其他回族则选择住进由单位提供或商业性质的单元楼。自建房地处坊上核心区域,是传统平房居住空间的延伸;单元楼则多处在坊上街区周边地带,属坊上社区新的居住空间。我们在预调查中发现,自建房和单元楼回族的语言面貌和语言态度均存在明显差异。正式调查时,将被试居住类型设为一个变量,以验证居住空间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回族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本文先介绍两种居住空间的特征,然后分析调查结果,说明不同居住空间对回族语言行为和语言认知的影响,进而论证回族通过移用已有语言变体差异形成新差异的途径以及构建身份认同的机制。
二、坊上回族的居住空间及其分化
(一)空间维度
居住空间的物理边界和内部格局,是社区居住格局最显著的特征。从空间维度看,坊上自建房和单元楼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地理位置不同。自建房是坊上历史传承的居住模式,围绕清真寺而建,处于坊上腹地。单元楼是后建的、现代化的居住形式,多建于坊上边缘地带。坊上居住空间整体布局由以清真寺为圆心的自建房核心区及其外围单元楼边缘带构成。第二,规模和地位不同。传统教坊制度使坊上成为集宗教、生产和居住功能为一体的独特民族社区,自建房是“寺”“坊”“居”格局中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坊上回族的主要居住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坊上平房无法满足居住需求,为维持“围寺而居”的传统格局,多数回族选择平房之上加盖楼层,少数选择搬离原有社区,住进单元楼。自建房是主流居住形式,其地位和规模均远超过单元楼。第三,住宅内部空间结构不同。自建房是大院平房基础上加盖而成,由大院大门进入,邻居间共享院落,院落与院落相连,形成热闹的街坊;单元楼属“细胞性”居住格局,独门独户,共享公共空间有限。总之,自建房和单元楼各有其空间坐落,区域界限清晰,规模及内部空间结构也各有差异。
(二)社会维度
回族日常交际在物理空间内进行,物理空间结构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说话者的行为,影响交际者的社会互动,并形成相应的社会交往模式。自建房社区的位置及内部结构形成了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熟人社会。具体而言,社区的封闭性强、成员的流动性低,居民的构成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属重叠性和交际性强度均较高的社会网络。单元楼是都市化的产物,原居住在自建房的回族在搬离街坊的同时,也离开了旧有的交际模式。单元楼居民构成相对复杂,租房、转租等导致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居民多在坊外工作,与坊外社会联系密切,网络关系超越了坊上社区的范围。独门独户的住宅模式,在提升个人空间的同时,弱化了邻里交往,居民间的依赖程度较低、关系较疏离,个体对坊上街区的依赖也趋于淡化,“去街坊化”倾向明显。总之,单元楼社区是从传统熟人社会分化出来的陌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空间差异和社会网络的区隔,使其成为坊上社区内部的“脱域共同体”。
(三)问卷调查和社会语言学访谈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为笔者2015-2016年西安坊上回族语言调查的一部分,涉及问卷调查和社会语言学访谈两项。问卷调查时间为2015年12月至2016年4 月,调查对象为坊上回族,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194份,有效率97%。问卷性别分布:男性99人,女性95人;年龄分布:18-29岁(青年组)57人,30-39岁(中青年组)44 人,40-49 岁 (中老年组)45 人;50-65 岁(老年组)48人;居住空间分布:单元楼住户51人,自建房住户143人;根据礼拜次数划分宗教信仰程度,其中程度较高的104人,其余90人信仰程度与年龄组的差异表现出一致性,下文的分析合并为一组。调查涉及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居住地点四个变量中,用于数据分析的是性别、年龄和居住空间三个。问卷针对坊上语言社区中10个交际场合,提供不同的变体供调查对象选择:(1)只说坊上话;(2)只说西安话;(3)只说普通话;(4)说坊上话或西安话;(5)说坊上话或普通话; (6)说普通话或坊上话;(7)坊上话、西安话、普通话都有可能说。10个回族日常交际场合是笔者2014年底至2015年初预调查数据基础上获得的,从1到10的排序可以体现坊上回族从最私密到最公开的交际场合连续统,是综合考虑说话人与交际对象的关系远近、关系类型、是否存在社会压力、交际内容层次(深度交谈和浅层交际)、交际场合是否对语言有特定要求等不同因素设计的,依次为:(1)想问题或自言自语; (2)父母; (3)配偶; (4)兄弟姐妹;(5)子女及其同伴;(6)同辈邻里;(7)长辈邻里;(8)打客服电话;(9)政府、医院、银行等办事窗口;(10)回答游客问路。
社会语言学访谈实施的时间跨度为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访谈对象为40人,男性20人,女性20 人;4个年龄组,分别为:青年组18-29岁;中青年组30-39 岁;中老年组40-49岁;老年组50-65 岁,每个组别男女各4人。
三、居住空间与语言变体选择
坊上社区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三种语言变体,其中坊上话最具本土特征,仅限于坊上回族使用,为低变体;西安话为强势方言变体,使用范围和权威性均高于坊上话,属中变体;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社会地位高,具有权威性,属高变体。这三种变体在坊上语言社区和谐共存,互有分工。下文依据问卷调查数据,结合量化统计公式,计算不同变体对自建房和单元楼回族语言行为的影响力,分析居住空间与语言变体使用的相关性。
(一)变体影响力强度计算公式
变体影响力强度计算方法:根据说话人的变体选择确定分值,通过公式计算,最后的加权值即不同变体的影响力强度值。公式如下:得分(score)= (A*6+A&B*3+A&C*3+A&B&C*2)/6/(194-n)*100,将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分别代入A,B,C,则得到各自的影响力强度值:坊上话强度得分=(只选坊上话*6+选坊上话和普通话*3+选坊上话和西安话*3+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2)/6(194-n)*100;西安话强度得分=(只选西安话*6+选西安话和普通话*3+选西安话和坊上话*3+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2)/6(194-n)*100;普通话强度得分=(只选普通话*6+选普通话和坊上话*3+选普通话和西安话*3+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2)/6(194-n)*100。由于问卷3、4、5题涉及婚配及子女交际场合,单身或无子女的频次为n,去除n后进行除权,确保强度值的可比较性。
(二)居住空间与变体影响力的关系
在调查问卷数据构成中,194份有效问卷,其中51 份来自单元楼住户,143份来自自建房住户。卡方检验单元房和自建房因素的P值小于0.05,具有统计学的差异显著性。下文表1内“均值”不区分居住环境。下同。

表1 居住空间与变体影响力对应表
从语言选择角度分析变体的影响力分布可知,不论自建房还是单元楼,均表现出显著的层化特点:坊上话具有明显优势,其次是普通话,西安话影响力最弱。自建房的坊上话影响力高于坊上话的整体影响力均值,单元楼的影响力则低于坊上话的整体影响力均值。普通话的影响力分布相反,其在单元楼的影响力高于普通话的整体影响力均值,在自建房的影响力只达均值的一半左右。可见,坊上话虽具有整体优势,但以居住空间区分坊上回族,坊上话的影响力在单元楼社区受到明显挑战,被普通话挤占了大量份额。
(三)坊上话影响力与居住空间、交际场域的关系
将语言使用细化为不同交际场域后,发现不同语言变体内外有别:交际外向性越强,普通话的影响力越强;内向性越强,坊上话的影响力越强。
立足坊上话,其影响力的数值在前七个交际场合中的差异较稳定(见表2),均在10以内,而在后三个交际场合,坊上话的影响力骤然下滑,尤其是坊上话在单元楼的影响力下滑幅度远超出不区分社会因素的总值和自建房数值,其中单元房被试“给客服打电话”的影响力只有总值的一半左右,而“政府等公共场合”和“回答游客问路”两项指标的影响力则降到个位数,仅为其自建房影响力的1/6。这说明,单元楼回族在与坊外人交流时,坊上话对其语言行为的影响力非常低,换言之,普通话的影响力在这些交际场合远远超过了坊上话。这是坊上语言社区中非常重要的语言事实。

表2 坊上话影响力与居住空间、交际场域对应表
坊上话影响力虽整体占优,但深入到交际场合可知,在特定交际场合,坊上话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变体使用因空间而分化,语言变体影响力分布对比变化呈现出一个顺序链条:自建房内向型交际→自建房外向型交际→单元楼内向型交际→单元楼外向型交际,其中交际场合中的交际对象即社会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居住空间与变体认知
在量化分析回族变体选择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语言学访谈,以质化材料为依据分析不同社区回族对不同语言变体及其使用的行为认知。
(一)不同社区回族对不同语言变体及其使用的行为认知
额我在坊上住,额我揍就说滴的是这种,咱方言(指坊上话),也比较认可这种语言(坊上话),要是在外头楼上(指单元房)住,额我感觉,说话揍就偏咧。人杂么,你来我往滴的,谁都不见得认哈能认识谁。……额我觉着也可以理解,为啥呢,他跟人家说这种话(坊上话), (其他人)不一定听滴得懂。 (LTM,38 岁,男,2016/12/09)
LTM 是自建房回族,在自家附近街道上做小买卖。他说坊上话,也“认可”坊上话。同时也认为在“外头”单元楼里住的“人杂”,住户之间不熟悉,“谁都不见得认哈”,因此,那里的回族说话“偏”了。
(单元楼里)说普通话滴的人多,这是一方面,唉我窝那个工作环境,不能说是要求说普通话,但应该说普通话,对顾客呀各方面,也揍就说(普通话)咧。应该说, (现在说话的时候)坊上话滴的那个口气揍就软滴得多咧,那揍就是另外一个口气咧。揍就是窝那样子。(MDB,28岁,男,2015/12/10)
MDB 住单元楼,在保险公司工作,他解释自己使用普通话变体多的原因是工作需要,另外是单元楼里说普通话的人多。久而久之,他说话的口气(风格)也就变了,形成了现在的语言面貌。
坊上有这么个(特点)……不要说八竿子,一两竿子,都能打着个亲戚,揍就这么些人么(坊上人口总数少)。么没有这种促进,么没有这种融合,就被同化咧,现在么没被同化滴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小集中(小聚居的居住形式)。你比方说,在窝那单元楼住哈滴已经住进(单元楼里),揍就是窝儿那样,说话撒滴啥的,都掺呢。掺滴得厉害!(ZS,38岁,男,2015/10/12)
ZS 也意识到单元楼回族说话跟自己不一样,“掺滴厉害”。坊上自建房回族在圈子内相互熟悉,关系密切,能够“促进”和“融合”,因此,没有像单元楼的回族一样被“同化”。他认为,语言风格的变化是“同化”的一种表现。
像唉我的对门,四丫他妈,刚从里头(自建房)搬上来带娃,窝那她说滴的,揍就窝儿那样儿,普通话太不标准咧!揍就是把娃们都带滴得,娃们说起来,额我都想笑,娃可终于到托儿所去,在窝那里可还能纠正一哈下,稍微能好一点儿。(MGL,65 岁,女,2015/12/09)
MGL 跟儿子在单元楼居住5年,她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语言面貌,但举了其他人的例子。“四丫”的妈妈“刚”从自建房(“里头”)搬过去带孩子,普通话说得非常不标准,导致小朋友说话听起来滑稽好笑。四丫妈妈尚未适应自建房的语言习惯,带孩子影响到孩子的发音。这说明两点:第一,在自建房带孩子说普通话很普遍,普通话太差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二,两个社区的语言使用已存在明显差异,居民的语言面貌不一样。
你听额我跟你说,(单元楼和自建房的回族住户说话的时候)揍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撒啥呢,街上(指在街坊里的自建房)人多,吵滴得很,所以说在窝儿那里(生活),说话得喊叫呢!(听起来)比较粗。在这儿(单元楼)住滴的话,你跟谁喊叫?都么没撒啥人,你跟人家(街坊邻里)不熟,在一块儿,说话尽量靠人家(接近汉族)。对不对?(XYX,27岁,女,2016/01/12)
XYX 住单元楼,在坊上开店。她首先确认单元楼与自建房语言使用的差异,进而分析其原因是自建房回族说话声音大,“比较粗”,主要是街上人多,嘈杂。单元楼里相对安静,邻里之间交往不多,在互不熟识的交际场合,说话尽量接近汉族的风格(说话尽量靠人家)。
以前我和我媳妇(在单元楼住),后来我妈又过来帮着带娃。门一关,各住各的,不像是以前在老房子(自建房),这了那了的(闲言碎语多),躲不开。你像我娃,进进出出都是普通话,反正平常就是学校和家,楼下吃的也方便,跟里边(坊上自建房区域)不牵扯(没有过多来往)。(BZF,32 岁,男,2015/10/10)
BZF 在事业单位工作,住单元楼。他认为,单元楼的居住模式相对独立,邻里之间互不相扰,同时对比了自建房(“老房子”)密集的交际网络(躲不开),强调单元楼生活有别于自建房,个人空间多,语言使用方面感受不到传统社区的压力,说话风格也比较自由。他以女儿为例,指出其社交范围主要是家里及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与自建房社区交往不多,因此“进进出出都是普通话”也没有问题。
平时(跟自建房的回族)交流得少,我跟媳妇都上班,娃他姥姥带,也在这边(单元楼上),不像里边做买卖的,或者那些闲人,成天都在一块儿。我有时到里头去了说(坊上话),在家里和单位几乎不说。(LZS,29岁,男,2016/05/08)
LZS 在培训学校工作,平常很少使用坊上话,只有“到里头去了”才说。他强调自己平时跟坊上自建房的回族交流不多,和妻子都是“上班的人”,“不像里边做买卖的,或者那些闲人”。这说明,语言面貌不同,对语言变体的价值评判也有差异。
(二)居住空间与变体认知的规律
(1)整体语言面貌的分化。无论自建房还是单元楼回族,都能意识到彼此语言变体选择和语言面貌的差异。自建房回族认为单元楼住户混杂了西安话和坊上话的变体形式——“掺”“掺滴厉害”,而单元楼回族则指出自建房回族说话风格“比较粗”,自己说话则是“另外一个口气”。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家里和单位很少说坊上话,孩子“进进出出都是普通话”,上述语言变体的选择均与自建房居民不同。与此同时,说普通话已成为单元楼社区居民语言变体选择的主流,坊上话则为自建房社区的主要语言形式。这种整体语言面貌差异会使单元楼回族在自建房社区说话时感受到社会压力,而在自己的社区时比较自由。两个社区语言风格的分化,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个体回族语言变体的选择。
(2)交际网络的分化。访谈对象提及的传统自建房社区中“一两竿子都能打着个亲戚”,邻里之间关系密切,“成天都在一块儿”,而单元楼则“各住各的”,住户之间相对独立,公共空间少,交流不多(“你跟谁喊叫?都么撒人”),加之两个社区彼此区隔,“平时交流得少”“平常就是学校和家”“跟里边(自建房社区)不牵扯”,导致两个社区内部关系网络出现密集型和松散型的分化。这进一步证明了Milroy(1980年,1985年)等的研究结论,即不同性质的交际网络与居民的语言行为密切相关。
(3)语言态度的分化。不管自建房还是单元楼回族,对各自的语言特征都表现出明确的价值评判。自建房回族认为,单元楼回族说话时掺杂普通话和西安话,语言不正宗,“揍就偏咧”“被同化咧”“掺滴得厉害”;单元楼回族评价自建房回族中有一些“闲人”,“成天都在一块儿”“这了那了的(闲言碎语多)躲不开”,他们的说话风格“比较粗”,单元楼回族的话则“软滴得多”。受访者还意识到自建房回族的本土语言风格对坊上小孩的语言风格造成了负面影响,需要到托儿所后才能得到“纠正”。上述种种说明,不同社区的回族对相关语言变体和表达风格的语言态度出现了分化。针对特定变体和表达风格,自建房回族认为坊上话很正宗;单元楼回族则觉得粗糙不妥,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类似的表现。总之,他们从各自的身份认同出发,对不同语言变体和表达风格做出了褒贬评价。
(4)社区意识的分化。两个社区回族已从内心深处区分出明确的空间和心理界限。不管自建房还是单元房回族,都会有意无意表露出各自的社区意识,即原本单一的坊上社区已发生分化。这一分化首先表现在指称词的使用方面。自建房回族指称单元楼时,使用“外头”;单元楼回族指称自建房时用“里头”“街上”或“老房子”。这些方位概念不仅表明自建房与单元楼空间位置的差异和新旧之分,也能说明居民以各自社区为出发点看待对方而产生的心理距离。
五、身份认同的二次分化
“对内”和“对外”是看待回族社区语言变体和语言互动社会意义的两个重要视角。三种语言变体的差异,特别是本土变体坊上话和超区域变体西安话与普通话的差异,原本是坊上内外即回族与汉族的社会身份、不同变体与其代表的社会意义之间的差异,在回族社区的形成和回汉互动历史进程中早已形成且深入人心。随着坊上社会的发展,其内部产生了新的子社区,即单元楼社区。自建房社区传统而封闭,居民宗教归属感强,本土意识鲜明。单元楼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标志,邻里关系疏离,独立性强,在工作类型、教育程度、消费模式、宗教意识等方面都表现出脱离本土的倾向。这些差异在社区内回族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观念上均有体现。基于语言变体影响力的数据分析表明,自建房回族的语言行为受坊上话的影响力更强;单元楼回族社区普通话的影响力较明显,其坊上话带普通话色彩。访谈案例显示,不同社区回族对不同风格的语言行为有明确的认知及不同的价值评判。由此可推断,同一语言变体承载的社会意义出现了对立,进而引发三种语言变体调整原有的对立关系。如图所示,普通话变体原本作为“坊外”汉族社区的标记,在坊上回族社区内部得到不同解读,成为单元楼回族身份构建的符号。在坊上回族身份构建中,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在特定语言使用模式中强化了使用者的社会身份。说话人利用多变体共存的现状,通过选择特定变体,并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形成独特的言语风格,从而与自身的社会定位相匹配。居住环境差异是人类社会隔离的指示器。诸如坊上回族搬入单元楼这样的社会性选择导致了社区的分化。而言语社区,表现为说话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则是社区分化的一部分,能反映和推动社区分化的进程。前文数据分析表明,语言变体社会意义的重新标注和解读是语言使用和态度分化的内在驱动力。在语言变异研究领域,从居住空间视角,深入探索语言变体社会意义的演变,将有助于揭示说话人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