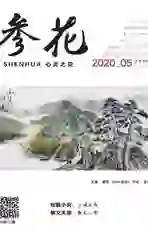古滇国铜鼓形贮贝器M12:2中祭祀歌舞场面的社会功能分析
2020-04-27童晖
摘要:古滇国铜鼓形贮贝器中的舞蹈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无论从舞蹈文化层面而言,还是从民族历史维度而论,其都凝聚了南方少数民族深刻而悠长的历史文化内涵。石寨山M12:2中的歌舞场面可以分为拊鼓歌舞组、献祭歌舞组、徒手人舞组,每组舞者各司其职,在相对和对称中呈现舞蹈场面的和谐之美。同时,M12:2上的歌舞场面中铜鼓和铜釜兼备,娱神与娱人兼具,呈现出祭祀与农事双重意义并存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铜鼓形贮贝器 祭祀歌舞场面 社会功能
在滇池区域曾有一个独特的古老王国——古滇国,因其鲜有文字记载而显得格外神秘。世人对古滇国的印象只停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1]等寥寥数百字的文献记载。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海贝和青铜器的出土,才将这个尘封了2000多年、繁荣昌盛的古老王国重新呈现到了世人面前。在出土的文物中均未发现文字,滇国将工艺精湛的青铜文化展现给世人的同时,刻画在青铜器上的日常活动、祭祀仪式等绚丽多姿的情景重现在世人面前。铜鼓形贮贝器就是青铜文化中集大成之器物。
铜鼓由炊具转化为乐器,日久年深丧失乐器功能无法进行演奏后,滇人在其基础上进行加工重铸,在器盖和腰身上刻录场面较大和有纪念意义的场景,形成铜鼓形贮贝器,最终促使铜鼓的功能转化。出土时贮贝器因其“储贝”的功用而得名,本身就代表了财富,又由象征权力和具有祭祀功能的铜鼓礼器改造而来。因此,其是古滇国国力辉煌的象征。贮贝器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因其写实而再现了战争、舞蹈、祭祀、狩猎等场面。尤其是祭祀歌舞场面颇为惊艳,舞者人数最多的歌舞场面就是石寨山M12:2。本文将根据此歌舞场面来分析其社会功能。
一、M12:2中的祭祀歌舞场面
晋宁石寨山铜鼓形贮贝器M12:2[2]器面上铸有祭祀歌舞场面,场面为双圈舞,又称“二十四人双圈环舞”。内圈铸有9位舞者,外圈铸有15位舞者,根据场面的分工不同,分为3组,内圈以铜鼓为中心的4人为“拊鼓歌舞”组,另外5人为“献祭歌舞”组,外圈15人为“徒手人舞”组。
(一)拊鼓歌舞组
以铜鼓为中心的4人,作歌舞状两侧对立呼应。从左向右依次描述:第1位舞者双手为四指指尖向上,虎口张开,拇指与手掌靠拢呈垂直状的翘掌手形,右臂弯曲打开于正旁,左手弯曲于胸前;步法是交叉半蹲状,右腿在前左腿在后。第2位舞者右臂弯曲打开于正旁,同为翘掌手形,左手敲击铜鼓,手中并无鼓槌,似是以手拊鼓;步法是右腿跪地,左腿跪坐于铜鼓右后方,身体向铜鼓方向微倾。第3位舞者右手为翘掌,左手为托掌,双臂弯曲打开于正旁,手高举与头持平。第4位舞者将乐器挎于身上,似是小铜鼓或铜锣,单手拊之,身体弯曲面向铜鼓。从动势层面来分析,第1位舞者步法,左脚离开地面且半蹲状态,极有可能为主祭师,在内圈两组中间左右兼顾执行仪式。在鼓声中第1位舞者边歌边舞,中间两位舞者在一人击鼓一人舞的基础上不断高低变换舞姿并歌舞,第4位舞者单手击鼓以和之。
(二)献祭歌舞组
内圈铸有5名女舞“娱神”,似乎是在向“神”们表演献祭的仪式。[3]5位舞者梳银锭式发髻,一人于鼓形釜左侧站立,从中倒出祭肴,一人手捧高足云纹大碗跪蹲于鼓形釜右前方承接,另外三人,依次向鼓形釜处行走,脚步一前一后,双手亦手捧高足云纹大碗于胸前。虽似生活动作剪影,却明显地摆脱自然俗态,具有整齐规范的舞蹈化特征。[4]
(三)徒手人舞组
外圈铸一组舞人,共15位女舞者,舞者随自己左侧人的方向顺时针行进,脚尖与头的方向保持一致,腳位基本以右腿为主力腿,左腿弯曲,步伐比较有规律性,环圈而舞。舞者手形与内圈舞者手形相同,均为翘掌手位。舞姿动作可分为4组:第1组是向左侧的拧身舞姿,双臂打开于正旁,掌心向外,胳膊肘、手腕弯曲,指尖上翘呈三弯;第2组是向左半侧身舞姿,左臂打开于正旁,右手弯曲于胸前,掌心向左,胳膊肘、手腕弯曲,指尖弯曲不变;第3组身体正对左侧,双臂均在身前,臂间距离似为与肩同宽,左手仅高于右手指尖,胳膊肘、手腕弯曲,指尖弯曲不变;第4组是向右侧的拧身舞姿,右臂打开于正旁,左手弯曲于胸前,掌心向右,胳膊肘、手腕弯曲,指尖弯曲不变。每位舞者的注视点置于前一人的背部,舞蹈中注重相互间的配合。[4]由于侧身围圈的形式,舞者的拧身动作在行进中始终保持不变则会不适,也会影响动作美观,所以她们之间的舞姿会随着鼓点而变动或互换。
杨德鋆在《铜鼓乐舞初探》中描述此舞蹈场面:“第13人前没有物体,许是舞队之首;第14人的侧身角度,顺展翅动作及身挎环状物等皆与众不同,像是队尾。”[5]现为能清晰地讲述,将“第13人”划为外圈第1位舞者,从左向右数,将“第14人”划为外圈第15位舞者。笔者认为,舞者前没有物体的确为队首,但14、15位舞者之间的动作有呼应,笔者认为这两人同为队尾。第2、第7两人动作为上述舞姿的第2组动作,两人身后均有4人做第1组动作。这代表此舞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1、2和12、13这四位舞者做第1、第2组动作,在队形中有对称意味;作为队尾的两人动作和身体朝向都与他人不同,相对而舞。队列舞者双手手腕上均佩戴4到5个手镯,在铜鼓的敲击声中,舞者们手上的手镯伴随着鼓点行进,发出的声响清脆且有节奏感,人与人之间分别放有花朵或高足酒杯各7件,舞蹈动作与花朵、酒杯配合,使场面更加具有立体感。外圈与内圈间舞姿、衣饰也都相似,在此祭祀场面中舞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以相对、对称为美,整个画面融洽、惬意,颇为惊艳。
二、M12:2中祭祀歌舞形式的社会功能
这个古老王国中专供王侯贵族使用的贮贝器,象征着权力、地位与财富,经过精心构思而刻画的大型场景铸刻在器盖上,向我们展示了滇人对神的敬畏之心。在没有文字产生的古滇国,滇人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和传递人的精神、意志与思想,不仅有自娱性的原始形式,也有祈求神灵、祖先保佑等娱神性社会功能。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M12:2中的场面是一场有组织的、大型的、神圣的祭祀歌舞场景,众多学者对这个歌舞场面的社会功能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大致总结出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由于古滇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形成古滇民族独特的风俗——跣足而舞,有普遍性的同时也具备滇族乐舞的风俗性。因此,具有民风浓厚的礼俗功能。第二种是内圈“献祭歌舞组”似为熬煮佳肴,有观点认为这是贵族的宴享乐舞图,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滇人的祭祀舞蹈,由于统治阶层享乐的需求不断增加,一种新的乐舞形式出现,宗教祭祀乐舞与宴享同时存在的双重功能。第三种是外圈舞者人与人之间分别放有花朵或高足酒杯各7件,此种陈设非常具有特殊性,领舞者身穿草莽之物似农神,许是庆祝农业丰收,像以歌舞祭农神的功能。第四种是第15位舞者,许是身挎生产用具的绳索,歌舞之人身穿出行春播的衣服,此为春播前的祈祷仪式。各学者的观点皆有独到之处,从跣足、内圈、外圈陈设、衣饰分别对画面的功能进行了分析,笔者也结合此场面的腰部图案进行分析探究,认为该场面应具有宗教祭祀与农事活动并存的社会功能。
此铜鼓形贮贝器的腰部铸刻的是众人携带铜犁、筐、形器、巨盘、杖等劳动工具前往播种的图景,女奴隶主在队列中间坐肩舆中,舆旁有随侍女子。将此场面和器盖上的歌舞场面结合起来看,外圈的女舞者步伐缓缓、手部动作均匀的环圈而舞,似是在模仿农事活动;内圈4人拊鼓歌舞,似是向神明祈祷以求庇佑,其余5人向作为“农神”象征的铜釜进行献祭仪式,应是滇人举行有关“春播祈年”的盛大宗教典礼。铜釜是一种敞口、圆底的大型炊具,铜鼓由铜釜衍变而来,在祭祀中铜鼓是必不可少的与神灵沟通的器物,滇人每逢播种前都要举行一次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他们丰衣足食,器盖上的歌舞场面中铜鼓和铜釜兼备,因此,可以认为此场面是大型的农事宗教典礼,其具备祭祀与农事并存的双重社会功能。
三、结语
古滇国时期文化发达,其青铜文化更是吸收并融合了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在出土的众多贮贝器当中也有很多其他场面,包括“诅盟”“剽牛”“報祭”,还有上述的“祈年”等仪式,其中不乏歌舞场面,其在祭祀仪式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给人带来神秘感。而镌刻在贮贝器上的祭祀舞蹈也因它的“动势”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历史上并没有文字出现的古滇国,通过它发达的青铜文化向我们传达当时国力的鼎盛,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记载的缺失,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探究古滇国的历史资料。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3]张福.彝族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
[4]彭小希.古滇国青铜器舞蹈图像研究[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10.
[5]杨德鋆.铜鼓乐舞初探[J].文艺研究,198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艺术学院2019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9XJ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童晖,女,硕士研究生,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舞表演)(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