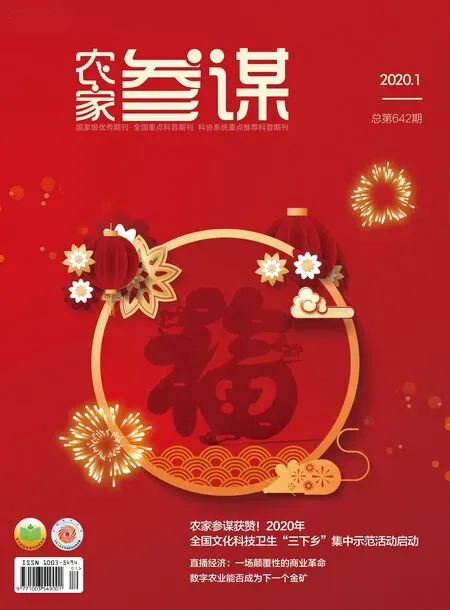记忆中的鲫鱼
2020-04-27张世斌
张世斌

我爱吃鲫鱼,亲朋好友们都知道,家人也经常到菜市场买几条烹调一番,红烧、清蒸、侉炖的都有。
几十年来,每次外出在饭店吃饭时,不管遇到多稀罕多有名的鱼,我都不为之所动,只点鲫鱼。我爱吃鲫鱼,不光因为它香嫩鲜美,更是想寻找那种味道,那种当年奶奶用原始的土办法烧制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味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跟奶奶在农村生活。那时家家都很穷,每餐都是粗茶淡饭。至于吃鱼吃肉,那是个长久奢望,等到过年时能吃上一两顿就很不错了。
老家的夏季雨水多,基本上年年都涝,水多得坑满壕平。但涝也有个时间段,立秋后不久,原来的坑和壕就只剩一半水了,沟壕里的水也只有齐腰深了。
每年这个时节,如果赶上个大晴天,就是村子里“翻坑”逮鱼的好时候。“翻坑”,就是好几十个人同时下到水坑里搅和,有的手持粪筐,有的拿竹篮,有的举着用柳条编的畚箕,五花八门拿什么的都有。大家在水坑里使劲儿搅,把清水搅成浑浑的泥汤。
水浑了,水下生活的鲶鱼、泥鳅(有时还能见到蛇一样的鳝鱼)等就会露出头来。这当儿便是人们收获的时刻。大家拿着工具,寻找张嘴的鱼头,一捉一个准儿,有时一下捉到的还不止一条。下水人捞到鱼,就兴奋地向岸上大声呼喊,岸上老人和小孩即刻应声。鱼扔到岸上,老人小孩笑着撵着摁住活蹦乱跳的鱼儿,然后把它们放到清水盆里——这自然是为了鱼的鲜活。
每次“翻坑”都在中午时分,能持续一两个小时,热闹得像过节。水里人喊着,岸上人观察着,指着,叫着,抓到大鱼的还使劲儿咋呼显摆。那个高兴劲儿,那种欢快的场面,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每次“翻坑”,我都不会空手而归。有一种身子宽宽的鱼,大家管它叫“槽鱼”,后来才知道是鲫鱼。每逢逮着鲫鱼回家,奶奶总是用清水冲洗一下,大点的鱼用剪子把肚子铰开掏出内脏,小鱼则不掏,然后再撒上些碎盐粒儿,用绿绿的北瓜叶子包起来。奶奶包鱼的手艺很高,鱼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埋到锅底下灶膛火的灰里。
北瓜叶子包鱼放在柴火灰里烧的过程,是个让人等得心焦的过程。说心里话,当时正在长身体的我比较馋,放进去不大一会儿就想把鱼扒出来。这个时候奶奶总是不急不忙,常常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对我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工出巧匠,等你长大了,做啥事都甭急躁!”听奶奶慢条斯理地讲着,我心里就不那么急了。不着急了,鱼自然就烧好了。
每当奶奶从灶膛里扒出烫手的绿叶包时,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别看它外面沾满了土灰,一旦打开,鲫鱼的香味儿即刻就出来了。一入口,那个好吃哟!肉嫩嫩的,鲜鲜的,那才叫“入口即化”呢!每当从奶奶手中接过来,馋得我连变软的鱼刺也舍不得扔,就和着肉一起咀嚼着,越嚼越香,越香越愿意嚼。偶尔有个大点的盐粒儿没化完,嚼在口中也是那么香。那时,便觉得它就是世上最好吃最好吃的美味了。
那时的奶奶还不到60岁,头发却已白了一大半,背也有些佝偻。每次奶奶看着我吃鱼的样子,心里的甜就会荡漾在脸上。儿孙高兴似乎就是她最开心的事。
此后,我上学、当兵,又到外地工作,吃过很多鱼,但不管是什么鱼,什么样的做法,鱼的味道都没有奶奶用北瓜叶子裹着烧出来的好吃。我信任厨师的技艺,只是他们做的缺少了当年的场面和奶奶亲切的气息,于是便寡淡乏味起来。
至今,奶奶已离开我们30余载。一提起鱼,我就会想起奶奶在灶火旁烧鲫鱼的场景和奶奶脸上的笑容,一想起来,那种酸酸的、甜甜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