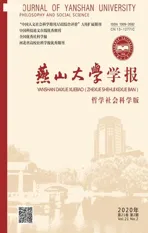凌静怡当代中国文学英译活动综论
2020-04-26张军锋冯正斌
张军锋,冯正斌,2
(1.西安科技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2.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710128)
一、 引言
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兼职教授,诗人、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 自1989 年翻译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以来,三十年笔耕不辍,译材多样,成果丰硕。 其译作涵盖李碧华、韩丽珠、王安忆、棉棉、翟永明等当代重要作家的中文作品。 凌静怡的译介活动在美国关注度持续趋热,屡获翻译奖项,广受业界好评,尤其在诗歌翻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对于凌静怡的翻译研究关注不足,长期停滞在引文前言等研究叙述的边缘,对其译作的本体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鉴于国内研究现状与凌静怡对中国文学外译的贡献严重不符,有必要在系统梳理其翻译活动的基础之上,缕析其翻译活动特征,探究其翻译惯习及其成因,以期引发学界关注并推进相关研究。
二、 凌静怡译作及其接受
凌静怡的翻译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小说和散文翻译,包括小说类翻译15 部,散文类翻译8 篇;第二类是诗歌翻译,包括翟永明和杨牧的2 个诗集,以及散见于文学杂志中的中国当代诗歌约100 余首;第三类是字幕翻译,包括《风月》等5 部电影。 因篇幅所限,仅将其主要译作整理如下(见表1):
就接受度而言,凌静怡的译作屡获翻译奖项,翻译质量颇受认可。 如2008 年,《莲花》的翻译获派恩翻译奖;2012 年,《更衣室》的英译本获北加州最佳翻译图书奖;2014 年,《风筝家族》的翻译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文学翻译奖;2017 和2018年因翻译王寅和曹疏影的诗作蝉联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中国诗歌与翻译奖。 在“好读网”等文学推评网站上,凌静怡的翻译作品如《霸王别姬》《糖》,亦广受好评。

表1 凌静怡主要译作一览
凌静怡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翻译及相关论述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对女性诗歌和台湾地区诗人诗歌的翻译。 美国出版的《20 世纪中国女性诗歌选集》中,凌静怡对冰心、林徽因、郑敏、夏宇诗歌特点的论述和其对翟永明诗歌的翻译被多次列举引用[1]。 同时,凌静怡的译作受到业界同行的肯定,如Jeffrey Wasserstrom 对《风筝家族》译本有过如下评价,“凌静怡的翻译文笔优雅,尤其是她的介绍部分,令人受益匪浅,解释了她如何将韩丽珠的文字译成英语并把香港迷人的、鲜为人知的文学景观融入世界的” ,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译文娴熟老到,使书中的香港叙述能引人进入韩丽珠的超现实和可识别的世界”[2]。
在国内,凌静怡的翻译活动也渐受关注。 刘江凯[3]98在中国当代诗歌翻译研究中援引凌静怡对翟永明诗歌的翻译和评论。 李德凤和鄢佳[4]33-34在对1935—2011 年中国新诗译介情况进行述评时,作为夏宇、杨牧、翟永明等人诗作的英译者,凌静怡已然在列。 吴赟[5]39-40在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译介探讨中论及凌静怡《糖》译本和正在翻译的《天香》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海岸[6]53在其论文中不仅提及凌静怡对《川岛芳子》《霸王别姬》《糖》《更衣室》等新诗的英译,还高度肯定了其译介行为。 陈培培[7]118-119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个译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凌静怡的译文“能够这样洞悉地揭开诗歌的表层肌理,准确地把握到诗歌的精髓颇为震撼”,……“更具人情味和动感美”。 张军锋和冯正斌[8]从翻译叙事角度研究王安忆短篇小说《弄堂里的白马》英译本的重构策略,认为译作“展现出译者的主动性和专业精神”。
凌静怡是一位勇于探索并不断汲取文化养分的翻译研究者。 截至2019 年初,凌静怡先后发表翻译研究学术论文5 篇,对诸如“顺应与冲突”“性别因素”“诗的语言特质”“翻译主观性”和“诗歌翻译伦理”等重要译学论题的探究深入透彻,不乏创见。 在自身学术研究的观照之下,凌静怡对其翻译的诗歌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钩沉梳理并多次重订发表,推陈出新。 除此之外,凌静怡还积极参加文学翻译类访谈以增进业界同仁的互动融通,开阔眼界,加强交流,提升翻译技能(翻译研究论文及访谈见表2)。

表2 论文及访谈
综上,凌静怡的翻译活动既包括她三十余年致力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她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诗歌翻译思想孜孜不倦地探索。 译作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屡获奖项,其翻译活动持续引起关注,颇受佳议。 然而,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与其译作的数量和质量不相匹配,对其译者行为和译作本体的研究尤显不足,对译者的翻译思想更是缺少应有的重视和探索。
三、 凌静怡的译者惯习分析
(一) 译者的社会轨迹
惯习是个体在自身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学校学习、社会工作和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内化及强化了的社会规律[9]。 具体到译者惯习,它主要包括译者的社会轨迹(社会阶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及其早期翻译活动中形成的认知结构[10]12。 结合译者的惯习形成过程并参照译材选择特征,大致可把凌静怡的译者社会轨迹分为三个时期:即初剑发硎、锲而不舍、渐入佳境。
1. 初剑发硎
凌静怡译者轨迹的第一个时期,包括从译者的前知识建构至《霸王别姬》的翻译出版。 17 岁时,凌静怡邂逅中国古诗英译,深受吸引,1981 年来华交流,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后在重庆从事教学,历时一年之久,中国文化惯习初步形成。 凌静怡先后获加州大学“汉语研究”学士学位,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熟谙中国当代文学。 长期任教于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文学翻译”和“创意写作”课程,曾兼任该校主办的《亚太聚焦》 编辑部主任,并长期为“Manoa”“Push Open the Window”“Chinese Literature Today”“Pathlight”“Chicago Review”“Frontier”等期刊撰稿,通晓中西诗学规范,英语写作技能娴熟,兼具学者惯习与译者资本。 就其译作质量而论,原文理解充分,译文严谨有度,语言建构力强,应是长期专业创作训练与学术积淀的结果。
凌静怡最早的译作当为夏宇诗23 首中的第1首:“甜蜜的复仇”,此亦为其诗歌翻译实践的起点。 夏宇的诗是台湾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和典型代表[11]93。 从其对夏宇诗歌的翻译,可以看到凌静怡翻译实践从一开始便与“诗”和“女性”这两个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凌静怡翻译的第一部小说是《川岛芳子》,而后是更加成熟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霸王别姬》。 这两本书的翻译,赞助者因素非常明显,译本中规中矩,拘谨生涩。 虽然如此,李碧华笔下建构出的小说空间对与性别有关的题材极为关注,文字渗透着对于现代性体验的反思[12]124。 藉此,凌静怡积累了对于女性文字和现代性作品的翻译经验和资本。 《霸王别姬》翻译完成后,凌静怡的学者惯习发生渐变,主张“书是独立存在的,她们为自己说话”,“译者应该把作者的声音内在化,措辞要遵循直觉,同时而在另一种程度上,这种实现也是技术性的。”[13]
2. 锲而不舍
译者轨迹划分的第二个时期:从《糖》的翻译完成,到《更衣室》的翻译出版。 这一时期,译者的自主性渐渐凸显,尤其是译材选择上,“兴趣”第一次出现在有关译材选择的翻译言说中。 凌静怡回顾说,在翻译之前,自己“被书中的当代中国文化深深吸引”。 抛开文本本身不谈,《糖》的翻译和传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读者对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猎奇,西方出版社对商业价值的追逐,使得这类小说在英、美、法、德语国家有效地赢得了图书市场”[14]27。 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认识与国内研究者所期待的传播内容尚存差距,这一痛见可为我们认识凌静怡的译材选择提供一定参考。
《糖》的翻译标志着凌静怡对译材自主选择的转向,也成为了其翻译翟永明诗歌的契机。 凌静怡意识到翟永明现代诗的价值和对自己的吸引力,在访谈中她第一次使用了“共鸣”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翻译翟永明的冲动[15]。 机缘凑巧,凌静怡与翟永明有了接触和对话,并在征得其同意后开始翻译《更衣室》。 凌静怡用了五年时间去雕琢这本诗集的翻译,2012 年的获奖也使她名声大噪,译者资本随之增加。 凌静怡第一次把自己对诗歌体裁的认识和翻译感悟写进译本序言中,“和这一群体中的其他人一样,她从美国自白派诗人那里得到灵感,有力地表达了女性的主观生理和社会经验”[16],并将翟永明归类为“意识流”诗人。 这表明凌静怡更加清晰地思考和探讨了性别、现代性和翻译的关系。 在此期间,凌静怡还为翟永明翻译了一篇关于现代诗歌的论文《黑夜意识》。 与作者直接对话并保持工作关系给凌静怡带来了深刻的体验,以至于其后的翻译活动无一例外都涉及与作者的联系及互动,以期与翻译对象达到某种程度的心灵契合。
3. 渐入佳境
第三个时期以《风筝家族》的翻译出版为起点。 随着凌静怡译者资本的积累,在译材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其主体性进一步强化,不再被动地接受指派或招募,而是依据个人喜好积极主动地选择作品和体裁。 这一时期凌静怡翻译的作品主要有:香港作家韩丽珠的《风筝家族》系列和最新出版的《飘马》,上海作家王安忆的两部中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台湾作家廖鸿基的短篇小说集,棉棉的中篇小说《失踪表演》,杨牧的诗选和其他现代派诗歌以及电影《盘丝洞》和《海上城市》的字幕。最值得注意的是韩丽珠作品的翻译,和李碧华不同,韩丽珠的作品走出了情爱书写香港故事的主旋律,用“身体书写”来延续千禧年后的香港“无爱”故事,背后关注的是香港都市生活中人性异化问题[17]7。 选择翻译韩丽珠作品同样意味着凌静怡翻译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确,译材选择更加慎重。
凌静怡目前正在翻译王安忆的《天香》和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 广受好评的《天香》对其翻译功力极具挑战性。 从文学价值上说,它“标志了新世纪以来当代长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18]68。 就文本而言,它的叙事错接时空,“绵密写实与深邃虚无的美学辩证或为极致,其独特文章叙事匹配‘绣画’而成锦绣,抒情‘文’直指人心又如抒情小赋”[19]63。 而《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亦是极具挑战。 该诗长约七百行,“将诗、文、笔记、随笔、自我阐释熔于一体”[20]127。 正如刘江凯所言,诸如作品“被禁”、电影改编以及海外获奖这些因素,固然会对海外译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创作本身[21]32。 凌静怡的最新翻译活动中,把译本选择转向更加经典、更具传播价值,更有翻译难度的作品,是一个良好的趋势并提供了让人期待的图景。将这两部作品列入翻译计划,可视为凌静怡翻译场域资本增加,翻译雄心大展的明证。
(二) 凌静怡译者惯习的表征及成因分析
梳理凌静怡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对描述其译者惯习和解读其译本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译者的惯习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和其对文本的选择[22]12。 限于篇幅,仅就译者惯习中的翻译观和译材选择进行探讨。
凌静怡的翻译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认同、形义并重和诗文区别。 在译材选择上,其译者惯习呈现出三个清晰的脉络:对现代诗歌的热衷;所译作家地域非常集中;所译作家和诗人主要为女性。
1. 凌静怡的翻译观
(1) 文化认同
译者在文学外译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其文化身份和翻译观密切相关:一方面,译者的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另一方面,译者的文化身份也会在翻译这一话语实践过程中不断得以构建并持续发展。 因此,考察译者惯习的翻译策略表征应以考察译者的文化认同为起点。 综观凌静怡的译者社会轨迹,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又是翻译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使其对当代中国文化显示出较为明确的认同感,并将之投射于译材选择和对译本价值的认识上。 在一次访谈中,凌静怡坦言,“发现自己的性情与中国的语文和文化相合”[15],不愿意“随意”地翻译,一直主张尊重源语言特点,平视甚至仰望源语文化。这一点,与很多西方译者有所区别。
(2) 形义并重
策略是思想观点的外化,凌静怡的翻译策略是其翻译观的具体体现。 除了平等之外,形义并重和诗文区别是凌静怡翻译观的两个特别凸显的要素。 凌静怡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对话,其根本就是平等性和信息性,因此译者就应试图忠实再现内容包括意义、意象、措辞、语气,甚至节奏、行长、换行符和节格式的全部存在。 凌静怡的翻译策略肇基于此观念,其诗歌翻译策略更是明确贯彻和发挥这一主张。 “在今日这时代,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不去把中文文本还以其原来面目?”[15]凌静怡直指部分译者不甚理解(抑或未曾尝试去理解)原文,就将一己之好加诸其翻译作品中,而无视原作的姿态与意图,此种轻率态度,可归因于文化霸权主义[15],其翻译策略就倾向于文本再现的周遍性和全面性。 这显然顺应了现代文化传播的主流价值:删节和改译等翻译方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译文的接受,但原汁原味的译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文学的魅力。[23]16。
(3) 诗文区别
在凌静怡看来,虽同属文学翻译,但小说和诗歌的翻译需要区别对待,它们有着不同的翻译策略:(1)结构腾挪策略:小说的结构比较松散,要以较大的自由度去腾挪重现其结构意义。 诗是凝炼浓缩,翻译过程中要重视结构重现。 (2)意象处理策略:小说中的意象表现自由,可以综合处理甚至改变。 诗的意象参与构建意义,翻译过程中应集中、有标记地转换,以免影响全局。 (3)形式转换策略:格律性和音乐性是诗最重要的特质,于小说却并不明显。 诗歌翻译策略的独有指向就是格律性和音乐性的重构。 (4)文化意象重现策略:小说中,文化指涉太过本土与厚重,难以重现于目的语文化场域,可通过篇幅增加或减少来解决。 而现代诗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篇幅调整和副文本附加,转圜余地不多[15],对于更加微观的措辞策略,凌静怡主张,在诗歌解读中应以整个段落为思考单位,在重构时则先诗行而后诗节,并尽量不去打破意象的次序、技巧和细节。 此外,凌静怡还考虑到诗的断句和句节,主张重视跨行现象,重视句子或词组中间的断句造成的意义悬空,以保留原文的节奏并重现某种悬念和呼吸的停顿[15]。
2. 凌静怡的译材选择
(1) 诗歌偏好
凌静怡与中国文化的结缘由诗开始,其就学经历与诗歌密切相关。 长期阅读、研究和翻译诗歌使凌静怡对自身中国现代诗的素养非常自信,在访谈中她多次表示“我本人就是诗人,我懂得诗里的每一个意象”[15]。 纵观她的诗歌翻译活动,不难看出此言非虚。 不仅在诗歌的翻译探索上用力甚笃,凌静怡所作论文和访谈也大多与诗歌翻译有关。 以此观之,凌静怡对中国现代诗的翻译选材偏好顺理成章。
(2) 都市书写
通过梳理译者成长轨迹可以得出,凌静怡的成长、受教育经历以及人际活动经验主要以大都市空间为主,与中国文化的人际及学术交集以香港、台湾和上海最为熟谙。 像许多海外译者一样,凌静怡对与西方文化深度碰撞并受之影响的地域文化有更多的心理倾向。 和他们不同的是,对于这个倾向,凌静怡有很明显的自我认识。 其译作绝大多数都是香港、台湾和上海作家的作品,第三时期的翻译更是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杨牧、韩丽珠、王安忆和棉棉等都市书写。
(3) 女性文学
凌静怡对于译材选择过程中的性别因素曾进行过多次否认,如“我主要考虑,这个作品我有没有共鸣,倘若有的话,我就会很乐意翻译这个作品”[24]76,又如“(关于翻译对象)不存在任何基于性别的理论障碍”[25]61。 不过,梳理凌静怡的翻译作品,不难发现其女性倾向并未如宣称的那么少。在译本选取中,除了与之渊源颇深的杨牧以外,几乎都是女性作家或诗人的作品。 仅举一例,凌静怡翻译最多的三位作家,包括以写情爱著称的作家李碧华,以及被公认为“身体书写”代表的棉棉和韩丽珠。 深受其重视的《更衣室》,更是弥漫着女性意识。 对女作家、女诗人的持续关注和译介,正是凌静怡所呈现出的女性惯习之一,这一惯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在翻译活动中的文本选择。
四、 结语
凌静怡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长期学习和执教的译者社会轨迹,及与中国作者亦师亦友的对话,有益于促进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和语言的交流。考察梳理其翻译实践和译者惯习可知,凌静怡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的翻译呈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综合分析凌静怡的译者惯习,不难发现,其不仅是一位致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的专业译者,还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的翻译研究者。 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以及对翻译中性别因素的持续关注,使得凌静怡的中国文学译介和言说,具有很强的挖掘必要和研究价值。
中国当代文化走出去的大趋势呼唤更多优秀的译者,“学”与“文”合一的译者模式是中国文学走进译入语世界的重要助力[26],凌静怡正是这样的译者。 就其翻译实践而言,凌静怡对源语具有敏锐的阅读和感知能力,对目的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秀表达力,翻译策略娴熟灵活,张力十足;同时,她对文本尤其是诗歌文本的构造特点、翻译活动的本体以及翻译与性别关系的探索卓有成效。这样一位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在国内尚未受到与其努力相称的学术关注,不能不说是研究憾事。 有鉴于此,谨以此文呼唤译界同仁的关注,以期助力文化远布,共撷海外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