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生与死
2020-04-19姜宇辉
姜宇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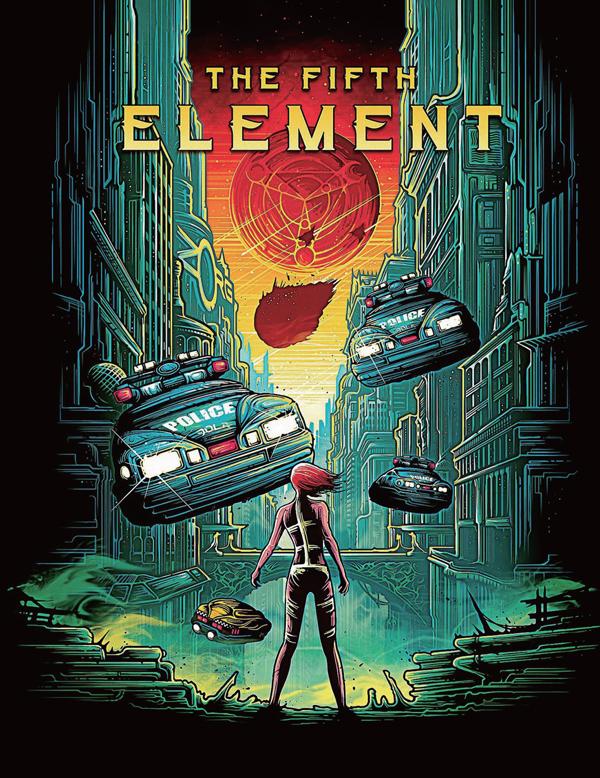
生与死,to be or not to be,对于任何人或物,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对于电影这样一种日渐位居主流的文化产业来说,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况味。电影之生,在电影史上似乎从未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但“电影之死”,却自电影的诞生之初就一遍遍地被反复谈起,或轻描淡写,或郑重其事。最晚近的一次当属著名导演格林纳威的宣判:当第一个人拿着遥控器走进客厅之时,电影就已经开始死亡。为什么呢?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遥控器,而是从那一刻起,跟电影相关的里里外外的要素和条件都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观影环境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脑海中一想到电影,必然瞬间浮现出那个漆黑的“梦剧场”。只有一束强光笔直投射向那片银幕,而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这样的观影空间并非单纯是一种实在的环境,而更是与人类的最深层的精神原型密切相关。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直到拉康的镜像阶段,从培根的剧场假相直到德波的景观社会,这个场景在历代的思想家的文本中被一遍遍复述。但家庭影院的诞生却从根本上将此种根深蒂固的幽灵魔咒一扫而光。我们不再是黑暗洞穴中的等待被影像催眠的半梦半醒的“迷影者”,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倒在舒服的客厅沙发里面的“休闲者”。电影不再打开另一个世界,它只是日常空间里面的一种娱乐,可以随手拿起放下,更可以任性地操控擺弄。你不喜欢的段落可以快进,你衷情的片段可以反复甚至静止。电影,不再“在别处”,而更是“在眼前”,甚至“在手边”。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格林纳威要感叹“电影已死”。那无非是因为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同”往昔,甚至早已“面目全非”。没错,走进黑暗的梦剧场暂时忘却“外面”的真实世界里面的忧伤烦恼,这仍然还是今天很主流的休闲方式;但别忘了,今天的电影绝不仅仅只在影院里面,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大屏幕上播放的电影只是庞大的电影生命体的冰山一角。今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观看电影,无论是案头床头,还是公交地铁,电影的生命在各种尺寸的闪烁屏幕上流动和蔓延。今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任何方式来观看电影,除了各种操控按键之外,如今还加入了弹幕和对话,看电影一下子就变成了近似打网游的互动体验。所以这都必然令我们发问:我们在看的真的还是电影吗?作为一种兼容并蓄的媒介,电影将种种传统的媒介形态——文学、音乐、戏剧等等——皆纳入其中,但在这种不断“拓展”的运动之中,电影的固有“本体”(Whatis)不也正变得越来越淡薄?如果电影可以是一切,那么它本身又是什么?
面对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质疑,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持辩护和乐观的立场。没错,电影确实今“非”昔比了,甚至面目全“非”了,但由此就说电影已走向穷途末路了,甚至哀叹电影已死,这并不是一种积极可取的态度。事实上,遍观人类历史,还没有哪一种艺术类型能够如今天的电影一般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吸收力和变化力。有容乃大,变化不已,这些不恰恰是生命力强健的体现,又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死亡气息?确实,当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赞颂“超人”般的强健生命力之时,就曾明确指出“人就是一种必须被超越的存在”。那么,在电影的不算长久但却足够绵延的生命历程之中,我们不是恰恰一次次看到这样的“自我超越”的契机和动力?也许当格林纳威说“电影已死”的时候,他只不过是用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啊,电影“又”变了,电影“又”死了一回。这没什么不好。会死,能死,这反而是生命意志的强大体现。晚近以来,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名词表明了这样一种朝向未来和可能性的积极态度,稍弱的形式叫“后电影(post-cinema)”,较强的形式叫“异电影(ex-cinema)”。和所有“后”字当头的复合词(后现代,后殖民,后人类……)一样,后电影也是一个相当纠结的表述方式。一方面,它有看对于传统的电影本体和迷影精神的迷恋但另一方面,它也并不认为新媒介和新技术给电影生命所带来的就完全是灭顶之灾。所以后电影理论里面经常会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痕迹(trace)”这个相当德里达的概念。痕迹,无非正是“过去”在“当下”留下的印记,但同时又向着不确定的“未来”敞开。所谓的“媒介考古学”,往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立场:今天的电影看似日新月异,但实际上它跟传统的媒介总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历史不是革故鼎新的线性进步,而往往是古今交织、新旧杂陈的多元力量的场域。
“异电影”就是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和立场了。它的重点并不在于与过去相贯穿的痕迹,而更在于向着未来释放的“潜能(potentialities)”。简单说,异电影的问题不再是“电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而更是“电影还可能变成什么样?”这也是“异”这个前缀和“后”的最大差异。“后”始终还是有一种乡愁的情结,但“异”则更带有生成的强力,它的另外一个形式更鲜明生动,那就是“expanded cinema”,“拓展电影”。电影只有在拓展出去的时候,它才真正具有生命。它只有在吸取差异的要素、朝向多元的环境之时,才能将自己的生命力带向肯定的极致。这样看来,这个概念更像是德勒兹式的,而不再是德里达式的。异电影或拓展电影这个说法,其实也强烈地呼应着今天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之所以“人工”,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人的自然智力的辅助(如纸笔辅助心算),而更是从根本上展现出一种无可遏制的拓展倾向,它不断将人的智力向着种种外部的条件(环境、技术、文化)进行延伸。智力本身就是“被嵌入(embedded)”到一个越来越大的外部环境之中,电影亦是如此。借用法国哲人柏格森的玄思,影像(image)本身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那一方屏幕上闪烁不已的视觉信号,而更应该被放到整个宇宙之中,被视作最普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所有“显现出来”的东西,不都是“影像“?“大脑就是银幕”,宇宙就是剧场。
但也正是在这个宇宙的尺度之上,我们再度遭遇了“电影之死”的另外一层含义。这个含义无法被后电影或异电影的乐观气息从容消解。这个根本的难题就是,在电影变成一切、影像渗透灵魂的时代,人到底在哪里?人到底是什么?面对这个康德的终极问题,福柯曾以戏谑的语气回应:人,就是画在沙滩上的面孔。伴随着下一次历史浪潮的到来,它注定会被抹去。后人类主义者说,人变了,但仍然还残存着与过去的痕迹。人类纪的理论家说,人变了,但不要紧,因为它将要融入到更为庞大的未来生命形式之中。加速主义者则反唇相讥,人变成什么样,人是生还是死,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因为未来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技术不可逆地加速驶向的终极深渊。但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本不该满足于这些或保守或偏激或折中的立场,而只想警示所有那些认真对待电影的人:在如今的时代,电影的生和死或许不再是一个要紧的问题,人的生和死才是。仅仅是“看”电影已不足够,而是必须“思”电影,必须如德勒兹在《电影2》的尾声处所提示我们的那样,将未来的数字电影作为重新激发思想的生死攸关的契机。这或许才是电影之死的真正含义。电影濒死之处,正是思想的重生之源。什么召唤思想?正是在技术加速的终极宿命面前保持自控和自省的人类意志。电影,或许本应该唤醒它的另外一种生命,不再是作为吞噬一切、蔓延拓展的影像机器(dispositif),而更是作为真实和真理的见证。我们仍迷恋着电影,不只是因为它好看好玩,而更是因为它“说真话”。
历史不是革故鼎新的线性进步,而往往是古今交织、新旧杂陈的多元力量的场域。
电影濒死之处,正是思想的重生之源。
电影,不再“在别处”而更是“在眼前”,甚至“在手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