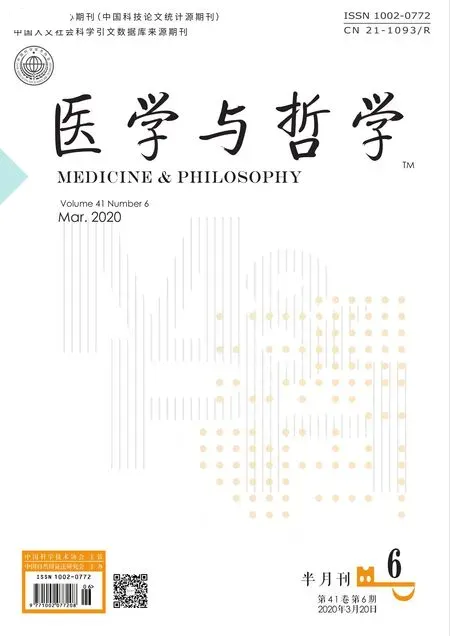蝴蝶效应与临床思维
—— 一例多器官衰竭患者诊疗反思
2020-04-07秦绪常邢利峰
秦绪常 傅 静 邢利峰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被视为一种混沌现象,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1]。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也可以视为一种动力系统。临床中,很多情况下,面对一些复杂、危重的患者,我们往往只会关注其当前所呈现出的临床表现,却忽视了寻找隐藏在该表现背后的始动因素。以下案例的诊疗过程中,“蝴蝶效应”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临床思维。
1 病历摘要
患者63岁,男性,主诉“乏力、腹泻4天,晕厥3次”,由下级医院转诊。发病时伴低热,最高体温38℃,不伴畏寒、寒战;腹泻呈水样,8次/日~10次/日,无里急后重,无明显腹痛。未就诊,腹泻无好转,后病情加重,伴间断意识丧失3次,每次发作表现类似,无抽搐,无二便失禁,持续十余秒后意识转清。当地医院就诊,完善检查及初步对症处理,诊断“多器官衰竭”,转诊笔者所在医院。
患者既往房颤病史,口服华法林抗凝,已停药2天,否认其他慢性基础疾病。
来院时患者精神萎靡,体格检查:体温37.2℃,心率43次/分,呼吸25次/分,血压102/56mmHg。皮肤巩膜黄染,心率慢,律不齐,腹部触诊脐周轻压痛,余无阳性体征。心电图检查提示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实验室检查提示高钾血症(7.1mmol/L)、肝功能异常(谷丙转氨酶3 210U/L,谷草转氨酶2 322U/L,总胆红素78.6mmol/L)、肾功能不全(肌酐323μmol/L)、凝血障碍(凝血酶原时间21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80s)、失代偿代谢性酸中毒(pH 7.1,剩余碱-13mmol/L)。
该患者初步诊断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收住急诊监护室(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EICU),经血液净化、纠正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脏器功能支持及对症治疗后病情逐渐好转,转窦性心律,肝、肾功能逐渐恢复正常,住院7天后好转出院,规律随访1个月,病情恢复良好,未再反复。
2 讨论
2.1 面临的问题
该患者的主诉有两点:腹泻和晕厥。就诊时所呈现给临床医师的结局表现为多器官衰竭。这时候医生面临着几个问题:(1)各器官、系统之间所表现出的异常,中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2)导致患者“多器官衰竭”结局的始动因素是什么?(3)这种始动因素又是如何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作用的?
对于该案例来讲,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多器官衰竭”是临床医师接诊时该患者所呈现出的状态,或者谓之“在场(present)”。同理,那些背后导致患者疾病发生、促使疾病进展至多器官衰竭的诸多潜在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在场(absence)”。患者当前呈现给我们的状态是与背后潜在的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的各式各类的因素息息相通、紧密相连的。真正要搞清楚上述几个问题, 就必须要将“在场”的东西超越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中去,把“在场”(即多器官衰竭的状态)与“不在场”(动力系统中的始动因素以及促动因素)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样才能真实地了解和把握当前呈现出的这个状态,才能准确回答上述几个问题,对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以及恰当的治疗。
2.2 挽救生命与刨根问底
随着国内分级诊疗制度愈发完善,当前基层医院承担的主要任务为慢性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首诊与转诊。该患者由于自身原因未在第一时间内就诊,基层医院首诊时所呈现出的就已经是“MODS”的结局,无论病因如何,危重的病情已远超出基层医院的处置能力,“急慢分治、双向转诊”,于是第一时间将患者转至上级医院急诊。
对于急诊科,有别于全科医疗及其他临床专科的特点,笔者认为其主要在于“挽救生命”和“刨根问底”的有机结合。“挽救生命”指的是在最短时间内稳定患者的生命体征,要求医生在病因未明的前提下对患者进行治疗及干预,目的是保证患者气道、呼吸、循环(airway,breathing,circulation,ABC)的稳定,是临床一线尤其是急诊科的首要任务。只有在“挽救生命”的前提下,才有机会进一步“刨根问底”。但实际上,随着医疗体系的专科化日趋精细,越来越多的医生忽视了患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整体性,忽视了疾病发生时各临床表现间、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该例患者,肾内科医生看到的是“肾功能异常”,心内科医生看到的“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而血液科医生看到的是“凝血障碍”。如果所有的诊疗都基于这种判断,人为地将“整体”拆散、打乱,那么必然诊疗过程中无法做到系统化,无法完成从“在场”到“不在场”的超越,更无法找到该患者疾病发生、发展过程这一“动力系统”中的关键所在,正可谓管中窥豹、盲人摸象,“刨根问底”更是无从说起。
因此,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讲,在该病例中,首先要做的便是稳定患者生命体征,纠正潜在的致死因素。所以,纠正高钾血症及其他内环境紊乱是该患者救治的当务之急。该例患者严重高钾血症合并失代偿代谢性酸中毒,且血流动力学极不稳定,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ies,CRRT)相较于常规间歇性血液透析,低血压风险更低[2-3],所以医生选择第一时间行CRRT维持治疗。在生命体征及内环境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系统、综合的治疗,安装临时起搏器,积极纠正心律失常;补充维生素K1及凝血酶原复合物,纠正凝血障碍;同时予保肝、降酶及对症支持,最终该患者得以康复出院。
对于开始面临的几个问题,结合该案例中患者的临床表现、疾病演变过程、相关辅助检查结果,医生推测出该例患者疾病发生发展这一动力系统中的始动因素及其他各因素间相互作用方式,如图1所示,这也是对急诊科“刨根问底”的有力诠释。
首先,结合患者病史特点,腹泻考虑急性胃肠炎所致,严重腹泻导致患者脱水,造成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进而导致肾前性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4],尿钾排泄障碍,继发高钾血症。高钾血症又进一步导致高度房室传导阻滞,诱发阿-斯综合征(Adams-Stokes syndrome)发作,故患者出现反复晕厥。阿-斯综合征发作时心排量减少导致肝脏灌注减少,恢复灌注后造成脏器的缺血再灌注损伤[5],表现为肝酶及胆红素升高;同样,肾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使已受损的肾功能恶化。患者因房颤长期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腹泻导致维生素K1吸收障碍,造成华法林的相对过量[6],表现为凝血障碍,而缺血再灌注损伤造成的肝功能异常,又会导致凝血因子合成障碍,进一步会使凝血功能恶化。

注:VitK1:维生素K1;AKI:急性肾损伤;AVB:房室传导阻滞
2.3 普遍性原则与个体化差异
通过对该案例诊疗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可以看出,即便是普通的胃肠炎,同样可以造成严重的不良结局。蝴蝶效应原理作为临床中的一种思维模式,要求医生将患者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根据我们获得的有限信息,进行归纳、总结、推理,超越看得到的“在场”的东西,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中去,完成由显现处超越到隐蔽处,以寻求各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整体把握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始动因素、各促动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对疾病做出准确的判断,找到最佳的治疗切入点,及时阻断病情的发展、恶化,最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
这种思维模式在类似疾病的诊疗过程或类似临床情境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临床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注意个体化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该案例中,患者年龄大于60岁,腹泻脱水严重,未在最佳时间进行医疗干预,首次医疗接触时,患者的疾病过程已从单纯的腹泻进展至MODS,即完成了从量到质的转变,很显然,这种质的转变是有害的。该案例中,患者房颤及长期口服抗凝治疗的基础,使他更容易发生心律失常、凝血功能及内环境的紊乱。因此,面对上述临床情境时,既要整体把握,又要针对不同个体做出细节上的调整。
2.4 “蝴蝶效应”的启迪
笔者认为,“蝴蝶效应”原理在该案例中带给我们的启迪,即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数,其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决定着必然发生的“变数”,“变数”的积累最终促使量到质的转变,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我们还应该知道,这种“变数”可以是坏的“变数”,也可以是好的“变数”,坏的“变数”很多时候不能避免,但我们要做的是争取制造好的“变数”。当面临复杂的临床问题时,医生首先要具备的是整体观,而不是只盯住“在场”的东西,即患者当前展现出的临床问题。要视患者及疾病本身、当前临床问题及背后潜在的致病因素为一个有机整体,不能机械地将两者对立。同时更要注重细节,把握事物变化轨迹,通过对“初始因素”的细节把控,来获得好的“变数”。正所谓做好一件恰当的事情,其产生的能量,足以推动更多好事情的出现,这便是所谓的正能量。
同样,这一原理不仅仅体现在疾病的诊断过程当中,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甚至医患沟通上同样适用。系统的疾病诊断,正确的治疗原则,最佳的治疗处置,精准的细节把控,良好的医患沟通,各环节、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勾连,这些都将会改变“动力系统”的发展方向,最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