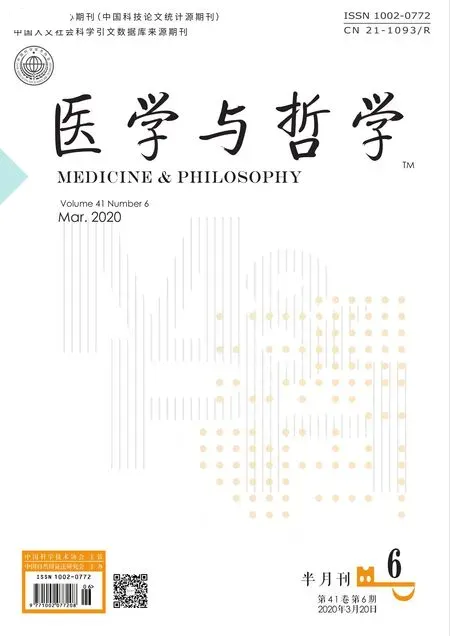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药物临床研究的伦理思考*
2020-04-07陈勇川
陈勇川
2020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地,随即扩散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随着疫情的暴发,各医疗机构和有关企业掀起了一轮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临床研究“风暴”。之所以称之为“风暴”,是因为自国家卫健委2020年1月15日正式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以来,到2020年2月23日,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显示已有234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的临床研究进行了登记注册,直接涉及干预性药物治疗的研究达126个[2],见图1。这与2003年SARS疫情暴发时注册临床研究数量为0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6年来我国在临床研究科技创新体制上的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成效,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如此众多的注册临床研究项目中,除了“瑞德西韦”药物临床试验项目为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的注册临床试验外,其余项目均是按照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登记注册。这些研究在此次疫情的特殊大背景下“一窝蜂”地上马,真的能为战胜疫情带来新的希望?亦或带来新的伦理挑战?

图1 234项新冠临床研究数量分类图
1 新冠肺炎疫情下相关药物临床研究的现状
截至2020年2月23日,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注册的234个有关新冠病毒的临床研究。按研究性质进行简单分类可以发现,其中涉及药物治疗的研究有126个,占到所有研究数量的一半以上,说明在疫情的紧急情况下研究者最关心的仍然是针对疾病本身有效治疗药物的研发。试验药物包括瑞德西韦、利托那韦、ASC09/利托那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其本身就是针对病毒设计开发的抗病毒药物。其他试验药物涉及中西药物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等辅助治疗,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颗粒、痰热清注射液、血必净注射液、糖皮质激素、利巴韦林+干扰素α-1b、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α2b等药物或组合药物。其中,不乏在近几年来国家临床合理用药管控中因疗效不确切或不良反应被列入了重点管控的品种,但本次疫情下却又“粉墨登场”进入临床研究。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床研究的伦理考量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临床研究,国际社会历来都高度关注,因为在此条件下开展临床研究,面临着一系列与常规条件下不同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在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ommitte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Sciences,CIOMS)联合WHO制定的《涉及人的健康相关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16年版)中,明确提出了“发生灾难和暴发疾病时开展研究”的伦理准则[3]76;2016年WHO发布的《传染病暴发中伦理问题的管理指南》对传染病暴发期间的研究进行了规定[4]24;2020年1月28日,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委员会发布《全球卫生突发事件相关研究的伦理问题》(ResearchinGlobalHealthEmergencies:EthicalIssues)最新报告,报告提出平等尊重(equal respect)、帮助减轻痛苦(helping reduce suffering)和公平(fairness)三大核心价值[5],其具体要求可表述为:平等尊重要求尊重他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包括尊严、人格和人权;帮助减轻痛苦强调所有行动需遵循建立在团结互助以及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基本义务;公正主要体现为不歧视他人以及风险获益的公平分配[6]。从中可以看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床研究的伦理关注仍然脱离不了《贝尔蒙报告》中所阐述的尊重、有利和公平三大伦理原则。本文结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下拟开展的药物临床试验现状,就以上伦理原则进行探讨,并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药物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和管理建议。
2.1 风险与受益评估的特殊考量
标准的注册药物临床试验基于成熟与完善的新药审评制度,药物前期临床前工作比较扎实,有完善的数据支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对这类项目的临床试验进行风险受益评估基本是约定俗成的内容,伦理审查相对简单,挑战性不大。但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登记注册的临床研究项目来看,除了瑞德西韦外,几乎均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clinical trial,IIT) 项目。此类项目往往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立题依据不充分,缺乏必要的研究背景;(2)研究基础不充分,缺乏必要的临床前实验数据;(3)研究条件不充分,缺乏必要的质量保障体系[7-8]。从登记项目已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绝大部分项目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问题。如对于一个抗病毒药物而言,它究竟针对病毒的什么特定蛋白,阻断病毒复制的哪一个环节,其作用机理应该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临床的治疗价值才有研究意义。而大量的作用机制不明或从分子设计上已证明对新冠病毒无效的药物仍然在登记注册进行临床试验。还有一些项目仅仅基于体外细胞试验观察到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但其报道的有效浓度往往是几十甚至于几百微摩尔,其在患者体内要达到此浓度几乎不可能。对于几十个拟开展的中药临床试验(包括中药注射剂)而言,不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连续多年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中反复提及的如双黄连、热毒宁注射液等品种。而对于在临床治疗中如何使用本身就存在重大分歧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也有不少的登记注册项目拟开展试验,这种研究究竟是基于患者受益的考虑还是基于“利用”本次疫情难得的“海量受试者”机会进行的科学验证,值得深思。而利用脐带血等新概念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其本身就不是治疗病毒感染的常规手段,从性质上与疫情早期大量非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蜂拥至医院造成对一线医疗资源的挤兑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后者是对一线宝贵的研究资源的挤兑。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在突发紧急状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针对患者(特别是危重症患者)而言大部分都愿意承担未经证实的试验药物所带来的高风险,从这一点上,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潜在受试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应该给予特别的伦理关注。应充分考虑在此情况下参与研究受试者的弱势特性:可能屈服于学术带头人的权威、不能在充分理解利弊前提下做出决定、因传染性而受歧视等。同时,紧急情况下的临床试验方案往往会有意降低纳排标准,从而影响试验结果。因此,更应当避免把无明确证据支持的药物进行大范围的紧急使用[3]78。
另外,如此众多抗疫药物的临床试验,如果真要在当下防疫极其紧张的临床一线开展,那就要更多的患者、更多的医护人员参与到临床试验的特殊流程中来,这在当下一线抗疫工作量极大的情况下其操作性存在极大问题。从目前登记注册项目所提供的信息来看,绝大部分项目的组织形式均为发起医疗机构(大部分为湖北省外且有驰援湖北抗疫任务的大型医疗机构)做牵头单位,本单位对口驰援医院为参加单位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模式。如此特殊的临床试验组织形式也是本次疫情的一大“创造”,但正因如此,组织形式上反而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试验目的究竟应该多大程度上关注于产生可普遍化的知识,多大程度上关注如何将新获得的知识快速应用于临床治疗和公共卫生实践,服务患者和公众健康[9]。这是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临床试验伦理审查时必须明确考虑的重点,且笔者认为在此特殊情况下应该更倾向于将新获得的知识快速应用于临床治疗而不是产生可普遍化的知识。否则,过多过滥的临床试验只会给临床一线人员增加巨大的负担,浪费宝贵的医疗和研究资源。
2.2 疾病暴发时期的同情治疗与临床研究的关系
目前,并没有数据显示瑞德西韦对于新冠病毒有治疗作用,仅在体外模型中,瑞德西韦显示对新冠病毒有活性,但这并不构成其进入临床试验的充分必要条件。真正让瑞德西韦走向 “聚光灯”下的是1月31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关于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接受瑞德西韦治疗过程的文章[10]。但该例患者并不是以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方式接受瑞德西韦的治疗,而是基于“同情用药”(compassionate use)原则进行的尝试性治疗。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同情用药制度的国家,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规定,同情用药是指对于患有严重或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在不能通过现有药品或入选临床试验来得到有效治疗时,可以申请在临床试验之外使用未经上市许可的试验用药物。根据美国FDA官网公布的数据,美国药品审评研究中心在2009年~2015年共收到了7 292份(年均1 215份)药物同情使用申请,申请的获批率约为99.5%。近年来,同情用药制度在国际范围内被逐渐接受,目前欧盟、日本等已经建立该制度。
我国新《药品管理法》也积极吸纳了“同情用药制度”,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并且符合伦理原则的,经审查、知情同意后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因此,从该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必须明确开展同情用药的几个基本前提,即适用的药物须是“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药物,适用的疾病须属于“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这就是为何在本次疫情下瑞德西韦无法以同情用药的方式用于抗疫一线患者治疗的重要原因,假设该药本身已在我国进行临床试验(不管其适应证为何),那么基于伦理的考虑,对于危重症患者而言同情用药就应该是比参与临床试验更可取的选择,毕竟基于科学性要求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使安慰剂组面临 “无效治疗”的风险。
显然,同情用药制度是在临床试验和已获批上市药物之外,为危重症患者提供了一条额外的药物可及的路径,在特殊情况下是履行“患者受益最大化”这一基本伦理原则的重要抓手。如果通过制度创新在此次疫情中适当使用同情用药制度,则会在不影响注册试验的基础上,让危重症患者获得尽可能有效的治疗用药。当然,在感染人数多、涉及范围广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使用同情用药制度,若仅局限于个例使用又会带来患者选择不公正的社会伦理问题,而规模化使用则面临现行法规制度的挑战。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不断增长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数量,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一药定乾坤,但在平衡风险获益与保障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如何调整同情治疗与临床研究的关系,增加治疗的可及性应该是未来需要尝试的方向。
2.3 利益回避与伦理监督
如上所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临床试验的目的不清晰(获得知识还是获得治疗),同时又涉及到特殊“弱势人群”的保护,在伦理审查时就应该建立特殊的利益回避规则,避免在此类临床试验中出现研究者(研究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局面。同时,考虑到突发状况下若按照标准程序的伦理审查机制进行评审,也无法满足紧急情况下的流程进度,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加快伦理审查机制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临床试验的需求。结合我国特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联系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体现出的“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既然防控物资、生活物资、医务人员等都能够通过国家层面统一进行调配,从而平衡好高效和公平的防控工作要求。那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临床试验伦理审查最佳的模式也应该是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伦理审查。理由如下:第一,这样可以极大避免无充分科学依据的项目盲目地开展临床试验,降低研究风险;第二,有效管理利益冲突,让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卫生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建立或紧急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专门针对此情况下的临床试验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床研究伦理审查新机制的建立
本次疫情的暴发激发了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研发企业针对新冠病毒感染治疗方面的研究热情。这对于推进我国创新生物医药研发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基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临床试验必须以科学、严谨、可靠的数据和结论作为研究依据。这就要求在此情况下进行的临床研究更应重视研究的合规性、科学性和伦理合理性。在具体方案审查的伦理把握上,更需要考虑研究的科学价值、临床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合理平衡;传染性疾病受试者时间和空间上的“受约束性”所带来的特殊知情同意要求和处理等[3]80,[4]26。
目前IIT大多是由医疗机构自行开展,项目的立项审批完全取决于机构的自律与责任心。由于缺乏明晰的管理法规,管理部门对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也难以预判和防范,更无法规避为了研究而研究的项目立项和审查。因此在审查机制体制上,强烈呼吁国家层面建立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临床试验统一的伦理审查工作制度。可以在目前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基础上,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情况,临时增补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应急情况下国家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疫情期间拟开展的临床试验进行严格审查,根据审查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网络通讯审查的形式快速形成决议,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的审查形式形成决议。如果审查项目数量多,也可以基于研究的需求采取紧急情况下集中办公,即在非常时期紧急抽调伦理审查委员到指定地点集中,通过现场召开会议审查的方式开展工作,直到疫情期间临床试验送审项目审查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后再解散。这样从机制上将紧急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由各级医疗机构自行管理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审批制,从而才能从源头上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临床研究项目规范有序开展,不会因重大疫情下患者和社会需求迫切而降低研究质量,使受试者经历实际无效甚至有害的治疗,浪费临床资源和社会资源。
诚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临床研究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在立项、伦理审查、实施、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还需要通过立法来加强管理,即从法律层面明确临床研究的分级分类管理,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临床研究哪些不能做,哪些应获得哪一级政府部门(科技部、卫健委、药监局等)的批准;哪些应该由企业发起,哪些可以由研究者发起;哪些需要由有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资格的医疗机构承担等。
4 结语
目前,从国家层面对以注册为目的的药物临床试验与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都有着相关的法规指南以及不同层面的监管措施,而对于医学临床科研的伦理审查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尤其是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临床研究中的伦理审查和伦理管理,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各机构伦理委员会首先有责任严格履行各阶段的审查和监管职责,研究者也有义务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和健康。可以大胆预测,随着本次疫情的结束,绝大部分登记注册的临床试验项目都将“无疾而终”,草草收场。但导致这种草率立项、仓促上阵的局面无疑会与我国政府倡导的建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符,因此建立新的适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开展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和监管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相信如能就上述认识的达成共识,在各方的共同重视和努力下,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开展的临床研究将逐步规范,临床科研的质量也必将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