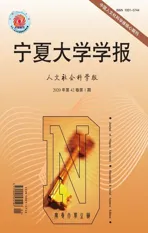论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中的审美意象
2020-04-06彭姣
彭 姣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意象”一词源远流长。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中写有:“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1]在这里,王充将熊、麋、虎豹等称之为“意象”,作为等级符号的代表。袁行霈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2]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男性创作女性题材诗歌,不少女性作家也身体力行参与其中,探索为文之道。因此,当时之审美风格独具特色,如“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3]。“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4]其中所运用的“日”“月”“团扇”等这些意象提高了包括女性题材诗歌在内的所有诗歌的表情达意的效果。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意象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月”这一意象,据统计《全唐诗》50836 首诗歌中,只“月”一字便出现了11055 次,再有李白的1166 首古诗中,“月”也出现了523 次,此频率远超《全唐诗》的平均值[5]。总之,研究这样具有先导性的文学审美形态,不仅能窥探当时女性内心的万般情绪,对于那时女性的生存境况、她们对社会的认知以及那一整个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状态等都能得到进一步了解。
一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寄情达意的审美意象群
意象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一种形象,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把意象当作思想和情感的一类复合体。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意象作为极其重要的概念,它能以景托情,也能寄情于景,又或是情景交融,是一种艺术性的创作技巧。魏晋南北朝文人将此很好地运用于女性题材诗歌中,寄托无限情思。
(一)伤春悲秋的季节意象
自古以来,国人便有类似“伤春悲秋”的“善感”情结。《诗经》言:“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6]。江淹作《别赋》:“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7]抑或是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8]。行至范仲淹,又有了“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9]。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能撩拨诗人的情绪。“春”“秋”这类富有代表性的季节更是如此。《说文解字》言春秋:“春,为推也,万物之始也”;“秋,禾谷熟也,其时万物皆老,而,秋之为言攀也。”[10]意为“春”乃万物之始,如同一个人的青春期一样,代表着生机与活力。而“秋”,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吟咏悲歌的对象,或残花落叶,或西风大雁,抑或黄昏唱晚,极尽悲凉之感。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女性题材诗将这类季节意象运用诗中,形成经验性的审美艺术形态。
西晋石季伦得一婢妾,名为翾风,作《怨诗》一首:
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
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
桂芳徒自蠹,失爱在蛾眉。
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11]
诗歌首句以“春”开头,春天一切都是美好的,阳气生发,花草树木崭露头角,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好比诗人的容貌,正值鼎盛时期。翾风来自西域,美貌绝伦,徐震《美人谱》将其列为四大美婢之首,可见其颜值之高。只是,美人再美,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摧残,随着时间流逝,绝美容貌犹如秋季万物逐渐萧索。翾风年老色衰,风华不在,遭人遗弃。诗人以盎然的春、寂寥的秋类比容貌的变化,同时抒发独守空房的哀怨愤慨,谴责男子的重色负心之情。再有陈思王曹植诗《闺情》“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12]“春思安可忘,忧戚与君并。”[13]女子只身一人,寂寞无聊,走出闺房,满目尽是茂盛苍翠的小草。这些小草已经铺满庭前台阶,洋洋洒洒地生长着。按理说,此情此景应心中畅快,可美好的景色反倒使诗中女主人公生发无限情思——思念在外的君子。春草再生,君却不在,该是何等的思念才使得女子无暇顾及长满台阶的春草,又该是何等的寂寥才使得春草因无人踩踏而肆意生长至此!细细思索,一个独守空闺、寂寞叹息的女主人公形象跃然眼前。此外,如徐干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14],潘岳的“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15],张华的“譬彼暮春草,荣华不再阳”[16]等都是借对“春”的描绘,或慨叹人生短暂易逝,或衬托女主人公容颜不再的凄凉,或烘托思妇的深深眷恋之情。
莺歌燕舞、活力满园的春逃不过充满复杂情感诗人的艺术创作,更别提草木摇落、悲凉苍寂的秋了。傅玄《秋兰篇》:“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回翔。君其历九秋,与妾同衣裳。”[17]君已在外历经“九秋”,女子见鱼、鸟皆是成双成对,不免引发相思之苦。女子该是数着日子等待着君的回归,即便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漫长等待,也要与君厮守,坚贞情谊溢于言表。魏文帝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开篇即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18]以萧条景象牵出女子的怀人之情,在清冷悲凉的秋季,女子独自一人细看万物凋零落败,白露凝结成霜。在接近于平线的节奏中将女子的柔情娓娓道来,笔法巧妙动人。谢朓《秋夜诗》云:“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19]“谁能长分居,秋尽冬复及。”[20]此诗先声夺人,以“促织”“捣衣”告知深秋将至,巧妇正急着为常年在外征战的丈夫准备御寒衣裳,定是在空荡少人处方能清晰听见“促织”“捣衣”声。尾句发出“有哪一对夫妻能够承受这样长久分离?”的诘问。秋日之寂与巧妇内心之伤相得益彰,虽题为“秋夜”,实则“闺怨”。
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虽有过统一,但放眼至整个历史长河,这些和平不过是昙花一现。这就使得女性独守空闺的命运能与一年四季这些节气的更迭产生潜在的某种联系。无论是在悲寂的“秋”意象,还是在拥有生命力的“春”意象中,于诗人或是诗中的女主人公群体而言,都是寄托感情的载体,生动而真切。
(二)幽闭狭窄的闺帷意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严格的等级观念,人分三六九等,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更加无法越出这个藩篱。《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妇人之美,非诔不显”[21],意思是妇人的美德只有在家中才得以显现,不依靠诔文得不到体现。可以看出,当时女子的生存环境大多限于家这个狭小的空间,这在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中也能得到进一步印证。
1.镜匣、衣物
“镜”意象,在先秦时期象征清明之道,至魏晋,其象征义愈加丰富,包括:一是占卜除邪,二是女子的闺怨情思以及男子的感时伤怀,三则体现“镜”与佛教之间的文化意蕴[22]。在魏晋南北朝涉及女性的诗歌中,“镜”意象主要代表女子的闺怨情思。王融《有所思》云:“欲知忧能老,为视镜中丝。”[23]要想知道忧愁有多催人老,只要看看镜子中的发丝就知道啦。作为闺阁中的必备物,镜子与主人息息相关,看着镜中自己日渐衰老的容颜,女子如何不愁怨?萧绎的《代秋胡妇闺怨诗》:“荡子从游宦,思妾守房栊。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24]何为“尘镜”?男子常年不归,在外做官,使得女子不得不心生怀疑且无意梳妆打扮,使得原本明亮的镜子布满灰尘,日日掩饰。诗人将一个感情真挚却缺乏安全感的独居女子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除却“镜”意象,“衣”意象也在诗中占据不少比例。谢朓《玉阶怨》:“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25]长夜漫漫,女子自缝罗衣,以期重拾恩宠,罗衣缝多久,思念便是多久,寓怨于思,含蓄隽永。王僧儒的《为姬人自伤诗》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还君与妾珥,归妾奉君裘。”[26]以被弃姬女的口吻控诉男子的薄情,可以想象当初浓情蜜意时,互赠信物,女子亲手织裘送给心上人,如今感情断裂,只能主动要回信物,无奈之际而又存有对男子回心转意的幻想。另有庾丹《秋闺有望诗》中的“罗襦”“金缕裙”,张率《远期》里的“单衣”,繁钦《定情诗》中的“衣巾”……有关“衣”意象的出现次数较为频繁。
2.帷帐、床枕
班固《白虎通义·嫁娶》曰:“闺阃之内,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27]属于内室之物的床、枕、帷亦是备受诗人青睐的意象。张华《情诗》(其三)便是这类意象的典型。首句以清风拂动帷帘拉开序幕,映入眼帘的便是一间幽深的空室,兰室因夫的缺席而了无生趣。紧接着笔锋一转,“襟怀拥虚景,轻衾覆空床”[28],抬头明月皎洁,低头却见空荡荡的床。一个“虚”字,传神地刻画出女子思念丈夫至恍惚的神态,待女子缓过神来,只得“拊枕独啸叹”[29],内心无处发泄的苦闷由“拊枕”这个动作体现得淋漓尽致。再比如鲍令晖《代葛沙门妻郭小玉诗》的“相思枕”,王宋《杂诗》的“床前帐”,范云《自君之出矣》的“罗帐”,此类闺阁器物意象的运用比比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那时女性活动空间具有封闭性。
除以上几类闺室意象,还有不少与之紧密相连的建筑类意象,如“兰室”“高台”“楼阁”“玉阶”“夕殿”等。虽较之于闺中器物一类给人感觉更“大”,然而,再大,诗中女性也只能是蜷缩于一片有限的空间内,至多是登上楼阁远眺,跨上高台神伤,下至平民女子,上至深宫嫔妃,无一例外。《礼记·内则》对女性的行为规范早已作出严格的标准:“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30]封建女性的生存空间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使当时不乏觉醒意识的女性,但在大时代潮流下,很难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因此诗中这类局促、狭窄的闺帷意象便是当时女子群体生存空间的缩影。
(三)传情达意的动植物意象
阿来在他的《博物学与我的写作》中谈道:“如果把自然关系抽空以后,只剩下人的关系,会导致这个社会不能建立足够的温情和信任。”自然于我们真的太重要了,尤其体现在文学方面。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学就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赏一圆月,备感思乡情愫;观一落叶,会吟一叶知秋;品一泉水,能知海纳百川。自然与人类必定是不可分割的存在。古诗作为文学中的一分子,同样离不开自然的润色,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古诗中的动植物意象丰富无比,以下仅是一部分典型。
1.动物意象
庾肩吾《赋得有所思》:“不及衔泥燕,从来相逐飞。”[31]女子日夜盼望着远方的人,于屋中踱步,翻出“离扇”“别衣”一遍遍回忆着当初一起时的甜蜜时光,谁知佳期难约,尾句女子以衔泥的燕子相互追逐的画面表达内心的不满与无奈,连燕子都是双宿双飞,我和你却长久分离,苦楚万分。徐干的“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32]。黄鹄即鸟类的一种,配偶固定,除非一方死亡,否则为终身伴侣。思妇以此比之,一方面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另一方面也希望丈夫在外洁身自好,莫要辜负自己。类似的还有“鸳鸯”意象,南朝大臣江总笔下的“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33]。寄托了夫妻恩爱、长相厮守的绵绵情谊。此外谢灵运《燕歌行》中的“蝉”,徐陵《中妇织布流黄》中的“蜘蛛”,抑或是王融《古诗二首》(其二)里的“飞萤”等动物类意象,它们均具有鲜明的时节特征,极易引起女子对时间飞逝的慨叹,同时,与女子独守空闺的状态构成动静呼应之势,一静一动,对比显著,成为诗中女性的精神寄托。
2.植物意象
说到植物,不得不提及《诗经》。《诗经》中含有大量的植物意象,如《卫风·氓》中以桑树的生长过程比喻爱情中的由盛到衰,《郑风·山有扶苏》以相关植物的特征或习性隐喻男女择偶,《周南·樛木》则以“樛木”“葛藟”的生长形态祝福夫妻和睦美满。这些意象为后世文人作品的传情达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古诗自然也受其影响,模仿传承屈原的“香草美人”手法,以特定的植物象征高洁品格,如陆机《拟青青河畔草》“靡靡江蓠草”[34],陆罩《闺怨诗》“独向蘼芜悲”[35],陆机《塘上行》“江蓠生幽渚”[36]。“江蓠”与“蘼芜”同一。《本草纲目·草部》记:“蘼芜,也称薇芜、江蓠。[时珍说]王逸说,蓠草生于江中,故名江蓠。”[37]是一种香草植物,一般生长在具有肥沃土壤的江边,可定气、辟邪、除虫。再有同样功效的“茱萸”,曹植《浮萍篇》:“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新人虽可爱,无若故所欢。”[38]以“茱萸”和“桂与兰”类比“我”和“新人”,“茱萸”外表也许不似“桂与兰”那般夺目,但多了长寿、驱邪的实际功效,就像“我”虽然不及“新人”美貌,却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告诫对方切莫喜新厌旧,伤人伤己。
除了象征高洁品格,也有对男女情感生活状态的比喻。刘孝绰《班婕妤怨》“况在青春日,萋萋绿草滋”[39],班婕妤昔日的得宠与如今的无人问津形成强烈对比,与皇上二人形同陌路。谢朓《王孙游》中“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40],疯狂生长的草和树预示岁月的变迁,两人已分开太久,待君归来,已是另一个季节。张正见的《有所思》也是如此,以“花”“塞草”意象唤起主人公的哀思,抒发情感。
无论是动物意象,还是“茱萸”一类的植物意象,诗人将这些意象运用于诗中,或构建隐喻,或女子自比,以一种极具新颖和审美的方式传达情感,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诗句立刻熠熠生辉,不仅丰富了诗中女子形象,同时也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由于篇幅所限,以上所举例子并未囊括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的所有意象,诸如“捣衣”“团扇”“书”“星月”意象比比皆是,均值得探索。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意象使得古诗拥有永恒的审美意蕴,诗中女子的“无处话凄凉”也有了归宿。
二 独照之匠,窥象运斤——借意象阐释女性情感百态
所谓“落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见全豹”,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中的各类意象便是“叶”,是“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神思》篇提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41]所以,从意象入手,剖析个中缘由,辐射全诗,诗中女性的百般情感自然得以呈现。
(一)忠贞爱情的执着
爱情自古以来便是男女竞相追逐的对象,在古时生活相对简单的大环境下,男女爱情在生活中所占比重更为明显,处于深闺中的女性,生活单一、百无聊赖,自然期望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唯美爱情。梁王卫敬瑜妻王氏在丈夫亡故后作《连理诗》:“墓前一株柏,连根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称何足奇。”[42]又有《孤雁诗》:“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43]王氏种下一株“柏”,结为连理,以“孤雁”自比,血泪独白,字字诛心,对亡夫的忠贞之情令人动容。再如鲍令辉《古意赠今人》:“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见。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44]妾设身处地感知君的不易,将情思寄予“飞燕”送至君处,坚贞情思在时光飞逝的映衬下更为深切。“愿为星与汉,光与影徘徊”[45],则是以“星”“汉”这类星月意象委婉地表达与心上人长相厮守的渴望。
(二)独守闺房的哀怨
魏晋南北朝朝代更迭,战争导致无数家庭离散,游子在外难归,女子家中留守成为常态。因此思妇与游子之间无形中建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张华《情诗五首》(其一):“初为三载别,于今久滞淫。翔鸟鸣翠偶,草虫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泪流衿。”[46]明明说好只别三年,如今却久久未归,“草木”“鸟虫”触目所见,皆能加重思妇感伤,止不住流泪打湿了衣裳。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47]“高楼”被“明月”笼罩,流光溢彩,如此唯美的景象,思妇却无心欣赏,连连叹气,美景衬哀情。再有徐干《情诗》:“顾瞻空寂寂,唯闻燕雀声。忧思连相属,中心如宿醒。”[48]空荡荡的房间使得“燕雀”声越发响亮,倍增空虚寂寞感。尾句写出女子的恍惚迷离之态,“宿醒”即为“宿醉”之意,《说文解字》“古酲亦音醒也”[49],“酲,病酒也”[50]。目之所见均没有能使女子感到宽怀的事物,忧念情思再沉重不过。
(三)坎坷命运的悲歌
当时社会以男权为中心,女性作为社会最底层而存在,大多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傅玄《苦相篇》(节选)言简意深,为女性发音:“男儿当门户,坠地自生神。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51]痛斥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病态。在当时,先秦两汉时期所建立的儒家伦理体系逐渐瓦解,加之道教和佛教的介入,人们的道德标准受到冲击,兴起淫逸之风,富贵抛妻之事时有发生。而且据相关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大规模战争约500 次,“乱世”之名名副其实,莫说平民男性战死,就连统治者也无法独善其中。这样的境况下便涌现出一大批弃妇、寡妇,导致女性的命运大多悲惨凄凉。类似于卞皇后《与杨太尉夫人袁氏书》、丁廙妻《寡妇赋》中亡子、亡夫的妇女不在少数。曹丕《寡妇诗》:“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候鴈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52]诗中列举一系列秋天才有的凄清景象——“霜露”“落叶”“候雁”“归燕”烘托遗孀残破的心境,由秋日的肃杀联想到女子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另有一女子遭遇更加令人扼腕,(王微《杂诗二首》节选)“途谓久别离,不见长孤寡。寂寂掩高门,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颜今就槚。”[53]“槚”在《说文解字》中的本义为“楸”,一种树,人们常把它与松树一起栽种于坟前。诗中女子到最后也没能见到丈夫的遗体。
诗人审美意象下的女性群体情感丰富,身处幽闭的闺阁之地,仍然阻挡不了她们内心情思的迸发。魏晋南北朝诗人以万千意象润色笔下的女性生活以及内心状态。文学源于生活,这些诗中的女性自然带有那一时代女性群体的影子,必然会反映出她们的真实内心世界。以小见大,以一窥全,便是审美“意象”的艺术价值体现之一。
三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探其审美意象之文学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上承先秦两汉文学,下继唐代文学,身处两个文学高峰期之间,其地位与影响不可小觑。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有言:“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54]强调了继承与革新对文学的重要性,无继承,文学便是无本之木;无创新,文学则为无源之水。当一时代文学有了“名气”,必然会影响后世创作。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中的审美意象也逃不过此般定律。
(一)对先秦、汉诗相关意象的吸收
首先有继承《诗经》中的各类意象。《诗经·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55]在这里“樛木”是对君子祝福的载体,是传达情感的最佳媒介;《诗经·召南·草虫》“陟比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56]“薇”是山菜的一种。以再次看见春天蕨菜的生长暗示等待君子时间之长;《诗经·小雅·谷风》“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57]以秋季“草木”之枯诉弃妇内心之怨。前文所举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中意象也有类似应用,不再赘述。
其次也有对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吸收。有意象的直接借鉴,也有意境的承袭,具体以张华《情诗五首》为例:
总之,无论是先秦诗歌还是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中的审美意象与它们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二)对唐诗的影响
唐朝是一个思想开放、言行举止大胆的朝代,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文人纷纷走出束缚,竞相书写,创造了我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唐诗至今光彩夺目。唐文学发展的前提条件自然少不了上一朝代作品的濡染。唐诗中有不少题目直接延用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的意象,如季节意象:王维《山居秋暝》、张九龄《春江晚景》、陆游《秋思》,再有动植物意象:贺知章《咏柳》、郑谷《菊》、杜甫《画鹰》。这些意象出现频率极高。另外,魏晋南北朝女性题材诗歌中的“月”意象也在唐诗中占了不少比例。情韵是唐诗的灵魂。“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雨暑云,冬日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58]“月”,夜晚的象征,它有满亏,有阴晴,体现了万事万物复苏的动态过程,特定的时间节点赋予了它别样情韵,因此“月”这类富有经验性的审美意象成为唐朝文人笔下的宠儿。李白《长相思·其二》“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59]这是月夜主人公的“愁不眠”;沈佺期《杂诗》(其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60]这是月下思妇的踌躇;王维《竹里馆》“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61]这里我们又感受到了“月”的浪漫多情、善解人意。
此外,唐诗中也有对“捣衣”“书”“星辰”“凭栏”“鹧鸪”等意象的沿袭,凝聚着文人们的艺术构思与审美情感。
四 结语
一时代之文学理应放在当时大背景下进行解读。“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62]显然,在乱世下,人们的话语权受到限制,尤其是文人群体,“不敢说、怕说错”的生存准则大家心照不宣。此时,把情感寄托于物,含蓄表达实为保守途径,这就为诗歌中的审美意象拓宽了市场。除却“乱世”,魏晋南北朝还是艺术与美学兼备的朝代,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时期,出现了诸如谢道韫这样一批女性作家,她们独立自醒,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并拥有与之媲美的才情,在她们的努力下,人们对女性逐渐有了关注度,也因此写出一定数量的女性题材诗歌,或为弃妇鸣不平,或因寡妇洒泪,或与思妇共情,当然其中也不乏借女性题材隐喻自身际遇的诗,可终究是由女性生发,这点进步万不能抹去。诗人借用“闺阁”“季节”等富有表现力的意象状写女子生活常态,镌刻女性内心情感,反映现实社会,无形中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相关佐证,打下基础,笔者亦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