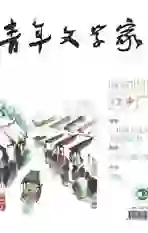浅论《陆犯焉识》的叙事艺术
2020-04-01李苗苗
摘 要: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以自己的祖父为原型,讲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跌宕起伏的一生。小说将背景设定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通过多重叙事视角、多条叙事线索以及多元叙事空间的运用,将风云变幻的历史书写与小人物的情感体味巧妙结合,体现了作者优秀的叙事表达技巧,也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叙事视角;叙事线索;叙事空间
作者简介:李苗苗(1995.10-),女,回族,宁夏同心人,文学硕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2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创作于2011年,小说借主人公陆焉识从1921年到1989年的人生遭际反映了20世纪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变迁,跨越了将近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演绎了历史夹缝中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小说中体现的灵活多样的叙事技巧,既展现了宏大的历史格局,也将小人物的人生百态、辛酸苦辣交织其中,留给读者深刻的阅读体验和思考。
1、多重叙述视角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观察者的立足点不同,感知者所得到的情感体验也就不同。正如布斯所说,在阅读《奥德修记》时,“我们会明确地对英雄们表示同情,并对求婚者们表示轻蔑,不用说,要是另一位诗人从求婚者的角度来处理这一情节,他也许会轻易地引导我们带着截然不同的期待与担心进入这些历险。”[2]视角在叙事文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1.1有限视角
小说《陆犯焉识》采用了多变的叙述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小说的一开篇介绍了西北荒凉的草漠环境。在这片大草漠上,生活着一群囚犯,“叫陆焉识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3],一句话就交代了故事的讲述者之一——“我”,陆焉识的孙女冯学峰。关于“我”的介绍在后面的文章中才提到:“我”是一个刚上大学的小女孩,也是陆焉识盲写书稿的撰写人,是他唯一的读者和评论者,所以“我”相当于祖父的发言人,监狱里的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留洋海外的放浪形骸、浪漫邂逅;逃亡路上的奇特经历、艰难凶险;对妻子的内疚忏悔、炙热情感等等都是通过冯学峰为祖父誊抄盲写的回忆录和散文所了解的。而祖父获释以后回归家庭的种种不适、妻子冯婉喻失忆以及儿女对父母婚姻的阻挠以及最后的出走等等都是源自于“我”的亲身经历,所闻所见,二者结合起来串联起了陆焉识坎坷动荡的传奇经历。
第一人称视角的介入既让故事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起到了陌生化的表达效果。“我”作为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生活在和祖父不同的政治环境、历史背景、道德体系之下,再加上生活阅历、人生观价值观的不成熟,对祖父那个年代的荒诞政治和文化环境不免有一种距离感,所以难免会带有一种调侃打趣的口吻,“我祖父用了无数种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他手臂的感觉,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镐落下 ,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他的内脏,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镐头撞击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垦荒,而是荒垦人。”[4]略带讽刺的口吻,给故事增添了淡淡的喜剧色彩,使读者发笑之后,引起深刻的反思。
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小说的叙述视角也会不经意间由冯学峰转换到陆焉识本人身上,以陆焉识作为聚焦者来讲述他的所闻所见所想。如“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事很蠢:他想跳下车。跳下车做什么?去跟婉喻跳脚发火,说她野得没边了,命也不要了?还是跳下车鱼死网破地迎着她跑过去?”[5]婉瑜得知陆焉识要转监以后,一个人在监狱外苦守七天七夜,跟着囚车一路奔袭才找到了转监后的地点。正是通过陆焉识的视角,使我们看到了温柔体贴的婉瑜还有为爱疯狂的一面,也让后来焉识不惜越狱也要再见婉瑜一面的情节更加具有说服力。再如,在梁葫芦被谢队长“加工”时,陆焉识的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让我们看到了在利益面前人性的卑劣与自私暴露无遗。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都是从主人公陆焉识的视角出发,充分展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真实情感,拉近了读者和文本的距离,使读者身临其境。
1.2全知全能视角
在小说中还时常出现另外一个叙述视角,“它可以时而俯瞰纷繁复杂的群体生活,时而窥视各类人物隐秘的意识活动。它可以纵观前后,环顾四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总之,它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控制着人类的活动……”[6]这一视角就是隐含的作家视角。这一视角置于冯学峰和陆焉识的视角之外,由作者直接进入作品表达情感。
“冯婉喻在得知陆焉识减刑的喜讯的那天夜里,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就像她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那样,想着自己是作的哪一番孽。她可以跟自己做交代了,但还是不能跟焉识做交代……他以为他把胡子留成一个绵羊尾巴就能掩人耳目了,他再乔装打扮也不会掩过她婉瑜的耳目。”[7]原来,焉识暗中探亲那几天的行动,从来都没有瞒过婉瑜的眼睛,焉识跟在婉瑜身后享受着偷来的重聚时,婉瑜也在“故意”的制造与丈夫重逢的机会,甚至“骗”过了自己的丈夫。一个为了保护对方忍受着痛苦的思念也只有默默跟随,一个明知对方的存在却佯装不知以此制造见面的机会。不动声色的背后,隐藏着两个人炙热的内心情感。如果不是通过隐含的作家进入婉瑜细腻的内心世界,我們就难以窥探到精明的婉瑜为了这场无声的会面所付出的努力。作为女性作家,严歌苓注重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探寻与关照,除了冯婉喻以外,她还在小说中刻画了冯丹钰、冯仪芳、韩念痕、颖花儿妈等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
冯仪芳是陆焉识的继母,嫁到陆家几个月之后就守了寡。她本可以回到娘家或者再嫁,但是最后却选择留在陆家,过着丰衣足食的守寡日子。长期的守寡生活使冯仪芳产生了病态的心理,为了把家中唯一的男性陆焉识绑在自己的身边,她不惜与自己的亲侄女暗中较劲。婉瑜为了讨好丈夫,变卖了恩娘冯仪芳送给她的嫁妆,结果恩娘知晓后勃然大怒,“恩娘看着婉瑜,似乎原先她当兔子养的东西,养着养着突然发现这东西原形毕露,是头大象。恩娘的眼泪就在看婉瑜的时候集聚起来,然后慢慢转过脸,看着虚无,膝盖上放了一把芭蕉扇。泪珠子又大又圆的滚落,出来了泪打芭蕉的声音。在这个岁数,流泪的恩娘依然动人。”[8]恩娘的眼泪就是武器,短短几句笔墨,就使得一个柔弱、可怜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塑造女性角色的功底。
1.3视角的转换
除了单一视角的展现,严歌苓还经常运用视角的转换完成小说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叠现。如“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踢跚前进、几乎把他心里的方向走失的时候,我的祖母冯婉喻正从一辆电车上下来,往自己弄堂口走去”。[9]这里将处于不同空间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缩短了人物的空间距离,集中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现。“两颗纯金袖扣患了四十元钱。比他心里估得价不低多少。这个店员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到没有乘人之危的坏心”[10]这里展现的是陆焉识的视角;“我祖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的生活环境,看见了就知道这个家是没地方藏他的”[11],这里的叙述视角又转换成为了孙女冯学峰的视角,表达了“我”的感受。叙述空间从西宁切换到上海,完成了由陆焉识的视角到“我”的视角的转变。多重视角的转变推动小说的情节齐头并进,在缩短小说空间的同时使得叙事更加灵动活跃。
2、叙事时间的自由变形
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小说家把握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小说中的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其中,“故事时间”是指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叙事时间”则是作家讲述故事所需要的时间,它是经过作家的想象力创造和艺术化处理的,它打破了故事时间与语言的线性,突破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同步的传统叙事模式。[12]叙事文的双重时间性使得作家可以任意排列时间顺序,使读者获得全新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在小说《陆犯焉识》中,严歌苓就灵活的运用了倒叙、预叙和插叙手法,让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交织穿梭,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
在《通缉令》一节中,陆焉识沿着青藏高原一路蹒跚前行20多天以后,终于在西宁城关落了脚,“陆焉识在到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左右看看,没有熟人,边走近一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13],这里使用了电影常用的表达技巧,作者将两个主人公的活动场景拼接在一起,构成了蒙太奇般的艺术效果,缩短了叙事空间的同时,拉近了主人公的情感距离。“这时冯婉喻又一次死心,从通缉令旁边慢慢走开,而陆焉识走进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上海的夜色远比西宁来得早,因此,当冯婉喻自家门前摸黑开锁的时候,西宁还剩下最后一缕阳光。”[14]流放西北的陆焉识在饥荒、寒冷和劳累的侵袭下幸运存活。为了自保,他在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里佯装口吃,在人性扭曲、情感异化的监狱中始终保持内心的独立,只为了心中的那一份执念:去告诉婉瑜自己有多么爱她;而身在上海的婉瑜,在焉识入狱期间独自支撑起了整个家。为了得知焉识转监的地点,她一个人在监狱外苦守七天,沿着押送犯人的火车一路追寻。当被告知焉识判处死刑,她把房产变卖成一份份厚礼一家家送上门,甚至最后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上海街头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会面,更是将小说的悲剧意味渲染的更加浓烈。在政治决定一切的特殊年代里,有为了一己之私扭曲人性、背叛灵魂的人,也有陆焉识、冯婉喻这样在异变中始终坚守内心的人。正是在这样善恶交错的极端环境下,他们的爱情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3、叙事线索
叙事线索贯穿小说情节的整个脉络。在小说《陆犯焉识》中,通过主人公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并行,使小说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效果。同时,小说中还多次出现物品线索。物品线索与人物线索共同贯穿全文,使故事结构更加完整严谨。
3.1人物线索
《陆犯焉识》中出现了两个人物线索,分别是以陆焉识为视角的明线,和以作者为视角而展现的冯婉喻的暗线。其中,以陆焉识为主的明线以1954年入狱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54年之前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婚姻家庭、爱情事业的经历,这一部分从1925年的十八岁的陆焉识出场开始,一直到1954年陆焉识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而结束;第二部分则讲述了囚犯陆焉识的劳改生活、越狱、自首以及获释以后的经历。两部分结合起来构成了陆焉识完整的人生轨迹,入狱前的放荡不羁、肆意张扬和入狱后的口齿木讷、凄惨落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夹缝中的悲惨遭遇。
除了以陆焉识为主的明线之外,小说还隐藏着一条暗线,这条暗线直到小说中间才浮现出来。1960年,陆焉识成功贿赂了邓指导员同意他去场部礼堂看小女儿演的电影,写到这里,作者把笔头一转,对准了远在上海的冯婉喻,“就在陆焉识向劳改农场礼堂最后迫近的同一时刻,我的祖母冯婉喻正在学校办公室里,读着一份求爱信”,小说的暗线——以作家为视角展现的冯婉喻的生活经历由此展开。这是一个集中国传统美于一身的女子,漂亮、温柔、宁静、体贴。在冯婉喻还待字闺中的时候,就常听家里人说起焉识表哥多么人中龙凤、一表人才,从那时起,她就对其芳心暗许。当陆焉识从人上人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之时,她不离不弃,代替丈夫支撑着这个家庭,盼望著有一天能和他团聚。“如果说陆焉识担负着表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与政治震荡的任务,那么冯婉喻这条线索就担负着揭示这样的社会运动造成的人心震荡的任务。”[15]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进行,相互呼应,展现了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下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3.2物品线索
严歌苓非常善于把握细节描写。在小说中,“欧米茄手表”和“蓝宝石领带夹”这两个物品多次出现,作为小说中的物品线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欧米茄手表第一次出现,是小梁葫芦从谢队长那里偷了回来放在了陆焉识的口袋里,“尽管手指头上没剩下多少知觉,陆焉识还是摸出赃物是一块表,并且摸出来它是谁的。”[16]这块手表牵引出了一段往事,也让梁葫芦差点被谢队长打个半死,衬托出了监狱里的人性丑恶和自私。后来,陆焉识拿这块手表去贿赂邓指导员,得到了可以去看小女儿电影的机会。邓指导员把手表送给了自己的媳妇,却发现指针走动异常,在陆焉识修手表的过程中,小说揭示出邓指导员的妻子出轨的事实。反复出现的手表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见证人性丑恶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欧米茄手表一样经常出现的,还有一个蓝宝石领带夹,是一个叫韩念痕的女人送给陆焉识的。这就引出了后文《重庆女子》这一章节。韩念痕是一个美艳大方的重庆女子,抗战的时候和陆焉识曾经有一段婚外情。也正是因为这段婚外情,使得后来的陆焉识不惜一切也要回到婉瑜身边,向她忏悔自己的不忠。“细节之处最动人”,这些反复出现的细节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折射出人物的情感,使得小说更加动人。
4、总结
严歌苓于上个世纪90年代赴美,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写作。为了学习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她如饥似渴的阅读了大量西方名家的经典作品,借鉴、吸收了西方新的叙述技巧并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对艺术技巧的探索和实验在严歌苓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的叙事方式在她的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倒淌河》中就曾多次出现,多视角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再如,在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和《雌性的草地》中,都出现了时空的交叉或交织。到了《陆犯焉识》中,更是达到了成熟的状态,她凭借丰富多变的叙事技巧,在挖掘人性的同时,将风云变幻的历史与动人心弦的爱情史诗巧妙结合,使小说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正是这份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践,使得严歌苓的作品呈现出绚丽而深邃的艺术景观,带给读者极高的视觉享受。
注释: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2][美]布斯(Buse,W.C.):《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3]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4]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5]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
[6]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41页。
[8]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页。
[9]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
[10]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11]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12][法]热拉尔·热奈特:《话语叙事·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3]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
[14]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15]胡水莲:《双线并织 时空交错——小说<陆犯焉识>的叙事艺术》,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19年版,第72-74页。
[16]严歌苓:《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参考文献:
著作
[1]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福斯特著.小说面面观[M].花城出版社,1984.
[3]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热奈特.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期刊论文
[1]吕帅.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研究[D].导师:孙淑芹.延边大学,2014.
[2]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当代文坛,2000(03):29-31.
[3]关珊.小说到电影:《陆犯焉识》叙事艺术探析[J].名作欣赏,2015(06):149-150.
[4]罗诗旻,薛斌.流散文学中的后现代生存书写——严歌苓作品语言及叙事策略分析[J].名作欣赏,2013(11):104-105.
[5]周冰欣.自由的时空书写禁锢的悲剧人生——论《陆犯焉识》的叙事时空艺术[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5(04):67-70+110.
[6]孙谦.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空间叙事[J].北京社会科学,2014(12):21-26.
[7]龚自强.与大叙事共溶的小叙事——看向《陆犯焉识》内部[J].中国图书评论,2013(12):36-41.